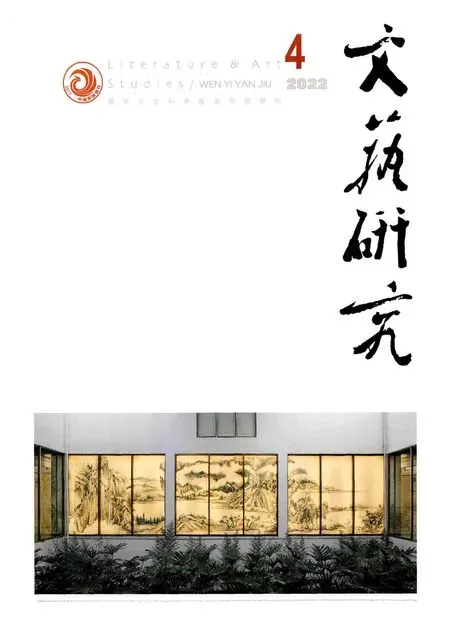东方古典戏剧“现实主义”问题的“身心”置换与再语境化
——以歌舞伎、京剧访苏公演为中心
江 棘
近年来,围绕中国戏曲与现实主义关系这个老问题,讨论热度不降反升,争论的核心是“京剧精神”是否仅指向强调外在形式的“身体性”,而拒斥内心体验的“表情”。换言之,“表情”究竟是戏曲表演传统的应有之义,还是受到了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外来影响?无疑,戏曲突出的程式特征与行当中介、精确的身体运用、漫长严苛的童子功,确实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前表演”方法论,与西方现实主义表演方法存在显著差异。然而无论是明清文人撰述,梨园逸事佳话,还是记诸《梨园原》、流传于艺人口中的艺诀,皆对设身处地、揣摩传神有重点提示。事实上,以“内在心理情感”和“外在身体形式”为区分标准,讨论京剧究竟有无“现实主义”,或只是一个纠结如何贴标签的伪问题,正反双方都能找出无数例子自圆其说,却难以形成有效对话。何为“现实”“真实”之问,本就指向依赖不同历史文化和个体经验的辩证灵活的判定区间,这与其说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毋宁说是更普遍的接受阈值问题乃至哲学问题。看一看全情投入装扮游戏、丝毫不疑其假的孩童,便不难理解这一点。

1935年梅兰芳访苏海报

第二代市川左团次剧照
在衡量戏曲与现实主义关系的天平上,纠结于戏曲之“身”应否传“心”,本身就显示出某种笼罩着天平两端的潜意识的强大。曾几何时,在戏剧领域一提起现实主义,便指向内心体验,尤其是在东西方跨文化戏剧比较中,这一认知似乎已被常识化、本质化,成为戏曲特征判定最重要的参照坐标。然而一个关键问题却被忽视了:现实主义是否天然包蕴着身心对举的内涵?提到现实主义文论,人们大概会更多想到“反映社会现实”“典型人物”“典型环境”“揭示规律”等与“反映论”相关的关键词,在现实主义/写实戏剧观念进入中国、与戏曲发生碰撞之初,“五四”前后的“新旧剧论争”也并未将戏曲游戏化的程式表现与“写实新剧”对社会现实的严肃反映,归为“身”与“心”的对位与对立。因此,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便显现出来:现实主义戏剧观念如何被“置换”为身心对举的言说?置换发生的起点在哪里?为何这一言说可以显示出如此强大的合法性,乃至成为笼罩、左右着跨文化对话与争论的潜意识?
一个同样业已常识化的回答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简称“斯坦尼”)将现实主义与内心体验紧密结合,上述情况正是“泛西方化”与“泛斯坦尼化”的结果。随着国内学界对斯坦尼晚年“形体动作方法”等理论修正的深入研究,这一回答也被修正为中国文艺界对斯坦尼理论的庸俗片面接受。然而,这一影响与接受的过程究竟如何?在“亲密接触”发生之初(以1935年梅兰芳访苏公演为代表事件),现实主义话语的身心置换是否已影响戏曲?我们对早期历史的某些判断,是否更多是基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剧界对斯坦尼的认知,乃至以果为因了呢?
仅聚焦于梅兰芳访苏公演或将其作为起点,无法回答上述问题。在同一问题脉络上,还有一次重要的公演事件被忽视了,即1928年第二代市川左团次的歌舞伎访苏公演,这也是日本古典戏剧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面向西方世界公演。在苏联剧坛围绕现实主义的长期论争中,日本戏剧作为他山之石的刺激作用,比京剧发生得更早、更直接。1928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尚未被正式确立,苏联剧坛的话语斗争处于政治定调前最激烈的阶段,公演剧评中大量出现的身心表述因此意义非凡。七年后京剧访苏的话语场与核心问题,不仅在此时便已预设和铺垫,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结。而那些被延宕的讨论和问题,在1956年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京剧”访日公演时又以另一种方式被重新开启。本文以公演事件为脉络,切入近代以来现实主义戏剧观与东方古典戏剧在互动中走向身心对举的历史,或可为这一当下学界仍在争缠不休的问题提供一个再语境化的新视角。
一、“素颜”与“傀儡”:戏剧身体的两种再发现
现实主义理论与身心观念的联系,本质上植根于“内在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即只有“内在的人”才可以是写实主义者。近代以来,文学的“内在化”趋势无疑先发于西方。柏拉图的灵肉二分论为其远源,随着维系等级社会的公共道德日趋瓦解,印刷等现代媒介打破信息垄断,叙述者/文学生产者不得不从古老的道德教谕走向更为真切地描摹深邃的社会肌理和个人体验,以保障叙述自信。均质化的市民阶级的兴起(也即构成社会主体的“个人”的诞生)、新的技术与社会关系下经验图景的贬值和转换,是推动文学领域的现实主义及与之适配的小说文类崛起发展的最大“现实”,“内在化”既是其特征,也是其必然结果。
在东亚率先引进“内在化”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是日本。坪内逍遥在1885年的《小说神髓》中以进化之眼尊小说于其他文体之上,认为其可以“令难以看见之物显现,令暖昧之物明瞭,网罗无限的人之情欲于有限的小册子中,令读者赏玩时生发自然的反省”。虽然推崇“内在”的人情和写实,逍遥却面临着文体难题,戏剧正是难点所在。他认为当歌舞伎被强调个性、自然的“人情”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化、严肃化、写实化倾向影响,就会“变质”,在日趋精致的同时丧失官能本位与游戏兴味。个中缘由,逍遥或已提及,“盖因小说既无诗歌字数之限与音韵之枷锁,且与戏剧、绘画不同,其性质可直接诉诸心灵,故作者可运其匠心之范围极广”,此乃小说“终能凌驾于传奇戏曲之上,成为文坛第一美术之理由”,也是小说与写实之“人情”适配的理由。当然,小说直接诉诸心灵只是假象,但逍遥对于现实主义的“内在化”难以突破戏剧表现屏障的敏感,确实不乏洞见。通过日常化、私人化的语言媒介,小说可以看似透明地直陈内心,然而戏剧却无法绕开最重要且常常是唯一的表现媒介和资源——演员的身体。所谓心理展现,归根到底是“心理脚本”通过身体外现的过程。不过,既然现实主义的发生发展有其必然性,受到其影响的戏剧舞台也必然会寻找某种更能制造透明效果的装置(即逍遥所言“变质”),这就是柄谷行人所说的“素颜的发现”。
相比于把对内心真实的再现视为现实主义戏剧的特征,“素颜的发现”显然更具洞见。首先,它明确了“素颜”仅是透明化处理后的“心之假象”,是不同于脸谱所代表的装饰性身体的另一种身体。其次,它突出了“发现”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行为及其所表征的主体性。山川未变,只是因为存在过剩自我意识的“内在的人”成了“看风景的人”,才有了“风景的发现”;始终存在的“素颜”,也只是在能够感知到“心理脚本”存在的“内在的人”的注视下,才成为“内面化的演技”。在中日两国,从直接在脸谱等象征符号上感受活生生的意义(古典戏剧的官能特质),到透过“素颜”去寻找和发现意义,并非遽然之变,它们所标志的两种主体状态在很长时段内是交织并存的。在现实主义艺术观念于东亚扩张的初期,日方评价中国戏曲时,“内在化”问题也始终是一个麻烦的热点。例如1919年梅兰芳访日公演期间,张厚载评梅“勉力做到与其自然同化”之论被日方特别挑拣出来,以为卓识,然而更多时论将《天女散花》视作与昆曲传统对立的“现代意图”和“西方影响”,并非因其对天女“内在化”的表现,相反是由于其冶艳媚人的外在歌舞形态。至1924年梅兰芳第二次访日和1926年绿牡丹访日,日方对演出中现代异质成分的认定已聚焦到写实表现上,但对于它到底指向的是更自然显白的外化模仿,还是努力表现“性格与心情”的细腻真实、巧妙幽微的表情动作,论调并不一致。可见,在此时,即使是在东亚占据理论先发优位的日本,现实主义的身心关系问题也还并未发展、固化到内外对举的程度。
与此同时,写实舞台盛行的欧美则酝酿着另一种身体的“发现”。自晚清以来,始终不乏西方人认为戏曲表演是对技巧与身体训练的无需动情的展示。从道理上讲,大概很少有人会反对“身体”本身就包含着“所有的生命活力、感知力、体验,以及精准的智力”,然而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那种如同把大脑从身体中驱逐出去的“傀儡化”视角,却未必只是荒谬的嘲笑对象。“傀儡的发现”同样有其必然性。在19世纪最后十年,通过马戏团杂技,日本舞台艺术渐为欧洲知晓。1899—1902年间,新派剧演员川上音二郎与妻子贞奴先后在美、英、法、俄和东欧进行了两轮巡演。自1902年开始,艺伎花子率团在欧美巡演近十五年。贞奴与花子皆非正宗歌舞伎演员,却被欧美观众误认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观众尤其震撼于那些猛烈的场面(如被杀或切腹的濒死场景)。毕加索等人为贞奴画像,罗丹以花子为模特创作了大量画稿和雕像(包括若干被命名为“死亡之首”的头像)。贞奴与花子独特的表现力究竟从何而来?仔细凝视过花子身体的罗丹,曾公开发表他对其脂肪分布、骨骼结构、肌肉形态的医学解剖式的观察,并与欧洲人种进行对比;梅耶荷德则为贞奴与花子的“柔韧、优美与强健”给出了另一个解释:自童年开始的漫长而特殊的身体训练。

罗丹所塑花子头像《死亡之首》
本来,那令欧美观众印象深刻的濒死表情,也可以被阐发为日本民族意志力的体现(即透过颜面的意义),但罗丹与梅耶荷德强调的先天人种和后天训练,都导向了体质与力学的身体。人种学视野体现出具有时代性的科学思维,而20世纪初,戈登·克雷、梅耶荷德等人也正是以具有类于杂技之经济、准确、精巧与定型特征的东方戏剧身体和傀儡作为理性化表演资源,对抗制造幻觉和移情效果的写实舞台,以图恢复、活化剧场的“戏剧性”。然而,如果认为“傀儡的发现”就是这样线索明晰的抵抗运动,那也会带来相当的遮蔽。毕竟在贞奴与花子之例中,我们也能看到其他的主体可能性——罗丹等人对花子的医学解剖式描述刺激了森鸥外等日本近代知识分子,使他们得以用文字、绘画再现出不同于传统描摹套路的“写实”的日本人形象(亦即日本人“素颜的发现”)。至1928年市川左团次率歌舞伎剧团访苏公演,真正的日本古典戏剧终于与西方世界贴身相触,也将“傀儡”与“素颜”之间博弈与合谋共存的历史互动,更充分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二、博弈与合谋:1928年歌舞伎访苏中的“正当化”言说及其反转
(一)演出背景与核心悬念
贞奴与花子“与其说与能乐或歌舞伎有直接关系,不如说还只停留在迎合欧洲人的日本趣味而已”。1927年,日本新剧家小山内薰应邀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与斯坦尼交谈时听闻贞奴之事,愤然回应“那种东西根本不算艺术”。小山内早年致力于效仿西方、革新日本演剧,与第二代市川左团次创立日本“自由剧场”,效法莫斯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莫艺”)排演了高尔基的《底层》,其后欧游观摩时又访问了“莫艺”。自由剧场停办后,小山内与左团次仍将苏联视作未来海外见学、公演的理想选地。1927年在苏期间,小山内在观摩梅耶荷德剧场的《怒吼吧,中国》、莫斯科职业组合剧场的《叛逆》等剧时,吃惊地发现了花道、柿黑青三色定式幕等歌舞伎手法。西欧戏剧以日本古典剧为活化资源的情形,刺激他重新认识东方传统。他欣然接受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VOKS)委托,与已加盟松竹公司的老友市川左团次商议,要将真正的日本古典戏剧介绍给苏联观众。
1928年7月11日至9月14日,松竹副社长城户四郎担任团长,市川左团次率市川松茑、市川莚升、河原崎长十郎等演员,义太夫伴奏及后台人员共48人,展开访苏之行。随行者还有代替重病的小山内担任顾问的剧作家池田大伍。剧团于8月1日至18日、20日至26日,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假名手本忠臣藏》(以下简称《忠臣藏》)《京鹿子娘道成寺》《番町皿屋敷》《操三番叟》《鸣神》《修禅寺物语》《鹭娘》《元禄花见踊》《鸟边山心中》等十余出歌舞伎剧目。现藏于早稻田大学戏剧博物馆的公演记录剪报,收录了苏方约70名作者刊于51种报刊上的剧评275篇,可见此次公演之备受瞩目。

《忠臣藏》剧照(2017年演出)
歌舞伎访苏背后还有更宏大的时代政治背景。日苏两国自20世纪初历经日俄战争、俄国革命、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等事件,相互忌惮已深。1925年,两国从各自利益出发签订《日苏基本条约》,恢复邦交。1927年,中苏因国共分裂而断交,英国保守党政府和资本集团的反苏活动也日趋激烈,苏联对外陷入孤立,对内面临列宁逝世后的权力斗争,与日本维系关系的重要性上升。同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登台,更强力地介入中国事务并寻机强化与苏联关系,日苏由此进一步接近。但这并不代表双方对于两国友好抱有幻想,比如日本同时还制定了治安维持法,对共产主义者和“危险思想”予以防范监控。微妙局势下,文化交流成为两国交往最好的切入口,这也是有官方背景的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先后向小山内个人和歌舞伎发出邀请的原因。鉴于当时日本政府对共产党及“可疑人士”搜捕的扩大化已影响到演出准备,社会上又普遍存在对市川左团次剧团被“赤化”的顾虑,特别是演出协议签订后,因日本出兵山东和皇姑屯事件,日本对华态势急遽紧张,情势动荡,公演成行更多有赖苏方努力。这次演出也确实对苏联意义更大:在刚刚结束新经济政策、迈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苏维埃政府不仅要维持与东邻的稳定关系,扩大对日本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也亟需展现其外交成功和文化胸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苏方将此次公演视作国家行为,不仅主动挪用驻日使馆修缮费以解决公演经费问题,也主导着公演的舆论走向。
在苏联舆论场中,歌舞伎之所以受到期待,离不开梅耶荷德的介绍之功。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梅耶荷德的剧界地位已显尴尬。虽然他凭借卓越的才华、在革命期领导戏剧运动的狂飙实践以及借鉴歌舞伎元素的构成主义演剧实验,被公认为首屈一指的先锋,但他的桀骜不羁和主张取消“莫艺”等一切旧式职业剧院的激进剧场革命及理念,在新政权建设的环境中变得不合时宜,引发了诸多矛盾,被托洛茨基和苏维埃政府文艺战线的实际领导者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是在“远后的将来”的“未来主义”,是“直接错误”的“形式的左倾与政治的左倾”。与此同时,在革命期被视作右翼布尔乔亚纤细心理主义和私生活式演剧体系的斯坦尼方则获得“重审”,不再被视为与无产阶级艺术对立的存在,反作为“清新的革命的写生活的演剧”成为当下必需。1928年夏,阶级话语和剧界斗争继续发展,歌舞伎于此时到来,注定将迎来一次绝非仅出于东方主义的凝视,其中内蕴着苏联剧界的核心诉求——确认歌舞伎的原真态及其对苏联的有用性。换言之,为何在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苏联要上演、学习歌舞伎?这一悬念如此灼人,而公演成功又不容有任何悬念。或许本次公演之所以被放在梅耶荷德滞欧疗养、斯坦尼等其他剧界巨头亦多缺席的莫斯科演出淡季,本就暗藏顾虑心机。由此,一批更年轻的评论者被推上前台,如曾与小山内交游的批评家戴维·阿尔金、研究东洋语言学并热心于歌舞伎的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尼古拉·康拉德,还有早在革命前就曾与梅耶荷德创办杂志《三橙之恋》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梅耶荷德的学生爱森斯坦等。而努力寻找理性中立、避免争议的语言,将此次公演乃至歌舞伎艺术整体“正当化”,就成为他们在公演前期宣传中所面对的主要任务与挑战。
(二)现实主义方法论与发现“意义”的新方式
最为简便的正当化言说,是强调歌舞伎在西欧戏剧与现实主义风格影响下的现代化转变。市川左团次早年曾游历海外,加盟松竹公司后也致力于传统歌舞伎的现代化革新,松竹公司还安排冈本绮堂等人为他专门编写新剧。这些剧本多以对话为主,削弱传统剧情的荒诞游戏感,着重表达现代人的境遇与痛苦,以内心冲突为构剧依据,质言之,更具“素颜性”。此次公演剧目中除了《忠臣藏》《鸣神》等传统名剧和《鹭娘》、武打“暗斗”等侧重舞蹈做工的幕间剧,余下便是《修禅寺物语》《番町皿屋敷》《鸟边山心中》这三出“冈本新歌舞伎”。苏联剧评家们当然看到了这点。早在公演前的六七月份,阿尔金、别斯金、K.卡尔洛夫斯基等人就在报刊中介绍歌舞伎“向苏联现代演剧最新探索靠近”的革新进步,将市川左团次视为日本传统剧坛的“现实主义者”。然而,这种评论还是太自我中心,不能有力证明在“文化大国主义偏见横行”的时代,苏联却成为胸襟宽广的特例这一公演意图,且对于梅耶荷德青眼有加的歌舞伎表演文化的独特性也有刻意回避之嫌。因此,这时还出现了一种“内生现实主义”的论调。阿尔金在6月24日《消息报》发文赞赏歌舞伎革新进步的同时,开篇即将歌舞伎定性为“与封建贵族私有性质的能乐对抗,新兴的都市布尔乔亚的民主的舞台艺术,且今天也并未屈服于明治以来的欧化之风,确立了国民艺术的地位”,同时将歌舞伎剧目类型“时代物”(历史剧)和“世话物”(世态剧)分别对应于英雄民众登场的悲剧和具有日常喜剧色彩的市民剧,以凸显其民众性与民主化特征。随后《劳动者与戏剧》杂志和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也在7月下旬发文,指出歌舞伎尤其是“世话物”“反映了正在兴起、成长中的布尔乔亚的要求”,是“活着的硕果累累的文化”,由此将歌舞伎的现实主义指认为日本社会内生的诉求,从而建构起歌舞伎正当性的历史前提。
另一方面,大量舆论仍在重申梅耶荷德对歌舞伎特征的概括——占压倒性地位的演员演技和身体控制力、复合艺术的有机总体性、义太夫体现的叙事性与音乐性,等等。然而,对本次公演抱有特别期待的剧评者们,既未必满足于陈说,也敏感于苏联剧坛当时的微妙动向,或将歌舞伎的优长框定在较安全的“纯粹”艺术和技术范畴内,指出“苏维埃戏剧亦以此显著的‘戏剧性’为志向”(康拉德);或力图从更圆融的角度沟通梅耶荷德与现实主义,借机将歌舞伎的“正当性”再推进一步。例如,对于歌舞伎道具与舞美的精湛匠艺,梅耶荷德曾称道为“利用事物的表演”或“表演的物质性”,但在阿尔金和索洛维约夫这里,歌舞伎中那带血的利刃、烂漫樱花和漫天朝霞中的鸡鸣场景,却被视作与“莫艺”和契诃夫式舞台相似性的印证,标记了一种经由精确细部想象出全体的高明的“现实主义”。更有代表性的是梅耶荷德的弟子爱森斯坦。他在《艺术生活》杂志发表名文《意想不到的接触》,认为第三者视角的义太夫三味线伴唱使得视觉、音响、身体运动元素有机结合,实现了做工的可听与声音的可视化,并使观者关注歌舞伎中复数之“艺”而非沉浸于剧情;同时,歌舞伎光辉鲜明的转换手法令诸多要素成为同等重要的素材,给予观众应接不暇的刺激和吸引。他特举《忠臣藏》场景为例:
大星由良之介舍弃了已被包围的城池,从舞台深处跑向台前。突然,与实物一般大小的特写(close up)般的背景城门被换下,第二背景呈露出来。那是一个更小的远景式(long shot)城门,这意味着由良之介正与城门渐行渐远。随着奔跑继续,柿黑青三色的幕布盖住城门,表示它已从由良之介的视野中远去消失,再跑几步,由良之介便出现在了“花道”之上。而此时用以强调距离之遥远的,则是三味线的乐音。
在生动描述下,一段由声、画、动作诸元素对位、转换“构成”的舞台表演,营造出宽广动态的时空纵深感和如临其境的分镜效果,歌舞伎的“蒙太奇”手法也因此具有了连接“构成主义”与“影像现实主义”的可能性。早在1924年底,爱森斯坦就完成了《电影吸引力蒙太奇》手稿,《意想不到的接触》显然延续了相关思考。在文章中,作者直言“既没有必要从左团次的演技中发现‘斯坦尼的理论确证’,也没有必要从中探究梅耶荷德‘尚未偷师之处’”。看来,蒙太奇理论不仅赋予了古老的歌舞伎与现代文明(电影)相勾连的时代正当性,也带给爱森斯坦融通、超脱两派论争的自信。无论是经由物质细节想象出全体,还是在演员身体与物质元素的蒙太奇编织中呈现出意义,以往令欧美观众倍感陌生的形式特征(也即隐喻层面的歌舞伎“身体”),如今都被描述为用以联通感官与意义的手段,达成了与现实主义方法的合谋,且具有了方法论意义。但更大的挑战也随之来临。
(三)“傀儡说”与现实主义的“澄清”
莫斯科公演过半时,报刊剧评中开始频现一个说法——歌舞伎以古老人偶表演为来源和传统,甚至有剧评直接将其说成“人偶剧”或“舞蹈人偶”。一般认为,歌舞伎源自江户初期民间念佛舞等表演,百余年后才与木偶净琉璃交流密切,并从其表演、音乐、脚本各方面汲取营养。当然,梅耶荷德、爱森斯坦也曾将歌舞伎的特点与傀儡相联系,但起源误解在公演后期的集中出现,却伴随着与之不同的舆论转向意图。
1928年8月8日,剧评人尤里·索博莱夫尚惊喜于从市川左团次表现复杂纠结人性的“内在的演技”中“看到了斯坦尼理论的明晰化”,12日,他就将观感改写为“惊愕与疲劳”,认为歌舞伎是“以出色机械性”为指归的“完全无感情”的死物(左团次只是欧化的异数),并将之归因于日本独特的舞台人性观念——人偶传统。就在12日,负面批评集中出现。雅科夫·托根霍利德发表于《东方之晓》的剧评同样结合人偶来源说,认为歌舞伎的象征程式和封建武士道意识都与苏联观众隔阂巨大。梅耶荷德的反对者、剧评人米哈伊尔·扎戈尔斯基发表于《现代的演剧》的《印象:关于忠实的侍者与不诚实的莫斯科人》一文,直指此前舆论佳评“不诚实”,与实际冷淡的观众反应不符。同样,他口中歌舞伎“打磨金饰一般无生命感的精巧”和“无感觉性”、雕像式的“不动性”,也不过是“人偶性”的另一种表达。
“人偶/傀儡说”的反攻,正针对着前述将歌舞伎现实主义化的言说。它从起源上直接反驳了建基于“布尔乔亚文化”的“内生现实主义”,同时还令歌舞伎只以手之震动或脸部肌肉动作传达精神苦难等“从细部呈现全体”的基础原则显得颇为可疑:在真人那里难以简单割裂的身心内外连接,在傀儡处则遭遇了毋庸置疑的绝对断裂。也因这种断裂的存在,身体“前表演”的蓄力与爆发、声画对位、快速转换等各显精湛的手法,“无法通过有意味的意识形态内容来获得统一性”,“始于龙卷风般的动态,却终结于灰色的静态……其落后于时代的艺术形式本身便是对不合时宜意欲复活它的人的复仇”。并不符实的“傀儡说”连带着相关负面判断被不断投向歌舞伎,也投向“不合时宜”的梅耶荷德。
1928年8月12日前后,苏联剧坛究竟发生了什么?除了新经济政策结束、舆论氛围收紧的大背景之外,共产国际六大8月正在莫斯科召开,其言论走向是否与剧坛风向转变有关?就在访苏的两个月前,市川左团次曾在明治座主演小山内刚刚创作的“英雄”题材剧《墨索里尼》,这或有迎合时事以求卖座和向世界介绍歌舞伎的营销考虑,但苏联是否早觉如鲠在喉?可以确定的是,在公演成功在握、外交友好信号已如愿释放之后,某种被刻意抑制的力量开始显示出其不可违抗的强大影响力。自此,歌舞伎的支持者们锐气渐消,似乎失去了继续将歌舞伎与现实主义连接的理论自信。阿尔金不无辩护意味地为歌舞伎的身(技法)心(情感)连接,找到了不同于自内而外的现实主义方法的另一种阐释,一种具有历史层累性和文化概括力的符号中介方式,即“立足于做工和音声基本手法的绵密分类,形成不同的记号。这些记号具有‘记录’不同感情的丰富表现力,给予观众尖锐的感受”;索洛维约夫则在谈及“我国最先锋的戏剧家们(梅耶荷德等)借鉴歌舞伎的成功”时,不忘小心翼翼补充“尚未有人可将日本戏剧之独特固有特征自动移植到俄罗斯土壤中”。与此相对,另一种声音逐渐垄断了歌舞伎之有用性这一核心论域。8月26日,康斯坦丁·托维尔斯科伊断言已无继续讨论的必要,因为“必须明确,在现代机能化的戏剧体系中,歌舞伎是最反动的”;29日,西蒙·德雷顿在《真理报》发文,将歌舞伎判定为以演技为中心的封建性质,苏维埃政府应将这一“意识形态绝缘”的艺术视同纪念碑、博物馆,予以保护研究并供劳动者“见学”,并最终将本次公演之于苏联的意义,归结于学习歌舞伎演员不畏难技、规则谨严的模范劳动,以及全团同心合力的工作精神,以颇为官方的口吻,客套地否定了其艺术层面的可借鉴价值。
1928年歌舞伎公演,是苏联文艺界对梅耶荷德引为普遍方法论的戏剧价值和可能性进行确认的大事件。这种可能性最终被否定,既与复杂国际局势下的政治考量有关,也说明此时虽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国家艺术方针尚有时日,但不可逆转之势已现。“傀儡说”这个曾被用来对抗现实主义舞台的武器,在1928年反成为苏联剧坛用以“澄清”现实主义的最便捷的“看门护卫”。“傀儡说”一举斩断感官与意义,扭转了歌舞伎与现实主义连接的可能,在将梅耶荷德的艺术观念进一步形式主义化的同时,也推动着本已在“素颜化”进程中的东方戏剧身体不断走向身心分离的话语场。
三、延续与延宕:有问题的会议记录与去问题化的男旦
苏联的歌舞伎热潮随着公演结束和时势迅速降温。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加快,日苏关系更趋严峻。中苏共同面对的日本入侵问题,也为两国缔结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增添了砝码。1935年春,梅兰芳率京剧团应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访苏,这次公演始终吸引着学人的目光,那份经过删改的4月14日“梅兰芳访苏总结座谈会”速记稿更是研究焦点。有学者感到此次座谈的空气中洋溢着一种空泛的尊崇,并未真正涉及京剧对苏联可能的切实影响,且苏方对于深入有效交流的可能性似乎并不抱太高期待。无疑,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立为文艺基本方法,是左右这次座谈言论的决定性事件,但从另外的角度说,1935年不过是1928年的延续,只要放在后者的延长线上视之,很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并未充分展开的交流,或正说明经过1928年关键一役,相关讨论已无必要。相比七年前那个剧界巨头们有意无意避忌的淡季,此次座谈会虽斯坦尼因病仍未出席,但已称得上群贤毕至。这反倒意味着问题的终结,因为它正提示了悬念的淡化,取而代之的要紧事是“表态”。
在这些“表态”中,艺术家的不甘依然隐约闪现,梅耶荷德活跃大胆的表现尤其刺目,这或是缘于他的不羁个性,或与正向他紧逼而来的“形式主义”指控有关,也或许是出于对1928年缺席的补偿心理。他热烈称赞京剧较苏俄当下演剧更为优越,可以想见,在记录稿中他的这些发言以及收获的支持言论大部分被删节,某种意义上又在事后“被缺席”了。比照删节前后的会议记录不难发现,陈词滥调地从“形式”层面称赏京剧的有机综合性、技术性与形象化最为安全,赞美戏曲胜于日本戏剧也可以,强调京剧“程式性”中的活力亦可通融,然而如果把“程式性”换成梅耶荷德标榜的“戏剧性”,就敏感得多。至于那些将戏曲与逼真、与现实主义,乃至与欧洲和苏联戏剧相提并论的言论,更是犯了大忌。删节背后的标尺与1928年歌舞伎公演中的“傀儡转向”一般无二。唯一一处未删节的从现实主义角度分析京剧的发言出自爱森斯坦之口,他更隐晦、更富策略性地将戏曲的符号象征性与现实主义从个别到普遍的理论相联系,如此谨慎的“正当化”言说,也许正得益于1928年的历练。爱森斯坦还曾发表介绍、称赏梅兰芳的名文《梨园仙子》,学界虽关注此文,却多忽视了其生动的开头——作者开篇便为中国戏曲安上了“陈平以偶人解刘邦之围”这一信史难证的“傀儡起源”。以此传奇开篇,究竟是难逃西方惯常猎奇之谬,还是“斗争经验”丰富者早早祭出的挡箭牌,后人不可不察。
延续中也有延宕。如果说1928年歌舞伎公演是以男役(生行)市川左团次为中心,因此对于同台的市川松茑等女形(男旦)的讨论并未得到凸显和展开,那么在梅兰芳访苏公演中,这个问题几乎被完全回避则匪夷所思。李湛给出的解释是1934年斯大林政府颁发的同性恋禁令。此历史线索颇有价值,但李湛文中恰恰忽略了关键论证:男旦如何与同性恋划上等号?苏方的认知显然并非是从“相公堂子”这样的历史现象出发。当时的一般常识认为,男旦从外在生理上是“反自然”的、是“假”的,从而也是“反现实主义”的,如果一个男人可以“比女人更女人”,那么只能从对女性理想本质、内在真实的达成角度来理解。这样一种本质性、内在性的达成,本来凝结着艺术家观察、提炼、理解、训练的综合工夫,然而在身心、内外二分的逻辑下,却易被归结于与肉身相对的精神情感及其发动之源——“心”。“以假至真”的男旦表演,随之亦被置换为以女子之心超克男子之身,从而有可能进入同性恋论域而成为禁忌话题。可以说,将男旦视同于同性恋,正说明身心对举观念不仅已成为此时苏联剧坛划定现实主义疆域的重要标尺,且已内化为某种集体性的潜意识。

《市川左团次歌舞伎纪行》书脊
苏联剧坛的身心观念和话语是否对当时的日本和中国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这是另一个被延宕的问题。中、日剧团皆置身于苏方刻意安排的外交友好场合,张彭春等人在座谈会上以及归国后对于梅耶荷德言论多有推崇,可见其并不那么敏感于友好氛围之下的张力,也不可能知晓此后发生的删节之事以及公演结束后苏联方面关于京剧的更多负面评价。虽然梅兰芳登门拜访了病中的斯坦尼并做了简单交流,但鉴于苏联剧坛对于将京剧与现实主义勾连的忌惮,若判断此时斯坦尼理论已对京剧和梅兰芳产生了如何真切的影响,亦失之草率。至于日本方面,为了避免反共右翼法西斯势力的骚扰,市川左团次归国后拒绝了苏联大使馆的欢迎会,松竹公司也暂停了访苏剧团成员的公演,仅以随团秘书大隈俊雄在翌年编辑介绍公演概况的《市川左团次歌舞伎纪行》一书匆忙做结。此后苏联始终是被日本忌惮的敌国,后者同样失去了检视歌舞伎苏联公演的最佳时机。直到1956年夏,中日古典戏剧因梅兰芳访日重逢,两国不同社会制度的现实语境,令这次相遇的关注点被再次放到了斯坦尼、现实主义和身心问题之上。接受过苏联现实主义凝视的两种代表性东方古典戏剧,展开了新的对视,这为曾经延宕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打开契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对女演员的培养扶持。代表团中以靓丽群像出现的侯玉兰、江新蓉等十几名女演员(包括“坤生”梅兰芳之女梅葆玥),与梅兰芳形成众星拱月般的奇妙组合,刺激日本媒体上出现正反两派对垒的“男旦存废”之争。虽有观点交锋,但日方总体上对中国女演员的清新自然表示认可,而男旦所面临的挑战也并不被认为是需要弥合的性别鸿沟和身心分裂,其最大难点、美学价值亦即“本质内涵”,在于演员“以阴阳、虚实、顺逆的变型表现手法将真实描摹出来”,将“作为所有技艺基础的序破急,散布镶嵌于最细小的章节中”。尤金尼奥·巴尔巴曾阐释“序破急”为将“生物过程”重塑转变为包含着节奏和能量运用且为观众可见的“思维方法”,其实无论序破急还是阴阳之道,本质上与1928年阿尔金所言歌舞伎经由历史层累形成的具有情感记录功能、文化概括功能和强大表现力的“记号”之说异曲同工。在将男旦美学历史化的同时,新中国崭新的社会面貌也刺激日方从社会制度性层面审视因封建社会女性禁忌而产生的男旦问题。比如,日本话剧女演员山本安英震惊于京剧团女演员几乎都是子女众多的年轻母亲,“羡慕诸位能全力专心于京剧本职。在我们虽也觉有些羞耻,却不能不考虑生活的问题”,并在对新中国保育制度的介绍中将问题引向了实现性别平等的现实支持基础,以及女性在现实中的身心安顿问题。鉴于同样不乏日方评论认为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艺工作方针是梅兰芳得以焕发艺术青春的支持因素,发展女演员与支持男旦之间的制度性紧张,实际成了参与讨论者虽未明言但都暗藏于心的问号;而此后中日两国男旦发展的不同态势,更从现实角度证明了本质化的身心分裂观所无法涵盖的历史复杂性。

《市川左团次歌舞伎纪行》封面书影

1956年梅兰芳率京剧团抵日,剧团中集体身着旗袍的女演员们引人注目

2010年于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举行第二代市川左团次展海报
余 论
从歌舞伎访苏到京剧访苏,再到1956年京剧访日,关于东方古典戏剧的身心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形成了一个跨文化言说脉络。歌舞伎访苏固然较少为国内学界讨论,而相比于民国戏曲海外公演的研究热潮,学界对1956年公演的研究也较少,这或许是因为这次公演担负着新中国以民间外交破冰的特殊使命,被认为缺少讨论空间。然而如前所述,此前的公演未必没有政治层面的“特殊”背景,从意识形态规定性的角度将1956年公演孤立视之,并不客观。千田是也、土方与志、木下顺二、松岛荣一、山本安英、冈崎俊夫等日本左翼剧界文坛代表,以及观世荣夫等传统戏剧大师,肯定京剧的现实主义传统,认为新中国戏改及与斯坦尼体系结合的“新京剧”的成果“更易懂”“更健康”、更具“民众性”,体现出了“与苏联情形一样”的“内在深度的强化”与更“内在化”的演技,这些观点当然与其政治立场和现实语境有关,但在1928年歌舞伎访苏公演的对照下,我们同样能感受到某种内在的、历史性的问题意识。此时日方对于京剧学习斯坦尼体系的认同点,正在于真实感/“人间性”与夸张精美的造型、精湛圆熟的表演和身体训练的紧密结合,这构成了与1928年和1935年的苏方评论最显著的不同。话剧界的山本安英认为“那猛兽一般强烈夸张的脸谱,比如《霸王别姬》中的项羽……比用普通人的脸面来演反倒更显出真实感,使人突然感觉有种不夹杂着任何异质的纯粹和朴素”,这种斯坦尼隐性在场的中日对视,令“脸谱”与“素颜”的关系呈现出新的辩证法。这样的反馈也许正是中方所期待的。50年代中期中国学习斯坦尼体系达到最高潮时,新旧兼擅的剧界领袖欧阳予倩针对列斯里等苏联专家贬低戏曲为“形式主义”,明确表示不满,他在1955年提呈苏联科学院艺术史艺术理论研究所的长文中指出,“有人认为中国戏专重外形,不注重表达内心活动,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欧阳予倩正是1956年访日京剧代表团的副团长兼总导演。这一“去苏联化”的期待,不仅与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时代政治有同步性,也是戏曲界内生的反思,体现出斯坦尼在中国接受的另一面向。
斯坦尼及其理论对于中国现当代剧坛的影响毋庸置疑,但动辄归功或归咎于斯坦尼的言说惯性,也提示我们被标签化的“斯坦尼”本身已成为巨大遮蔽。因此,将日本戏剧这一共时性存在纳入考量就更显必要。以“发现素颜”的方法为歌舞伎的异质传统正名,以“发现傀儡”的视线划割现实主义疆界,这些历史“反转”正体现了诸多僵化标签原本互为因果、互相转化的关系。在他者的脉络上,不仅是斯坦尼们,还有梅耶荷德们,以及在“脸谱”“素颜”和“傀儡”背后诸多视角不同、位置各异的“发现”之眼的存在,合力形塑着近代以来关于东方古典戏剧的身心言说。只有把视线从“身”“心”等概念对象孰更真实、优越的争论,转移到对“发现”行为本身的观察和追索,跨文化研究的意义庶几能够超越真理判断的哲学性困境,在语境化的历史纵深中得到显现。
① 代表文章有邹元江《梅兰芳的“表情”与“京剧精神”》(《文艺研究》2009年第2期)及众多与之商榷的文章。郭宝昌在2021年的新著《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中也多有对相关问题的回应。
② 在新旧剧论争中,“旧戏”的特点被概括为“假象”“规律”“音乐和唱工上的感触”(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对其的负面评价主要包括:刺激性强、形式固定、音乐轻躁无美学价值(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进化观点下的野蛮原始(周作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新剧”的写实特点也多被置于进化论和道德功利的视角下衡量,比如认为新剧有悲剧观念和文学经济方法,符合自由发展的进化(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能够真切反映当今平常人与社会生活,引起观者批评判断的兴味(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能够在客观准确的前提下发挥社会批判功能等(胡适《易卜生主义》)。
③⑦⑧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第39页,第40页。
④⑥ 伊藤整(ほか)編集『日本現代文学全集』(4)(講談社,1980年)166頁,153頁。
⑤ 坪内逍遥「女形の前途と歌舞伎の前途」,逍遥协会編『逍遥選集』第十巻(東京第一書房,1977年)149—172頁。
⑨ 村田乌江『支那劇と梅蘭芳』(玄文社,1919年)59頁。
⑩ 参见江棘:《穿过“巨龙之眼”:跨文化对话中的戏曲艺术(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270页。
⑪ 坪内士行「日本に於ける緑牡丹の感想」『支那劇研究』1925年第四輯。
⑫ 南部修太郎:《梅兰芳的〈黛玉葬花〉》,李玲译,《戏曲艺术》2013年第4期。
⑬ Lawrence Gilman,“Review:The Book of the Month:Stark Young”,,Vol.217,No.809(April,1923):558-559.
⑭⑯ 熊鹰:《“日本人”的发现与再现:以森鸥外的小说〈花子〉为例》,《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⑮ 伊藤愉「メイエルホリド劇場と日露交流:メイエルホリド、ガウズネル、ガーリン」,永田靖、上田洋子、内田健介編『歌舞伎と革命ロシア:1928年左団次一座訪ソ公演と日露演劇交流』(森話社,2017年)242頁。
⑰㉓ 北村有紀子、ダニー・サヴエリ「異国趣味の正当化—1928年訪ソ歌舞伎公演をめぐって」『歌舞伎と革命ロシア:1928年左団次一座訪ソ公演と日露演劇交流』92頁,94頁。
⑱ 小山内薰「ロシアの年越し」『小山内薰演劇論全集』第三巻(未来社,1965年)33頁。
⑲ 小山内薰「劇壇種々相」『小山内薰演劇論全集』第五巻(未来社,1968年)195—198頁。
⑳ 小山内薰「滞露日記」『小山内薰演劇論全集』第三巻,274—275頁。
㉑ 松竹公司于1906年开始在大阪经营歌舞伎事业,并向东京进发,不仅收购了新富座、本乡座等诸多剧场,且在1912年开设女演员培养所,市川左团次亦于该年归至松竹旗下。
㉒ 上田洋子「1928年のソ連が見た歌舞伎」『歌舞伎と革命ロシア:1928年左団次一座訪ソ公演と日露演劇交流』43頁。
㉔㉖[57] 内田健介「日ソ国交回復前後の文化交流とその政治的背景」『歌舞伎と革命ロシア:1928年左団次一座訪ソ公演と日露演劇交流』76—77頁,83頁,84頁。
㉕ 大谷竹次郎「歌舞伎海外進出の実現」,茂木千佳史編『歌舞伎海外公演の記録』(松竹株式会社,1992年)30頁。
㉗㉙ 特罗次基:《革命艺术与社会主义艺术》,升曙华(梦):《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画室(冯雪峰)译,(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版,第158页,第156页。
㉘ 路纳却尔司基(即卢那察尔斯基):《演剧革命的回顾》,《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第19—27页。
㉚ 阿尔金1927年赴日期间曾发表歌舞伎相关论述,并与小山内薰会面。在《小山内薰演剧论全集》第三卷中收有《D.阿尔金氏的日本演剧观》一文。
㉛㉜㉝㉞㉟㊱㊴㊶㊷㊸㊹㊺㊻㊽㊾㊿[51] 「1928年歌舞伎ソ連公演新聞·雑誌評」『歌舞伎と革命ロシア:1928年左団次一座訪ソ公演と日露演劇交流』287、289、296、300頁,298頁,284—287頁,303頁,299頁,286、354頁,316、323—324、356頁,305頁,314—316頁,322—324頁,318頁,339—340頁,321頁,327頁,354頁,347—351頁,352頁。
㊲㊳㊵ セルゲイ·エイゼンシュテイン「思いがけぬ接触」,鴻英良訳,岩本憲児、波多野哲朗編『映画理論集成』(フイルムアート社,1982年)54—55頁,61頁,60頁。
㊼ 歌舞伎一行离苏后,松竹副社长城户四郎与市川左团次就因创演《墨索里尼》的机缘,迅速于1928年9月24日到意大利会见了墨索里尼,此举被城户称为“跨越思想的南北极来介绍歌舞伎”(城户四郎「歌舞伎初の海外公演について」『歌舞伎海外公演の記録』35頁)。
[52] 代表性研究有陈世雄《梅兰芳等中苏艺术家讨论会记录(未删节版)及其价值》(《文化遗产》2019年第1期)、李湛《4月14日(周日)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座谈会:发言者与发言内容的种种谜团》(冯伟、宋瑞雪译,《戏曲艺术》2018年第4期)等。
[53] 李湛:《4月14日(周日)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座谈会:发言者与发言内容的种种谜团》。
[54] Sergei Eisenstein,“The Enchanter from the Pear Garden:Introducing to Russian Audiences a Visitor from Chi⁃na”,,Vol.19,No.10(1935):761-762.
[55] 李湛:《内尔与沙吉尼扬就梅兰芳1935年苏联演出的新闻评论》,常赛、冯伟译,《戏曲艺术》2021年第2期。
[56] Janne Risum,“Minutes of‘Evening to Sum Up the Conclusions from the Stay of the Theatre of Mei Lanfang in the Soviet Union’at the All⁃Union Society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VOKS)on Sunday,14 April 1935”,,Vol.31,No.2(Fall,2020):346.
[58] 如《产经时事》6月1日专题“关于京剧和歌舞伎的旦角”,即分“肯定”“否定”两方组织文章。
[59] 改成戸部銀作「京劇と歌舞伎「女形」をめぐって」『産経時事』1956年6月1日朝刊。
[60] 「希代の名優梅蘭芳 伝統と訓練の芸術「京劇」」『週刊朝日』1956年6月17日。
[61] 尤金尼奥·巴尔巴:《纸舟:戏剧人类学指南》,连幼平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18年版,第83页。
[62][66] 「浜村米藏·土方与志·山本安英三氏の座談会」『赤旗報』1956年7月8日。
[63] 代表文章如木下顺二「梅蘭芳を支えるもの」『芸術新潮』1956年8月号。
[64] 比如,剧作家木下顺二写道:“比起歌舞伎似更虚幻的京剧,不但在中国的剧院,在此地舞台上也经由梅先生的演出证明着其与斯氏体系显然有着紧密结合。……民族遗产的贵重传统,和令它活在现代的创造性,融于梅先生一身,令我们感动至极。”(「京劇東京公演を見て」『赤旗報』1956年6月7日)据曾在京剧团教习能乐的能乐师观世荣夫回忆,此段经历令他决心“为了解决自身问题”而“跟随话剧老前辈学习导演方面的知识……跟冈仓士朗先生学习斯坦尼,随千田是也学习布莱希特”[「伝統芸術と社会性」『華より幽へ:観世栄夫自伝』(白水社,2007年)73—75頁]。戏剧家土方与志认为“新中国后发生了飞跃剧变。表演的内在的东西一口气地冲出来,看苏联的情形也一样”(「浜村米藏·土方与志·山本安英三氏の座談会」)。
[65] 除了描摹女性悲哀与空虚的《醉酒》,日方在对《三岔口》精密如杂技般的表演的讨论中,也多次提到这种真实感(岡崎俊夫「京劇の魅力(3):三岔口」『東京朝日新聞』1956年6月3日、大佛次郎「京劇の演技について」『東京新聞』1956年7月8日)。
[67] 欧阳予倩:《话剧、新歌剧与中国戏剧艺术传统——为苏联科学院艺术史艺术理论研究所作》,《欧阳予倩全集》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