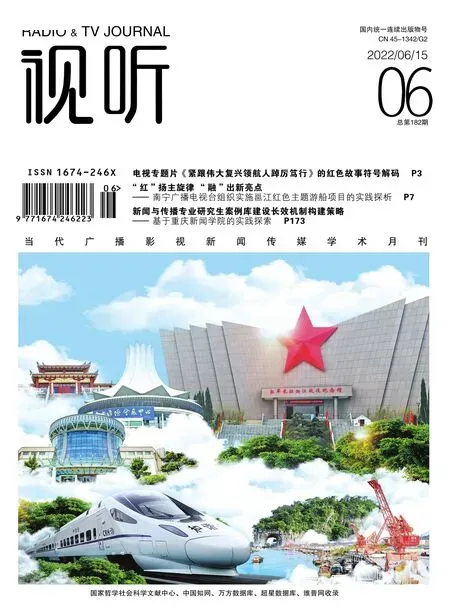浅析融媒体语境下的纪录片文化建构
——以纪录片《中国》为例
张兴动 贾子谋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引导下,纪录片领域涌现出诸如《传承》《本草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一批现象级的传统文化题材作品,也成功地掀起欣赏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发展,纪录片的文化传承不应止于影像的呈现,更应在受众交流与媒介互动中实现更为高效的文化传播。纪录片《中国》将镜头聚焦在传统文化的历史流变上,并借助网络化技术、融媒体资源,让传统文化能在受众和媒介中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探讨,从而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因此,探索融媒体语境下纪录片的影像传播特性与文化建构路径,能为互联网时代的影像传播与文化传承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发。
一、影像维度的文化形塑
叙事和表意是影像进行信息交流的两种方式,随着媒介间融合程度的加深,纪录片影像中的叙事能力与表意潜力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纪录片《中国》在融媒体思维的助力下大胆地突破传统电视纪录片的视听规则,通过故事性的历史讲述与意境式的情景感知创造性地延展了纪录片的影像呈现方式,也让纪录片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能以更为多元的形式被影像形塑,从而用情用力地讲好中国故事。
(一)故事性与文化溯源
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在谈到电影与现实的关系时,提出了“电影是生活的渐近线”这一观点,强调了电影如同渐近线般无限制地趋近于现实,但与现实永不相交的影像特性。当纪录片与历史相望时又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影像方式“渐进”呢?讲求客观叙述与史诗感营造的传统历史纪录片固然是一种方式,但随着电视平台与其他网络平台的融合互通,具有教化说服意味的传统纪录片讲述方式似乎不再适合于网络场域下受众的观看习惯与审美认知,而亲切质朴的故事化叙事策略往往更加符合互联网平台的传播逻辑与受众偏好,也能让纪录片在电视平台与互联网平台的联动中实现更为高效的影像文化传播。
纪录片《中国》作为由湖南卫视与芒果TV联动播出的融媒体纪录片,在影像创作上保留了“画面+解说词”的电视纪录片特征,但在历史的呈现上更具故事性,通过口述历史与情景再现相结合的讲述形式来捕捉历史长河中那些意味深远的瞬间,利用关键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的命运抗争,以小见大地映照出文化与制度的流变。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影像再现的形式出现在画面之中时,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地缘文化和民族文化也在其中悄然地演变与成长。该片并没有引导观众来了解什么是传统文化,而是使他们“参与”到形塑传统文化的影像观察中,让全片更像是一场“以史为鉴”的传统文化溯源。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故事性文化溯源中,令观众产生了文化认同感。这种创新性的叙述方式不仅为该片吸引了大量的受众,也为讲好中国故事探索出更多的可能。
(二)诗意性与文化感知
即使是在数字技术与影视艺术互融互通的今天,真实感在纪录片创作中依旧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但数字技术的可供性与融媒体受众的包容性从某种程度上拓宽了纪录片真实感的边界,使得融媒体纪录片不再像传统的电视纪录片那样被记录外在真实宰制,而是能更多地转向对内在真实与哲理真实的探讨上。这也让抽象化的感知与情绪有了被影像形塑的可能,进而增强了纪录片的表现力。
当文化在影像中流淌,巧妙的诗意建构可以为抽象的文化感知赋予温度和质感。在纪录片《中国》中,传统文化不只存在于叙事的时间维度,更是以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意境韵味在诗意空间中被感知。人在空间里活动,空间也要承担诗意的情感任务①。当失意的孔丘在乌云密布的山坡上咏叹,释然的孟轲在苍翠葱茏的竹林间远望,完成大业的嬴政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前驻足时,不难发现,纪录片《中国》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往往与人物在情感基调上保持着一致性。如讲述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单集中,将孔子陷于七日之围时所处的空间环境安排在了一处乌云密布的乱石坡中,此时困扰孔子的不仅是身体上的饥饿与劳累,更是儒家文化无法被统治者接受时内心深处的迷茫与压抑。导演巧妙地利用乌云与乱石的空间环境对孔子的内心情感进行了写意性的视觉外化,使得人物的情绪状态在情景的呈现中得到了呼应。当这种情景相融、虚实相生的意境感知在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下循环往复地出现时,传统文化不断流转变迁的命运感也伴随着这些历史人物的情绪变化在情与景的勾连耦合中被感知化形塑,进而通过共情性的文化感知实现了融媒体纪录片从记录外部真实到呈现内部真实的表意性升华。这种独具东方韵味的中国影像美学,也让中国故事在诗韵意境中被讲述得更加精彩。
二、受众维度的文化交流
在融媒体的传播语境下,影像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交属性,从而带来了传播关系的泛化。这种传播关系的改变不仅能够让受众以更为深入的方式参与到影像互动中,更能让受众通过话题性讨论进一步加深对影像内涵的理解,使得影像背后的文化传承从单向性的价值输出转变为传者与受众之间双向的文化交流。
(一)互动式影像参与
网络传播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单向传播关系,使得受众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更能对信息进行主动的反馈与探讨,让受众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而这也给融媒体纪录片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可以通过观影时的良性互动让传统单向的影像接受转变为更具互动性的文化交流,从而让观众从影像信息的接受者变为影像传播的参与者。
弹幕作为一种具有实时性、参与性与娱乐性的视频互动文本,为影像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语义空间,也增强了观看行为的互动性。然而,在纪录片《中国》的网络平台播放中却出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即一向以反叛和恶搞为特色的弹幕亚文化在纪录片《中国》的弹幕交流中却变得“正经”起来。其中虽不乏有“前方高能”“剧情预警”之类的弹幕评论,但绝大多数弹幕都集中在了对视听语言与传统文化的交流评论上,甚至有些弹幕引用了诸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类诗文来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价。这不禁让人思考,到底是什么触动了这些原本追求娱乐的网络受众?或许答案就隐藏在影像中。纪录片《中国》通过亲切质朴的传统文化形象成功地激发起观众内心深处的身份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在影像传播与弹幕反馈中形成了良性的交流互动关系。该片让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在影像中被感知,更在观影过程中被探讨,从而在影像与观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让观众在弹幕互动评论中不断体悟到传统文化带来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
(二)多元化话题讨论
长尾效应是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统计学术语。在长尾效应的概念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头部和尾部。头部代表着主要需求,也可以说是潮流需求;尾部代表着小众需求,具有零散性、个性化的特征②。长尾效应强调对需求曲线中的长尾部分进行整合,进而实现市场需求的优化。纪录片中的长尾效应则更多出现在影像播放完成后的传播阶段,可以利用与受众的话题讨论来延续影像的传播热度,为影像传播赋予更强的生命力。
以纪录片《中国》在微博平台的话题营造为例,该片主要通过发布多元性的文化话题来引发网友、专家学者和影视从业者对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讨论。一方面,纪录片《中国》的官方微博通过对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文化习俗和文化演变等进行科普,引起受众对传统文化的话题性讨论。如在冬至时,该官方微博发布了“你不知道的冬至那些事”“北吃饺子,南吃汤圆”等话题,并将片中角色与各地不同的节日习俗联系在一起,让微博用户在文化共情中被热点话题吸引,进而自发地参与到文化讨论与内容传播中来。另一方面,该片的官方微博还通过文化研讨会和导演观后感等形式邀请学界专家与业界导演在微博平台上共同探讨片中的传统文化,挖掘出影像背后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认同。这种多元性的话题探讨形式不仅让该片获得了更多的受众关注,而且让影像之中的传统文化在微博用户、学界专家与业界导演的多维度交流探讨中实现了温度与深度的并行,使得受众在多元性话题的讨论中进一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可。
三、媒介维度的文化互通
在崇尚“合力而为”的互联网时代,纪录片也在多屏联动与全媒体互动的助力下形成了立体化的影像传播路径。这不仅延展了影像传播的广度,而且使得影像中的文化价值在媒体间的互融互通中被深度挖掘。纪录片《中国》充分利用了媒介融合带来的传播红利,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影像传播之中,在进行文化传承之余,还为传统文化探寻出更多的当代价值。
(一)多屏联动
当影像以跨媒介衍生的态势贯通了电视大屏与手机小屏之间的界限时,屏幕终端的传播潜力也被进一步整合,以合力之势拓宽了影像的传播路径。这种融合式影像传播矩阵的打造,并非简单地将影像搬运到不同的屏幕终端,而是利用不同屏幕终端的传播特性对影像加以改造,形成了多屏联动的媒介造势,也让影像背后的传统文化在多屏联动中实现更为高效的传播。
随着电子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屏幕终端的呈现形态愈发多样。无论是侧重便携性的小屏、强调沉浸感的大屏,还是拥有震撼感的巨屏,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助力影像的放映与传播。纪录片《中国》将传统文化巧妙地融入不同的屏幕终端,在小屏移动端的影像传播中采用微影像与短视频相结合的影像传播策略,推出了时长在1分钟左右的“群星配音版《中国》”与“揭秘文化彩蛋”等横屏微影像。同时,制作了包括“传统文化科普”和“剧中角色混剪”在内的竖屏短视频,利用短小而精致的文化影像填补了观众在移动终端的碎片化时间。而大屏的电脑、电视端则是纪录片《中国》正片播放的主战场,通过电视台与网络视频平台的联动播放,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转变迁以影像的形式加以呈现。不仅如此,纪录片《中国》还采用了城市巨屏广告的形式,让上海中心大厦、杭州市民中心的LED巨屏上充满了包含着传统文化元素的浓浓中国红。从小屏到大屏,再到巨屏,纪录片《中国》利用不同屏幕终端的传播联动,不仅满足了互联网时代多样化的观看需要,而且在多屏幕终端的合力推动下完成了纪录片的宣传造势,让传统文化在跨屏传播的过程中彰显出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自信与文化繁荣。
(二)全媒体互动
融媒体时代,影像的传播并不会随着播放的结束而停止。全媒体互动所产生的环形传播路径不仅能够充分探寻影像活动在不同阶段的传播价值,而且能在媒体间的全方位报道与探讨中深化影像所传达的文化观念,进而利用当代媒体为传统文化挖掘出更具时代温度的文化内涵。
以纪录片《中国》的环形传播路径建构为例,该片的影像传播开始于播放之前的新闻媒体宣传,通过官方媒体与网络媒体相结合的报道方式助力影像的传播。在纪录片《中国》的放映当日,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传统电视媒体通过《新闻联播》与《午间新闻》栏目对该片的视听风格与文化传承价值进行了肯定与宣扬。而以红网和北青网为代表的网络新闻媒体则更加侧重于对该片进行跟踪式的新闻报道。在单集播出前,以文字与图片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新闻宣传,并且还对当日单集中的传统文化背景、历史人物背景进行了适当的介绍,不仅保证了新闻宣发的时效性,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正片的影像呈现与文化传播。
在影像播出之时,纪录片《中国》并没有单向性地享受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传播红利,而是以画面广告的形式与合作媒体进行传播互动,实现了影像对媒体的传播反哺。当影像播出完成后,纪录片《中国》利用社交媒体,充分挖掘影像传播中的长尾效应,发起了“中国主创说”“文化60秒”和“文化校园行”等讨论性文化话题,在知乎、豆瓣和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与用户共同探讨影像背后的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影像与媒体的全过程互动形成了“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良性传播循环。这不仅便利了影像的跨媒介衍生,也使得影像背后的传统文化能以更为多样的传播路径被宣传与探讨,从而通过现代媒体探索出传统文化的时代意味与人文温度。

四、结语
随着媒介间融合程度的加深,影像的传播不再只是单纯地通过媒体进行作品宣传,而是以一种共生共融的传播样态弥散在影像创作、受众接受和媒介互动中。因此,对于纪录片传播的观察与研究,更应当利用融媒体思维来多维度思考影像传播所带来的效果和价值。纪录片《中国》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方式和诗意性的美学风格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影像形塑,并且利用网络传播的互动性和话题性激发受众对传统文化的交流与探讨。从媒介维度看,该片通过打造融合式传播矩阵与良性传播循环的影像传播模式,使传统文化得以在多屏联动与全媒体互动中实现立体化传播。这种多维度文化传播路径的建构不仅使影像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还为传统文化找到了一条更易被时代接受的影像传播道路,充分体现了当代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坚持守正创新”的责任与担当。
正所谓“学古不泥于古,破法不悖于法”,中华民族有着绵延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而这也给中国的文艺创作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当代的文艺创作不仅要学会继承,而且要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特别是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语境下,无论是影像创作还是影像传播,都被赋予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这也给中华文化内涵与艺术创造力的融合、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的结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因此,只有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流淌在富有时代精神的文艺创新中,才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呈现与传播。
注释:
①宋杰,徐锦.抒情传统下的中国诗意电影[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01):4-14.
②夏菁.新媒体新闻传播的长尾效应[J].传媒论坛,2020(15):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