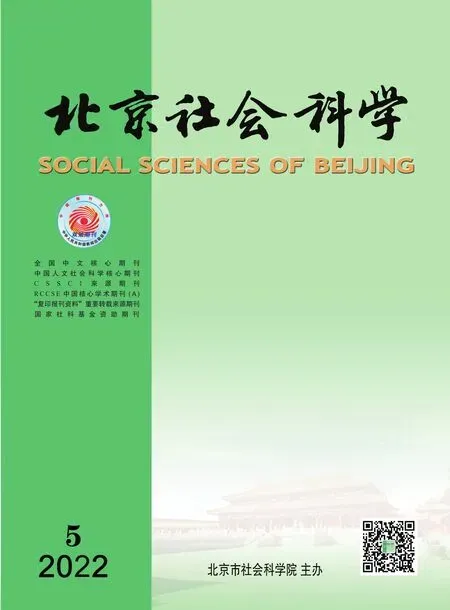从《顾文彬日记》看晚清琉璃厂书画文玩交易
阚红柳
一、 引言
北京琉璃厂, 自清中期“成为清代中国最大的书籍市场和文物集散中心”,古书和书画文玩交易吸引了海内外来京、 寓京人士。 苏州学者顾文彬于同治九年(1870)三月二十八日进京至吏部候缺, 十一月十八日离京,在京231 天,所记日记载录游厂肆内容的计九十余天, 大致以每隔两三天的频率光顾琉璃厂古玩铺, 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晚清琉璃厂文玩字画交易记录。 顾文彬还留有寓京期间写给其子顾承的信札23 通,两相印证, 可大体还原其此次在京行迹。 他不仅在位居北方的琉璃厂大量购入文玩寄回家乡,或收藏或再售, 也少量出售在南方老家苏州搜集的藏品以维持在京生计, 实质上成为沟通南北方文玩市场的活体枢纽。 在京期间, 顾文彬与新朋旧友等同好在文玩鉴藏方面合作交流, 对南北艺术品市场文化信息的传播流布及价值观念的碰撞和融汇做出了实际贡献。 本文以《顾文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为中心, 梳理顾文彬在京期间所参与的书画文玩交易情况, 并由此探析顾文彬及晚清琉璃厂在书画文玩南北文化交流及传承中所起的作用。
二、琉璃厂书画文玩交易活动
顾文彬(1811-1889), 苏州府元和县人。 字蔚如, 号子山、 紫珊, 晚号艮庵居士、 艮庵老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 先后任刑部主事、 陕西司员外郎, 咸丰朝任福建司郎中, 在京游宦14 年, 后外任湖北汉阳知府、 武昌盐法道。咸丰十年(1860)丁父忧回乡。 同治九年(1870),经江苏巡抚丁日昌力荐, 顾文彬进京候缺, 离开15 年后重返京城。 “(三月)二十八日巳刻,砚生备车来接, 同至西河沿公馆。 所住之西边楼下两间, 即昔年砚生入赘新房。 相隔二十年, 迭为宾主, 亦是奇缘。 此房前有楼榭, 后有树石、亭子, 墙外长窑, 古木郁葱。 昔年旧居, 此来重住, 颇惬于怀。”顾文彬寓所西河沿正是琉璃厂的北界, 为畅游厂肆提供了极大便利, 他抵京次日即到访博古斋, “晤李老三”。依《日记》所见, 其后, 到过松竹斋、 筠青阁、 论古斋、 润鉴斋、 亦古斋、 德宝斋、 英古斋、 彩笔斋、 宝古斋、 凝秀阁、 渊鉴斋、 松茂斋、 青云斋、 宝珍斋、 蕴珍斋、 涵雅斋、 绪古斋、 宝石斋、 隶古斋、 宝名堂共21 个文玩书画店铺。 《日记》以京外人士的眼光, 大量记述了琉璃厂古玩铺的店名、卖品及交易情况, 在晚清文献中颇为珍贵。 笔者按《日记》所载, 对其中古玩铺情况加以统计, 具体铺名及顾文彬到访次数的数据详见表1。
由表1 可知, 顾文彬光顾较多的店铺为德宝斋、 论古斋、 博古斋、 松竹斋。 这大体反映了琉璃厂古玩店铺的实际经营状况和商业实力: 德宝斋是开业时间最长的古玩铺, 开业于咸丰元年(1851), 1945 年歇业, 一共存续94 年; 论古斋的创始人为萧秉彝, 同治元年(1862)开业, 至1924 年倒闭; 博古斋开设于清道光年间, 光绪二十六年(1900)歇业; 松竹斋则据说始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 后更名为荣宝斋, 历史更为悠久。 顾文彬此前曾寓京14 年, 对厂肆极为熟悉, 更信赖那些经营时间较长、 有良好信誉的古玩店铺, 并以之为交易对象。

表1 顾文彬到访琉璃厂文玩店铺情况表⑥
长安居, 大不易, “京中红白分子甚多, 外官在京应酬, 较京官还要宽些”。 即便省吃俭用, 也有数额不小的消耗, “每月约需四五十金”。 顾文彬叮嘱儿子顾承, “嗣后, 逢双月须寄百金, 以应我用”。京城官场盘根错节, 吏部候缺旷日持久, 顾文彬明知部选无期, 对归期毫无把握, “所带川资行将告罄”, “若久待下去, 为之奈何?”只能依靠自身所长, 自筹生计。 他携带部分藏品进京, 委托老相识博古斋古玩商李老三帮忙变卖, 以解决部分生活难题。 顾文彬随身携带进京的南货, “销去座位帖一本、石谷碎墨一本、 廉州山水一卷, 得价一百四十两”。此后, 又销去明人扇册得15 金、 曼生墓志得15 金, “其余尚销不动, 盖价虽可得, 而销路不广也”。 无奈又令顾承再寄, “则川费及收买书画皆取给于此矣”。顾文彬游厂肆, 在南北文玩市场买进卖出, 赚取差价, 固然是为了满足艺术追求, 同时也是出于很实际的生计需要。 他在信札中对顾承明言: “我在京候选, 川费不轻, 兼做贩书画家, 不无小补。”
京中生活的窘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顾文彬的选购行为, 南北文玩市场兼顾的生意经则实际上成为主导其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 从顾文彬在琉璃厂所购文玩的品类来看, 他对汉玉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出手购买往往带有北货南售的意识。“汉玉器, 大小十余件, 价约数十两。 此间买汉玉者甚少, 故价不甚昂, 而精品颇多, 然精者亦不贱。 我所得者, 价不昂, 故亦不能甚精, 然到苏销售必可获利, 故择其可爱买之。 闻有玉印甚精者, 已为有力者所据, 当设法图之。”顾文彬以营利为目的购置文玩颇为谨慎, 自认为“所买书画精品居多, 设使变价, 均可占钱, 即绫本各轴, 谅亦可得价。 惟所买玉器古泉等, 或有吃亏, 然亦无几, 况此后已定见不买”。 或因旅途置办转运不便, 或因价格过昂则不易盈利, 他对价高体重的文玩品类兴趣不大。 如《日记》载,在博古斋看到的“石谷(王石谷, 即王翚)临山樵长卷, 索价四十两, 方方壶(方从义)小立轴,索价四十两, 以此二件为最, 惜价昂不能买也”。 又“宝珍斋大玩甚多, 字画亦不少, 余在京十月竟未与成一文交易, 可谓无缘”。
顾文彬把在琉璃厂获取的市场信息通过信札传递给远在苏州的儿子顾承, 作为选购藏品及采购南货北销的远程指导。 “昨日到琉璃厂博古斋, 旧识之李老三尚在, 此公看字眼光颇好,搜罗亦广。 略看数件, 颇有佳品, 内有石谷临山樵长卷, 索价百二十金, 方方壶小立轴, 索价四十金。 据此可见京中字画之贵。 我所带之物, 将来或可希冀得价也。 绫绢本长幅字画,或尚可搜罗, 稍暇日即当访之。”又“天发神谶, 此间甚贵。 国初拓本已值二三十两, 明以前拓更贵, 能觅寄否?”南北信息的沟通, 有助于把握市场行情, 对书画文玩销售的总体情况及商业价值做出更为理性的判断, “前所寄绫本字画, 南中搜罗已尽, 此间亦复不多, 尽可居奇, 切勿贱售”。
尽管遇到一些经济困难, 但其购藏过程中艺术品位及收藏爱好仍然是放在第一位的。 顾文彬为经济困窘一再感叹, “所见书画, 颇有铭心之品, 而眼馋手窘, 只可割爱”, “若书画之爱不能释者, 且俟带出之物销去, 再作推陈出新之计”。 他重金买下王石谷十万画册, 花费四十两; 恽南田仿子久水墨山水袖卷, 花费四十五两,这两件当属艺术水准上乘因而割舍不下的心爱之物。 收藏方面的偏好也影响到了他的视野, 顾文彬不喜收绢本, 故有几次徒劳而返的经历, 如六月十七日, “在德宝斋闲坐, 适胡石查来, 偕至宝珍斋, 见当号赵字册, 未必真笔, 且绢本, 蓑衣裱不足取矣”。
正如博古斋掌柜李老三所言, 外地来京人士是京城书画文玩的重要消费者, “京官爱书画者有数人, 然皆无力量, 即使买去, 难免拖欠, 须遇外官方好”。 顾文彬是典型活跃在琉璃厂的寓京南人, 在京期间较为广泛地参与了琉璃厂的书画文玩交易活动, 并推动南货北销、 北货南售, 亲身推动了艺术品市场的南北交流, 对活跃市场、 促进书画文玩的流通做出了实际贡献。
三、琉璃厂书画文玩交易中的掌柜、同乡与同好
除了必要的官场应酬活动外, 顾文彬在京交谊圈主要围绕琉璃厂的文玩书画交易鉴藏等活动开展。 书画文玩店铺的掌柜、 在京的同乡及在书画文玩鉴藏方面的同好成为主要的交游对象。
顾文彬进京次日就拜访博古斋掌柜李老三, 这是他在京城的旧交, “此公看字画眼光颇好, 搜罗亦广”。 顾文彬对李老三非常信任, 并以诚相待。 据《日记》载: “(四月一日)午后, 李老三来观字画, 令其评价。 余复往博古斋, 约其店伙将字画一箱抬去, 托其销售。”顾文彬将从苏州家中带来的字画委托李老三作为中间人销售, 后“尹耕云托蒋子良问书画价, 先是余以书画三十余件托博古斋之李老三销售, 李老三送与耕云阅看, 耕云知系余物, 故托子良来问。 余虽告以所择八件索价四百余金, 然因李老三是经手人, 嘱其不可撇却也”。 顾文彬不肯在交易活动中抛开中间人, 为此特地亲至博古斋, “晤老三, 告以耕云问价事”。 通过亲身接触, 顾文彬熟悉并了解这些琉璃厂生意人的品行, 从中择选品行端良、 讲求信誉的生意人作为结交和交易对象。 如德宝斋掌柜李诚甫, 在琉璃厂一带颇为知名, 据张祖翼记载, “德宝斋主人李诚甫, 亦山西太平人。 肆始于咸丰季年, 仅千金资本耳, 李乃受友人之托而设者。 其规矩之严肃, 出纳之不苟, 三十年如一日, 今其肆已逾十万金矣。 诚甫能鉴别古彝器甚精, 潘文勤、 王文敏所蓄, 大半皆出其手”。 顾文彬对李诚甫颇为推重, 以友相待。 《日记》中说, 李诚甫“虽市井中人, 颇讲交情, 故余与之颇投契”。 生意关系在长期交往中转变为朋友关系, 故“德宝掌柜人李诚甫定于明日起程往山西置货, 因送之”。 松竹斋掌柜张仰山, 书法篆刻堪称一绝, 顾文彬“至松竹斋晤张仰山, 谈古颇洽”, 后“张仰山在宝兴堂为母做寿, 往拜之”。 论古斋管事萧钟山, “素耳余(指顾文彬)名, 相接甚殷勤”。 此外, 与其交往的买卖人还有筠青阁管事王泉坡、 润鉴斋管事雷际云等。
与文玩铺掌柜的交往既是书画文玩交易之所需, 也为顾文彬在琉璃厂活动提供了不少方便。从《日记》来看, 这些古玩界的行家里手不仅与顾文彬一同鉴赏书画文玩, 互相交流经验, 增广见闻, 而且还热情地为顾文彬提供市场交易信息和鉴赏、 会晤场所, 主动推荐书画文玩藏品并提供各种玩赏便利, 如介绍藏家情况、 允许取货回家细细揣摩、 允许赊欠等。 他们还免费充当购买和售卖的中介, 如帮买主与卖主和会,甚至主动出手, 撮合买卖双方的交易。 景其濬收藏汉玉钩两枚, “其一与余(顾文彬)藏钩竟是一对, 惟腹上亦作琴式而花纹不同, 否则几乎分别不出”, 为将两只玉钩配作一对,“德宝斋以旧瓷、 印盒、 水盂五件售与景剑泉(其濬), 换其汉玉琴钩, 归于余, 余代还瓷器价作六十两”。 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 令旧藏家可以淘汰旧存, 买入新品, 新藏家得其爱物, 一遂心愿, 古玩铺自身也可从中售出货品,获得盈利, 可谓一举三得。 古玩铺不仅在本店经营方面打开方便之门, 甚至可以帮忙在不同店铺间还价, 撮合买卖, 有力地支撑并保障了琉璃厂文玩经营的有序进行。
在京的江苏同乡有书画特长及嗜古同好者,是顾文彬交往的第二大群体。 顾文彬晚年回忆昔年居官京城之时, “寓居与琉璃厂相近, 公余之暇, 辄游厂肆, 肆中售书画者麇集, 余颇爱流览而鉴别未精, 真赝莫决, 同乡华亭秋、 秦谊亭、淡如三君, 皆莫逆交, 雅擅丹青, 尤精赏鉴, 每拉与同游, 藉资印证。 笛秋目光如炬, 礬山绢海中, 遇有佳品, 辄拔其尤。 如伯乐相马, 冀北以顾, 其群遂空, 夸示同人, 余从旁窃睨, 盖不胜其羡且妒焉”。 此次进京候缺, 顾文彬与秦炳文(谊亭)再续前情。 秦炳文(1803-1873), 清画家, 原名燡, 字砚云, 号谊亭, 江苏无锡人, 道光举人, 擅长画山水、 花卉, 精鉴赏, 收藏书画甚富, 所藏多精品。 顾文彬和秦炳文互相交换藏品玩赏, “(五月初十日)秦谊亭来晤, 索观书画, 将新得各种及旧藏沈石田三卷、 石谷一卷、南田一册并博古之大痴、 方壶、 天游三轴与观”。 “谊亭送来柳如是《五柳高隐》卷, 纸本,钱牧斋题右方, 袁简斋题引首。 顾横波画《梅兰竹菊》卷, 纸本, 龚芝麓题卷首, 吴梅村题七绝于卷尾。”相互交流品鉴书画文玩藏品, 有益于开阔眼界、 提升素养。
同乡友人之中, 除收藏界同好外, 还有一批客居京城的艺术家。 如袁崇, 丹徒人, 字崇山,客京师时与俞承德、 秦炳文等于松筠庵结画社,善山水; 沈振麟, 元和人, 字凤池, 一作凤墀,道光初即供奉画院, 同治十三年(1874)任奉宸院卿, 总管如意馆, 工写真, 亦善山水、 竹石、花鸟、 虫鱼, 画牛颇佳, 能创作于画轴、 册、扇、 贴落等; 顾肇熙, 长洲人, 字皞民, 号缉庭, 举人, 官工部主事, 擢道台, 晚年居木椟,工画, 书法苏轼; 赵宗德, 常熟人, 谱名宗藩,字价人, 号白民, 喜藏书抄书, 能诗文, 善画山水, 仿王翚笔意, 画多不署款, 只盖白民小印。与同乡书画家们的交往在《日记》中着墨不多,往往只记其名, 推其情形, 交游主题当为以书法绘画技艺为主的艺术交流。
顾文彬在京期间, 还广泛接触了不少文玩界的藏家, 与之交流经验, 共享藏品, 分享心得体会。 依《日记》所见, 顾文彬与松云庵心泉和尚的交往颇多。 心泉和尚为顾文彬旧交, “我闲暇无事, 日往琉璃厂闲游。 可与谈者, 旧识惟博古斋之李老三、 松云庵之心泉和尚, 新交有松竹斋之张仰山, 此人颇明于金石, 向与沈韵初交好”。 心泉和尚是京城有名的藏家, 顾文彬赏看了不少他的藏品, “(四月十二日)巳刻, 访心泉和尚, 见其所藏书画各件。 一夏珪纸本山水卷, 有俞紫芝、 黄大痴、 柯丹丘、 文衡山跋; 一恽香山纸本水墨山水册; 一恽香山青绿山水册;一王西庐山水册, 先画七页, 后补三页, 有王员照跋; 一恽南田山水册, 诒晋斋藏本; 一恽南田花鸟册; 一恽南田扇面册; 一黄瘿瓢画册; 一蒋南沙绢本花卉册。 皆真迹, 其中以南田山水册为最佳。 有陶九成绢本山水册, 乃伪迹, 盖旧画添款者。 又见汉玉各件, 大拱璧两件、 圭一件、 杠头两件、 文带两件、 书镇一件, 其中以杠头为最佳”。 通过鉴赏同道的藏品可以互相分享鉴藏体会, 增加经验, 有效地纠正误判。 后心泉因经济情况不佳, 大量出售藏品, 顾文彬也由此收购了一些心泉旧藏中的精华。 据六月廿七日《日记》眉批: “心泉收藏颇富, 赏鉴亦精, 近为境遇所困, 大半散去, 所存者以南田山水袖卷、 又山水小册、 又花鸟三种为最, 皆为余物色得之。心泉书画船从此减色矣。 余所欲购未成者, 只智永《千文》卷, 然究非开门见山之物矣。”
当顾文彬游逛琉璃厂, 发现“此间古钱刀币颇多, 惜我目不识丁, 将来拟请明于此事者代购”。 了解到李眉卿对古泉和字画颇有研究,特地主动拜访结交, “往晤李眉卿, 山东人, 刑部员外, 其父竹朋, 刻《古泉汇》者, 知其识古泉, 兼识字画, 一见如故, 约他日同游厂肆”。 与同好结伴游厂, 可取长补短, 互相校正。 经李眉卿推荐, 顾又结识胡石查, “往晤胡石查(义赞), 河南人, 辛卯同年胡仁颐之子。前日李眉卿称其精于鉴古, 故往拜之”。 顾文彬在京结识的收藏家还有景其濬, 字剑泉, 贵州兴义人, 咸丰二年(1852)恩科进士, 选翰林院庶吉士, 散馆授翰林院编修, 官至内阁学士。 他好收藏, 精鉴赏, 善楷书, 体态圆润, 平淡天真, 自成一格。 此外, 顾文彬还结识了孔广陶,广东南海人, 以藏古籍、 书画有名于时, 有粤省四大藏书家之誉, 所藏古泉亦甚精; 王景贤, 绍兴府山阴县人, 能承家学, 有画名。 在此不一一赘述。
从顾文彬的在京交游圈可以看出, 琉璃厂周围活跃着一批对文玩鉴藏有着共同爱好的人士,他们或为同乡, 或为同道, 交互鉴藏文玩, 携游厂肆, 交流甚或交换藏品, 实际地参与并丰富和提升了京城文化圈的艺术品位。 顾文彬与古玩店铺掌柜、 京城古文藏家以及书画界名家均有一定程度的交往, 这为他在琉璃厂的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活动创造了人脉, 使他能够更为充分地参与京城书画文玩的商品流通和鉴藏讨论, 进而为提升个人鉴藏水平, 沟通南北市场信息以及促动南北艺术品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四、琉璃厂交易中的沟通南北与家国情怀
对京城琉璃厂而言, 与顾文彬一道进京的,除了作为居京生计补偿的一箱待售的南货外, 还有他浸淫文玩界多年所形成的鉴藏眼光、 经验和能力、 艺术水准等。 顾文彬以个人为媒介将这些通过一系列鉴藏活动予以再现。 顾文彬的鉴藏素养, 与他带来的南货一起, 卷入琉璃厂的文玩买卖, 进而汇入南北文化交流乃至家国情怀共融的历史洪流。
文玩收藏, 首重眼光, 辨别市场导向, 把握市场主流, 关系到投资的成效。 就鉴藏眼光来说, 顾文彬初进京城之时, 对个人鉴藏才艺颇为自诩。 他提出: “自古一代之兴, 有能经文纬武、 名垂史册者, 落落不过数人。 书画特六艺之一耳, 然一代之中空前绝后者, 亦复不过数人。 ……国初以来, 四王、 恽、 吴推为六大家,论者谓可直接元四大家, 而于明四大家骎骎欲度骅骝前矣。 厥后作手非无矫然特出, 别树一帜者, 卒亦无能驾而上之, 于是风行一时, 收藏家于六大家苟不能兼收并蓄, 辄欿然不足, 以故搜罗日亟, 声价日增, 片楮零缣, 珍如拱璧。 余素抱书画之癖, 亡儿承之亦有同嗜, 竭数十年之精力, 所收古今名迹, 汗牛充栋, 而于六大家尤所心醉。 凡遇精品, 不惜重赀, 所蓄不止百种。”顾文彬认为, 四王、 恽、 吴六家之作为有清一代画艺之巅峰, 当为南北市场所公认, 他对顾承称, “所带字画已令李老三评价, 与汝所拟之价不无出入, 而总数不相上下。 京中所重亦是四王、 恽、 吴, 与沈、 文、 唐、 仇, 我所带之物甚合销路。 至于眼光, 虽李老三已算巨擘, 然不如我与汝远甚。 见石谷两册, 深信为真, 其易欺可见, 我即托其代销”。 顾文彬通过博古斋掌柜李老三的反应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南北市场均推重四王、 恽、 吴画作, 说明进京前的市场预估非常准确, 故对进京以销售书画作为解决生计的手段很有信心。 应该说, 一方面, 文玩交易过程部分证实了顾文彬的判断, 六大家之作定价高, 受欢迎, 但另一方面, 琉璃厂的文玩交易体验也逐渐改变了顾文彬的认识。 由南携来的书画实际销售并不乐观, “然带出之物, 既销不快,不得不再望续寄一二十件, 以为接济”。 而后续“寄来书画各件, 恽、 王扇面最为易销, 此外尚恐稍滞。 京中价值较苏虽昂, 而售主寥寥, 所谓有行无市也”。 市场呼声推高了书画价格,但实际买卖行情则受经济发展的制约, 要想在南北市场游刃有余, 顾文彬的鉴藏眼光还需两者兼顾, 尤其需要把握琉璃厂市场的实际经营情况和潜在的买方市场信息。
识别真赝, 既是鉴藏经验的积累, 也是鉴藏能力的体现。 顾文彬确实有多年的鉴藏经验, 颇有能力, 他纠正了一些同好的误判。 比如, 他在《日记》中指出心泉所藏陶九成绢本山水册, “乃伪迹, 盖旧画添款者”; 在论古斋以四金买得沈石田水墨山水立轴, 店主不知其为真迹, 心泉和尚也怀疑是伪作, 顾则断为真品; 有徐姓到德宝斋求售烟客山水立轴, 店主认为是赝品, 顾却认为真而且佳; 在凝秀阁见廉州水墨山水册十页,秦炳文鉴为真品, 顾却认为是伪作, 后证实果然为伪。
造假手段层出不穷, 防不胜防。 琉璃厂依仗京城地利, 文玩品类齐全, 甲于天下, 南方寻访多年不易得之物, 北地则可以轻易买到, 为此顾文彬感叹, “乃知京师之大, 无物不备”。 但深入到这样一个琳琅满目的文玩市场, 偶一失察, 就可能判断失误。 顾文彬起初还对古玉、 古泉有浓厚的兴趣, 很快就意识到, “至古玉、 古泉, 究不内行”, “惟所买玉器古泉等, 或有吃亏, 然亦无几, 况此后已定见不买”。 他也有误判误收的情况, “在英古家以十金得恽南田临米行草卷, 汉玉虎头一枚”, 后才意识到上当, “恽字不真, 玉虎头亦是提色。 恽字款是辛未, 乃南田已故之明年。 玉虎头用力盘之, 黑色易褪, 此皆不得之明证。 及携归苏中, 见者皆叹赏, 可见真鉴之难”。 顾文彬花费二十两买下的大痴轴, 后被鉴为伪迹。
鉴藏方面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的感悟也接踵而来。 顾文彬与藏家袁崇会晤, “观其所藏高房山设色山水绢本袖卷, 仇十洲设色《深柳读书》绢本卷。 此二卷廿年前曾见过, 当时不辨真伪,今日复观, 皆真迹也。 又祝枝山草书卷纸本, 真而且佳, 后有郑板桥跋”。 与精于鉴赏的同好一起游厂, 则可拓展视野, 增强鉴藏能力。 “先是前在论古斋见查二瞻山水册, 爱其工致, 向其借观。 携在车中, 出示石查, 一见决为赝本。 余询其于何决之, 曰家藏亦有一本, 取出勘对, 画境、 题字并于升双款, 丝毫无二。 审视之, 觉款字亦嫩, 始识其伪。 若给石查说破, 几乎以善价得之。 甚矣, 赏鉴之难也。”
鉴藏品味的提升, 是鉴赏家有别于古董商的重要方面。 顾文彬在琉璃厂的行迹, 表现出了超出一般性文玩鉴赏的学者气度和文化传承的家国情怀。 顾文彬醉心书画文玩收藏, 有明确的嗜古倾向。 他喜欢谈古, 青睐古书画的古香古色, 如鉴赏论古斋的萧照山水长卷, 称“画极古厚, 非明以后人所能到”, 喜汉玉, 爱其制之古朴,但又非食古不化, 于鉴赏一途, 以作者的品行气节为先。 他教育子弟书画技能, 强调“先论其人, 次论其书法、 画理, 再论其价值”,由推重为人再至推崇其作品。 他常常强调书画作者的气节, 对抗清名士黄道周、 明遗民傅山等非常敬重, 亦极为关注其作品, 每在厂肆中遇到,无不驻足。 他在给顾承的信中写道: “绫本石斋卷既已售去, 我家并无石斋手迹, 陈伯蕴所藏相眼册乃石斋精品, 题跋亦精, 此册志在必得, 汝当亲往图之, 价即昂亦不必吝惜。 此间石斋字既少而声价亦昂, 可见此老真迹, 宇内海外均知宝贵, 安可交臂失之?”“在德宝斋见傅青主草书大轴一帧, 草书唐人七绝条幅十二帧, 皆纸本, 屏末幅自跋三行, 秃笔狂草, 字多不识。 后见其父子杂书册两本。 青主所书皆断简残编, 首页仿颜楷书为最, 余皆信手。 寿毛所书小楷甚工, 余法晋人, 胜于前日所见行草卷。”观顾文彬所处之时代, 内忧外患交至, 两次鸦片战争后政局动荡, 民议沸腾, 此时此刻, 在收藏书画文玩之时强调作者的品行与气节, 无疑沾染了时代的气息, 反映了现实国情与民情的呼声。
琉璃厂购置的藏品中, 顾文彬最为钟爱者,当属购得的八十枚马泉和从景其濬处易得的汉玉钩。 据《古泉汇》载, 马钱存世只一百二十枚,“今一朝而十获其七, 岂非快事? 虽费多金, 何悔焉!”购得之物与家藏之物合体, 则成马泉百品。 同样, 顾文彬家中藏有一只汉玉琴钩, 又从景其濬手中获得另外一只, “此钩与余昔年得张柳亭汉玉钩制造出于一手, 色泽、 分寸若合符节, 惟下半钩所镂琴轸一凹一凸, 似分阴阳, 当时必是一对。 千百年后, 散而复合, 洵奇缘也”。 顾文彬为此将双玉钩与马钱百品汇藏一室, 将书斋命名为“金马玉琴之室”, 撰对联云“磅礴百金马; 摩挲双玉琴”, 旁注云: “艮庵来游京师, 得燕庭刘氏马泉八十余品, 合之家藏十余品, 集成百品。 又得景剑泉阁学所赠汉玉琴钩, 与家藏一钩制造出于一手, 色泽、 分寸若合符节, 千百年物, 珠联璧合, 洵奇缘也。”马泉的百品汇聚, 玉钩的双钩合璧, 体现出顾文彬整合南北藏品, 汇为一体, 以化零为整、 变散为聚的观念。 顾文彬指出, “大约书画日少一日,次者、 赝者固宜售去, 其真而佳者亦须买进, 如待价而沽, 总可得善价。 据此, 则孙辈讲书画一节尤不宜缓耳”。 于小处, 固然是为子孙某未来之生计; 于大处, 何尝不是为民族谋未来文化传承之根本。
顾文彬所生活的晚清, 政治衰败, 经济困顿, 珍贵的典籍、 书画、 文玩等聚而又散, 更有大量珍品流散海外, 收藏家们凭借一己之力购买、 汇聚和存藏的行为, 实质上是一种可贵的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态度, 反映了收藏家珍视、 抢救并保护民族文化的情怀。 即此而论, 顾文彬在琉璃厂的书画文玩交易, 不仅是以一身兼通南北, 更是以一人兼顾家国。
五、结语
晚清文献档案浩如烟海, 而能翔实系统地聚焦北京琉璃厂市场交易情况的并不多见, 顾氏日记、 信札如吉光片羽, 对晚清北京史、 艺术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重要史料价值。 顾文彬在琉璃厂的社会活动, 反映了晚清琉璃厂的书画文玩货品、 市场、 交易、 鉴藏及士林交游、 文化交流等丰富的历史内容, 凸显了琉璃厂在南北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核心作用, 同时反映了晚清艺术品鉴藏活动的市场动态、 士林风气和学术主流。 顾文彬其人其行堪称晚清琉璃厂以书画文玩交易形式参与南北文化交流、 传承历史文化的典型个案,其价值和意义弥足珍贵, 值得认真总结、 大力弘扬。
:
① 文中数据按日记所载统计, 不排除《顾文彬日记》并未将游厂肆活动完全记录。
② 苏州市档案馆和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整理的《宦游鸿雪》第一册收录顾文彬同治九年的信札29通, 按时间计, 其在京期间发出的信札共23 通。
③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中进士后, 顾文彬曾在京任官14 年, 咸丰五年(1855)外任湖北汉阳知府, 才离开京城。
④ 以《顾文彬日记》为中心探究琉璃厂文玩交易的研究成果, 以笔者所见, 有艾俊川《过云楼的书画生意》(《文汇报》2017 年3 月3 日), 述及顾文彬在琉璃厂参与书画买卖的大体情况; 李特《德比圭璋 与古为徒——晚清民国(1851-1945)德宝斋古玩铺艺术品经营初探》(《美术大观》2019 年第9 期), 着重利用顾文彬日记为史料还原德宝斋的艺术品经营状况;沈慧瑛《顾文彬京城淘宝记》(《中国档案报》2020 年9 月18 日), 侧重概述顾文彬在京城的文玩交易活动。 此外, 白谦慎著《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涉及顾文彬所参与的“四王”画作南北交易的情况。 本文在梳理顾文彬在琉璃厂参与文玩交易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究其在南北文化交流层面所扮演的角色、 发挥的作用。
⑤ 参见高福民. 过云楼梦——大变革时代江南文脉之一隅[M]. 文汇出版社, 2016.
⑥ 表格数据源于《日记》所载, 因《日记》载录顾氏游览店铺及参与文玩交易时偶有未及铺名的情况, 故本表数据当不完全, 但可供研究参考。
⑦ 参见顾文彬同治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日记, “与论古斋议定宋拓《定武兰亭》卷、 王石谷《十万图》册, 价银八十两。 近日快心之事, 除军机进单外, 此事为最。 然进单一节尚属分内之事, 此则得之意外者。平心而论, 即石谷册已值此数, 《兰亭》卷只算凭空拾得, 论此卷价值, 即三百金不为贵也”。 顾文彬著, 苏州档案馆、 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 顾文彬日记[M]. 文汇出版社, 2016: 22.
⑧ 《日记》所见顾文彬在京交游甚广, 笔者仅以琉璃厂文玩书画活动为中心, 对部分交流对象加以考证和说明。
⑨ 据张祖翼《海王村人物》, “至博古斋主人祝某, 鉴赏为咸同间第一, 人皆推重之”, 或二人非同时执掌博古斋。 详见张祖翼. 清代野记[M]. 中华书局,2007: 197.
⑩ 据《日记》, “(十月初五日)在德宝斋, 有徐姓持来烟客山水立轴求质, 店主李诚甫斥为赝笔, 余审为真而且佳, 托店主和会, 惜索价太昂, 未成, 然念之不置也”。 顾文彬著, 苏州档案馆、 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 顾文彬日记[M]. 文汇出版社,2016: 36.
⑪ 据《日记》, “(十月廿四日), 以六金得汉玉方勒一枚, 此勒于数月前见于东城古玩铺绪古斋, 还价三金, 不售。 嗣后托德宝店伙屡次添价, 今始买得,亦前缘也”。 顾文彬著, 苏州档案馆、 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 顾文彬日记[M]. 文汇出版社,2016: 39.
⑫智永《千文》卷后亦为顾文彬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