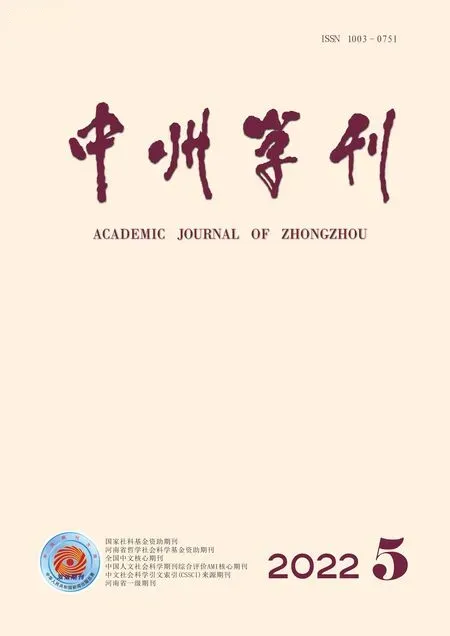从文本盗猎到文本围猎: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建构
付 佳 赵 树 旺
基于新媒体语境下的赋权与赋能,当今时代的媒介用户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和互动意识。他们不只是接受信息,也会积极地参与媒介内容生产过程。以用户生产内容为代表的参与式文化成为网络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式文化空间得以形成。所谓参与式文化,即网络用户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积极主动地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而形成的一种平等、公开、共享的媒介文化样式。身处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媒介用户在消费信息的同时参与文化生产实践,同时扮演着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且其生产出的文化内容具有自身独特属性,形成了全新的媒介景观。
一、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文本对话:从游牧、盗猎到围猎
参与式文化的概念由美国学者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一书中首次提出,用以描述媒介文化中的互动现象。深受约翰·费斯克文化研究视角的影响,亨利·詹金斯在肯定用户能动性的基础上,提出文本盗猎、粉丝文化、参与式文化和融合文化等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为文化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活力。
在《文本盗猎者》一书中,詹金斯考察了电视媒介时期作为文化工业话语边缘群体的粉丝群体是如何通过对大众文化资源的拼贴重组进行话语抵抗和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同时批判了当时学术框架下粉丝群体“头脑简单且痴迷成性”的污名化标签。詹金斯对法国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德赛都“盗猎、游牧式”的读者理论表示赞同,并进一步肯定了读者的能动性,将读者视为文本意义生产的中心。他认为,读者就像没有固定位置的游牧民族,不可能定居,他们为一种自然天性所左右,自由地穿梭在他人的土地上,以掠夺财富、掠夺文本为乐趣,过着偷猎式的游牧生活。当他们遇到感兴趣的文本便稍作停留,并根据自己的蓝图进行重新拼贴组合,使文本在读者的阐释以及与其他读者的交流过程中得以不断延伸及重新塑造,在此过程中完成文本盗猎活动。
詹金斯将这一群体具化为粉丝群体,粉丝文化是对主流文化中等级秩序的公开挑战,其否定了作者权威,侵犯了知识产权。粉丝群体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文本的热爱,不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字与知识产权所恫吓,力图将媒体的呈现与自己的社会经验结合起来,从大众文化中攫取可运用的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作为自己的文化创作与社会交流的一部分。在詹金斯的笔下,粉丝群体被视为一群文本盗猎者,他们肆无忌惮地盗取大众文化资源中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将其据为己有,正是在此过程中,文本的意义得到了新的诠释与延异。
尽管文本盗猎者的概念提出于电视媒介时代,但这个具有前瞻性的概念在新媒体时代依然适用。在当今参与式文化空间的搭建过程中,媒介话语权被重新分配,传统的媒介权力格局被打破,用户之间的互动显著增多,对于文本的诠释已形成围猎之势。所谓文本围猎,即众人的盗猎,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文本对话形式正由个人的盗猎活动转变为声势浩大的群体性围猎活动。整个社会架设在互联网之上,精英文化祛魅,草根文化崛起,大众文化异军突起,成就了个体赋权后的围猎景观。各社交平台粉丝群体是积极的文本围猎者,他们追踪媒介生产的内容,但更看重自创或二次创作的衍生作品,如精修图、同人文和视频混剪等。他们通过社交媒体沉浸于粉丝文本流之中,并在创作、散播、讨论中收获文本带来的快感。这种趋势模糊了原初作品与复制品的界限,也消解了根源性的宏大叙事。
在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隐藏文本走上前台成为日常景观,并导致创作的高贵性崩散,艺术品的神圣性崩散、珍贵感消散,卓越的人、物及其关注度的削弱与离散。从个体走向集体的媒介用户期望通过参与有意义的对话来维护共同利益、表达共同愿望,这就使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文本呈现出更高的互动性,用户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集体沟通表达主张,并利用线上平台发起集体活动。
二、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文本类型
英国学者麦特·西尔斯将约翰·费斯克关于粉丝生产力的开创性研究与网络“民主化”以及参与式文化联系起来,并将文本生产行为归纳为四种:第一种为原生数字与模拟修复,前者指粉丝手绘图,后者指利用技术手段修图。第二种为模拟与变革,前者指利用特定技巧生产模拟文本,如扮装游戏;后者指对源文本进行非直接模仿的重新改造,如同人小说。第三种为非正式与正式文本生产,指用户生成文本常常在粉丝与官方之间游移,如发表在商业粉丝杂志上的粉丝信本身是偏向粉丝群的,但刊发后偏向官方文本。第四种为显性与隐性文本生产,詹金斯将前者理解为内在动机行为,而其他学者认为新媒体时代文本生产的显性参与之下还存在着隐性参与,如用户常被软件和界面设计所引导而将某个平台中的账号头像更换为偶像照片等。
可见,在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式文化空间中,文本类型已被学者置于不同的微观层面进行细分研究与拓展。文本的外延也已获得延展,凡是由主体生产的、具有一定表征意义的、能够传递某种价值观的内容都可以被视为媒介文本。因视角的不同,参与式文化空间中文本生产类型的划分也会有所差异。
从文本生产过程来看,参与式文化空间中文本生产类型包括原始文本和二次创作文本。原始文本是指从一开始就流通在文化空间中的文本。二次创作文本则指用户以原始文本为基础,并对其进行改编、挪用、颠覆甚至创作出的全新文本,如一些视频平台中媒介用户热衷于利用影视剧的原始素材,通过剪辑、转场、拼接的方式重新塑造一个人物形象、一段新的故事或是改变某个人物的结局,以满足观众对于某一人物的幻想或弥补剧情遗憾等。
从文本生产主体来看,主体的多样性造就了文本样态的多样性。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文本样态呈现出用户生产内容(UGC)、专业人士生产内容(PGC)和职业生产内容(OGC)并存的态势。UGC模式即充满内容生产与传播热情的普通用户在参与式文化空间创造大量文本的模式。作为通过社交关系链进行分享并构建个人音乐主页的音乐社交形式,网易云音乐是用户生产内容模式的典型代表,参与式文化在其中得到全新诠释。其用户生产内容模式具体表现为制作歌单、参与话题讨论、发表歌评和动态等行为,为音乐社交生态奠定基调,保证了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文本数量。PGC模式指出于个人爱好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在参与式文化空间发布内容的模式。其特点是更加专业、更有深度且垂直化。他们发布的内容通常会受到较高关注和众多普通用户的追捧和喜爱。一些视频平台中的意见领袖,通过发布个人作品来获取粉丝的高关注度,其内容包括视频教学、干货分享等方方面面具有一定专业性的内容,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垂直化的内容进行观看,并通过弹幕、评论的形式与之互动。这样的参与式文化创作平台可以聚合大量用户,形成一个虚拟社区,创作者和用户都能在其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情境与体验,并逐渐对该种情境产生依赖,在此过程中用户与平台之间的黏性不断增强。OGC模式是指由具有一定专业背景的行业内人士进行内容生产的模式。如网易云音乐官方通过推荐优质内容、发布专栏等来整合用户,沉淀优质文本,网易云的专属场景歌单专栏中就包含众多类型的歌单,用户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挑选自己感兴趣的歌单。综合来看,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用户生产内容确保了文本数量,专业人士生产内容提升了文本质量,而职业生产内容整合与补充了用户生产内容和专业人士生产内容。三者合力奠定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内容与文化基调,提升文本数量和质量,平台方也会借此维护空间内的文本环境。
三、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用户的参与方式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建构提供了可能,“两微一抖”等开放性社交媒体满足了人们日常沟通及获取信息的需要,豆瓣、知乎、网易云等平台则因其自身属性吸引了大量用户,各具特色的虚拟社区因此形成。在这些虚拟社区中,具有相同兴趣、爱好和立场的用户通过交流、创作、分享与互动逐渐实现了身份认同,并通过政治及社会参与、知识生产参与、娱乐性参与,在意见交锋的过程中凝聚成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1.政治及社会参与
政治及社会参与是指公众以网络为途径和手段参与社会公共事件和政治活动的行为。在社交媒体时代,参与式文化空间为公众的政治与社会参与拓宽了渠道,提高了效率,提供了新思路,反馈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公众意见在政治及社会事件中的影响力愈加扩大。
除了社交平台自身,传统主流媒体也开辟有“两微多端”的社交平台出口,为用户提供在线参与性平台。用户通过社交平台进行留言、评论等形式表达个人意见,能够与后台采编进行直接在线沟通,这体现的是一种集中的交互模式。通过多元化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能够针对社会变革和新闻事件等热点针砭时弊,进行政治和社会参与。政府决策部门在对相关事件的意见文本进行整合后,能够了解舆情走向,并将用户意见作为舆论引导决策的重要参考。在此过程中,媒介用户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参与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决策工作,集中体现了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
2.知识生产参与
在开放性的参与式文化中,每个人都是知识链中的一环,人们自愿把分散的个人技能、知识资源进行整合,并通过群体协作形成有效的问答机制,推动问题的解决。詹金斯用法国数字文化理论家莱维的集体智慧概念描述用户的参与、互动。在参与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人们也实现了个人知识的积累与升级。参与式文化空间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网络社会中愈加扩大的知识鸿沟。
克莱·舍基视“认知盈余”为全世界受教育公民自由时间的集合体,其核心观点为人们的自由时间不仅用于内容消费,还应用于内容分享和创造,分享和创造的价值远大于消费。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公众进行知识生产参与的渠道被打通,其参与知识生产的热情也进一步被激发,收费制与公共性并存的知识生产模式逐渐形成。得到App即是典型的收费性质的知识生产平台,其在研发知识产品阶段,围绕个人发展推出覆盖30多个领域的知识产品。得到App的运营模式为通过与头部知识生产者签约,利用这些知识生产者完成为其他用户整合知识内容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将知识系统化地传授给目标用户。以用户为主导的知识分享平台知乎App则不同,其用户大多是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都市白领及大学生,主要以青年人为主,互联网从业者居多,男女均衡。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是知乎用户的三大特点。知乎平台中的内容相对来说更有深度,尤其知乎热榜上主要是反映社会热点、体制问题等较深层次的内容。用户在知乎App中提出问题,另一些用户回答问题,形成了平衡高效的问答机制。
知识生产参与能够有效缩小社会不同阶层的知识鸿沟,使知识生产呈现出知识的去精英化与再精英化混合的趋势。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知识生产的方式能够更加激发用户的主动性,再次确认了用户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主体地位。在这个公众自发形成的知识生产与分发的体制中,知识资源被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
3.娱乐性参与
与传统媒体空间不同,用户始终是社交媒体参与式文化空间得以构建的重要推动者。他们凭借自身的经验与情感对空间中的原始材料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并赋予其全新的内涵。面对日益加快的社会内卷化进程和日益沉重的现实压力,越来越多人产生了“避世”和“佛系”心态,他们沉溺于网络社会中的娱乐化内容以缓解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焦虑。因此,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用户的娱乐性参与就成为其不可忽视的参与方式之一。
作为一种开放性文本,弹幕视频得到众多用户的喜爱,这是由于新媒体用户的参与性被大大激发,而弹幕视频恰好为用户参与视频生产与传播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弹幕的出现使用户能够在观看视频的同时参与关于剧情、演员的讨论,能够和其他用户进行实时的意见交流与互动。用户发布的弹幕是基于视频原始文本的二次创作,用不同于原视频的视角重新构思,对视频文本进行重新解读,赋予其新的意义,许多具有较强传播性的“梗”均出自弹幕中。另外,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网络流行语极易引起用户的迷因式传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凡尔赛文学”热就曾一度刷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这是一种“以低调的方式进行炫耀”的话语模式,呈现出滑稽、讽刺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先抑后扬,明贬暗褒,自说自话,假装用苦恼、不开心的口吻炫耀自己。这种话语模式引起了用户的热切追捧,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引发群体性模仿行为。在此类娱乐性参与行为中,用户发表的个人看法和产出内容即成为参与式文化中的构成部分。用户在参与过程中不仅增加了平台黏性,也找到了具有相同兴趣与立场的群体,实现身份认同。用户在对文本内容进行意义解读和二次创作的同时找到了情感宣泄的突破口,也丰富了参与式文化的内涵。
四、参与式文化空间建构的内在逻辑

1.新媒介赋权改变原有权力关系

具有强大交互性、及时性、高渗透性的新媒介使赋权行为逐渐发生改变,原来的弱者开始占据主动地位。网络赋权打破了原有社会权力分化的阶级性并模糊了权力关系的边界。新媒介赋权所造成的弱者弥散化更导致了社会结构中强弱界限的模糊,使原本在政治、生理和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个人和团体与主流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弱者与强者的角色开始相互转化。媒介赋权帮助普通用户撕去弱者标签,并使其在网络社会站于话语权舞台的中心。
用户群体在网络社会中的影响力逐步扩大。面对热点事件,用户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扮演着信息发布者、接收者和反馈者等多种角色,并通过转发、评论、点赞等方式表达个人立场。他们贯穿事件传播的全过程,其发布的内容构成参与式文化的一部分。参与式文化空间成为参与式文化得以传播和不断丰富的重要场域,助力新媒介用户获取传播权,并进一步反哺参与式文化空间的建构。
2.趣缘群体的身份认同与话语狂欢

趣缘群体的成员虽身份各异,但存在着高情感卷入度的强关系。通过特定门槛筛选出的群组成员之间会建立一种高度的信任感和认同感,群体内的信息交流与情感互动也呈现出更加隐蔽、深入的特征。这种强关系能够在成员之间形成高黏合度,有效将之凝聚在一起,形成群体内的特定语言形态,分散的个人资源也得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资源。

3.社交媒体中弱连接关系凸显

社交行为由线下转移到线上,由日常生活延伸至网络空间。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使用使人们的关系网得到无限延伸,由于特定原因而建立联系的两人或多人能够完成实时互动,低成本、高效能的传播效率实现了信息和情感的快速传播。在此传播活动中,人们不仅扮演着参与式文化创造者与传播者的角色,也担负着建构参与式文化空间的使命。
4.虚拟社群中的互动仪式与情感宣泄

虚拟社群是通过互联网联结起来的人们突破地域限制,进行交流沟通、分享知识和信息,从而形成相近的兴趣爱好或情感共鸣的关系网络。其核心要素包括网络技术的支持、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相同的兴趣点、持续的互动行为以及能够获得情感满足。因此,作为最终目的的满足情感需求成为新媒体用户持续互动的根本动力。虚拟社群中的互动往往是社群成员之间的情感互动,图片、文字等互动表征在本质上都承载了一定的情感内涵。作为参与式文化空间的社交媒体平台,成为用户表达个人想法、进行情感交流的主要场所,承担起情感“树洞”的角色,带有明显情感倾向的评论和互动内容在整个参与式文化空间中蜂拥而至。虚拟社群中的互动仪式与情感交流提升了用户的参与意愿,而用户也在逐步构建参与式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深化了归属感。
五、参与式文化空间建构的关键:多方力量的平衡与协调

在参与式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社交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是关键矛盾。作为参与式文化空间的构建者,他们通过合作、抵抗和互相制约的方式推动并塑造着空间行为。对于用户而言,参与式文化空间意味着更加开放的创作环境、更加丰富的文本,他们在这里拥有饱满的热情和充足的动力。对于社交平台而言,他们更看重优质内容背后的庞大用户群体和源源不断的流量,内容也不过是流量的代名词。离开了用户,平台就丧失了内容生产来源;离开了平台,内容就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整合,散落于空间中的只是尚未成形的文化碎片。因此,参与式文化空间构建中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找到用户与平台的平衡点。当用户的身份发生转变,不再只是隐匿于文本背后,而是正在承担创造性工作时,社交平台就需要转变思维,以一种新媒介素养的引领来面对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转变。
新媒介素养应该被视为一个大型社区中的互动方式和社交技能。在参与式文化空间中,对用户的考验更多是个体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和团队协作的能力,而新媒介素养的养成需要政府、媒介、学校和用户等多方共同努力。在新媒体时代,作为参与式文化创造者和发展者的用户很难有效分辨信息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常常会感到无所适从,这会消耗其进行内容生产的热情。因此,用户应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批判意识和判断能力,避免人云亦云的参与方式,增强道德意识,提高社会责任感。参与式文化空间中的用户多以青年人为主,未成年群体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未成年人的社会经验不足,人生观、价值观尚不健全,在匿名的网络世界中极易做出非理性行为,学校不仅要传授理论性的媒介知识,还要重视对学生媒介素养的教育并加以引导。另外,政府和媒介应友好协作,在坚持正确文化导向的基础上,营造一个更加开放、平等的对话环境,为参与式文化的成长搭建良好的发展空间,赋予其多元而不失共识、自由而不失理性的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