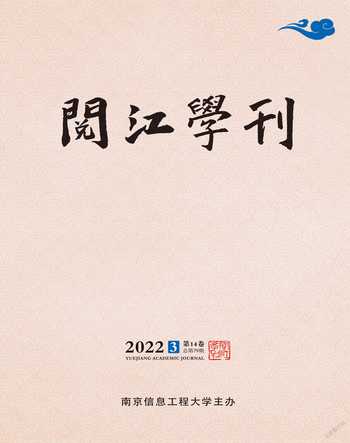为什么应当考虑历史排放
卢卡斯?麦尔
摘 要在当代人之间公平地分配气候变化政策所带来的收益与负担时,应当考虑历史排放,这个观点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证明。首先,历史排放如果(而且仍然)确实给当代人与后代人带来了收益,那么,它就应当成为理想的分配正义所要关注的问题。其次,我们很难证明对历史排放导致的伤害采取补偿措施具有合理性,原因有三:非同一性问题,过往世代对其排放之长远影响的有限认识,过往世代对当代人的责任分担问题。与其把气候伤害视为补救错误行为的一个理由,还不如把它们用于证明对不应得的收益与负担进行再分配的合理性。最后,在影响发达国家人民对自己当下的排放预期方面,历史排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要实施一套公平、有效、可合法地强制实施的全球气候规则,那么,就必须要兼顾发达国家人民的这种预期。
关键词历史排放 补偿正义 分配正义 代际义务
一、导 论
代际正义问题,指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亏欠问题和如何规范地阐释过往世代人们的行为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当前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应当采取的措施具有核心意义。在确认当代人目前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时,思考过往世代与未来世代之责任是非常必要的。在气候正义的争论中,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以一些有趣的方式被联系起来。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应当如何在对当代人排放权的最初分配中把历史排放及其有利影响考虑进来?我将在本文第二部分指出,作为一个分配正义的理想议题,如果迄今历史排放的影响能够被解释为是对当代人与后代人有利的,那么历史排放就应当被考虑进来。在《气候变化的正义》中,波斯纳和韦斯巴赫没有讨论这个议题。①
我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注的是,谁应当为历史排放的伤害买单,尤其是在假定人们(作为个人或者作为集体)的排放尚未达到其公平份额并且未来仍然不会达到其公平份额的情况下。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同意波斯纳和韦斯巴赫的观点,即基于他们在《气候变化的正义》第5章给出的理由,补偿支付的合理性很难得到证明。]Eric A. Posner,David Weisbach, Climate Change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103-108。正如下文所解释的,这两个理由是:第一,过往世代的人们对其行为的长期后果(作为其排放行为的副产品)一无所知;第二,我们不能说,当代人需要对在他们出生之前的其他人的行为负责。]即使这些理由能够成功地证明某些补偿性措施的合理性,它很可能只为那些导致气候变化或遭受气候变化伤害的人证明了补偿性措施的合理性。然而,我将补充一个重要理由——在某种程度上,后代人的存在的偶然性和个人身份的同一性取决于当代人的决定和行为,伤害和利益的通用概念并不适用于解释这些行为的影响——来证明,就代际关系而言,补偿理据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同时涉及当代人的行为对后代人幸福造成的影响和过往世代人们的行为对当代人幸福造成的影响。我将进一步指出,由于当代人没有履行他们的义务,可以说他们对后代人是有所亏欠的(未采取补偿性措施)。我同样认为,与其将气候伤害理解为对错误行为进行补偿的根本理由,我们更应该将气候伤害看作对不应得的利益和伤害进行再分配的理由。平衡历史排放所带来的非常不平等的影响,这是分配正义的合理关切之一。最后,我将指出,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形成他们对于当前排放的预期时,历史排放有着重要作用。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阻碍人们的这种期待:达成一种公平、有效且能合理地强制实施的全球气候规则。
二、我们应当如何分配排放?
关于分配排放的论证包括以下四个基本步骤,我将会在第二部分第一小节介绍前三个步骤。在接下来的两个小节中,我将讨论我的观点对排放分配权的启示。
(一)排放分配的三种预设
首先,我们需要讨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排放限制和仍然被允许的最大排放量。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出,作为一个代际正义的问题,当代人必须尊重后代人的基本权利。与这个背景相适应的正义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是充足主义的,即把保护所有世代人们的基本权利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我认为,用充足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代际正义,是有许多特殊且重要的理由的。参见Lukas Meyer,“Past and future: The case of a threshold notion of harm”, in Lukas Meyer, Stanley L. Paulson, Thomas W. Pogge, et al, Rights, Culture,and the Law: Themes from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oseph Raz,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Lukas Meyer, “Intergeneraionelle suffiziengerechtigkeit”, in Nils Goldschmidt, Generationengerechtigkeit,Walter Eucken Institut,2009. 我预设了一种多元主义的正义概念,该概念反映了人们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支持代际充足主义的那些理由反映了代际关系的非偶然性特点。对于同时代人之间的关系,标准更高的原则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对于国际关系,我提出了下文所述的优先论。参见Lukas Meyer,Dominic Roser,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climate change: The allocation of emission rights”, Analyse & Kritik, vol.28, no.2(2006).]這种对代际正义要求的最低限度的理解,有助于规定一个仍然被允许的最大排放量。
其次,我们需要阐明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对剩余可排放量的公平分配。这里所讨论的物品(Goods)是人们在实施这类行为——该类行为不可避免地以排放为副产品——时所获得的好处。现在几乎我们所有的行为——比如生产工业商品、耕种以及飞行——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排放这一副产品。产生排放是大多数有利于我们福祉的行为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虽然我们没有理由对这类排放本身感兴趣,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关心我们的福祉。因此只要排放是我们行为不可避免的产物,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被允许排放。所以,我建议将“分配排放”理解为分配那些会产生排放行为的许可的简称,而这些产生排放的行为通常使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受益。这些许可通常被称为“排放权”]对“排放权”的一个说明参见Lukas Meyer,Dominic Roser,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climate change: The allocation of emission rights”, Analyse & Kritik, vol.28, no.2(2006).]。因此,分配排放就意味着通过分配排放权来分配通过排放行为而获得的利益。60DE4A6E-6096-4957-A948-16EF7524901D
最后,我们需要明确用于评判分配排放量的原则。为此,我提出了优先论的观点。]参见Derek Parfit,“Equality and priority”, Ratio,vol.10, no.3(1997).]按照优先论的观点,无论其他人拥有多少,使人们受益都是重要的,但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境遇更差的人们的利益,而不是境遇更好的人们的利益。优先论观点的一个合理版本规定了以下优先分配原则:那些境遇更糟的人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好处,我们应该使那些应优先被考虑的利益总和最大化。
显然,优先论的观点并不会遭受严格的平等主义正义观所遭受的诸多批评。根据上述优先原则,平等本身并不重要。因此,优先论观点不会遭受向下拉平异议的批评。一种严格的平等主义观点认为平等具有内在价值,这意味着我们有理由为了平等而使较富裕者的处境变差,即使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向下拉平是令人反感的。]参见Nils Holtug,“Egalitarianism and the levelling down objection”, Analysis,vol.58,no.2(1998).]即使优先论的支持者认为社会、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差异都没有任何内在的坏处,他们的优先论观点也往往具有平等主义的含义。优先论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如果X的处境比Y更糟,那么我们至少有一个初步理由来促进X的福祉而非Y的福祉。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优先论原则要求对相关物品进行平等分配。但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优先论原则将认可给予一个人更多的物品是合理的:第一,这个人的处境更糟;第二,鉴于优先论是一种集合论,这个人可以更好地利用该物品实现更大的整体收益。接下来我将讨论,在考察优先论对排放权分配的意义时,这两个不平等分配的理由是否相关以及二者如何相关。
(二)如何不考虑历史来分配排放
我将证明,如果且只要历史排放的影响被认为是对当代人和后代人有利的,那么,把优先论应用于排放权分配时,历史排放就应当被考虑进来。我的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在这一部分,我将说明,当我们忽略当前世代人们的历史排放和过往世代人们的历史排放时,优先论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要求对排放权进行人均平等分配。然后,在第二部分第三小节,我将阐述,对历史排放的巨大差异的说明如何能够证明排放权的不平等分配是合理的。
我们应如何将优先论原则用于排放权的分配?我将会采纳的一个选择是,在将排放权的分配与其他物品的分配完全分离的情况下,再考虑对排放权的公平分配。第二个选择是,将目前对所有物品(或至少與分配正义相关的所有物品)的高度不平等分配视为既定的,]对正义理论主题的其他理解可能包括:任何物品——只要它们能够影响人们的福祉或影响分配物品的制度设计——就应当被考虑。]再对排放权进行分配,以平衡当前与正义相关的所有物品的分配不平等。第三个选择是,将排放权的分配与全球正义理论所倡导的对其他物品的公平分配结合起来考虑。
这三种选择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大体上遵循第一种选择,将每一种物品与其他物品分离之后再进行分配,我们不一定能够实现优先论原则所要求的那种总体物品分配:不同的物品(由于它们被不平等分配)以多种方式相互作用,这些方式会影响人们从这些物品中获得的利益。如果我们遵循第二种选择,并且将所有物品的分配都作为既定的分配考虑进来,那么,这可能就会要求把所有的排放权都分配给全球的穷人,也就是分配给那些很少拥有其他物品的人;只通过公平分配一种物品来实现物品的整体公平分配,似乎不是那么令人信服。第三种选择的问题是,当与其他物品一起考虑时,将优先论原则应用于每一种单一物品的分配将会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将无法具体说明这对任何单一物品的分配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排放权的分配意味着什么。
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理由,我建议采纳第一种选择。在我们这个非理想的世界中,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配自然资源(或通常意义上的所有物品)并不是一个具有很大政治可行性的议题,但如何分配排放权却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具有政治可行性的议题。考虑到后代人的权利,如果我们有强烈的理由来给全球排放(这种先前可以无限获得的物品现在变成了一种稀缺物品)设定上限,那么,我们就面临着如何分配这种新的有限物品的问题。如果我们决定将这种物品的分配与其他物品的分配分离开来,那么我们以后可能不得不改变规范的要求——根据一个物品的分配对其他单个物品的公平分配或所有物品的总体公平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参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本文把他的方法论理解为,限定研究的主题,以便使剩余的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
在第二部分第一小节,我区分了两种基于优先论原则进行不平等分配的理由,在典型情况下,这两种理由都仅仅要求对这些权利进行平等的人均分配。优先论证明,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对固定数量的物品进行不平等分配才是合理的:首先,如果一些受助者比其他人的境遇更糟糕;其次,如果这些受助者中的一些人可以从这个特定物品中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利益。]一旦考虑到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平等分配的第三个合法理由就出现了。优先论原则可以通过迎合责任的观点来考虑这些选择,也就是说,尊重自由选择的价值,即使这将改变最佳的优先论分配。]当我们将优先论原则单独应用于排放权分配时(换句话说,从现有背景下所有物品的分配中抽取出来),这两条认可不平等分配的理由是否仍然适用?显然,它们不适用于此,因为,当我们把排放权的分配与其他物品的分配分开考虑时,这两条理由都被排除了。第一,如果我们忽略了其他物品的分配,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分辨出排放权的哪些获得者是境遇更好的,或者哪些获得者的境遇更差。第二,人们能从排放权中获得多少好处,取决于他们能否获得其他物品,比如财富、自然环境或者所在国家的产业结构。因此,当把其他所有物品的分配都视为与排放权的分配无关的要素时,优先论将要求在个人之间分配平等的排放权,也就是平等的人均排放权。本文其余部分的讨论所依据的前提是,按照第一种选择并在不考虑历史排放的情况下,运用优先论原则将青睐人均排放权的平等分配。60DE4A6E-6096-4957-A948-16EF7524901D
(三)在排放权分配中考虑历史排放
历史排放对当代人(和后代人)有着非常不平等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是有利的也是有害的。过去和现在的排放水平与财富水平具有紧密的联系。从因果责任的角度看,高度工业化国家在1850—2002年的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三倍。]参见Kevin Baumert, Timothy Herzog, Jonathan Pershing, Navigating the Numhers: Greenhouse Gas Data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2005.]尽管(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大部分是由现在高收入国家的工业化造成的,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特别是后代人——将不成比例地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更多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鉴于历史排放既有有利的影响也有有害的影响,区分两种可被视为具有规范意义的历史排放的方式似乎是合理的。第一,历史排放的有利后果可以被认为与当代人之间被允许的剩余排放量的公平分配有关。这涉及减排负担应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配。谁应该承担那些将排放量减少至合理配额而付出的成本?第二,历史排放的有害影响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的公平分配有关,这些成本是无法避免的或必须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考虑到一部分人的确曾经排放了比他们应得的排放量更多的温室气体,并且他们的排放仍然没有保持在其公平排放份额之内。这里,我们关注的是适应气候变化的负担应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配。
虽然在政治谈判中,减排和适应的议题经常被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独立的议题。正如第二部分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所述,分配排放权(减排问题)可以被看作分配正义的议题。许多理论家认为,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买单(适应议题)属于补偿正义的议题。]参见Maxine Burkett, “Climate reparations”,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0 (2009).另见Eric A. Posner,David Weisbach, Climate Change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 99-118.]最后,我将论证,它也应该被看作一个分配正义的议题。
历史排放的有利影响是否应该被认为与当代人之间被允许的剩余排放量的公平分配有关?如果是这样,它们是如何发生关联的?我们先区分反对抵消历史排放的主要意见。]当然,这里也存在实际的困难:一方面是估算过去的排放量,另一方面是把它带入谈判过程,因为它既不是一个简单的提议(实际上非常复杂),也不是为那些拥有最多讨价还价能力的人的利益服务的。]
第一,就美国来说,过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都是在1975年之前造成的。波斯纳和韦斯巴赫指出,在美国现有人口中,一半以上都出生在1975年以后,并且超过27%的美国人年龄小于20岁。]参见Eric A.Posner,David Weisbach, Climate Change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 103.]这些年轻的美国人可能会提出异议:“为什么我应该为我的祖先犯下的过错负责?”这种反对意见表明,当代人不应该为他们祖先的行为负责,不应该仅仅因为在他们之前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排放了太多的温室气体而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波斯纳和韦斯巴赫建议,“我们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排放,即在气候变化问题广为人知之前——或者说在理性的人们意识到问题之前——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其后的排放。”]参见Eric A.Posner,David Weisbach, Climate Change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 104.]在這个时间点之前,人们可能会反驳:“我们并不了解温室效应。”这个反对意见表明,只有当一个人知道或应该知道某一行为的有害影响时,他才能因为该行为而受到指责。然而,直到最近,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对排放的有害影响的认识是否足够广泛)仍然存在争论。]参见Eric A.Posner,David Weisbach, Climate Change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 104,110-116.这里涉及关于“罪责问题”的讨论。]
第三,波斯纳和韦斯巴赫没有提到第三个一般性的反对意见。它以如下方式解释了过去的行为在影响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构成方面的非同一性问题:没有人可以声称自己的境遇比在足够遥远的过去实行另一项气候政策时更差或更好。]非同一性问题使我们无法说后代人从其前辈的行为中受到伤害(或受益),其前辈的这些行为是他们作为个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参见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351-379. 如果我们把伤害理解为因某一行为而使境遇变得比原来更糟,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然而,另一种伤害概念成功回避了非同一性问题:声称人们可以被那些使他们低于某个预定临界点的行为伤害,后代人也可以说成被作为他们存在的必要条件的那些行为伤害。关于这些议题的处理,参见Meyer,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这些反对意见的影响范围也有所不同。第一种反对意见与现在已经死亡的人的排放有关;第二种反对意见与时间有关,涉及例如在199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一份报告之前的排放;]参见Axel Gosseries, “Historical emissions and free riding”, Ethical Perspectives,vol.11,no.1 (2004) .该文列出并讨论了一些可以替代1990年的显著时间节点:1840年(巴西提案提出),1896年(瑞典科学家Svante Arrhenius发表了第一篇有关温室气体的科学论文),1967年(第一次认真地建模),1995年(IPCC发布第二次评估报告)。我们还可以用2001年IPCC发布第三次评估报告、2007年IPCC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以及18世纪工业化开始等作为时间节点。与其试图确定一个时间节点使得我们能够合理地将相关的知识条件归于高度工业化国家的许多人或大多数人,不如将其作为一个程度问题来研究,并对个人和行为者进行区分。感谢Stephen Gardiner概述了这个备选方案。]第三种反对意见与早期的排放量(以及影响排放量的政策)有关,早期的排放量足够大,是影响当代人的数量和同一性的决定性因素。60DE4A6E-6096-4957-A948-16EF7524901D
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成功地证明,历史排放不能被视为与当代人之间可允许的剩余排放量的公平分配有关。相反,我们可以将过去的部分排放考虑在内,而且至少有两种考虑方式不受这三种反对意见的影响。
第一种考虑方式依赖于人们对可允许的剩余排放量的公平份额提出的要求。我们可以要求人均排放权的平等分配(或按照其他的公平分配标准)在某个时间点上实现,例如,每一天,或在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考虑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似乎更合理。]讨论参见Nils Holtug,Kasper Lippert-Rasmussen,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egalitarianism”, in Nils Holtug,Kasper Lippert-Rasmussen, et al, Egalitarianism: New Essays on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Equ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以及Thomas Hurka, Perfectio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人们并不是时断时续地排放,人们的排放需求也不是偶然出现的。相反,人们无法避免产生排放的活动。造成排放是人们在其生命的所有阶段实现其人生计划的前提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将继续存在。除非有一场技术革命可以使我们以较小的成本来避免、补偿或提取大量的温室气体,否则净排放水平将与人们的福利水平密切相关。
因此,当代人将在他们的一生中都造成排放。如果他们要求的公平份额是指他们整个生命周期的公平份额,那么就必须要把当代人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造成的排放都考虑进来。可以肯定的是,这只是其历史排放量的一小部分。正如第二部分第一小节所解释的,公平的排放份额代表着公平地分享排放行为所带来的那些利益。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人们在一生中已经通过自己的排放行为享受到了许多利益。如果我们想对排放行为所产生的利益进行人均分配,那么,排放行为(从事这些行为的人会因这些行为而获益)许可量的更大一部分应该由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获得。这是第一种方法,即在决定对剩余的允许排放量在当代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时,应把过去的(一小部分)排放考虑进来,并且,依据当代人在其一生中造成的不平等的历史排放,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均排放权。
由于这些历史排放是当代人自己造成的排放,因而第一种反对意见和第三种反对意见显然不能反对把这种历史排放考虑进来的办法。然而,人们可能在自己还不知道应当如何行动以减缓气候变化时就已经造成了历史排放。因此,我们可能想依据第二种反对意见,主张把这类历史排放排除在外,理由是,由于过去那些污染者的无知,我们不能将这些历史排放的责任归咎于他们。这将会是一个错误,因为主张把这些历史排放考虑进来的基本理由并不能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就应该拥有更多的排放权——作为工业化国家的人们对其过去的错误行为的补救。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诉诸这一理念——人们在一生中所获得的排放利益应当平等——来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应当获得更多的排放权。因为,“一个人已经用完了(部分或大部分)属于他的份额”是一个重要的分配理由,而他这样做时是否知情并不重要。]作为一个过渡性正义的问题,这个近似的结论需要加上某些说明。参见第三部分。]
正如前面的论证所表明的,我們对排放本身并不感兴趣,只是对人们从产生排放的行为中获得的利益感兴趣。在确定目前的公平份额时,考虑(一部分)历史排放量的第二种合理方法应当把过往世代的人们从排放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纳入相关利益的计算中。迄今,我们的先辈所追求的工业化已经产生了许多利益,而且,对生活在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利益比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能获得的要多得多——这一点在我们的讨论中非常重要。这些利益包括提供基础设施,例如,学校、医院、街道和铁路等,这些都是在当代人出生之前就建造完毕的。在当代人之间分配排放行为的利益时,这一点——现在已经去世的人们的排放行为的产物正在不平等地造福着当代人——应当被考虑进来。]基于我在第二部分第二小节中陈述的理由,我假定我们应该把这种物品(即从产生排放的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的分配与其他物品的分配分开考虑。]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并未要求当代人为过往世代人们的排放行为承担责任,也不会提出当代人是否知道气候变化及其原因的问题。因此,前两种反对意见显然并不反对将历史排放考虑进来的这种方式。但是,我们可能想根据反映了非同一性问题的第三种反对意见,反对将人们以往排放行为所产生的利益考虑进来。这将会是一个错误,因为考虑人们以往排放行为之利益的观点,并不依赖于这样的说法,即今天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比在遥远的过去未出现排放行为的情况下生活得更差。我们也没有在这样的意义上声称,发达国家的人们从遥远的过去的工业化中受益,即他们的境遇比没有工业化时更好。这就是非同一性问题的含义:没有人可以声称自己的境遇比没有工业化时更好,因为如果当时人类社会踏上一条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那么,当代的这些人很可能就不会存在。然而,这个论点与这样的观察并不矛盾,即从被孕育时开始,人们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将是更有利的或是更不利的。由于出生在工业化国家,人们获得了某些利益,出生在其他国家的人却没有享受到这种好处。对于每个人来说,命运可能确实会各不相同;如果一个出生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的人在出生后就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他的境遇会比在发达国家长大的人更糟。把历史排放考虑进来的第二种方式依赖于这样的观点,即就当代人而言,从他们被孕育时开始,排放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就已经或多或少地传递给他们了。因此,根据优先论的标准,从历史排放中获利较少的人——通常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应该获得较大份额的排放权,因为其他人——通常是高度工业化国家的人——已经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了很大一部分的排放份额。60DE4A6E-6096-4957-A948-16EF7524901D
我的结论是,在分配排放权时应考虑到历史排放的某些部分,即至少包括那些发生在当代人的生命周期内的历史排放,以及作为创造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利益的副产品而产生的历史排放。]参见Simon Caney,“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reparations, and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vol.37,no.3(2006).该文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消除排放的不平等依赖于集体主义的框架。通过关注当代人所享受的历史排放的利益,我可以提供一个不依赖集体主义框架的解释。]我所捍卫的这两种考虑历史排放的方式将不允许我们把所有的不平等的历史排放都考虑进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已经死亡的人的历史排放和对当代人没有产生任何好处的历史排放都没有规范意义。
一个一般性的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三种反对意见都没有对上述两种把历史排放考虑进来的方式构成威胁。这三种反对意见都依赖于这样一种理念:把低于平均水平的排放份额分配给高度工业化国家的人们,理由是错误行为者(或错误行为的受益者)必须要给受害人提供一些补偿。这种对赔偿的理解出现在以下三种反对意见中。第三种反对意见(即基于非同一性问题的反对意见)否认过去的排放是有害的,因此,如果沒有损害,那么就不该有赔偿。它同样否认这样的观点,即有些人通过排放而使自己的境遇变得比其他情况下更好,所以不存在受益者。第二种反对意见(即基于对气候问题无知的反对意见)宣称,即使过去的排放可以被认为是有害的,但仍然不能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不应该有任何赔偿。第一种反对意见(即一个人应当对自己祖先的行为负责)进一步指出,即使过去的排放既是有害的又是错误的,仍然不应该支付任何赔偿,原因在于赔偿是行为错误的人自己必须支付的,而不是他的后代应当支付的。
即使这些反对意见在运用于其他立场时都有合理的前提,]我不认为这些异议全都基于合理的前提。参见Meyer,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讨论了非同一性问题)。]它们都与我的论点无关,因为这两种考虑历史排放的方式根本不依赖于要对过去的错误进行补偿这一观念。这两种方式把排放权的分配视为一个分配正义的问题(如第二部分第二小节所述);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完全没有提到伤害或错误。相反,我的想法是,将与排放行为有关的利益在当代人的完整生命周期中平均分配给他们。正如我所论证的,因为这种利益的继承是不平等的,并且人们通过自己的行为获得的利益也是不平等的,所以,除非我们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提供更高的排放权份额,否则我们将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三、对气候损害索赔?
当我们试图为一个不同的问题提供答案时,这三种反对意见在规范的意义上就是相关的。这个问题不是指如何公平地分配排放行为所获得的利益,而是指如何公平地处理排放行为所产生的有害影响。谁应该为历史排放造成的损失负责?尤其是在人们的排放已经超出而且将来仍会超出他们的公平份额的情况下。这些成本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气候损害本身;第二,最大限度地降低或减少气候损害所必须支付的适应成本——这是因为排放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它们所导致的气候变化的程度,而且还取决于人类对这种变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我建议,与其把气候损害主要看作对错误行为进行赔偿的理由,不如把它们主要看作对不应得的利益和伤害进行再分配的理由。区分再分配和补偿的一种方法是,把存在着某种公平分配物品的底线视为前提。这种分配底线一方面取决于某种分配标准(如优先论的、平等主义的或充足主义的分配标准]人们可能会把现状作为一个既定事实,并宣布它是相关的底线。我批评并反对这种观点,参见Lukas Meyer,Dominic Roser,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climate change: The allocation of emission rights”, Analyse & Kritik, vol.28, no.2(2006). ])决定的,另一方面取决于(以前述分配标准为基础的)分配的改变,这种改变源于参与分配的这些人所做出的负责任的(与无过错的)选择。偏离这一底线,可以做出两种不同的反应。如果反应是基于以往行为的错误性,那么我们就是在补偿正义的领域做出回应。如果反应是平均分配那些不应有的利益或伤害(例如基于运气的利益,有害但合理的行为造成的伤害),那么,我们就是在分配正义的领域做出回应。
那么基本的问题就变为:哪些为适应气候变化而偿还的义务是基于以往行为的错误性?换句话说,哪些义务可以被确认为基于补偿性的理由?那些不能被确认的以补偿为基础的义务都可归结为以再分配为基础的义务,其目标是平衡不应得的利益和伤害。补偿支付的规模取决于支付适应成本的理由是补偿还是再分配。
对此,可以提出两条恰当的评论。首先,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通过再分配来平均不应得的利益和伤害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参见Peter Cane, Atiyahs Accidents, Compensation and the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有些人(充足主义者)认为,这种评价只是在每个人都拥有“足够多”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我将假定,根据优先论的标准,不应得的利益和伤害需要被平均,但是,对于那些不认为不应得的利益和伤害可以为再分配提供重要理由的理论家来说,区分补偿性理由和再分配性理由的基本观点仍然有吸引力。其次,我所使用的是狭义的补偿概念。基于非错误性伤害行为的支付也可以被称为补偿支付。]参见Joel Feinberg, “Voluntary euthanasia and the inalienable right to lif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7, no.2(1978).]我所论证的是,在气候变化的代际背景下,区分基于错误行为的支付与不基于错误行为的支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而且,后者的关切与前者不同,即后者关切的是再分配而非补偿。60DE4A6E-6096-4957-A948-16EF7524901D
我同意波斯纳和韦斯巴赫的观点,即基于许多理由,对气候损害进行补偿支付的合理性很难得到证明。]参见Eric A. Posner,David Weisbach, Climate Change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99-118.]我们可以根据谁有义务来提供补偿支付这一标准来区分几种不同的补偿支付。补偿支付最自然的责任主体是实施了错误排放行为的排放者本人。我将此称为排放者支付原则(EPP)]排放者支付原则仅针对有错误排放行为的排放者,并且应该与“污染者付费原则”(也被称为“严格责任原则”)或Moellendorf的因果原则区分开来。Moellendorf的因果原则要求任何排放者——无论是否有错误行为——都要支付补偿。参见Darrel Moellendorf, “Cosmopolitan justice”,Utilitas,vol.15,no.1(2003).]。第二种类型的补偿支付,即受益者支付原则,让错误排放行为的受益者负责提供补偿。第三种类型的补偿支付即共同体支付原则,将支付补偿的义务划归实施错误排放行为的共同体。
我将简短讨论排放者支付原则(EPP)。毫无疑问,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是说,不考虑它是否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气候变化的问题),这种补偿的观点能够得到我们的道德直觉的有力支持。该原则与受益者支付原则和共同体支付原则形成了对比,即使不考虑将它们应用于气候變化问题,后两项原则也是存在明显争议的。所以我的问题是:在气候损害这一特定情境中,排放者支付原则能否证明补偿支付的合理性?
在气候损害的背景下证明补偿支付的合理性时,存在五个基本问题。波斯纳和韦斯巴赫讨论了前三个问题。在分析从历史排放中获得利益的规范相关性时,我们已经讨论了不宜谴责的无知问题和非同一性问题(即下列第三、第四、第五个问题)。
第一,潜在的支付者可能已经死亡。]参见Eric A. Posner,David Weisbach, Climate Change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02.]
第二,潜在支付者的排放量可能没有超出其公平份额。]参见Eric A. Posner,David Weisbach, Climate Change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109-115.]
第三,潜在支付者的无知可能是不宜谴责的。]参见Eric A. Posner,David Weisbach, Climate Change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04.]
第四,由于非同一性问题,潜在的受助者可能只是根据存在临界值的伤害概念而被认为受到了伤害。
第五,同样由于非同一性问题,潜在的支付者不能被视为已经获得了利益。
要想用排放者支付原则(EPP)来证明补偿支付的合理性,我们就必须辨别出错误行为的排放者和被错误行为伤害的受害者。一个人的排放如果超出了他的公平份额,同时,他也知道或有可能知道他的排放行为的危害性,那么,他就实施了错误的排放行为。由于他人的错误排放行为,另一个人的境遇变得比原来更糟,或者他人的错误排放行为使另一个人处于特定的伤害临界点之下,或者两者兼具,那么这个人就是错误排放行为的受害者。如果所有的排放者都可以用无知作为借口被合法地原谅,那么,我们就无法用排放者支付原则(EPP)来确认谁才是需要支付补偿的有过错的排放者。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仍然只能把补偿义务归于无法确认其责任的某些人(尽管还有很多人对现在和将来的气候变化负有因果责任)。排放者支付原则(EPP)在辨别受害者方面也面临困难;只有当我们能够为非同一性问题的解决方案辩护时,才能说那些处境变坏的人是受害者,继而成为赔偿的合法获得者。我在其他地方曾论证过,对于非同一性问题,最合理的回应应当依据某种包含临界点的伤害概念和对这一临界概念的充足主义的理解。因此,如果受害者的处境低于充足主义的伤害临界点,他们就有资格获得补偿。]参见Lukas Meyer,“Past and future: The case of a threshold notion of harm”, in Lukas Meyer, Stanley L. Paulson, Thomas W. Pogge, et al, Rights, Culture,and the Law: Themes from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oseph Raz,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143.]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成功证明某些补偿性措施的合理性而言,这些依据很可能只为造成气候变化或遭受气候变化的部分人证明了补偿性措施的合理性。然而,我还想补充三点说明。
首先,在气候正义方面,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履行对后代人的代际正义义务。如果说当代人不仅知道他们的排放行为会对后代人造成严重的有害后果,了解保护后代人基本权利的有效措施,并且实施这些政策并没有对他们提出过多的要求,那么他们就负有这种义务。我曾在其他地方论证过,当代人并非不了解其行为的后果或需要采取哪些政策,这些政策的要求也不高。]参见 Lukas Meyer,Pranay Sanklecha, “Inditidual expectations and climate justice”, Analyse & Kritik,vol.33,no.2(2011).]从后果的角度来看,个人不大可能有任何更好的道德理由来继续选择实施远远超过公平程度的人均份额的排放行为;个人选择的任何排放水平在侵犯后代人的权利方面都很可能产生相同或非常相似的影响——换句话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更好的道德理由。]对于像美国这样在全球排放中占据很大份额的集体行为者来说,这甚至可能是真实的,这取决于我们对其排放如何造成危害的描述。]如果当代人在气候正义方面对未来的人负有代际正义的义务,那么当代人未履行他对后代人义务的行为就构成了有害的错误行为。]参见Eric A. Posner,David Weisbach, Climate Change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108-109. ]如果的确是这样,并且如果当代人没有履行对后代人的义务,那么他们就应当对后代人采取某些补偿措施,以防止后代人成为当代人错误行为的受害者。60DE4A6E-6096-4957-A948-16EF7524901D
其次,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遭受如此多的气候损害,其他国家似乎需要对此做出某些回应。当然,补偿(在狭义上是指有过错者为其不公正的行为向受害者支付一些费用)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回应。相反,鉴于气候变化的许多影响可以被视为不应遭受的伤害,而且是与其他人不应获得的利益同时产生的伤害,那么在关注分配正义的基础上拉平这些影响似乎是一种合理的反应。如果分配正义的原则,尤其是优先论的确适用于全球范围,那么在对这一义务(即向遭受气候损害的人们支付适应成本)进行分配时,这些原则也能被采纳。在假设优先论是分配排放权的正确原则时,我预先假定了分配正义原则的确适用于全球范围。]参见 Thomas W. Pogge, Realizing Rawl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因此,我认为,分配正义原则也能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对这一义务(即向遭受气候损害的人们支付适应成本)的分配。当然,对于一般的道德直觉来说,补偿正义的要求似乎比仅仅为了拉平不应获得的利益或不应遭受的伤害而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层面)更加有力。]参见David Miller, “Holding nations responsib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4,no.2(2004).]我没有必要质疑这种观点:即补偿支付相对于再分配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先性。然而,就气候损害的情形而言,补偿支付只在一小部分情形中才是合理的;对于大部分情形而言,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再分配的要求上才是合理的。鉴于补偿支付的适用性有限,我们必须将重点转向平等地分享不应获得的利益和伤害,而不是专注于对受害者的补偿。
最后,第三个说明反映的是关于历史排放的规范相关性的另一种视角,我相信,这种说明与我在本文中所论证的观点是一致的。生活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的人们和其他地方的人们已经形成了关于他们可以达到的排放水平的期望,这种期望远远超过了依据人均排放权来分配排放份额时他们应得的排放量;如果把历史排放考虑进来,他们超过人均排放量的幅度就更大了。这种期望部分地、也是必然地基于他们的政治社会的集体的历史排放水平。作为高度工业化国家成员的人们在追求可供他们选择的生活计划和谋划时,作为实施其生活计划之副产品,他们的排放量都远远高于公平分配排放权的理想观点所认可的水平。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的期望——能够排放远远高于理想的正义所允许的水平——能够被证明是合法和可行的,那么,在思考人们应该如何达成某种理想的集体解决方案时,这种期望将成为一个相关的因素。在建立权威的全球气候制度时,必须要考虑到这种期望,以便使这种规则不被视作破坏性的,同时又能够有效且公平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参见Lukas Meyer,Pranay Sanklecha, “Inditidual expectations and climate justice”, Analyse & Kritik,vol.33, no.2(2011).]
这一主张是为了确认某种用于评估向公平的全球气候规则过渡的标准。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源自他们前后叙述不一致而引发的误解。特别是在讨论过渡问题和理想正义问题时,我们可以用一种相反的方式来考虑历史排放的相关性,从而加强某些历史排放受害者的要求,削弱某些历史排放受益者的要求。
四、结 论
本文的目的是想概述,在确立用来分配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减排和适应成本的理想分配方案(尤其是依据历史排放所带来的利益与损害来加以分配)时,我们应当考虑哪些相关的因素。我预设了一种优先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而且,我从现存的不平等的背景出发来展开相关的讨论。我先讨论了减排问题,并且得出一个结论,即相比高度工业化国家的人们,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应当获得更高的人均排放权,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获得了较少的来自历史排放的利益。之后,我讨论了谁应当支付适应成本的问题,我认为,很难将高度工业化国家的人们对那些非常脆弱的人们所负有的义务视为补偿义务,相反,我们应当主要把这种义务视为基于分配正義的义务。
说明:原文刊发于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3, no.2(2013). 该杂志与作者授权本刊刊发中译版。
〔责任编辑:沈 丹〕
作者简介:卢卡斯·麦尔(Lukas Meyer),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哲学教授,人文学院前院长,格拉茨大学气候变化博士项目主管,格拉茨大学气候变化问题发言人。
译者简介:杨通进,哲学博士,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董子涵,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60DE4A6E-6096-4957-A948-16EF752490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