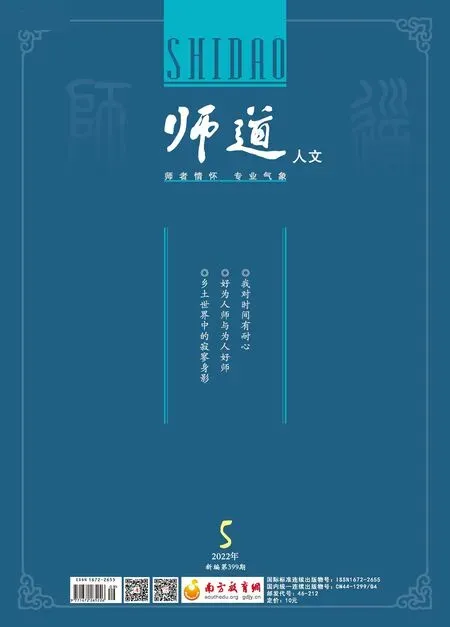我的精神家园
杨大忠
去年年底春节回老家,我去了一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过去的“关马初级中学”,如今的“关马中心小学”。

走进校园,目之所及,都是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大屏幕和电子白板相结合的微凹形黑板代替了过去的粗糙黑板;一人一位的钢架桌椅代替了两人一位的课桌条凳;曾经的挂钩式木窗户全部被换成推拉式的塑料飘窗,显得窗明桌净;教室地面,也由水泥地换成了图纹精美的地砖;教室外面的小树林彻底消失了,被塑胶跑道和体育场取代……在惊叹现代化设施给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也不能不感叹:让我魂牵梦绕的那种特有的学校氛围已经彻底湮灭无痕了。
1995年8月底,我入职家乡安徽省当涂县的关马初级中学。那时学校面积很小,只有25亩地。走进学校大门,迎面所见是一条笔直的水泥大道,那是学校的中轴线。大道尽头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花坛,里面栽种着一棵粗壮劲拔的雪松,松针碧绿,充满生机。水泥大道两边,是一棵棵耸入半空的法国梧桐。微风吹拂,梧桐树叶飒飒作响,偶尔有一两片飘落在水泥路面或路边的草地上。水泥大道的东西两侧,各有两幢红砖瓦房。据说上世纪60年代末,第一任老校长带领刚入学的学子们扒平了一片乱葬岗后,以坟地为地基建造了这些瓦房。西边两幢瓦房是学校的仓库和教师办公室,东边两幢则主要是教师宿舍。唯一的教学大楼坐落在雪松的南面,在学校的最南侧。大楼前是一个用水泥砌成的小池塘,波光粼粼。因为那时还没有安装自来水,这个小池塘就成为午饭后同学们洗碗的地方。教学楼共有三层,每层两个教室。如果赶上某年学生数量较多,教室不够用,就要把水泥路东边瓦房的一个大教室空出来作为备用教室。这个大教室一般都是初三年级的重点班所在,远离教学楼的喧嚣和闹腾。大教室前面是一片小树林,栽种的全是并不高大的马尾松。树林里清幽静谧,小鸟啁啾,各种小虫子的叫声此起彼伏。初三学子在繁重的学习之余,常来小树林漫步,疏散身心的疲乏和劳累。
学校四周都是农田,一条弯弯的小河在西边静静地流过,唱着永不停歇的欢歌。西边的和尚桥村是距学校最近的小村庄,直线距离大概400米左右。学校坐落在田野之中,只有一条并不宽阔的石子路把学校和乡镇主路连在一起,成为学校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关马中学就这样成为一片世外桃源,一个理想的求学之地。
那时的校园,春天繁花似锦桃红柳绿,夏天绿草如茵凉风习习,秋天松针遍地秋草枯黄,冬天屋瓦铺霜天寒地冻。莘莘学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学习的。那时没有现代化的教学工具,教师都是凭一支粉笔在黑板上书写美丽的知识符号。教学用语几乎全是当地土话,因为师生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土话授课令人感到很亲切;偶尔有几位新入职的外地教师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授课,反而使学生感到很不自然甚至偷偷发笑。时间久了,蹩脚的普通话终于向当地土话缴械投降——外地教师也被同化了。教学材料和试卷都是教师自己先用钢板刻印好然后油印出来的。字写得好的老师,刻出来的试卷让学生叹为观止。上课的时候,校园里非常宁静,只听到嗓门大的教师在抑扬顿挫地诵读课文或讲解方程式;学生都正襟危坐,专心致志,生怕遗漏教师传授的每一个知识点。当然,思想开小差的同学也是有的,尤其上午最后一节课,西边食堂飘来饭菜的香味,引诱得同学们的肚子“咕咕”地叫,盼着敲打下课铃的老头早点过来敲铃铛。
我入职关马中学的时候,教师队伍还是以代课教师为主,教育部门分配入职的大学生并不太多。入职那年,包括我,学校一下子来了三位大学生,引起了当地百姓的惊叹。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也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 “公家人”(当然,他们后来绝大多数也都转正了)。和今天的学生相比,那时的学生似乎更加淳朴。他们对老师非常尊敬,也更清楚“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也难怪,如果没有教育,他们很可能会成为鲁迅笔下的双喜和阿发,一代一代重复着田间地头的辛苦劳作。所以,农村孩子大多有强烈的学习意愿,渴望通过读书跳出农门。家长也非常客气,对老师非常尊敬。每年开学季,他们带着孩子来报到,总是热情地邀请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到家里做客。到了老师来做客那天,家长从早到晚在家里手忙脚乱地杀鸡宰鹅;下午放学后老师到来,经过短暂寒暄,家长就把家里的八仙桌摆开,搬上自家的土酒佳肴。酒桌上气氛热烈,主要话题就是对孩子的学习提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教师能到学生家里吃顿饭,对家长而言是莫大的荣幸,因为这意味着孩子成绩优异,将来很有希望考上理想的高中和大学。
有了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学校就是年轻教师奋斗的天地。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新来的三位年轻教师,对教学投入了极大热情。备课、上课、听课、测试,周而复始,工作看似枯燥乏味,但能和积极向上的孩子们在一起同喜同悲,每一天都是充实的,没有任何疲惫和倦怠。夏天的夜晚,有时看书看累了,就信步踱出宿舍,走向操场仰望星空。月亮高挂长空,冷冷清辉遍洒寰宇,几颗闪亮的星星在空中不停地眨着眼睛。月亮、星星竟然和我们这么接近哪!校园里一片静谧,朦胧的月光投射到每个角落,如同笼着轻纱的梦。耳边是各种不知名的小昆虫在嘀嘀咕咕,田野里到处是青蛙“呱呱”的鸣叫,更显出夜的宁静幽沉。夜深了,入睡了。睡梦中,校园里各种花的香气透过门窗的缝隙一丝丝飘进单身青年教师的宿舍,使梦境更加香甜……
学生的勤奋,教师的尽职,成就了关马中学辉煌的中考成绩。每年中考季,学校都会向地方重点高中输送一批优秀的学子。他们带着对母校的留恋进入更高层次的学府,身上都留下了关马中学的印记。因为中考成绩优异,周边乡镇的很多家长通过种种关系把孩子送到关马中学来求学,而关马中学也几乎没有让这些家长失望过。她的辉煌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撤校并校。
年轻的大学生不断地进入关马中学的教师队伍,他们慢慢地成熟了。作为“公家人”,他们是当地一些农村姑娘倾慕的对象。渐渐地,年轻教师一个一个成了家,生活也开始稳定下来。但也有不甘于困守小地方的有志青年,他们有的调离了,有的考研深造 (我是2004年考研离开的),更多的则继续坚守在关马中学,默默地为当地教育事业发光发热。
关马中学很小,但那是本校师生纯粹的精神家园,是他们内心守望的一片净土。从建校的那一天开始,学校就将她的教育使命和关马父老的内心渴望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源源不断地为关马地区的教育事业提供支持的力量。就教学热情、学习动力和学生素养而言,关马中学可谓本县农村初中的典范。无论教育政策如何变化,她始终以令人信服的中考成绩岿然不动,成为当地父老足够信赖的精神阵地。但是,时代的发展终究迎来了撤校并校的大潮,很多乡村中学都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其中,关马中学也不例外。

于是,2009年,关马初级中学完成了她初中教育的历史使命,变成了“关马中心小学”。原先的教师则被列入城关镇的编制,进入城郊初级中学。意外的惊喜使年轻教师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人人羡慕的 “城里人”了。但是,仍旧有一批将青春奉献在关马中学的老教师们不愿意前往县城,甘愿留下来做一名小学教师。他们的确安土重迁,舍不得离开曾经挥洒汗水与青春的心灵归宿地,这也是人之常情。
关马初级中学,一所毫不起眼的乡村中学,就这样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命运对她的安排。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她就默默无闻地支撑起乡镇的初级教育事业,从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盼;等到时代大潮要求教育做出改变的时候,她又以另一种身份继续承担起教育赋予她的新的责任。如今的关马中心小学,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校园多了冷冰冰的现代化设备,却少了之前的纯朴灵动。但是,不管她如何改变,我们在那里留下的青春印记和奋斗激情,却永远在梦中不断回响,成为慰藉我们疲惫心灵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