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德语游记中的戏曲印象
魏梅
游記这一写作形式,既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是权威的历史考据之一。在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赴南美洲探险发表《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后的一个世纪里,旅行在欧洲学者眼里成了获得其探访地权威信息的一条重要途径。如自然科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六年探访拉帕戈斯群岛写就的《动物学的小猎犬号之旅》,植物学家弗兰茨·威廉·容洪(Franz Wilhelm Junghuhn)科学旅行爪哇群岛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发表的《爪哇地形与科学之旅》和四卷本《来自爪哇内陆的光影图片》,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二年在中国实地考察完成的《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等等,都是十九世纪欧洲游记作品中最具辨识度的代表,为近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诚如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所言,旅行在十九世纪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此前或此后的任何一个时代”(《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盛行学术旅行的十九世纪,也是人类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纪。在西方,英国、法国、德意志社会经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率先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并开始向东扩张;在东方,早前欧洲耶稣会士笔下令人向往的“中华帝国”因为腐败、保守而日益衰落。于是,“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爱德华·W. 萨伊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的“东方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人心中生根、发芽、成长。随之,欧洲人看待东方(包括中国)的基本视角发生了巨大转变。之前欧洲人颂扬的,代表着浪漫、异国情调、美丽风景、非凡经历的东方,沦为了贫穷、愚昧、肤浅、落后的代名词。因此,十九世纪也是最大程度地拉开中国与包括德意志在内的欧洲社会文明差距的世纪。
不过,有一点是相似的,即频繁的戏剧活动在双方社会人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中国,戏剧早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城乡各处的舞台上,可以说“未有不好歌唱看戏者”(刘继庄《广阳杂记》卷二)。对此,普鲁士海军作家莱茵厚德·冯·威尔乃(Reinhold von Werner)、旅游作家恩斯特·黑森-瓦泰格(Ernst Hesse-Wartegg)、青年学者尤利乌斯·威廉·奥托·瑞希特(Julius Wilhelm Otto Richter)、萨克森商会代表古斯塔夫·施匹斯(Gustav Spieß)、口译官甘寿(A. Genschow)和地理学家弗拉基米尔·奥布鲁切夫(Wladimir Obrutschew)等人的游记中有关中国戏曲及其演出实况的记录可以证明。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游记为我们了解当时戏曲演出场所及其建筑结构、演出氛围、表演形式和音乐伴奏等实况信息提供了较为客观的描绘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来自不同文化的欧洲观众,尤其是德意志观众,在中欧文明差距和文化差异的双重阻碍下,面对“提鞭当马、搬椅当门”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接受情况。

一八六一年三月七日,身兼普鲁士东征考察舰队运输船“易北河号”(Elbe)船长的海军作家冯·威尔乃,从吴淞口岸抵达上海。自汉堡港出发前,他曾受莱比锡巴洛克豪斯出版社(Verlagshandlung F. A. Brockhaus)委托,要将东征途中的所见所闻及时寄给《德意志综合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发表,以便让德意志民众也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东方世界。作为一位戏剧艺术爱好者,看戏被冯·威尔乃视作消除旅途疲劳的首选方法。在离外滩不远处的一条街道上,他看到了一座“只比普通房子大一些”的剧院建筑—戏园。走进其内部,发现这座戏园与他熟悉的欧洲剧院很不相同,并在游记中这样写道:
剧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大小,而绝非其坚固性和贵重的舞台布景。竹子和藤条是构成剧院建筑的主要材料:前者形成全部屋梁构架,后者则用于墙壁和屋顶。剧院的内部装饰也同样是原始和简陋的。一个凸起的木板框架形成了舞台,乐队坐在舞台的前面。舞台与衣帽间由彩绘墙纸或者藤条编织的墙隔开,同时也就具有了背景墙的作用。为观众摆放着的未加工的粗糙长凳就像圆形露天剧场的(amphitheatralisch)座位那样排列着,其中也有为富人准备的专门椅座。此外,(剧院)入口处还有为收银员和检票员准备的一个木质的简易棚屋。至此,一座中国剧院内部和外部的样貌就完全展现在眼前了。(Reinhold von Werner,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 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Leipzig: F. A. Brockhaus, 1863)
在冯·威尔乃的描摹下,我们常在书本中见到的,“勾栏瓦舍”四字高度概括的戏园以一种更具象、更生动的模样浮现在了我们眼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戏曲剧院建筑及其结构样式并非仅流行于当时地理意义上的中国。

拜罗伊特马尔格雷夫歌剧院外观照片(1910)
与“易北河号”一起从汉堡港出发的“阿科纳号”(Arkona),于一八六○年九月短暂停靠新加坡期间,青年学者尤利乌斯·威廉·奥托·瑞希特和旅游作家恩斯特·黑森·瓦泰格等人一同在当地看到的华人剧院,也是“一座用木头和竹子组成的长方形建筑”(Julius Wilhelm Otto Richter, Die preußische Expedition in Japan 1860-1861, Altenburg: Stephan Geibel Verlag, 1908),“其舞台高出地面几英尺;中间的空间被长凳占据,许多中国观众坐在上面;在剧院一侧有个比较狭窄的入口。”(Ernst Hesse-Wartegg, China und Japan: Erlebnisse, Studien, Beobachtungen auf einer Reise um die Welt, Leipzig: J. J. Weber, 1897)与一般中国戏曲剧院不同的是,新加坡这家华人剧院让瑞希特的同伴—施匹斯感受到中国人对“所有欧洲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和友好”。他们每人只要花半个美元,就能走上舞台,并“被以最友好的方式安排在粗糙的椅子和长凳座位上”。但他同时也觉得“欧洲人概念中的剧院这里是找不到踪迹的”。(Gustav Spieß, Die preuß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während der Jahre 1860-62,Berlin: Verlag von Otto Spamer, 1864)

拜罗伊特马尔格雷夫歌剧院舞台视角照片
那么,此时欧洲的剧院建筑在外观和结构上与他们看到的中国剧院有何区别呢?
从欧洲剧场发展史来看,其剧院早在巴洛克时期就呈现出了结构繁复、外观恢宏、内饰华丽之相,如至今仍保持着原貌的德国拜罗伊特马尔格雷夫歌剧院(Markgräfliches Opernhaus)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十九世纪中叶,德意志各邦基本上都拥有了自己的永久性剧院,其中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慕尼黑王宫剧院(Residenztheater München)、汉堡塔里亚剧院(Thalia Theater Hamburg)和柏林德意志剧院(Deutsches Theater)等。到十九世纪末,慕尼黑王宫剧院建成了第一个用马达驱动的旋转舞台(Drehbühne)以实现快速换景;瓦斯灯的发明及其在戏剧舞台上的应用,让灯光除了照明功能外,还能通过对其明暗的控制来赋予它参与叙事的能力。正如清朝赴欧使团官员斌椿和张德彝,一八六六年五月八日在巴黎观看皇家歌剧院《唐·璜》演出所感叹:“山水瀑布,日月光辉,倏而见佛像,或神女数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议。”“昼夜阴晴;日月电云,有光有影;风雷泉雨,有色有声;山海车船,楼房闾巷,花树园林,禽鱼鸟兽,层层变化,极为可观。”(周一天《清廷使团访欧观剧考》,《读书》2018年第4期)事实上,中欧剧院建筑与舞台技术发展之差距,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仍然存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游学欧洲的程砚秋在巴黎给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同人的一封信中就曾写道:“(一月)二十五日,打从莫斯科经过,承莫柳枕先生招待,又参观几处大戏院,都很壮丽美观;回想我国剧场,矮屋一座,光线微弱,灰尘满地者,真是惭愧得很!”(《程砚秋戏剧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当然,众所周知,剧院的大小、坚固与否、其舞台机械化程度和戏剧艺术本身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和进行戏剧活动的场所,中德剧院间的差异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彼时双方社会工业化文明发展的差距。而这与接受主体的文化基础、审美经验,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精神一样,都是跨文化接受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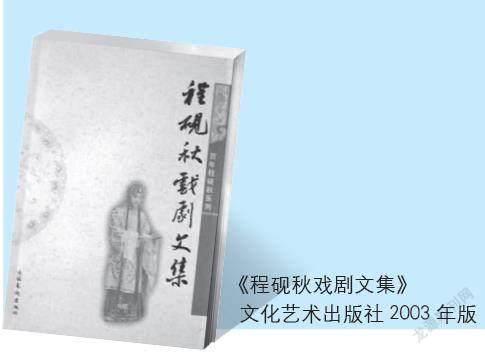
事实上,十九世纪中欧戏剧差异最突出的还是在于其遵循的不同美学观。诚如黄佐临曾在《漫谈戏剧观》中概括道:“中国戏曲是写意的,外国话剧是写实的。” 前者遵循的是“提鞭当马、搬椅当门”的程式化表演风格,其舞台以假定性为基础,重写意;后者在十九世纪时则强调自然的表演风格,将还原生活的写实性和准确性作为其最重要的美学原则。因此,与斌椿和张德彝针对欧洲“奇妙”的舞台布景发出的赞叹不同,在冯·威尔乃眼中,中国高度符号化及程式化的戏曲布景和表演被认为是一种“原始和幼稚”体现,他写道:
如果不算固定在舞台上的彩绘纸伞的话,舞台上完全没有舞台布景和其它场景装置,彩绘墙的后面偶尔场景外的人会走进去。留给观众的就是借助想象力,去想所有暗示的场景,既原始而又幼稚的。例如,一个军官被派去一个比较远的省份出征,他一只手拿着缰绳,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马鞭,让它发出噼啪声。在被锣鼓喇叭喧嚣声充满的空间里,这个军官在舞台上走了三四圈,时而停下,时而和观众互动,似乎是达到了一些地方。他的旅途应该还渡了河,因为他拿了一个帆船的模型在胳膊下,并迈步在舞台上。以扫帚柄来代替马,换场是由一个像导演角色的演員向观众进行必要的讲解。
对于“中国人如何演戏”,旅游作家黑森-瓦泰格在其游记中这样描述道:
中国戏院的舞台布置与莎士比亚时代的舞台一样简单可笑。在背景中有一种画布,上面有两扇门通向演员的房间;从那里,脸上画着怪诞的脸谱,穿着同样怪诞戏服的扮演者出来,其角色大声喊叫,然后消失在门口;同时音乐在不间断地喧嚣。音乐家们坐在舞台的一边作为背景,显然他们的喧闹声和演员的演唱没有任何联系。舞台上摆放的几把椅子、几只箱子和几只盒子便完成了布景,根据需要,这些布景辅助设备在剧情的发展中,由员工堆放在一起等。后者被假定是公众看不见的。总的来说,观众的想象力被过度使用了。我记得广州有个女演员,或者说,看到一个装扮成女士的演员,费力地爬上由椅子和箱子组成的金字塔。它应该代表一座山,而这位女士的手势动作和转身表明她正在穿过一片森林。在另一次演出中,看到六个汉子互相叠在舞台中间。奇装异服的战士们从两边奔向对方,一方把躺在那里的人推到一边,然后和另一方手拉手。我的翻译向我解释说这六个人代表了一堵堡垒墙!还有一次,一名战士做着骑马的动作,从舞台的一边跳到另一边,好像在给一个看不见的人递信。据我所知,这是一个骑马的信使,在剧中由一个表演者把它分成几部分送到蒙古的。但为了让观众理解这件事,这位信使一边站在舞台边,一边解释说,他现在已经抵达蒙古,正在完成他的使命。
上述文字还告诉我们,冯·威尔乃和黑森-瓦泰格对戏曲舞台及其表演的假定性特点并非没有意识,但他们却觉得那是“简单可笑”及“原始幼稚”的。而这种接受抗拒并不局限于德意志观众。一八九五年在北京观看戏曲演出的俄罗斯地理学家弗拉基米尔·奥布鲁切夫也指出:
没有场景变换,最多是在观众眼前拖进几张新的桌子、椅子或长凳。山和树,太阳和月亮,河流和街道,房子和庙宇,塔楼和大门都必须由观众结合戏剧导演的微弱暗示,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才得以“看见”。这样的想象力更多是被苛求的。(Wladimir Obrutschew, Aus China: Reiseerlebnisse, Natur- und Völkerbilder, Bd. I,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und Humbolt)
生角演员高度程式化的出场步伐又被他调侃成“像受到足痛疯困扰的可怜人,用非常不自然和僵硬的腿在舞台上散步”。而在奥托·瑞希特看来,戏曲演员的表演方法则被描述成“绝对拘谨的、做作的、夸张的;朗诵和手势看起来是完全奇怪的”。只有喜剧演员的表演方法—“接近自然的呈现方式”才是他眼中正常的表演方法。
如果说写意的程式化戏曲表演,没有欧洲戏剧写实的表演方法那样一目了然,而令德意志观众不得要领的话,那么,基于曲牌体或板腔体进行创作的,并受其文本歌词平仄音制约,以中国民族乐器伴奏的戏曲音乐,到了这些听着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作品长大的德意志观众耳朵里,又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呢?
在施匹斯耳朵里,“热闹”的戏曲音乐就像“所有演员在用最尖叫式的假声唱歌”,“似乎在表明只有他(按:所有角色都由男演员扮演)能赢得桂冠。而这些竭尽全力发出的高音,传到我们(按:欧洲人)的耳中就变成了绝望的爆发,这样的艺术呈现只会让人感到耳痛”。对于戏曲伴奏乐器发出的喧闹声,他觉得“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唯有演员嘶吼的假声才能冲破这种杂乱无章与最不和谐的音调”。奥托·瑞希特听到戏曲演员的演唱是“使用了从最高假声到最低咕噜声的所有音域,以及人体器官能够发出的,和谐的及不和谐的所有音调”。即便对于经常出入中国文娱场所的甘寿—一位了解中国文化,且无语言障碍的德意志口译官而言,“宁愿呆在小旅馆里安静地躺着”,都不愿意再次走进中国戏院去忍受那些“可怕的能伤害欧洲人耳朵的噪声”(A. Genschow, Unter Chinesen, Rostock: Volckmann, 1905)。
当然,并非他们所有人都像甘寿以躲避的方式来对待戏曲音乐。一向对“他文化”富有莫大兴趣的黑森-瓦泰格,就曾试图去理解戏曲音乐。为了找到欣赏中国戏曲音乐的方法,他曾“多次在观赏戏曲演出过程中,非常努力地从蹲在舞台上的锣鼓、琵琶和小提琴(按:指二胡)乐手不断发出的可怕噪音中寻找其音乐节奏、旋律和演奏方法”,可惜的是“从未成功过”。而始终困惑他的是,“中国人说话时每个词都有不同的音调(按:这里指汉语发音的四声音调),但歌唱(为什么)却是单调的。”对此,冯·威尔乃同样认为,“鉴于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以及孔子对这种艺术的保护及给予的鼓励,人们应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门艺术本应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与其他一切一样,它几千年来一直保持静止”。他发现直至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人还不太知道半音、对位法(Kontrapunkt)或乐句的划分;(在音乐演奏中)没有固定的调,只是大调与小调间的恒定转换;能听到一个经常重复出现的旋律;却无和声(Harmonie)可言”。然而,冯·威尔乃根本不会想到的是,他用欣赏欧洲音乐的耳朵发现的戏曲音乐的一些“缺点”,很多都是戏曲音乐不同于欧洲音乐的主要特点,也是戏曲音乐的一种特有创作美学。如,无固定乐句划分的节奏是戏曲音乐节奏中的散板;一个经常重复出现的旋律则很可能是戏曲曲牌音乐的主腔;“不知道半音”是因为那是中国特有的五声音阶。故而再次证明,遵循不同美学基础的两种艺术表现形式,仅用其中一种审美方式去欣赏另一种,是造成其负面接受主观性和偏见性的原因之一。
不过,客观上,就乐器音准而言,德意志学者们抱怨戏曲音乐伴奏发出的声音是“会伤害欧洲人耳朵的噪声”,虽然夸张了,但也可以被理解。因为相对于戏曲舞台上一直不受重视的伴奏音乐来看,十九世纪的德意志音乐无论是作曲技巧还是乐器发音的精准度,以及音乐表现力都更胜一筹。所以,对于第一次接触戏曲音乐的欧洲观众来说,既要迅速适应戏曲音乐外部表现特征而带来的陌生感,还要辨别其音准,确实勉为其难。
歌德曾说:“德意志民族天生尊重一切地道的外国事物,乐于适应他人不同于自身的特性。”(《歌德谈话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年)然而,这种对他文化的包容精神在这些十九世纪德意志学者的游记中并未被感受到。相反,在這些游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接受主体个人审美经验、所处社会文化及时代精神对其接受产生的影响,即以一种欧洲中心的视角去认识和评价中国戏曲。而这正是“跨文化接受”潜在机制所包含的局限性。
回顾德意志接受中国戏曲史,从十八世纪中叶《赵氏孤儿》译介在德意志掀起的翻译热与讨论热,到本文所揭示的十九世纪德意志学者对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美学的排拒,再到二十世纪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表演理论对中国戏曲表演程式的学习和借鉴,让我们认识到,中欧/中德文化差异既可以是相互吸引的魅力所在,也可能是加深彼此文化隔阂的推手。正如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充当过助推剂的中国文化(包括元杂剧《赵氏孤儿》),到了狂飙突进运动时,随着德意志“去法国化”的呼声一同被否定了。

冯·威尔乃游记中有关中国戏剧作品的一段评述可以作为其最明显的例证,他在第十章写道,“中国剧作不是为造就伟大的艺术家而设计的。戏剧性文学在中国有着非同一般强大的代表性,一些最好的戏剧在不同时期被翻译成英语或法语”,但又话锋一转说其“诗歌创作并没有超越平庸的水平。无论是在旧的中国戏剧作品中,还是在新的中国戏剧作品中,人们都无法找到更深层次的直觉或生动的感染力。虽然他们的悲剧表面上与古希腊人的作品相似,但他们的价值远低于索福克勒斯、埃斯赫勒斯或欧里庇得斯的成就”。
如果中国的戏剧创作是“没有超过平庸水平”的,并“无法找到更深层次的直觉或生动的感染力”的话,那么,《赵氏孤儿》译介为何会掀起十八世纪欧洲学者对它的翻译热及改编热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大量的戏曲文本继《赵氏孤儿》之后,仍然能被译介到欧洲?如果中国戏曲的程式化表演是“僵硬的、做作的”,是如此不堪的,那又是什么力量让 “提鞭当马、搬椅当门”的中国戏曲成为了二十世纪欧洲戏剧家学习的榜样?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德语国家对中国戏曲的接受研究”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