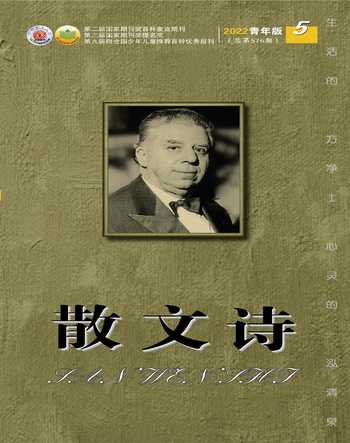三月,旷野之野
安蓝
野 火
不知是谁放的。
呼啦啦地,烧过了一丛又一丛枯草。
也不知照亮过谁的冬夜,驱散过谁的寒风,灼痛过谁的脸颊,舔干过谁的泪水。
放火的人已不知去向。那火,便成了无主的野火。兀自燃烧着,噼噼啪啪地唱着歌,听上去,既像是悲伤的哀鸣,又像是欢快的呻吟。
一朵微火,若是遇到心怀善意的风,便徐徐地熄灭了,趁早结束这没有结果的燃烧,好使枯草们安下心来,顺着风,顺着自己的命运,安安静静地荣荣枯枯。
倘若遇到不怀好意的风,便推波助澜,怂恿着火,一路东奔西突,愈燃愈烈。一场燃烧演变为毁灭。最终,只留下黑糊糊一片灰烬,触目惊心地悔恨着。
不可避免的,一生中总会有被点燃的时刻。熊熊火焰,跳荡着,相拥着,痴缠着,亲吻着,像要把对方吞下去,又仿佛要把自己徹底燃烧干净。这纯粹而充分的燃烧,是生命中最宝贵的经历,它使我们的中年安于平静、淡泊和安稳。
回首青春,总像在看一个个火灾现场。但谁也不能干预什么。
倘若再来,也许,我们还是甘愿沉溺于那样痛苦而幸福的燃烧中,野火一般热烈、孤独、虚幻。
野 树
常常一个人走向旷野。
旷野荒凉,除了无尽的荒芜和寂寥,似乎也无甚可看。
有树若干,不知植于何时。面相冷峻,姿态迥异,犹如艺术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
三月初春,挺拔的钻天杨,树色渐转,青色枝干上,累累芽苞,看上去充满希望。
凝神静听,树干内,春水向枝头、向蓝天汩汩流淌。
喜欢仰着头看在蓝天映衬下,粗壮的枝干上被阳光照亮的叶片。叶片闪着光,斑斑点点,像极了蝴蝶的翅膀。想飞,又不能飞,如此契合我的心情。
从夏天的碧绿不慌不忙活到秋日的金黄,它们始终直挺挺地站着,即使在狂风暴雨中,也不会弯一下腰。
这,让我格外衷爱,像衷爱着我心里的诗歌王子一样。
几棵面目沧桑的榆树,站在不远处。秃枝老干上皱纹纵横,像是经历了凄风苦雨的洗礼,又像是久被情所困。
相比夏秋的繁茂和喧闹,我更喜欢它们冬日的淡泊和宁静。
有雪的日子,我总会踩着嘎吱嘎吱的积雪,缓步慢行来到那处离它们很近的沟渠边上,点燃一支烟,静静地欣赏着它们。虬劲的枝干,错综细密的枝条,零落的枯叶,偶尔飞临的鸟雀……像是一幅水墨画,茫茫雪原,因为有了它们,而显得生动又俊秀。
在沟渠边上转身向西,可见两棵并肩而立的槐树,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五月,它们开满洁白而芳香浓烈的槐花,此时,虽已落光了叶子,但依然枝条挨着枝条,根茎握着根茎。
时常,它们化作我诗歌中相亲相爱的伴侣。
一起迎着风,一起沐着雨,一起生死轮回。
野 风
二月。那尚未被教训过的青春期的风,开始蠢蠢欲动。
在旷野里撒欢,像一匹刚刚学会奔跑的马驹。试探着,冲突着,跌倒又爬起。偶尔,还冲着虚空,嘶吼上一阵,表示不服气。
三月。风,成群结队地经过旷野,像是吹着口哨骑过广场的少年。挥舞着青春的旗帜,闪耀着青春的光辉,哼唱着青春的歌谣,将人间吹拂得花花绿绿后呼啸而去,既无心机,更无忧愁。
四月,情绪依然不稳定。刚刚它还轻柔地抚摸着麦苗和梨花,还在树梢上荡秋千,转眼就变得狂躁起来,抓起黄沙,就往人脸上扔。它使劲地摇动着旷野里那几棵命运多舛的树,像蒙克画里的那个呐喊者。
野风,这西北的汉子,浪荡成性,狂野不羁。裹挟着北方大漠的黄沙,以摧枯拉朽的气势浩浩荡荡而来,瞬间,就将天地搅得一片混沌。过不了多久,它便软沓沓倒下来,昏昏然地睡起了大觉,第二天,便又是一个响晴天。
有时候,也像西北的婆姨,热情又豪爽,盲目又冲动,热辣辣地吹过来,直把五月的旷野吹得晕晕乎乎地沉醉着,像是喝多了甜酒酿。
什么也挡不住野风的脚步。见墙翻墙,见洞钻洞,见山头就爬上去。常常是,它悠悠荡荡甩着衣,不知去了哪里。
久困水泥丛林,不禁生出叛逆之心。常常也想学一学这野风,放下一切,远天远地地走上一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野却是骨子里生就的,学不来。
我只能安于现实,继续读书、生活。
野 地
天空的蓝有些困倦。
风,不管来自哪个方向,都已经放下了刀子,扑在脸上,凉丝丝的,像小羊羔冰凉的舌头。
旷野依然荒凉,但我知道,睡了一冬的虫蚁和小兽们早已舒展热乎乎的身体,爬出洞穴,悠闲而警觉地翻晒着春日的阳光。
向阳的田埂上,水渠边,黑色的灰烬里,野草们率先发表了嫩绿的诗行。
那初露的锋芒,是否戳痛了春风柔软的手掌呢?
阔广的田地里,细密而匀称的犁沟,像春风吹开的涟漪,轻漾着希望的喜悦;又像初为人母的少女所怀的甜蜜与咸涩。
这永不厌倦的母亲啊,从不抱怨生活的乏味,也不悲叹日子的单调。该休息时,就安安静静地修养;该劳作时,就勤勤恳恳地劳作。热爱每一个季节,也衷情每一次日升月落。
更多的荒地被抛弃了。嶙峋的石头就要撑破憋闷的胸腔。荒草们昂首挺胸,仿佛凯旋的战士。
野地里,高大的榆树见证着一切,它从来不言不语,偶尔随风唱着歌儿,既像是祝福,也像是追忆。
又或许,只是一些无词的谣曲。
我们在这三月的田野上走着,仿佛被命运抛撒的种子。
人到盛年,才渐渐明白: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走在自己心灵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