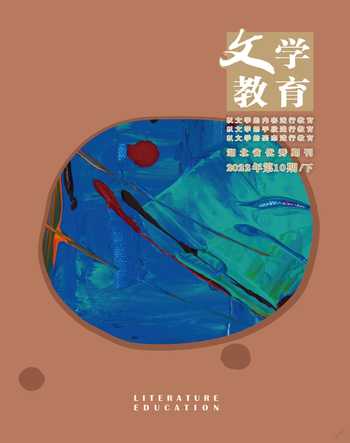陈大佐诗歌中的浪漫与赤诚
李苑玮 甘应鑫
内容摘要:陈大佐的《我在今生里走走停停》一如其之前两部诗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同时又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质朴且浪漫、孤绝且内敛,有着一种赤子般纯粹的持守,是捍卫爱情仿佛忘记了全世界的轻盈,是对于理想追求却不可抵达的沉重。
关键词:陈大佐 厚重与轻盈 赞美与批评 纯粹与从容
广西河池市作家协会副主席、70后诗人陈大佐,先后出版三部诗集,分别是《我的今生只是后世的一件衣裳》《一个人的村庄》《我在今生里走走停停》。这些作品诗风迥异,透露豁达的气魄和高远的境界,如他在创作谈中所吐露,名声美色钱财权势皆身外之物,要拿得起放得下,只有道德和法律才能为人提供庇护空间。
其中《我在今生里走走停停》出版引发社会及媒体热议,《诗刊》《诗选刊》《广西文学》《红豆》等主流刊物纷纷转发诗作。随后,“陈大佐诗歌朗诵会”由河池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在市内连续举办了五场。中国诗歌学会驻会副会长、《诗选刊》主编刘向东表示:“他爱诗,是真爱,可谓热爱;只有热爱,才能为此投入生命。他的诗是朴素、真挚的,力求从生活中来,到灵魂里去,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河池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潘红日认为,“他是河池作家群里最坚定、最执着的诗人之一,他以诗人的热诚和赤子之心,平和又不失幽默地呈现了桂西北人民淳朴的民风、向上向善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河池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河池学院教授谭为宜认为,“他的诗语犀利、洞察入木三分,他的诗风劲健而又孤独,因为劲健,所以抒情表意掷地有声;因为孤独,所以思考便能独辟蹊径。”[1]
诗集《我在今生里走走停停》[2]共分为“人在江湖、家乡味道、一颗粮食的爱情、我在今生里走走停停”等五个小辑。他的诗善于在细微中探究人心,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现实描摹,对一颗粮食的爱情袒露,对前世今生的神奇跨越,让我们在诗句中遇见了诗人带来的时代之问、纯洁之重和历史之轻。
一.整容失败的故乡
浪子,自古是文人一种悲观主义的理想形象,人在江湖,独来独往,介于入世与出世之间,有一种知世故而不世故的潇洒姿态。
第一辑“人在江湖”的序言引用的是古龙的文字,古龙是一个浪子,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人在江湖,可以见出陈大佐外在的不羁与内在的多情。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社会问题,诗人并没有“躲进小楼”,而是始终保持着贴地的思考。《江湖》中“水太深/聪明的鱼都跑到庙里去”,诗人跳出了水面,谈诗的底线,谈鸭子的问题,谈住旅店交押金和努力要睡回本的心酸。用后现代的游戏手法来呈现,展示“站在一张人民币面前我如此地矮小”,几乎是一字一行,以频繁的断句来突出,金钱对于底层群体的挤压,已经到了无法呼吸的程度;或者进行故事新编,重写了捞月亮的猴子,让忧天的杞人去调查研究,将现代的状况代入掩耳盗铃和井底之蛙;或者把自己也写进诗里去,让自己与佛祖对弈,甚至调侃自己“衣冠楚楚”,当然,这其实影射的某种现实中的怪相。
陈大佐的诗风多变,主题却是不变的“孤独”。这是一种时代的孤独,从陌生的地方来,到陌生的地方去,经过陌生人的窗口,没有人挽留。“他书写历史,批判现实,以一种解构的姿态,将字里行间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化为了孤独,这就像是在与无物之阵作斗争,比真枪实弹更加艰难。”[3]
第二辑“家乡味道”,是诗人所热爱的,所离不开的那片土地。在那片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寻找家乡的人,都被历史牵绊着。在他诗里,家乡是一个分分钟可以回去,又永远也回不去的地方,只能被讲述,永远不能被再次抵达。诗人再也回不来的父亲,是他再也回不去的家乡,大山中跟父亲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和村落是家乡,为所有那些小村落奉献人生的人也都是家乡。比起一个地理名称,家乡更是一种信念,无数有着精神追求的人都是家乡,一首诗也可以有家乡。家乡是一种理想,是用来追求的,而不能用来回归。家乡是“以灯为火点燃心中不死梦想”的那股执念,家乡更是用来寄存丢失记忆的那座老屋,寻找家乡的人就像等待春天的种子,不管发生什么,他们愿意始终“让生命成为阳光的衣裳”,他们始终坚信“没有哪一个春天会拒绝种子”。同时,他们又不是盲目。
事实上,像浪子一样,追寻家乡的人也是浪子,是另一种悲观主义的理想,他们怀着一股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热情,演绎着崇高的悲壮,他们会说,“干一杯吧/杯子是圆的啊/把酒干了/把梦/放进杯子里”,这样,就算是圆梦了。这种天真的沉重,举重若轻,产生阅读冲击力却是久久萦绕的。
不只是追求理想的人背负着家乡的纯洁之重,还有那些贫穷的小村落里,被帮助的村民身上,也展现着沉重而纯洁的感觉。鳏寡老人李老憨,会因为一份慰问品,以及因为没有同样成为鳏寡老人的父亲,而感到幸福;随遇而安的王天神,对于窘迫的生活条件,仍能做到知足;还有365个月亮被偷吃得只剩渣了还乐的老百姓。这些人不是悲壮的故乡,而是整容失败的故乡,但,毕竟也是故乡。
二.追寻世外桃源
第三辑“一颗粮食的爱情”,一颗粮食,那么小,却是整个世界。这一种是少年的爱情,干净、澄澈、无所保留,相信一生一世,甚至相信永恒。
诗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意象是花,风、雨和月亮。花是轻盈的,就像詩中的爱情,小心翼翼,想写一写的时候又怕“你”生气,这种爱情落下来,不给对方任何压力。花是美丽的,是手中的笔无法得其神韵的美丽,美得像是妖,“我”不知道能拿什么给“你”,只能默默守候,而把情思深深地藏在心里。花是纯粹的,只关风月,当“我”在写“你”、写对“你”的爱情时,其他人都消失了,其他事物都忽略了,“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你”,“我们”住到一粒粮食中,粮食中有春夏秋冬,有风雨雷电,有“你”、有“我”,有白天有夜晚,但是没有任何打扰。这样纯粹、轻盈的爱情,一般只属于情窦初开的少年,诗人难能可贵地保持了纯洁之轻。
诗中的风雨也不是狂风暴雨,而是轻风细雨,月亮也是蓝色的忧伤的月亮。但与此同时,这种爱情又不是全然的空中楼阁,它纯粹轻盈,不以名利为意,又不同于少年仅凭一腔热血的爱情冲动,岁月不着痕迹地影响了它。这份爱情是住在粮食里,而不是住在花里,花是短暂的,终究要被雨打风吹去,而粮食随着光阴的流逝,不是凋落,而是日渐成熟,成熟了也依然还是纯粹的、轻盈的,粮食更加务实一些,将粮食和爱情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了诗人质朴且天真的爱情观。
这一辑还是跟诗人八年前的“有一种年轻叫做爱情”那样,清澈、热烈,简简单单,干干净净,仿佛爱情就是“找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带你去看海”,在八年后,出版的诗集中又更多了时间的因素。
这种时间的因素,就是他的爱情诗隐含着一种命运的味道。在爱情里他不断地想到一生,甚至想到前生。对于爱情,他有一种类似于命中注定的信念,而这种前世今生的时间观,在第四辑中尤为明显。
第四辑“我在今生里走走停停”,是写于在西北旅游的所见所闻所感,西北部地区佛教文化氛围浓重,而佛教文化中有因果轮回的观念,所以这一辑也相对比较出世,同时有一种时间的厚重,虽然使用的语言仍然是轻盈的,但一定是今生有遗憾的人才会想到前世后世,所以虽然他在诗里“把前世一笔带过”,看起来都是轻描淡写,但骨子里是一个忧伤的人。
《我的今生只是后世的一件衣裳》第二辑“在家的和尚也念经说道”中也有类似的佛教的影子,他想象与佛的对话,想象如果济公变成陈大佐,除了佛教,他还想象老子、孔子、孟子,通过这些想象其实在暗暗勾画现实,当然现实也可能并不总是高雅和文明的,有时,“整个寺院里/不会放屁的/只有木鱼和铜钟”。而回到这小辑里的诗都可以算是游记,游记大抵是地理上的走走停停,陈大佐却不是在西北部地区走走停停,而是在今生里走走停停,是时间上的走走停停,不是急于赶路,没有强烈的目的性,而这种从容得益于他的命运感,命运感来源于历史之重。
陈大佐的诗歌一向是在间离中保持着介入的姿态,在克制中蕴含着丰沛的激情。《我的今生只是后世的一件衣裳》第一辑“我的祖国”同样也是传达了一种历史之重,但我们时刻能感受到诗人澎湃的内心。他多次把祖国比做恋人,“年轻的共和国啊/不管历史沧桑不管道路坎坷漫长/我都是你/永不离弃的恋人”,“还有一个多情的我正在热恋/我把年轻的阳光涂满热烈的双唇/我亲吻十月/我亲吻祖国/我亲吻所有布满灰尘和汗水的脸庞”。当他书写历史上的人物,不论是英雄,还是如“女犯2号”或者“杀人犯A”一样的烈士,都好像是在写自己身边至亲的,同时又让自己尊崇的人,让热烈的感情自然地流淌出来,充满了感染力。写县委书记、写检察长,都不是采用史诗般的取景框,而是从非常个人化的细小的角度,用特写一样的镜头去刻画,如此手法,足以让读者含泪倾听。
从这些诗歌中,我们不难看出陈大佐的历史之重,追求深度,追求介入,追求掷地有声,他的纯洁之轻则是追求高远,追求超脱,追求世外桃源。
三.平凡中寻求神圣
诗人在介入现实而产生厚重感的同时,与现实保持着一种间离的姿态,“现代社会要求司法人员有一种‘绝对公平的理念,作为检察官,诗歌力图和具体的现实保持着某种‘间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歌就是高蹈的空中楼阁。”[4]这种间离使得陈大佐的诗歌能够既充满理性,而同时又使人感受到一种天真。
每个人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活在这个世上,当他将他者视为同自我平等的主体时,虽然仍感到彼此独立,因为主体一定是独立的,孤独是绝对,因为有着对于世界的普泛的爱,他愿意关照更多的他者,愿意把他者当做自我一样去为之设身处地,比如在“我是一个劳动者/我和千千万万个劳动者一起”里,诗人把自己放置于无数的劳动者之中,去感受他们的感受。
陈大佐的诗有着强烈的浪漫主义诗风,他现实题材的诗歌正是通过自我与他者的连接实现了真实。因为对现实的介入,创作者必然要注视,但他不仅注视他者,也在注视自我,并且以他者的目光注视自我,不过这种注视并不是那种窥视,是一种自由的指向,这种自由即是责任。
唯有将他者视为与自我平等的主体时,才能主动担负起责任,当然责任不是一种消极的捆绑,而是一种积极地回应。对于诗人来说,这种责任意识就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一个拥有话语权的人,为无数同样应作为主体,而没有或者失去了话语权的他者发出声音。这些没有话语权的人可能是“李老憨、王天神、白裤瑶少年”,以及千千万万个劳动者,而失去了话语权的人是那些失去生命的人。诗人实现积极介入同时又保持自身个性,这种诗意的栖居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
诗集中除了“对于理想爱情的表达,更主要的是还传达爱,一种对于人类的苦难与辛劳的同情,这种同情不是居高临下的可怜和施舍”[5],而是真正站在对方的位置去感同身受,是一种人类之间共通的情感,是在平凡中寻求神圣,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去发现永恒的主体间性,自我与他者的相遇形成了真实的人生。因为拥有自我,才能意识到他者,而通过与他者的相遇,自我又逐渐被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诗作很多是交流的语气,没有说教,而始终像是在对话。这种对话的感觉有时通过人称来体现,比如大量的第二人称,“我深入秋天/为你/探寻蝉翼”,或者第一人称复数,“下辈子我俩在哪儿相遇啊”;有时通过直接的对话与互动,比如“我问王天神/你相信风水文化吗/他说,我只会/写自己和家人的名字”,或者通过假想的对话与互动,“--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口袋没钱,度日如年”;有时则只是一种交流的感觉,“如果胆怯或饥寒的人路过/--有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在相遇过程中的交流与沟通。有交流就会有倾听,诗人并不只是输出者,也是倾听者,这种倾听有时是通过耳朵,有时是眼睛,有时是大脑和心,他用全身心去倾听。他会倾听太阳,倾听白云,倾听“你”,他明白过去和未来相似又不同,变化是绝对的,但又希望着永恒,他希望“重写昨天的日落”,但也只是希望而已,因为“前世已经走得很远了/后世还没有醒来/我只好在今生里/走走。停停”。
陈大佐的诗歌有着对现实的明确介入。他写乡村扶贫、乡村振兴,怀着对于现实的深切关照,回顾历史,也记录将成为历史的今天,写前世今生,带有着想象的色彩,以佛寺的空间为媒介,对于时间进行了交叠。以浪漫的笔法和赤诚的表达,凝望历史与现实,纯粹、从容,而又不失厚重。
参考文献
[1]光明网.南丹:以诗为媒唱响乡村振興“好声音”[EB/OL].https://m.gmw.cn/baijia/2022-03/03/35561310.html,2022
-03-03.
[2]陈大佐.我在今生里走走停停[M].团结出版社,2021.
[3](法)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4]陈代云.介入的诗歌——兼谈八两与陈大佐的创作[J].河池学院学报,2013(2).
[5](德)叔本华.所有的爱都是同情[M].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
(作者单位:河池学院创意写作中心;广东省小小说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