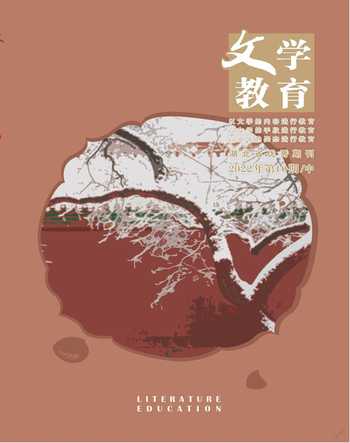《爱丁堡监狱》与《水之乡》中女性人物比较
陈启 洪君
内容摘要:司各特的《爱丁堡监狱》与斯威夫特的《水之乡》时隔近两个世纪,分别是经典历史小说与后现代历史元小说的代表,情节结构上必定存有差异,尤其是其女性人物情节。本文依据沃霍尔提出的四种可能“不可述”中的“不应叙述”与“不愿叙述”,比较了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情节,认为虽然经过两个世纪的变化,伦理与禁忌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女性受到的限制和约束已有明显的放宽,但在两部作品中女性并没有冲破叙述的束缚,还是要么嫁人要么死亡,她们的故事依然是“不可述”。
关键词:《爱丁堡监狱》 《水之乡》 女性人物情节 “不应叙述” “不愿叙述”
《爱丁堡监狱》(The Heart of Mid-Lothian, 1818)(下文简称为《爱》)与《水之乡》(Waterland, 1983)(下文简称为《水》)分别是英国文坛上两位重要的历史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Water Scott, 1771–1832)与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 1949 -)的代表作。以往的研究对这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情节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也无比较研究。事实上,两部小说的“不可述”情节多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尽完全相同。与此同时,两部小说时隔近两个世纪,又分别是经典历史小说与后现代历史元小说的代表,整体上情节结构存有很大差异。本文希冀对这两部小说中的“不可述”女性情节进行比较分析,以求辨博社会道德规约与文类特征的变化及其对女性人物表现的影响,认清两个世纪以来女性社会身份地位的变化。
何谓“不可述”?普林斯(Gerald Prince)于1988年在《风格》杂志上提出“否叙述”(disnarrated)这个概念,意指“那些叙事中的段落,认为过去或现在并未发生的事”(Prince 1988: 1)。就普林斯的“否叙述”,罗宾·沃霍尔(Robyn Warhol)进行了讨论,认为只用“否定叙述”一词难以“穷尽所有可能的不可述(unnarratable)形式”,于是,她提出了“不可述”的四种可能形式,即“(1)‘不必叙述者(the subnarratable),(2)‘不可叙述者(the supranarratable),(3)‘不应叙述者(the antinarratable),以及(4)‘不愿叙述者(the paranarratable)”(沃霍尔, 2007: 244)。前两种形式分别指够不上叙述门槛的平庸之事和难以用叙事方式再现的事件;后两种形式则分别指因社会常规不允许而不应被叙述的事件,以及由于遵守文类常规而不愿叙述的事件。沃霍尔之所以对普林斯的术语进行更详细的分类,主要原因就是不满于普林斯“只关注话语的叙事功能,对叙事行为、意图等未展开论述”(孙桂芝,2014: 112),而她分类中的后两种形式,即是对这种缺失的有效补充。本文主要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文本外部条件,即考虑社会道德规约与文类规则对女性情节建构的影响,因此讨论中主要参照的,是沃霍尔上述分类中的后两种形式。
一.《爱》和《水》在“不应叙述”上的差异
“不应叙述”主要是指叙述事件往往违反社会常规或禁忌,因而不被叙述”(沃霍尔,2007: 246)。《爱》和《水》这两部作品的核心故事情节,都涉及未婚先孕这样一个社会伦理道德事件,但经过两个世纪的时间,对于是否违反社会常规或禁忌而 “不应叙述”的判断理应有所不同。从表面上看,身处二十世纪的斯威夫特在《水》中的叙述在很多方面比司各特要开放且多元。例如,对于“性”的描述已经不再是禁忌。再如,《爱》中丁斯家的小女儿艾菲与纨绔子弟乔治私定终身,偷偷产下私生子,这不仅有违伦理更是触犯法律,被判死罪。然而,《水》中女主角玛丽与汤姆两兄弟同时保持性关系,还私自找女巫去堕胎,这些当然有违于伦理道德,但算不得违法。那么由此是否可以判断女性已经突破了一定限度的禁锢,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空间?通过深入的分析,答案似乎并非如此。
首先,父权从一开始就直接对几位女主人公的人生进行着控制。两部作品中,母亲们都早年离世,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缺位。父亲则取代了母亲,按照社会规约或者说父权的意愿对女儿的人生进行安排。贞洁、端庄、恪守妇道是他们对女儿的期盼。《爱》中,父亲戴维斯对大女儿珍妮“从学步时起就尽心地加以抚育,使她每天从事种种力所能及的劳动”(司各特,1980:95),很快,她在家务和农活上就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尚未成年就已经担当起家庭中实际的女主人角色。父亲虽不希望艾菲能像姐姐一样成熟独立,但对她的品行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要求。为保小女儿品行端正,戴维斯把她送到“为人正派,谈话得体,家境也富裕”(同上,119)的萨德尔垂太太那里去做学徒,期望她能做好这份“正当职业”,并能在附近的教堂里聆听教诲。在《水》中,玛丽的父亲哈罗德只是一介农夫,可他却颇具野心,且信奉罗马天主教。女儿取名为“玛丽”,这不仅寓意了圣母玛利亚,也表示父亲想“将她培养成[了]一个小圣母,将来再适时成为一位公主”(斯威夫特,2009:41)。与戴维斯一样,哈罗德“几乎从不问玛丽自己的意见,就把她送进了圣·冈希尔达修女学校,坚信他所作的一切努力和安排终将有所回报”(同上)。
其次,虽然艾菲与玛丽不满足于父亲划定的人生轨迹,然而她们的越界行为,立即被社会道德规范所限制,她们鲜明的个性逐渐黯淡,再难做出自由的选择,余下的人生都是在痛苦和赎罪中度过。《爱》中艾菲因道德败坏获罪被捕后,本有机会越狱,但她放弃了,因为“既然失去了好名声,那么活着也无益”(司各特,74)。获赦免之后艾菲回归了世俗规范传统,她与乔治完婚并远赴欧洲大陆,希望人们淡忘他们以往的过错。若干年后,已经成为上流社會贵妇的艾菲依然无法走出孩子下落不明的困扰,摆脱自己无法再次为丈夫添丁的苦恼。她最终心如枯槁,在女修道院终了一生。艾菲的结局正印证了小说结尾处的总结,“罪恶可以显赫一时,却决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同上)。
《水》的女主人公玛丽在堕胎之后,随即失去了那旺盛的生命力,像“一个饱经风霜、面容冷漠的老妇人”(斯威夫特, 49)。此后,失去孩子和生育能力的玛丽逐渐在故事情节中变得模糊。她不仅和艾菲一样逐步回归世俗道德规范之内,而且被排斥在历史叙述之外,因为她“那蠢蠢欲动的好奇心。现在突然消失不见了”(同上,51)。失去好奇心在《水》这部作品中非同小可,因为“好奇心,[是]让我们陷入苦思冥想,让我们书写历史的东西”(同上,45)。《水》这部后现代历史元小说试图打破宏大历史叙述的理性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品继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相反,作品至始至终都在追问“为什么”?因为“历史的另一个定义:人类,就是寻求解答的动物,是会问为什么的动物”(同上, 90)。男主人公汤姆一直都在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述历史,解答诸多“为什么”的问题,因为“人需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将现实掌控在手”(Janik, 1989: 83)。玛丽被剥夺了好奇心,无法自由表达,失去了历史叙述中的话语权,也就无从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故事中的女性做出了冲破社会常规和禁忌的尝试,但她们最终并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女性真正的独立自主并没有进入情节之中,仍然是“不应叙述”的。
二.《爱》和《水》在“不愿叙述”上的差异
分析了两部小说的“不应叙述”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不愿叙述”的状况。沃霍尔认为不愿叙述的事件,“并不是因为事件不重要,或不可言表,或讲的事件属于禁忌,而是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这在小说中是叙述者不愿讲述之事:讲了就是不行”(沃霍尔:250),南希·米勒(Nancy K. Miller)在对18世纪以女性为中心的小说(feminocentric novel)进行研究时观察到,女性人物到最后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嫁人,要么死亡(Miller, 1980: x)。在《爱》这部小说中,主角珍妮与妹妹艾菲从性格、品貌到人生经历,都被着力描述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物,但情节最终的归旨,仍然是米勒所说的嫁人或死亡这样的模式。
《爱》的主干情节是姐姐为挽救失足的妹妹,不畏艰难,远赴伦敦觐见女王以求赦免。但从情节行进的角度来看,珍妮的远行也是为了自己的婚姻大事扫除障碍。妹妹的罪行让珍妮全家名誉受损,也“不能使我[珍妮]适于作一位尊敬体面的牧师的妻子”(司各特:344)。因此,只有救下妹妹,珍妮才可能完成婚约。但在这之后故事并没有结束,女主人公还不能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误入迷途的妹妹艾菲,在获得赦免之后,还没有完成“嫁人”的情节。艾菲跟随乔治远走他乡,这让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无法理解,但珍妮告诉读者,事实上艾菲的选择是最恰当的归宿。珍妮“相信他[乔治]同艾菲已经结了婚。要真是那样,他既有继承财产的前景,又有上层社会的关系,……因此她妹妹不仅不会一生穷愁潦倒,而且也没有走犯罪道路的危险”(同上,566)。这是给珍妮和读者一个非常肯定和明确的答复,“艾菲已经结了婚,根据一般的说法,成了一个正当的已婚女子——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同上, 594)。“嫁人”之后的艾菲肉体存活在世,然而她却在精神上经历了另一种死亡。那个出生即失踪的孩子所带来的“痛苦无法减轻,它是消除不掉的”(同上,608)。几年之后,艾菲的私生子找到了,然而他已经成了匪徒,并在一场混战中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从此流亡海外。虽然此后艾菲重回社交圈,然而“在欢乐的外表底下隐藏着一颗受创疼痛的心;她多次拒绝了十分高贵的人士求她再婚的表示”(同上,679)。最后孑然一身的艾菲,“在她曾经受教育的那个女修道院里定居下来。她没有当修女,但一直到死过着严格的隐居生活”(同上,679)。
沃霍尔在分析19世纪早期到中期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时提到,“[她们]能跳出要么婚姻要么死亡的结局,简直不可想象。……[这种]文学文类常规的规律性,比社会常规更少灵活性,且在整个文学史中,导致了比禁忌所产生的、更多的未能叙述性(unnarratability)”(沃霍尔,249)。在二十世纪创作的《水》中,玛丽是否能有其他的出路呢?毕竟斯威夫特的这部后现代历史元小说,在整体上比《爱》有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叙述结构。作品采用“循环的,散漫的叙述模式”(Irish, 1998: 919), “有两条交叉缠绕的情节线”(Higdon, 1991: 92),“六个结尾点[moments of closure]”(同上,90)。然而纵观整部作品,玛丽这条情节线并未有实质的突破。玛丽堕胎后,父亲“的羞耻和怒火逐渐消散,转换成了对他女儿健康和未来幸福的忧虑。他咽下自尊——认命地接受他女儿不会在这个世风日下的世界里出人头地这一事实”(同上,102)。他不得不去找汤姆的父亲,安排两个孩子的婚姻。而汤姆的父亲更是“相信這桩婚事是命中注定的,而命运的力量是强大的;而只要命运插手协助,再艰难的任务也定能完成”(同上)。婚后的几十年,玛丽的生活可以用平淡如水来形容,直到她去超市偷盗了一名婴儿。当年被扼杀的孩子以及永远无法生育的痛苦把玛丽逼疯了。“[她]避免了牢狱之灾,但现在她坐在另一间监狱里,[就是]现代人喜欢用较为普通的‘医院或勉强为之的‘精神病院代替它”(同上,312)。虽然在《水》中,“故事循环、反复、非线性,但这对玛丽来说都是无效的,因为她能有的故事,除了做母亲就是做疯子”(Powell,2003:74)。
困在精神病院里的玛丽并不是小说中第一位女疯子。汤姆的曾曾外祖母莎拉,被丈夫托马斯“打了一个耳光撞在写字台角上。这一撞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几个小时后她尽管恢复了意识,却再也没有恢复智力”(同上,67)。此后整整五十四年,关于莎拉的传闻谣言众多,无论是女神,预言家也好,疯子也罢,都说她不再属于正常的理性世界。这一切,都是因为托马斯“犯糊涂,而且——横生嫉妒”(同上)。托马斯的这记耳光打在1820年1月的一个晚上,这正是《爱》发表之后的两年。丁斯姐妹的故事按照书中所说,发生在1736年,而《水》所讲述的故事,自汤姆的祖辈于18世纪中期发迹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伦理道德与禁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女性受到的限制和约束已有明显的放宽,女性在争取平等的斗争中,身份和地位已有明显的改观。然而,在经典历史小说《爱》与后现代作品《水》中的女性角色,并没有冲破叙述的束缚,除去做“妻子”或者“母亲”的角色,她们并没有更多的选择,在婚姻之外,她们失去话语权,无法被理性的社会所接纳和承认。她们的故事依然是“不可述”。
参考文献
[1]Higdon, David Leon. “Double Closures in Postmodern British Fiction: The Example of Graham Swift.” Critical Survey 3.1 (1991): 88-95.
[2]Irish, Robert K. “‘Let me Tell You: About Desire and Narrativity in Graham Swifts Waterland.” Modern Fiction Studies 44.4 (Winter 1998): 917-934.
[3]Janik, Del Ivan. “History and the ‘Here and Now: The Novels of Graham Swift.”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35.1 (Spring, 1989): 74-88.
[4]Miller, Nancy K. The Heroines Text: Readings in the French and English Novel, 1722-1782,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0.
[5]Prince, Gerald. “The Disnarrated.” Style 22 (1988):1-8.
[6]Powell, Katrina M. “Mary Metcalfs Attempt at Reclamation: Maternal Representation in Graham Swifts Waterland.” Womens Studies 32.1 (2003): 59-77.
[7]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水之乡》,郭国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8]罗宾·沃霍尔,“新叙事:现实主义小说和当代电影怎样表达不可叙述之事”,《当代叙事理论指南》,詹姆斯·费伦,彼得·拉比诺维兹主编,申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41-256.
[9]孙桂芝,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联姻——论罗宾·沃霍尔的“未叙述事件”, 《文艺争鸣》2014(3):111-116.
[10]沃尔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陈兆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说明:华东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学部刘艳老师,作为第三作者也参与此文创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