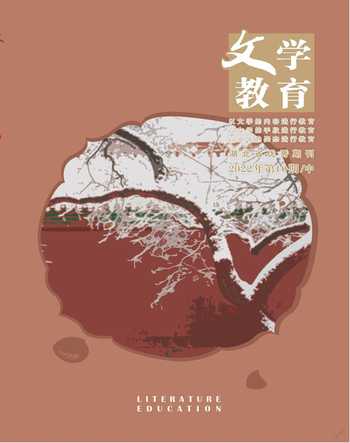经济语境下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刘浩
内容摘要:英国16、17世纪正值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期,早期重商主义经济以及科学的发展有力冲击了人们尤其是作家的传统思想观念,大量该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经济话语的渗透。在著名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莎翁使用了早期现代经济话语,展现出剧中人物的婚姻危机以及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女性被作为商品进行价值衡量,其婚姻的定夺和维系都被卷入商业利益的较量漩涡中。对于在社会和婚姻中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剧中女性做出勇敢反抗,与压迫势力斗智斗勇,最终获得了婚姻自由,解除了婚姻危机。
关键词:《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经济学 女性商品化
16世纪至17世纪早期,当今称之为“‘经济学的专业术语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概念逐渐成形”[1]。根据David Hawkes,“在莎士比亚的一生中,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他的努力,英语发生了变异以适应新市场经济的要求”(see Shakespeare : 161),诸如“价值”“财产”“利息”等大量经济学词汇出现在他的戏剧作品中。本文从16、17世纪经济学语境出发,分析剧中女性被商品化的现象以及其背后深层原因,并进一步探究这种现象对婚姻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呈现出女性逃脱商品化困境并最终解除婚姻危机,赢得戏剧圆滿结局。
一.未婚少女安·培琪的婚姻危机
都铎王朝统治时期,统治者重视并大力推崇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16-17世纪,英国开始从“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到商品交换的经济转型”[2]。此时的人们热衷于追求财富,诚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所言,“只要得到货币,随后再购买任何商品都毫无困难”[3]。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未婚少女安·培琪便沦为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以及交换婚姻财产的商品。
安·培琪拥有爷爷遗赠的丰富遗产——“七百磅钱”还有“金子银子”,以及父亲给的嫁妆[4](I. i. 47-48),斯密曾说(详见《国富论》:310),“在任何国家,积累金银都被以为是致富的捷径”,因而物质上极其富有的安·培琪小姐成为了“婚姻市场中的一件有利可图的商品”[5]。安的父母培琪先生和培琪太太都对未来夫婿有一番自身考量,同时也指定了最佳人选。培琪先生认可温和乖顺的斯兰德,但他缺乏主见对自己的叔叔夏禄法官言听计从,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叔叔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I. i. 200)、“叔叔,您叫我娶她,我就娶她”(I. i. 231-232)。培琪太太的女婿人选是卡厄斯先生,他脾气粗暴、容易发怒,对“何以为人”的界定总有自己的一套变化无常的说辞,譬如,他用“我要是不娶培琪为妻,我就不是个人”这样的狂言来明确自己的娶妻决心(I. iv. 115 -116)。然而,培琪太太却认可这样一个霸道蛮横的人,“他是我中意的人,除了他谁也不能娶我的小安。那个斯兰德虽然有家私,却是一个呆子,我的丈夫偏偏喜欢他。这医生又有钱,他的朋友在宫廷里又有势力,只有他才配做他的丈夫”(IV. iv. 82-87)。于是他们夫妻二人都在戏剧最后捉弄福斯塔夫的闹剧中各自打着如意算盘,培琪先生让斯兰德先生趁乱把自己女儿偷走,到伊登去结婚(IV. iv. 72-73);培琪太太亲自去通知卡厄斯,让他和自己的女儿去教长家里举行婚礼(V. v. 197-198)。无论是没有主见的斯兰德还是脾气火爆的卡厄斯,都成了安·培琪父母的女婿人选,他们并没有考虑和理会女儿自身的幸福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是将女儿看作一个物品、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可以换来更多的财富和宫廷势力,甚至可以被“偷走”。这无疑体现出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下,女性被轻易物化、商品化,可以随意进行支配和操控。
将安·培琪物化的除了其父母以及两位未婚夫人选,还有她自己相对较为心仪的对象范顿先生。培琪先生强烈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范顿先生,他指责范顿图谋不轨,将其女儿“看作一注财产”,而安·培琪也对父亲的猜忌颇为赞同,“他说的话也许是对的”。这时范顿立即为自己辩护同时明确表露自己的真心:“不,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存心!安,我可以向你招认,我最初来向你求婚的目的,的确是你父亲的财产;可是自从我认识了你以后,我就觉得你的价值远超过一切的金银财富;我现在除了你美好的本身以外,再没有别的希求”(III. iv. 12-18)。范顿先生情真意切的一番告白中使用了经济学话语,即“价值”(value)、“财产”(property)以及“金银财富”(gold;sums in sealed bags)。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根据马克思(Karl Marx)[6],“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use-value)”,而交换价值(exchange-value)“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换言之,就是具有一定量的商品按照各种不同的比例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范顿的话语于无形中将安·培琪商品化,用“金银财富”来衡量安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即交换价值,被商品化的安在范顿的心目中分量相当之重,因而其价值相当之高,以至于“金银财富”也无法与其进行交换,这同时也印证了范顿自己所坦白的接近安并且意欲求取安的原始动机,是为了得到其父亲的财产,即安是作为交换财产的商品,具有交换价值。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随着长时间以及更进一步的接触,范顿所看到的安的价值已经不是外在的商品价值,而是其内在价值即精神和品质上的富有(the very riches of thyself),因而于醒悟后的范顿而言,安不再是交换财富的商品,而是一个具有宝贵精神财富和美好品质的人。安在范顿心目中从商品向人的转化也散发出文艺复兴宣扬的“人文主义”精神之光芒,人们注意到了人自身的重要性,同时,这也促成了安在此番对范顿的爱慕之情进行考量和把握后,不惜违抗父母之命勇敢做出选择,和范顿结为夫妻共度余生,获得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对于安的选择,Rachel Prusko[7]做出如此评价,他认为,“我们没有必要知道范顿是否为安所求,以及嫁给他是否就意味着安听取了范顿的建议——‘自己做主。但我们明确可以知道的是,安摆脱了她不想要的:父母规定的婚姻——嫁给斯兰德或者卡厄斯医生”。因此,安的最终选择彰显了她挣脱了父母对其婚姻管控束缚的藩篱,拒绝被当作交换财富的商品,追求自己作为人的权利。
由此看来,安·培琪的被物化反映出女性的悲惨遭遇,同时也表达了莎翁对女性的同情,因而他在剧中塑造了一个勇敢追求自身幸福、与操控势力斗智斗勇的反叛的安·培琪,最终她取得胜利并解除了自己的婚姻危机,同时也冲击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轻易将女性商品化的压迫势力。
二.福德太太的婚姻危机
贪财好色的没落骑士福斯塔夫爵士觊觎起福德太太和培琪太太的财产,他将她们二人看作是“取之不竭的金矿”“国库”“一个是东印度,一个是西印度”,声称自己要“接管他们两人的全部富源”并在这两地之间开辟他的“生财大道”,于是他分别给二位太太写信献殷勤,语出暧昧(I. iii. 63-67)。此处特别将两位太太比作东、西印度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密切联系。在该剧创作时期(16世纪末17世纪初),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尚不属于英国的掌控范围,西印度群岛一直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东印度属于荷兰的殖民范围。自都铎王朝以来,统治者重视发展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了“发展贸易,实现英国的商业霸权”(详见《英》:313),英国进行殖民扩张,开拓大量海外殖民地。出于“对黄金的渴望;对西班牙的憎恨和对其占有丰沃领地的嫉妒;對其在英格兰拥有一些统治权的强烈敌意以及对宗教自由的渴望”[8]等动机,英国殖民者意欲向西印度加勒比地区进军;根据浅田实[9],“虽然英国从德雷克时期就先于荷兰在‘亚洲海域展开扩展活动,但由于其活动以掠夺抢劫为中心,在商业发展方面较为落后”,尽管如此,英国对于这一地区的殖民野心一直在膨胀,因而无论是西班牙掌控的西印度群岛还是主要由荷兰控制的东印度群岛,都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意欲纳入商业以及殖民版图的猎物。莎士比亚有意在此处将两处地区类比成福斯塔夫的“富源”映射着英国当时也渴望占领控制这两个猎物,在两地之间开辟“生财大道”。
由此观之,两位太太在此处被比作两个财富之地充分展现着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女性被物化,被作为获取财富的渠道或者财富的象征。Walter Cohen[10]认为此处的东、西印度被“性别化”后具有隐喻功能,“调用两个区域的财富来赞扬女性的富有,这暗示着(即使是无意的)女性被商品化了,即女性被看作国际市场中用来交易的物品”。从情节发展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女性的商品化成为了福德夫妇婚姻危机的导火索,正是福斯塔夫将福德太太看作获取财富的商品才诱发了接下来的调情风波、私会风波以及福德先生的捉奸风波,间接造成了夫妻二人的信任危机。
福斯塔夫的两个随从因拒绝给福斯塔夫送信而与其产生矛盾分道扬镳,他们将福斯塔夫的阴谋诡计告知福德先生和培琪先生。培琪先生信任自己妻子的能力,他认为福斯塔夫除了会遭到妻子“一顿臭骂之外”,并不会得到任何好处(II. i. 171)。然而,于福德先生而言,福斯塔夫的出现催生了他的性嫉妒,芬兰社会学家韦斯特马克(E. A. Westermarck)[11]指出“性嫉妒是由于失去或担心失去对于作为自己性欲对象的某个人的独占权而产生的一种愤恨之情”,福德先生便是在这种“愤恨之情”的驱使下,变身为一个原始部落的人,愚昧地将“自己的妻子当成自己的某种财产,把奸夫看成窃贼”。于是他伪装身份为白罗克先生接近福斯塔夫,以试探妻子忠贞与否,生怕自己的这份财产被人偷走。他向福斯塔夫编造了一个谎言,自己有万贯家财并且愿意将自己的钱财供福斯塔夫花销,而他的目的就是,“只要请您分出一部分时间来,去把这个福德家的女人弄上手,尽量发挥您的风流解数,把她征服下来”(II. ii. 226-227),“假如我能抓住她的一个把柄,知道她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就可以放大胆子,去实现我的愿望了”(II. ii. 235-237)。都铎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念,金钱逐渐成为人们“能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12],也正如福德先生在剧中的台词“有钱路路通”所彰显出的金钱的强大功能(II. ii. 164)。深受此价值观念影响的福德先生将福德太太物化,将其道德品质与金钱捆绑在一起,企图利用金钱来验证自己妻子的忠贞。因而福德太太的再一次被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危机。
幸而福德太太在一开始就识破了福斯塔夫的诡计,与同样遭受言语侵犯的培琪太太一同出谋划策以戏弄的方式惩罚福斯塔夫,破除了丈夫福德先生的“捉奸”行动和信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福德先生因为不信任妻子而采取的“捉奸”举动也间接为这场惩罚游戏推波助澜,尽管如此,受惩罚的不止图谋不轨的福斯塔夫,还有福德先生自己——由于两次“捉奸”落得一场空而引得众人指责和训斥。在嫉妒以及对妻子控制欲的驱使下,福德先生终究落得自取其辱的不堪下场,这也促进了其最后的幡然醒悟和忏悔。
莎士比亚通过经济话语的使用展现了16、17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女性被商品化以及婚姻危机。无论是安·培琪的婚姻危机还是福德太太以及培琪太太的婚姻危机,其产生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女性的被商品化。女性成为财产的象征,成为获取财产的交易商品,安被追求者以及其父母商品化,福德太太和培琪太太被福斯塔夫商品化,此外,由于福德先生将福德太太看作是自己所占有的财产的一部分,福德太太又被其丈夫商品化。David Hawkes曾说,“一旦某物被看作是一种‘财产,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它会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变成更大整体的附属品”(see Shakespeare:163)。因此,剧中女性不堪忍受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操控,更不愿作为财产的象征而沦为男性的附属品,诚如培琪太太在剧中所怨憎的那般,“我要到议会里上一个条陈,请他们把天下男人一概格杀不论”(II. i. 26-27),于是她们利用自己过人的智谋和胆魄奋起反抗,最终去除了自己身上被迫赋予的商品化,让心术不正之人得到了惩罚,同时也解除了婚姻危机。这也足以彰显“情感的纽带比经济联系更加可取”,不论是父母和子女、夫妻还是恋人,都不应该过度用物质经济来衡量彼此的情感关系,不应该被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异化,丧失人文的魅力。
参考文献
[1]See David Hawkes, Shakespear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Bloomsbury Arden Shakespeare, 2015:2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Shakespeare”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详见姜守明等《英国通史.第三卷,铸造国家:16-17世纪英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英》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详见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国》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William Shakespeare,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ed. G. R. Hibbard, Penguin Books, 1973:62.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引文所在幕次、场次和行数,不再另注。中译文参考了朱生豪译本,(详见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們》,朱生豪译,裘克安等校,收入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朱生豪译,第138页).
[5]Peter Grav, “Money Changes Everything: Quarto and Folio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and the Case for Revision”, in Comparative Drama, 40 (2006):221.
[6]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48-49.
[7]Rachel Prusko, “‘Who hath got the right Anne? Gossip, resistance, and Anne Page in Shakespeares Merry Wives”, in E. Gajowski and P. Racki, ed. ,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New Critical Essays, 58.
[8]Hume Wrong, Government of the West Indies, Oxford: OUP, 1923:22
[9]浅田实,《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顾姗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0.
[10]Walter Cohen, “The undiscovered country: Shakespeare and mercantile geography”, in Jean E. Howard and Scott Cutler Shershow, ed. , Marxist Shakespeare, 143.
[11]E. A. 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李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266-267.
[12]伊丽莎白·拉蒙德编《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1:119.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