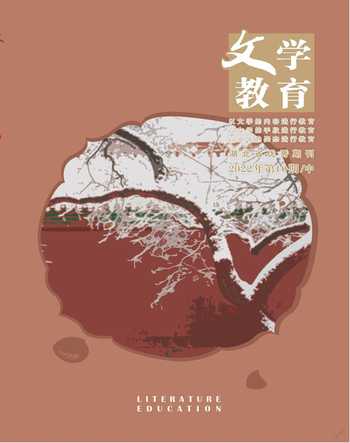《阿尔巴尼亚圣女》的女性空间书写
赵越 杨笑青
内容摘要: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阿尔巴尼亚圣女》描绘了两位背景迥异却有着相似经历的女性探索自我空间的旅程。女性主义地理学者认为空间具有性别化的特征,女性空间在父权社会中历来受到压制和束缚。探寻了空间批评视角下女性自我空间的缺失、追寻与重构的过程,展现女性逃离父权社会的多重禁锢和家庭空间的苦闷单调,积极建构真实自我空间的空间实践。门罗透过其经典的女性书写,传达了拥有独立的、流动的自我空间对于女性成长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门罗 《阿尔巴尼亚圣女》 女性空间 重构
女性主义地理学者琳达·麦克道威尔在1999年提出了“性别化空間”这一概念,即“空间经常被认为具有性别特征,这个世界至少被象征性地分为男性空间和女性空间”[1]。空间批评中的女性空间研究同女性主义地理学有着广泛的共性,都聚焦于空间中的性别差异,旨在“关注针对女性空间上的束缚,而绘制一份实际的或隐喻的地图”[2]。
空间也是艾丽丝·门罗作品中的重要元素。被称为地域作家的门罗将其家乡和周边小镇等场所作为展现人物命运的物理空间;通过在性别、身份、自我之间建立联系,门罗探索了权力话语主导的,建立在一系列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和社会空间,尤其是历来受到压制和束缚的女性生存空间,通过展现女性在面临人生各种境遇和挑战时从压抑、迷茫到逃离、觉醒的成长历程,不断探寻着女性自我空间的建构,书写女性的精彩人生。
《阿尔巴尼亚圣女》讲述了两位背景不同却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女性探索自我空间的旅程。故事始于遥远的阿尔巴尼亚,异域的场景,交织的时空,以及颇具好莱坞风格的情节为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本文采用空间批评理论这一全新视角解读文本,探讨《阿尔巴尼亚圣女》中女性自我空间的缺失、追寻与重构的过程,展现女性逃离父权社会的压制束缚和家庭空间的苦闷单调,重构女性真实自我空间的空间实践。门罗借此传达了拥有独立、流动的自我空间对于女性成长的重要意义。
一.禁锢:女性自我空间的缺失
作为社会的产物,空间中不可避免地留有社会分工和社会身份的印记,性别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身份印记。自古以来,男性普遍有一种“要将女性固定在时空中的渴望”[3]。达芙妮·斯佩恩指出,“性别之间的空间状况是社会安排的,它为男性提供了获取知识的机会,同时制约了女性获取知识的机会,于是性别空间的日常生活环境促成了不平等现象”[4]。
门罗的多部小说反映了社会空间和家庭空间的矛盾和对抗。在具有自传特征的短篇小说《办公室》的开篇,身为作家的女主人公即道出心声“对于你们男人来说,住房是再好不过的工作场所。而女人本身就是一幢房子,毫无分离的可能性”[5]79。门罗这段关于男女空间差异的经典言论有力地佐证了男性的空间霸权和女性的从属地位:男人可以自由出入不同的社会空间,而女性则仅仅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存在,共同为男性的需求服务。
《阿尔巴尼亚圣女》以一个风格迥异的故事再现了相似的主题。加拿大女游客洛塔尔因不满黯淡的生活而独自去远方旅行,无意中闯入了阿尔巴尼亚部落,她遭到绑架并受伤,被羁留在一个小村庄。她养伤的地方是一间石头小屋,是一座被称为“库拉”的粗石建造的大房子。自此她被圈禁在这个女人们聚居的地方,每天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承担着既琐碎又繁重的体力劳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男人们的自由世界。不仅如此,洛塔尔还随时面临着像商品一样被卖掉的风险。避免成为男人之间交易牺牲品的唯一选择就是成为一名“圣女”,同时也意味着她不得不放弃婚姻和生育的权利。虽然可以不再辛苦劳作,但也只能独居在山间石屋,终日与羊群作伴,陷入无人交流的窘境。
洛塔尔意外来到的这个异域空间是典型的父权社会缩影。她唯一的栖息处“库拉”象征着男性对女性的专制空间。在阿尔巴尼亚男性霸权的话语体系中,洛塔尔和其他完全被“物化”的女性一样,是男性支配和压制的对象。她的生存和生活空间被极大地压缩,被切断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意味着空间的封闭和隔离,同时也失去了审视自我、反抗压制的力量。
与此同时,小说的另一位女性克莱尔也面临着婚姻即将解体,女性自我空间匮乏的境地。她是夏洛特(回归后的洛塔尔)异域传奇的忠实听众。彼时的克莱尔,正陷入一段纷繁杂乱的情感纠葛:丈夫唐纳德总是带有“一种谨慎而冷淡的和善”[6]113。沉闷、单调的婚姻生活让克莱尔与租住在家里地下室的尼尔森彼此诱惑,产生了婚外情。被尼尔森的妻子发现后,四个人只能尴尬地面对这段混乱的关系。唐纳德只是不停地抽烟,当晚就直接去找他们诊所的秘书同居;尼尔森在短暂的忏悔后开始逃避,留下克莱尔在凄凉冷寂的房子里独自落寞。
克莱尔的困境正是源于所处的家庭空间。家不仅仅是生活和居住的场所,“家是一种理念,它展现了空间、场所和情感之间紧密的相互关系”[7]。在这个本该让女性获得自我认同的空间领域,她们的梦想、对自由的向往和冒险的念头却被以房屋为表征所包围。克莱尔的家并没有成为她幸福生活的“爱巢”,反而成为了分崩离析的空间。面对丈夫的离去和情人的善变,家俨然成了一个让人触景生情,引发伤心回忆的场所,一个禁锢之地。
二.流动:女性自我空间的追寻
针对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关系、社会空间等方面所处的不平等位置,女性主义地理学一直致力于打破男强女弱的预设,揭示性别权力关系的维持方式以及如何在不同的空间里挑战和瓦解它们。琳达·麦克道威尔主张将流动性放置在性别研究的框架里。流动性不仅意味着个人从一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的移动,“也是性别的另一个空间符码”[8]。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身体流动能力呈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另一位女性地理学家多琳·玛西认为,父权社会对女性空间流动性的控制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在意识形态上灌输女性与家庭、本地的天然联系,使女性和“家”成为稳定的象征,从而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发展[9]。只有挣脱空间束缚,建立超越家庭和狭小私人空间的更大流动性,女性才能真正获得独立和平等。
克莱尔的婚姻变故使她的家成为了一个苦闷、压抑的精神空间,在如此困境下,她所能做的唯有逃离。第二天凌晨,情绪无比低落的克莱尔毅然收拾行李,决定远走他乡。从那一刻起,她走出了摆脱男性权威,追寻女性自我空间的第一步。在那个伤心、漫长的早晨,她宁愿乘坐三天的长途火车去往一个遥远的城市。车窗外的景物衬托了克莱尔迷茫、忧郁的心境,同时也触动了她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和感悟,“我人生中的剧变就发生在这个十二月……我当时难道没想过,期待一个男人与另一个截然不同是多么荒谬?生活归根到底不过是有杯像样的咖啡和一间能够舒展身体的房间?”[6]116一连串的反思和拷问直击克莱尔心底最深层的伤痛和渴望。仿佛一刹那间她看清了男人的本质,不再期待浪漫与奇迹。如果说克莱尔之前的生活选择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那么她在逃离过程中对两性关系的深刻反思对未来之路的走向具有非凡的意義,引导着她一步步去发现、寻觅,开启新生活的旅程。
克莱尔之所以对洛塔尔的故事如此着迷就在于她们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是富有的女继承人,都急于逃离现有的生活,开拓自我发展的新空间。洛塔尔在阿尔巴尼亚的遭遇也是源于与朋友的一场旅行。她对这群看似体面实则世故的人们满怀失望。为了逃避他们安排的一次无聊会面,她与导游前往一无所知的阿尔巴尼亚山区,经历了重重艰险。即使成为“圣女”之后,洛塔尔的危机并没有解除。她并不真正属于库拉,因而没有人会给她土地,让她可以独自在那里生活。幸好有牧师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她的处境,为她精心筹划,带领她踏上了逃离之旅。尽管历尽漂泊,洛塔尔终于逃离了阿尔巴尼亚男权空间的禁锢,在大自然的穿梭中找到了久违的自由与内心的宁静。
克莱尔和洛塔尔面对社会和家庭空间的束缚勇敢地选择逃离的空间实践打破了女性只能在有限的私人空间活动的二元结构。她们或只身一人,或相伴而行,在城市的流动空间中漂泊,不断追寻着女性独立的自我空间和自我认同。尽管未知的旅途充满不可预知的因素,但流动的空间状态让人始终保持一种审慎和警觉。通过辨识、观察、感知和体验各个不同的空间,女性能更好地探寻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从而实现自我的蜕变。
三.发现:女性自我空间的重构
对两位女性来说,逃离不仅仅是摆脱当下现实生活的无奈之举,更是一场自我发现的成长之旅。克莱尔在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一个不受干扰的自我空间内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每天她手捧一杯咖啡,漫无目的地读书。书中优美独特的散句经常让她陷入一种特别的状态:“恍惚而又警觉,与所有人隔绝却随时觉察着这城市本身”[6]109。正如吉莉安·罗斯所说,“隔离让女性有喘息的空间,得以思考、冥想、汲取力量和重获身份”[10]。克莱尔对自我空间的追寻还表现在她主动构建了书店这一独立的空间。这里是她的宝藏,“里面都是自己最为珍视的东西[6]110。对克莱尔来说,书店已经不仅是一个容身之所,而是一间“林中木屋——是一个避难所,一种正当存在”[6]110。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店也是她对抗男性中心主义的阵地。在这样一个曾经由男性主导的空间里,她成为掌控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喜欢的书、做喜欢的事,也可以冷静、超然地思考自我和人生,不必顾及他人的眼光。虽然生活窘迫,但她“并不沮丧,感觉自己已经以全新的面貌重生于世”[6]109。克莱尔在异乡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精神家园,一个真实的女性自我空间。
随着书店经营状况的好转,克莱尔渐渐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回归后重拾身份的夏洛特。克莱尔对她的认同源于两人颇为相似的抗争历程:面对乏味的生活和空间的局限,宁愿选择在异乡漂泊。与克莱尔一样,夏洛特在新的空间里找到了自我价值和幸福感。虽然穷困潦倒,颠沛流离,却始终保持着傲骨和尊严。受邀去作客的克莱尔被他们那种“真正的匮乏和大胆的真实”[6]123所震撼,同时也被夏洛特率性、洒脱的品性所吸引,“希望受到她的熏陶,变得轻快、自嘲”[6]124。两个女人惺惺相惜,彼此鼓舞,在对方的故事里汲取养分,获得成长。
夏洛特的一生都“在路上”。在故事的结尾,她与丈夫的再一次离开似乎不足为奇。但无论身在何处,他们都始终没有停下追寻真实生活的脚步。克莱尔也开始想象和尼尔森在遥远的地方共度全新的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两个女性找到了一个追逐自由和梦想的舞台,重构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一个人看似走向外界,其实是走向内心,去发现真正的自己。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说,“有一个能够同难于相处的世界融合一体的自己。人必须跨过一段完整而漫长的时间,即穿越自我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造就”[11]。
门罗在《阿尔巴尼亚圣女》中构现了一幅女性摆脱空间束缚、追寻自我空间的文学地理景观图。小说也反映了门罗的空间观:女性通过积极的自我空间建构,打破传统女性身份被空间定义和书写的僵局,是对单一空间二元论的有力反击。夏洛特和克莱尔努力拓宽女性生存空间,最终成为女性自我空间的主宰。她们的自我放逐,看似孤单落寞,带来的却是重生与蜕变:重新审视自己和两性关系让她们更融洽地与自己和他人相处,不断走向独立和成熟。
参考文献
[1]Cain E W. Between the Angle and the Curve: Mapping Gender, Race, Space, and Identity in Willa Cather and Toni Morrison[M]. London: Routledge, 2006:19.
[2]Nelson L & Seager J. A Companion to Feminist Geography[M].Oxford: Blackwell, 2005:3.
[3]Owens C. The Discourse of Others: Feminists and Postmodernism, in H. Foster(ed.), Postmodern Culture[M]. London: Pluto Press, 1985:75.
[4]达芙妮·斯佩恩.《空间与地位》见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编.《城市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295.
[5]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M].李玉瑶,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8:77-79.
[6]艾丽丝·门罗.《公开的秘密》[M].邢楠, 陈笑黎,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7]Warf B.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Vol.3.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1439.
[8]McDowell, L. Gender, Identity &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y. UK: Policy Press, 1998:58.
[9]Massey, D. Space, Place and Gende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178-179.
[10]Rose G.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153.
[11]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224.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