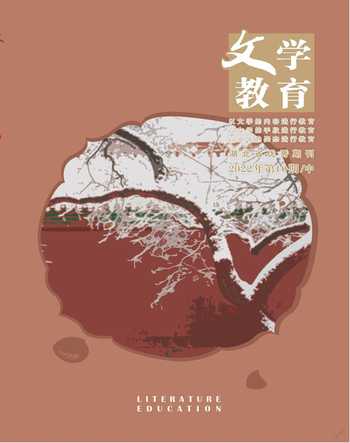张爱玲《封锁》中爱情的另一种解读
丁洋
内容摘要:张爱玲是近现代一流的小说家,她创作的作品都以两性关系为题材,借剖析两性关系来揭露人性的真实。小说《封锁》讲述了一段已婚男性和未婚女性之间发生的奇遇,巧妙地利用特殊时空处理手法讲述了吕宗桢和吴翠远在电车上偶遇的故事,借两人的“合拍”相处来展现人性的另一面。封锁下的电车让时间和空间既被凝缩又被放大,使人性在这个特殊节点中完全暴露。以往的研究认为吕吴两人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把两人的状态定性为恋爱,但这种定论在进一步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本文将从吕宗桢和吴翠远的对话和心理之真与假对文本进行解读,进而探索人性的深刻和真实。
关键词:《封锁》 张爱玲 真与假
《封锁》是收录在《传奇》中的一部短篇小说,讲述了封锁期间一对男女在电车上发生的故事。鉴于张爱玲的作品多以婚恋关系为叙事重点,因此历来的研究者都认为《封锁》是一个男女间恋爱构建又破灭的故事。[1]小说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时空叙事,让这对男女的搭讪和调情更加顺其自然,于是他们在短暂地相处后陷入了爱情[2]。如果把两人间的关系定性为恋爱,这其实并不合理。吕吴两人在电车上由陌生人飞速成为互诉衷肠的知己,甚至话题一度转向了谈婚论嫁,但如此亲密的关系却在封锁一解除就瓦解了,两人重又恢复到陌生人模式。因此,这里的恋爱就无法成立,不过这两人之前的相处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这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琢磨吕宗桢和吴翠远在对话和心理上的真实和虚假,探究张爱玲笔下的人性的真与假,也是具有意义的。
一.对话的真与假
张爱玲写作惯于从日常生活入手,以上海小市民为主角,从真实的时代背景切入,希望在虚构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这种传奇出现在虚构作品里的普通人身上,往往是为了在虚构中得到另一种人性真实。《封锁》中有大篇幅的笔墨用于书写吕宗桢和吴翠远两人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都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果,看似和谐的交流实际上使两人处于对峙的局面,看似诚心的交流实际上是营造的假象。
小说里的吕宗桢是一个善交际、油滑的中年人,在电车封锁期间他在准备好的调情计划下对陌生女子吴翠远进行了搭讪。精于世故的他从夸赞吴翠远入手,“你知道么?……后来你低下头去从皮包里拿钱,我才看见你的眼睛,眉毛,头发。”[3]338吕宗桢把对吴翠远的初次一瞥诉说得很戏剧化,吕宗桢看似是被吴翠远的相貌吸引住了,可实际上对他而言,这戏剧性只是碰巧得到的,不能归功于他,以至于说完这些话后他再回忆时早忘了自己说的内容。
被搭讪者吴翠远是一个朴素无华的普通女性,面对吕宗桢的花言巧语,她看似不必在意但内心却起了波澜,她感到快乐而觉得炽热,忍不住背过脸。于是吕宗桢改变道学气的交流方式,把话题转向了生活和工作。但作为话题发起人,吕宗桢却表现得万分为难。这种欲言又止的态度反倒像在探求最适当的说辞,吕宗桢内心在揣测吴翠远希望听到的话。如此斟酌着发言,吕宗桢的这番话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他圆滑地转变话题、揣度用语,看似真实地对话却是在虚伪着与人相处。
除了吕宗桢在逢场作戏,吴翠远也只是随身附和。在听到吕宗桢谈到妻子和文凭,吴翠远不禁微笑道:“你仿佛非常看重那一纸文凭!其实,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3]340可说完这句话吴翠远又觉得伤了自己的心,这说明这句谎话只是说给宗桢听的。
小说里的吕宗桢和吴翠远看似意趣相投、相处融洽。但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终究无法赤诚相待,谈话内容都有多少保留,甚至有所隐瞒,两人都在维持精心营造的美好氛围,谁都不愿戳破。
二.心理的真与假
为了迎合他人和表现最优自己,矫饰语言再发言可以隐藏真实的自己,但语言背后潜意识里的心理活动则是人性最直接的暴露。这种人性一方面被世俗浸润而呈现一种社会化的虚假,另一方面因保留本我而呈现一种无意识的真实。
1.社会化了的惯性心理
吴翠远和吕宗桢都属于社会人,遵循社会法则和规训,在人际交往中会下意识出现社会化惯性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是他们长期迎合社会、扮演“假”好人形象的结果。因此,社会化了的惯性心理并不是真实的心理,而是裹挟着虚假的心理。
听到吕宗桢抱怨妻子,吴翠远想:“她知道他们夫妇不和……他需要一个原谅他,包涵他的女人。”[3]340吴翠远虽然是个未婚女性,但她生长在一个新式的、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因此夫妻之道,翠远早已耳濡目染。她完全认同男子需要女人的同情,女人应该出于本能的包容男子。尽管吴翠远是一个新式的年轻女性,但仍难逃中国封建伦理礼教的束缚,是个被腐朽文化驯化了的人。在思考男女恋爱关系时,吴翠远也是不自觉陷入男权文化主导的女性(奴性)意识。“恋爱着的男子向来是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3]341吴翠远认同女性应处于被动地位,要完全的附和男性。虽然吴翠远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在高校教书,但她仍被世俗浸染了,这种畸形的观念、社会化的惯性思维反而是她真实的心理。在和吕宗桢谈及婚姻,吴翠远心想的是,“可不是,还是钱的问题。他的话有理。”[3]342尽管吴翠远想用找吕宗桢这个已婚没钱的人当丈夫来气自己的家人,但这只是冲动之下的想法,她的实际心理表明她已经接受了家里人要求要找有钱人结婚。
与吴翠远的世俗化不同,中年男性吕宗桢完全是被男权社会同化的代表。在电车上吕宗桢看到熏鱼便想:“女人就是这样……她一点也不为他着想。”[3]333吕宗桢认为合格的妻子应该为丈夫着想、给足丈夫体面,家庭中夫权应该高于一切。吕宗桢最直接的心理想法是传统伦理观下的产物,他无条件接受男权主导世界的规则和教条。当吕宗桢以为吴翠远为自己着迷后,他的心理是最大化的真实,“你不要她,她就悄悄地飘散了……你說真话,她为你心酸。”[3]341在吕宗桢的观念中女性应该是男性的附属品,是无私为男性奉献的圣女。吕宗桢的意识形态受过男权社会的洗礼,当他在男女关系里处于上风地位,他的大男子主义、自私虚伪便全部暴露出来了。吕宗桢油滑着扮演单纯的男子,享受吴翠远的脸红。
吴吕二人都置身于同个社会文化背景,思想和观念都向传统礼教靠拢,潜移默化地成为社会化了的人,如出一辙地使用社会化惯性思维来做人做事。在日常中,每个人都为了融入社会表现得八面玲珑,而更加圆滑世故的人则善于隐藏真实的自己,扮演一个“假”的好人,这种“假”好人难于识破,但即使被发现了也没有人会拆穿,因为这种互相扮演好人的做法太司空见惯了。
2.自我体认的真实心理
弗洛伊德在《自我和本我》中提到,人的人格是一个整体,它包括三个部分,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7]吴吕二人的真实心理除了社会化的惯性思维,还有属于自我体认下的真实心理。这种心理是最真实的本我心理,不具备欺骗性。
吴翠远起初对吕宗桢的搭讪不愿理睬,但当吴翠远注意到他的手臂不再轻浮,以为是自己端正的人格促使吕宗桢转变态度。吴翠远知晓自己的形体容貌不足以有魅力吸引男性,但她自信于自己是个好女儿、好学生,自信于自己端凝的人格,因此当吕宗桢规范了行为,便愿意和他聊天。吴翠远对自身是有着真实认知的,这种真实的认知藏在潜意识里形成某种心理,指导她做出某些行为。吴翠远毕业留校做了助教,接触最多的群体还是学生,虽然她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人,但她还是过于稚嫩和年轻。“以后她多半是会嫁人的,可是她的丈夫决不会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股的可爱——封锁中的电车上的人……”[3]342吴翠远被吕宗桢表现出的真情所感动,以为他是可爱的人,可她理智上知道这一切都是泡影,她仍旧会按照父母的要求找有钱人结婚。吴翠远的真实想法没人在意也无法和吕宗桢诉说,当希望变成虚妄她只能哭了。“可是那不是斯斯文文的,淑女式的哭。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脸上。”[3]343
吕宗桢和吴翠远通过交谈,关系似乎是亲密的,但是这种亲密仍只是扮演对方眼中完美自己的表象,他们的身体动作出卖了他们的真实心理。“宗桢与翠远奇怪他们刚才怎么这样的糊涂,就想不到自动地坐近一点。”[3]342两个人的语言都套路着互相配合,可是他们的身体却都保持着原来的距离。他们潜意识下的真实心理都认为应该坐近一些来搭配他们聊天的话题,可他们的肢体语言却暴露他们在自说自话。这一方面也是印证了吕宗桢和吴翠远之间是没有真情的,他们只是在表演。
三.《封锁》再解读
《封锁》中的背景是战争年代,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市民的生存空间不断挤压,恶劣的外部环境让每个人都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张爱玲捕捉到这群小市民的生存状态,在小说中设计了一群“封锁”期间坐电车的乘客,在巧妙的时空下给人生世相以另一个窗口演绎。[4]
电车停止运行,乘客可以暂时避开喧嚣,处在一个相对静止、自由和平等的环境,可以阻断世俗的侵扰,释放日常生活的紧张焦虑。停下来的时间给予每个人属于自己的空间,用于思考或者反思,摘掉伪装的面具暂时成为最单纯的人。但《封锁》中的所有人却没有这么做,没有一个人愿意以真心待人,更不愿让人看到自己的真心。这副人情面具和每个人融为一体,本我的真实体认被社会化认知取代,每个人都在虚伪着真实,真实着自私。[5]一方面他们无知觉地落入传统礼教的圈套,把规训和教条当作人生的指向标,用这套思想武装自己进行人际交往。另一方面他们又躲不开自我体认下的真实,无意间在心里真实流露,而这种真实往往显出人性虚伪。
封锁中电车上的多数人是缺乏自我反思:中年夫妇只关心裤子干洗的价钱,老头儿用搓核桃消磨时间,董培芝想借机同吕宗桢熟络。所有人中只有吴吕两人是可能自我反思的,因为一个不愿屈从父母的指令——嫁给有钱人,一个不愿听从妻子买包子的要求。他们受到协迫而缺乏真正的表达,渐渐也没了自我独立性。可是当他们在特定时空内有所挣扎,制约和束缚就会出现,使这种虚晃一枪的挣扎在出现后立刻被现实打倒。吕宗桢本质上是缺乏自省意识的,顺从于现实对自己个性的压抑。他精于扮演一个“单纯”的男子,得意于年轻女子被自己吸引,享受与陌生人的调情。当封锁解除,他立刻回归社会化自我,回家后记不清吴翠远的样子却记得自己慷慨激昂的发言。吴翠远是接受新式教育的传统女性,因为家庭压抑而导致女性自我意识膨胀。她欣赏敢于抨击现实的叛逆学生,是因为她内心也渴求抗争,她自恋地认为学生在卷子上的话是只说给她听的,是因为她沉浸在自己世界,把自己想得很大。吴翠远是尚存自省意识的,但这种自省实际上既不正确也不健康。封锁结束后她失落于男子的获取又消失。因此在《封锁》中这一群人真实又虚假,是极现实又极讽刺的。
张爱玲不喜欢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而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虚伪之中有真实,对真假进行剥离可以看到真实的人性,把所有掩藏的拨开,可以得到人性的阴暗面和真实面,从而揭开张爱玲笔下的苍凉现实。[6]在现实中每个人都被社会同化吞噬,阻断了真实情感的交流,即使是看似的真实却还是表演着的虚假,真与假之下全是自私。
对真假的剖析,是对复杂人性的开掘。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说:“因为我用的是参照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8]94说作品主题欠分明无疑是作者的谦辞,张爱玲只是在作品里拒绝对善恶是非给予判断,这样避免了个人意识形态对文本的干预,持中立的态度、不倒向善恶的任何一方,体现了张爱玲对人的包容和理解。但张爱玲知道真与假是不容易糊弄的,她用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笔法对人进行刻画,把人的真性情全部暴露出来,让读者看到这种虚假才是人性的真实,尽管对现实人生不满但还是选择互相欺骗、虚假着活。
由于“参差对照”的美学观念作支撑,《封锁》也并不是表现真假的分野,而是真假之间的虚实。张爱玲深谙人的多面性,诚实面对这种人性,真实地把人性的复杂再现给大众,这种只再现而不现身来鞭挞的写法,又体现一种美学的开放性。
综上所述,苏珊·桑塔格说,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封锁》正是这样一篇常看常新、独具艺术的作品。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大时代中的负荷者,不论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范柳原,还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亦或是《封锁》里的吕宗桢、吴翠远,他们都是俗世下生存的小人物。在社会大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小人物,永远有束缚自己的枷锁,也永远有自己挣脱不了的局限。他们困于世俗化的虚假中,又难于避开自身的真实,他们真正生存的是真与假掩映下的灰色地带。
张爱玲敏锐观察这些沉溺在花花世界里的人,诚实地写出他们的生存现状。不论是小市民生存压抑呈现无意识的昏昏沉沉,还是他们鲜少呈现的自我反省,张爱玲都以客观公正的笔法写尽小人物的一举一动,让读者得以在人物身上进行不断地挖掘与探索,从而揭开这种真与假,得到最真实的人性。这不仅体现了张爱玲写作的开放性,避免了作者过多的自我意识对于作品的主观干预,也印证了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句话。这样好的作品总能给读者以大量的思考空间与深刻的哲思。
参考文献
[1]庄萱.时空艺术与精神分析的多棱镜:重读张爱玲的《封锁》[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7,000(001):23-29.
[2]陈怡.“封锁”下爱情的建构与破灭:论张爱玲1943年小说的情节模式[J].理论界,2013(01):140-142.
[3]张爱玲.传奇[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万燕.短暂的两性之梦——重读张爱玲佳作《封锁》[J].粤海风,2020(5).
[5]王晓平.封锁于倾城之内——对张爱玲小说《封锁》的五重分析[J].名作欣赏:鉴赏版(上旬),2015.
[6]魏書鹏.从李欧梵对“封锁”状态的解读看《封锁》的传奇性[J].作家天地,2019,000(008):21-22.
[7][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8]张爱玲.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