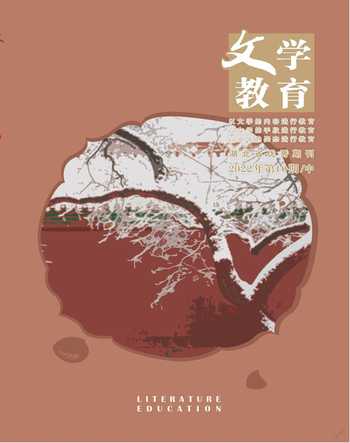《盲刺客》:多个空间下的女性救赎之路
许陈丹
内容摘要:《盲刺客》被称为是一部回忆录,它以现实空间为主线,创造出第二空间,即“劳拉”的《盲刺客》,由此再建立了第三空间“盲刺客”的叙事线。在这三个空间里,“我”即艾丽丝蔡斯是多个空间下的联结者,她借三个空间里的人物建立起自我对话。每个空间里的女主人公都是本体叙事者艾丽丝隐藏的另外两面,同时分别隐喻了男权制时代下女性共同的命运。从三个空间的隔空对话、多重身份的多种含义、救赎之路三个方面来分析艾丽丝是如何在多个空间中建立起对话并进行救赎的,以此来探讨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生存之路。
关键词:《盲刺客》 空间叙事 女性主义 象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代极富代表性的女性作家、诗人、评论家。她的作品《可以吃的女人》《别名格蕾丝》《盲刺客》等都很有影响力。《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2000)是她第十部长篇小说,出版于2000年,并获得了该年英国布克奖。无论是从叙事学、后现代、还是女权主义等方向,国内外学者对《盲刺客》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进行了解读,然而在众多学者的文章中,最后都只是揭示了女性遭受困境的原因,却未能提出解救女性的生存困境之法。例如柯倩婷的文章中探讨了小说的记忆与空间叙事,并揭示了作者利用这种叙事方式来写作的隐含目的。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对空间叙事进行非常清晰的梳理,也没有对小说所揭示的女性困境提出救赎方法。本文重新对文本所呈现的多个空间进行了清晰地逻辑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条女性救赎之路。
一.多空间对话
《盲刺客》是部结构十分复杂的作品,故事里套着故事。这种复杂的结构一方面得于作者的叙事技巧,另一方面也得于作者写作的隐含目的。阿特伍德运用其超强的叙事能力在作品中为读者建立起了三个空间。首先文本一开始就将读者带入了第一空间——现实空间。在现实空间的基础上,作者又虚构出了第二空间,在第二空间里又虚拟了第三空间。每个空间里都以不同的人称讲述着不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之间又建立起了一种交流关系。
1.“隐忍与困惑”的现实空间
现实空间在小说中指的是以第一人称“我”展开的叙事空间,是高龄82岁的女主人公艾丽丝·蔡斯以记忆叙事方法来回忆过去和讲述当下生活的故事。
在现实空间里,由女主人公的妹妹劳拉的死来引出作品的第一个故事,也是整个作品的主题故事。文中开篇写道:“大战结束后的第十天,我妹妹劳拉开车坠下了桥。”在这里阿特伍德运用了倒叙手法,为整个故事制造了悬念:劳拉为什么坠下了桥?是意外还是自杀?在故意宣告劳拉死亡和引起的种种疑问之下,“我”开始回忆与劳拉的成长过程。首先在现实空间的回忆当中,整个线索都是由从小照看艾丽丝姐妹的女佣瑞尼来提供的。作为本体故事的主要线索提供者,将艾丽丝、劳拉以及蔡斯家族的发展历程完美地串联在了一起。在艾丽丝的回忆中,还穿插了许多则新闻报道,为艾丽丝的“回忆之旅”提供了时间框架。但是这些新闻记录的只是生活的表面,小说通过最后揭示的真相中来颠覆了各种新闻报道的事实。在此使用新闻报道不仅体现了作者本人对新闻报道存在质疑的观点,同时也将小说里现实空间里的本体故事的真实性提高到了一定高度。现实空间里除了回憶的故事情节外,还穿插着艾丽丝当下的生活片段。小说中描写到了年老的艾丽丝受着身体、心理上带来的双重痛苦,进一步暗示了艾丽丝对自己妹妹劳拉的愧疚之情。
2.“放纵与反叛”的第二空间
主人公艾丽丝假借劳拉之名发表了文本——《盲刺客》。《盲刺客》在“我”的回忆中,套入了“他”和“她”的故事,是在现实空间的基础上以第三人称为叙述视角建立起来的第二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人公分别为“他”和“她”。作者借用这两个人称代词来指代左派激进青年亚历克斯和艾丽丝。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指出:“第三人称一般是指其中根本不提及写作的‘我的虚构作品。”看似为读者营造出了一个虚构的空间,但却是暗示了艾丽丝婚外情的真实故事。
整个第二空间是由“他”和“她”进行约会而展开的。作者通过塑造不同约会场景、场所、环境的好坏和变换来暗示艾丽丝与亚历克斯约会的不易。比如文本中“路面只有犁沟那么宽。到处是餐巾纸、口香糖的包装纸,以及鱼鳔似的用过的安全套。瓶子、鹅卵石和泥路上的一道道车辙,一切都乱糟糟的”。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约会,艾丽丝表现出来的却是愉悦、兴奋之感,她与亚历克斯的每场约会都是其释放内心被婚姻束缚住了的情感的地方。
3.“无法摆脱厄运”的第三空间
在小说塑造的第二空间里《盲刺客》中作者又虚构了第三空间——“他”给“她”讲述了发生在塞克隆星球的盲刺客故事。塞克隆星球上的萨基诺城曾是一座美丽繁华的城市,后来毁灭于部落战争。在国王统治下,那里的居民信仰众多之神,以少女的血祭奠神灵,同时把这些当祭品的女孩割去舌头,成为献身哑女。在故事中盲刺客致盲的原因以及他的身世是这样描述的:“这座城市还以编织品而闻名——这种地毯总是由奴隶中的儿童来编织的——由于长时间不断地把眼睛凑近织物劳作,他们一般到八九岁时就全都瞎了。而地毯的价值是卖主根据它完工后瞎了多少个孩子来衡量叫卖的”;“这个年轻人小时候曾经织过地毯,后来沦为了童妓,逃脱后就以他的无声无息、行动诡秘以及无情的杀人手腕而名声大噪。”
哑女和盲刺客的爱情是处在一个危险境遇的,犹如第二空间里的艾丽丝和亚历克斯。四个人虽扮演着不同的身份,但是所面临的爱情与残酷现实之间的问题是有所相似的。他们有结实的爱情、有双方的信任,也有恶劣的环境、有不能公众于世的苦楚。
4.三个空间的嵌套
阿特伍德在现实世界里创造出第二空间,再由第二空间里的人物虚构出第三空间。读者可以在现实世界里的艾丽丝、劳拉的成长过程中发现,劳拉的死与其从小生长的环境而形成的性格分离不开。性格倔强、孤傲的劳拉身上有种不同于姐姐艾丽丝的强烈反叛特征。反之,艾丽丝却是个‘保守、‘任人摆弄的旧女性。在现实空间里的“我”是压抑的、失去自由的、肉体与灵魂是相斥的。也正因为这样,得不到情绪释放的艾丽丝以劳拉的名义发表了《盲刺客》,在现实空间里创造了第二空间。因此,第二空间里的艾丽丝与现实空间里的“我”产生了强大的反差感。“我”通过第二空间里的艾丽丝,与之对话,把隐藏在身上的自由放荡、叛逆之情全部投射到第二空间里的“她”身上。
在当现实空间与第二空间完成一组对话后,第二空间里的艾丽丝与第三空间的哑女也建立起了对话。她将自己与亚历克斯实现双宿双飞的愿望寄托在哑女身上。虽然哑女自身也遭受着所属空间里的困境,但她终究是与之相爱的盲刺客时刻在一起的。而这正是第二空间里的艾丽丝所不能做到的。这三个空间以这种嵌套式的结构向读者展现了以艾丽丝所代表的女性是极其复杂的。
二.多重身份的象征
多个空间的对话使得艾丽丝这个人物变得更加立体,也使艾丽丝在现实世界里实现不了的情感通过隔空对话传达给第二、第三空间里的“她”和“哑女”。阿特伍德不仅是在叙事上运用了空间嵌套的技巧,而且在这些构造的不同空间里,所塑造的人物:“我”“她”“哑女”都带有不同的象征性,她们象征着男权社会中各类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命运。
1.“我”即叙事者身份的象征
为了摆脱工厂困境,父亲把“我”许配给了富有的中年实业家理查德。然而此时的艾丽丝已爱上亚历克斯,但由于她从小所受的教育造就了她顺从的性格,无奈之下只好同意成为理查德妻子。在后来的生活中,始终被理查德的一家掌控于手掌之中。即便是自己的妹妹被丈夫送去了精神病院也无可奈何、无计于施。在《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杂志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无论是由于艾丽丝的个性,还是由于她母亲早逝而强加给她作为姐姐的责任,艾丽丝对自己有自决能力的信念已经被埋葬在虚假的自我之下,她构建了这个自我,以获得她情感上依赖的男人的爱和认可。”可见在男权制社会下,大部分女性即便是贵族小姐或是富家夫人,都是生活在她们的父亲和丈夫的掌控下。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小说中也写到了“我”在接受来自家族的安排和丈夫支配下,内心充满着无尽的叛逆。例如“我”在小时候会故意地将妹妹推倒在草坪上,或是在小说后半部分讲述到“我”出于妒嫉而告诉妹妹自己与亚历克斯的恋爱关系。以上这些都暗示着“我”这类女性在自身欲望中有着觉醒意识。阿特伍德用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大的艺术张力将“我”身份赋予了这一层象征意义。现实空间里的“我”是处于困境中带有觉醒意识的女性,虽然没有自由、没有权力,但是在她们的意识中往往有着微弱的反抗意识,也是一种无声的挣扎。
2.“她”者身份的象征
位于第二空间里的“她”者身份又有着另一层象征意义。在这个空间里,艾丽丝与亚历克斯的历次约会被描写成一场场侦探情色片。上流社会的贵族夫人穿越在大街小巷,隐藏自己的面目,去公园、去列车风格的咖啡馆、去五金店楼上的小房间,作者将这些约会变成了一种主人公的冒探险经历。然而这对于生活在枯燥乏味中的艾丽丝来说,这种约会形式对她来说具有极大的感官体验,比如其中描写道:“她需要一件在大甩卖时的买的外套,塞入手提箱,进一个饭店的参观,把自己的外套留在前台,溜进化妆间换衣服,然后再弄乱头发,擦去口红,出来时就成了另外一个女人……她可以扬起双眉,那种坦然真诚的目光只有双重间谍才能装出来。”
艾丽丝在紧张的时间、狭窄的空间里,享受着每一次的自我释放。他们的约会是紧张与激情的二重奏。阿特伍德将戏剧性的约会布景赋予了艾丽丝一种“逃离”浪漫色彩。因此,“她”者身份其实是象征着敢于反叛现实困境、追求自我空间与自由爱情的女性。
3.哑女的身份象征
哑女是带着“失语症”的特征出现的一类女性。她的身份是一种对自由的失望和无奈的象征。在哑女这个故事里女性是物化的、可以被操控的祭品,是与锁链相伴的受害者。在这虚构的星球里,哑女处于被摧残的生存境遇中。原本以为盲刺客与哑女在逃离后会在无人认识的一片净土里开始自由生活,但故事的结局是盲刺客带着哑女逃出了萨基诺城,在几经磨难后戏剧性地被“狼”吃掉了。阿特伍德并没有简单地抨击社会对女性的压抑,而是运用了一种欧亨利式——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模式。正是以这样的一个悲惨结局,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女性的悲惨命运。
阿特伍德用啞女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他者地位形象,一方面揭示了对男权统治的反抗意识,另一方面表示女性在男权制社会中经历着没有自由、没有权力、没有自我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以这类哑女为代表的女性仍未有觉醒意识,或者说她们在这样的困境中充斥着无限的恐惧和孤独。
三.女性救赎之路
作者从多方位的、虚拟的、现实的空间,再到不同空间里人物的隐射,向读者揭示了女性在面对困境时的不同选择,以及女性在特定时代下所遭受的共同命运。当然作者并没有到此截然而止,而是针对这些女性命运问题之后,向读者传达出女性该如何在困境中开创出一条救赎之路的信息。从现实空间到第二空间再到第三空间,多个空间结合在一起后呈现出来的是一条女性救赎之路。这条救赎之路从艾丽丝的成长轨迹到虚构的故事空间中,显现出来的是由“他救”“互救”“自救”三种模式相组合而成。
“他救”在这里是指来自异性间的救赎。文本中对艾丽丝来说亚历克斯是“他救”者。生活于婚姻牢笼中的艾丽丝在亚历克斯的爱情催发下,不顾一切地放下身段去各种地方进行约会。可以说如果没有亚历克斯的爱情与那份敢于偷情的勇气,艾丽丝的自我意识、自由意识不会得到释放,从而就会导致她在婚姻牢笼中逐渐迷失自我。她在与亚历克斯的爱情中找回了真实的自己,这是一种来自异性者的“他救”之路。
“互救”在这里指的是同性间的互相救赎。小说中艾丽丝摧毁了劳拉,这个事实无可更改。比如劳拉对亚历克斯在战争中身亡的事实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她面对姐姐的坦白却难以接受。艾丽斯原本可以选择撒谎,继续维持劳拉的幻想,但却因为嫉妒,她撕破了一切,把妹妹推向了死亡。如果艾丽丝能够在理查德决定把劳拉带回家中时就提出反对意见,或者当得知劳拉被理查德送去精神病院后能及时把妹妹救出来,那么劳拉或许也不会自杀,同样艾丽丝在晚年也不会过得如此凄凉。如果艾丽丝能与劳拉携手抵抗理查德家族,那么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在男权社会里,同性间的互相救赎是不可或缺的。
“自救”是除了“他救”和“互救”之外小说想体现的更为至关重要的一个途径。每一位女性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个体的自我救赎是除肉体之外灵魂得到重生的重要途径。阿特伍德用三个故事,以小说中大故事的叙事者“我”作为主体,通过回忆叙事、塑造第二、三空间来暗示这是女主人公艾丽丝的一场自我救赎。例如在小说的最后一份新闻报道里写着:“她坐在她家的后花园里,十分平静地离开了我们”。这里的“十分平静”可见艾丽丝在走之前不是痛苦的,所展现的是一种对过往的释然、对自己的谅解。
《盲刺客》的故事套故事的结构固然复杂,却看到了以艾丽斯为代表的女性在对自己的人生处境上是如何经历困境、觉醒、反叛的过程。艾丽丝在三个空间中建立起了自我的隔空对话,在这对话中含有的三种不同身份又各自代表了女性三种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了一条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生存之路。
参考文献
[1]阿特伍德.2003.盲刺客[M].韩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柯倩婷.《盲刺客》:一部关于记忆的小说[J].外国文学评论,2007(01):104- 110.
[3]黄向辉.论《盲刺客》的结构艺术[J].当代外国文学,2007(04):76-81.
[4]何瑛.《盲刺客》:女性的叙述欲望与生存地图[J].上海文化,2015(07):113- 119.
[5]饶静.盲目与洞见——读《盲刺客》[J].世界文学评论,2008(01):181-183.
[6]王岚.《盲刺客》:一部加拿大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杰作[J].外国文學,2005(01):75-79.
[7]“Alias Laura”: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in Margaret Atwood's “The Blind Assassin”[J].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2006,101(2).
[8]Laura Flores. Tres caras en el espejo A propósito de The Blind Assassin de Margaret Atwood[J]. Revista de Culturas y Literaturas Comparadas,2008,2(0).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