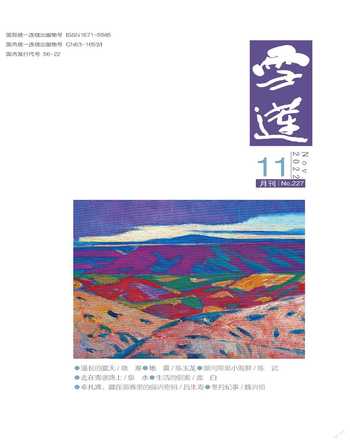爸爸的天空
接到电话时,王建国正在单位开会,从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熟悉的声音,却隐隐流露出一点异常的气息,就是那一点异常让他心里猛然一颤,他立即预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这种直触灵魂的感觉让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习惯性地匆匆挂断电话,而是选择了另一种不同以往的做法:他中断了会议,匆匆走出会议室,去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那一刻,他比谁都更想知道,隐藏在母亲带给他的那种异常感觉之后的实质性的内容。果然,母亲在电话那头闪烁其辞地应付了几句之后,也就不再转弯抹角了,她直奔主题告诉王建国,他父亲失踪了。她跟建国说: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这把王建国吓了一跳。
随后他就一直心神不宁,草草结束了会议以后,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准备回家。
事实上,早早回家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意义,妻子回娘家了,女儿在外地上大学,家里就剩下他一人,回家又能做什么呢?只不過,在现在这种焦虑的状态下,待在单位也无非是干耗着。
独自静坐在书房里,王建国想起自己已经有很多年没回老家了,他掐着手指算来算去,不是十年就是十一年。他总是在电话里回应说忙忙忙,不是说自己工作忙,就是说孩子学习忙,然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都是借来一用的。真实情况是,他跟家里闹了一点小矛盾。刚一开始,他憋着一口气坚决不回去,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文化人,明着跟家里闹翻是不可能的,他只是用这种方式宣泄内心深处无言的反抗。然而时间一长,他的想法就变了,他觉得也没有必要回家了,家里还有哥哥姐姐,他回不回去意义不大。他是无关紧要的人。不过逢年过节他总是往家里寄一些日常用品,从酒水、糕点到服装、家电。另外,他每年还往家里汇几万块钱。他想,只要往家里汇了钱,他也就算尽到义务了,还非要回去干什么呢?现在他对老家没什么特别怀念的,在他心目中,老家已经不是以前的老家了,他再也不想回去。回想自己心路历程的变化,从最初因为闹别扭拒绝回家,到后来变成习惯不想回家,王建国算了算,前后只用了十年或者十一年。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王建国记得以前他是经常想家的,每逢长一点的节假日他就想往老家跑,每到年底他总想着回老家去过年,以前他对家乡充满了怀念。但是自从年龄过了四十以后,他对家乡的怀念戛然而止。人到中年想法出现了变化,就像突然长大的孩子脱离了对母亲的依恋,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想家了。
也并非一直都是无动于衷的,他也曾反思过,在一些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也曾想起过,应该回去看看。特别是从前年开始,前年他接连不断地接到母亲和哥哥姐姐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他,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他一下子懵了,整个人都不好了。在经过短暂的思维休克后,理性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他在电话里一一安慰他们,先安慰母亲,然后安慰姐姐和哥哥,他以一个权威者的姿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以缓解他们内心的焦虑,他说人老了生病是正常的,他说人就跟机器一样,年辰长了身上的各种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病症,他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父亲得那种病也是正常的。一阵心理按摩之后,他没忘记给出自己的建议,关键在于静养,他嘱咐他们在家多费点儿心,多当心留意着一点儿。最后他说,会在适当的时候回去看看。然而,当他心中的焦虑期一过,拖延的毛病又翻过身来占据了主导,一直拖延到现在,他一次也没回去。
究竟是什么原因淡漠了自己曾经对回家的无比热爱呢?独处的时候,他也曾经仔细琢磨过这个问题。他想,也许是因为老家曾经给他留下过魂牵梦绕过于美好的印象,所以他以前喜欢回家;而现在他不喜欢回家,也许是因为过去的每一次回家都令他失望。以前他每次回家,都在寻找某些曾经美好的印象,然而每次都是失望而归,他再也找不到与他脑海深处的记忆相匹配的那些美好的场景了,这让他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最后他得出结论,老家已经不是以前的老家了,那些曾经美好的印象已经随风远逝了。
至于究竟有什么美好的印象,他也说不上来,如果非要让他在记忆的废墟中仔细搜寻,他想,也许是阳光。他记得以前的阳光是纯粹的,尽管现在的阳光也不错,但是小时候的阳光要比现在的更美好十分。
在艳阳高照的日子里,王建国喜欢凝视窗外的阳光。阳光灿烂明媚,但他总是摇摇头,好像是在说,阳光没有以前的好了。他总是感觉以前的阳光比现在的美好,具体好在哪里,他也说不清楚。就跟现在有很多人觉得以前的鸡蛋比现在的鸡蛋更好一样,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感觉就是不一样,阳光亦是如此,珍藏在王建国心底的那一抹遥远的阳光是最美好的。有时候他想,那时候的阳光照在干燥的土地上像是撒满了黄金,那时候阳光的美好是可以触摸到的,不像现在,看起来再灿烂的阳光也只是一种无法触摸的虚无。
然而就在上个月,他的心理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上个月他刚满48周岁,在大学念书的女儿特意坐飞机回来给他过生日,订了很大的蛋糕。他喝了点酒,感到很幸福,就在这天晚上,他忽然发现自己还不知道父母的生日,这让他心里倍感愧疚。生日那天的酒后回忆让他深有感触,他想,是应该回家看看了。而今天母亲的来电又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感觉,他在心里嘀咕,是应该回去看看了。父亲已经老了。他心里想得更多的还是父亲,很久以前的温馨画面再次涌向眼前。
王建国每次对老家的回忆最终总会收敛到对父亲的回忆里。父亲是小学校长,在别人眼里是一个严肃郑重、冷若冰霜、令人畏惧的人。但是在王建国的记忆里,父亲也有温柔的一面。在他的记忆深处,珍藏着父亲少有的温柔时刻,当其他记忆全被遗忘消失殆尽时,这一抹记忆还在他的脑海深处永存。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至于他常常会想起。王建国记得那时自己还没上学,他后来一直想弄清自己那时的年龄,他想也许是四五岁,也许是六七岁,直到最后他发现纠结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时间不能倒回,他注定是永远也无法弄清了,他唯一清楚的是那时自己还很小,有关那天发生的事也许是他能记起的最早的事情,所以整体的记忆是遥远而又模糊的,只有一些片段还算清晰。
他记得那天阳光明媚,父亲带他去远方的一所学校拜访朋友。学校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一路都是山路,父亲一路步行,他骑在父亲的肩上,看到一条干白的土路曲折蜿蜒,向前无限延伸,没有尽头,身旁的树木在不停地往后倒退。他们走过了一片又一片稻田,走过了一块连着一块的玉米地和红薯地,穿过了大片大片的树林,还翻越了一座高山。一路上他听到小鸟在树上鸣唱,微风在耳边吹拂,空气里漂浮着花草的芬芳和木叶的清香。他记得有那么一个时刻,当他们穿过一片玉米地时,他还和父亲面面相对蹲在路边的玉米地里拉了一泡屎。每次想到这里,王建国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对于这一幕镜头,他记得格外清晰。
他还记得他们在去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谷场。谷场在山腰上,有几个大人在谷场上干活,孩子们在谷场上玩跳房子的游戏。跳房子游戏那时风靡全国,几乎所有地方的小孩都在玩。也许是遇到了熟人,也许是要向人打听什么,但也许仅仅是因为走得太累了,想要休息一下,他記得父亲走向那个谷场,把他从肩上放下来。父亲走过去跟谷场上的大人们说话,而他则加入了那群孩子,玩起了跳房子的游戏。他玩得很开心,及至后来父亲要走时,他正玩在兴头上,不愿意离开。父亲急着要赶路,而他则很委屈地哭起来。后来父亲向他承诺,等回来时一定让他和那些孩子们继续玩,玩个够。
等到下午回来再路过那个谷场时,孩子们都不见了踪影,场上空无一人。王建国幼小的心灵顿时受到了伤害,嘴巴一瘪,忍不住又哭了。父亲只好哄他,没人陪你玩,我陪你玩。王建国后来一回忆起那天下午的情景,就觉得不可思议,就在那个遥远的下午,父亲带着幼小的他,在那个离家很远的大山深处一个平整开阔的谷场上,玩起了跳房子的游戏。他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金色的阳光洒满了谷场,他和父亲跳了一回又一回,当太阳下山天边挂满彩霞时,他还不愿意走,一直玩到暮色四垂,他们才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还记得,当他们走到半路时周围一片漆黑,父亲向路过的一户人家借了手电筒。他一直骑在父亲的脖子上,父亲一手扶着他,一手打着手电筒行走在夜间的山路上。后来他在父亲的脖子上睡着了,他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回到家的。
在后来回忆时,王建国记得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骑在父亲的肩上,搂着父亲的脖子,所以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个脖子,脖子强壮有力,上面有三颗黑痣。从王建国幼小的心里开始一直到后来,他总是觉得父亲强壮无比,也许跟那个脖子不无关联,用他当时那双幼小的眼睛来看,父亲的那个脖子堪比老虎或者雄狮的脖子,因此他始终觉得父亲就像一头老虎或者雄狮那样强壮无敌无所不能。及至后来,在他心目中他依然认为父亲总是能搞定一切,而且永不衰老。直到三年前,当他接到电话得知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时,他才蓦然醒悟,原来父亲也会苍老。而在上月自己的生日聚会上,当他面对水房里的镜子观察自己花白的头发时,他的醒悟又更进了一层,连自己都老了,更何况比自己还大三十多岁的父亲呢。今天母亲的来电让他感到格外焦虑,也许比他三年前刚听到父亲患病时的那一刻更加担心。他心里明白,若非情势紧急,母亲也不会特意给他打电话的。
父亲究竟去哪儿了呢?他现在在哪里呢?王建国独自一人思考着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他在不知不觉间睡着了。
在那短暂的睡眠期间,他做了一个梦。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站在一个空旷围场的中央,微风吹来花草的芳香,流莺在场边的树荫里鸣唱,白云在湛蓝的天空里飘荡,火红的太阳挂在天上,地上洒满了金色的阳光,他忍不住大声欢呼,这就跟梦境一样。然后他醒了,原来果真是一场梦,他感到有点失望。
王建国懂得梦由心生的道理,所以他明白,梦见的也许正是他经常回忆的地方。梦境非常清晰,把那遥远的记忆一下子就拉近到了眼前。只是那个地方的名字,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以前他是知道那个地方的名字的,他记得自己曾经在一张报纸上用毛笔写过那个地名,是两个字,但是现在,他绞尽脑汁却一无所获。
王建国后来打开电脑或许跟那个梦境有关,也许是梦境让他兴奋得难以入眠,也许是梦境唤醒了他对回家的渴望。他打开电脑后开始查看航班信息,刚好看到有一个早晨的航班,时间和价钱都从未有过的那么合适,他当即就订了一张票。之后他干脆觉也不睡了,忙着收拾物品,放进一个双肩包里。要带的物品并不多,反正他也不准备在老家多待,他估计也就待个两三天然后就回来。
天亮之后,王建国乘坐一辆出租车直奔机场。飞机准时把他运到省城,长途车把他送到县城,随后他就坐上一辆揽活的私家车。一路上他都在想,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可是,他一直想不起来,这让他感到浑身很不舒服,如鲠在喉。他越是想不起来,就越是老往那上面想,并非是他刻意要去想,实际上是不由自主的,这是他的一种习惯。王建国觉得自己钻进了牛角尖里,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一路上,司机师傅总是无话找话,想要跟他聊聊天,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脑子里却还在绞尽脑汁、冥思苦想。
突然,他眼前一亮,想起来了,虎涧!那个地方的名字叫虎涧!
虎涧,你知道吗?一想起这个名字后王建国感到浑身舒坦,他情不自禁地问司机师傅,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叫虎涧的地方?
我当然知道,司机说,虎涧林场嘛,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在哪里?王建国又问。
还有五六公里吧,司机说,大约往前五六公里有一条岔路,从那里右转,再开个七八公里就到了,一路往上,在大山里头,以前车不通,只能步行,现在好了,公路通了。
王建国一直听着,没有说话,若有所思。
你想去吗?司机见王建国一直没反应,就无话找话地问他,他说,虎涧林场是值得一游的,经常有县城的人去那里爬山。
那就在前方右转吧,王建国说。他的回答几乎没有犹豫。
汽车后来驶离了正道,向右驶上了一条狭窄陡峭曲折颠簸的山路。一路都是上坡,两边长满了茅草,里边是悬崖,外边是山涧,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被阳光晒得泛白的土路,只能容一辆车通过。偶尔有摩托车从上边迎面驶下来,骑车的人只好把摩托车歪向道路里边贴在岩壁上,才能让汽车缓缓通过。
汽车沿着山路转来转去,往上开了挺长的一段路,直到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掩映在竹林之中,细看大约有十几户人家。司机跟王建国说,只能到这里了,往前的路车不能开了,只能步行,你自己走上去吧,已经不远了。
王建国付了车费,背上双肩包下了车,接着往前走。
沿途他看到了几块荒芜的梯田,枯黑腐烂的稻茬显示出它们已经被遗忘良久。他还看到了几处覆盖着青瓦或者茅草的土房子,那些破旧的门窗、生锈的铁锁和泛白的春联都显示出,它们早已被主人抛弃无人居住了。往前看是巍峨的高山和一望无际的林海。脚下的路越走越窄,因为平时行人稀少,茅草都长到了路中间。就是这一条狭窄的被阳光晒得干燥泛白的山路,它像一条曲折的羊肠蜿蜒向前,一直通向远处巍峨的高山林海。一阵风吹来,送来了多种山间木叶芳草混合在一起的芬芳,王建国顿时感到神清气爽,遥远而又模糊的记忆沉渣从脑海深处徐徐泛起,让他觉得这眼前的一切似曾相识。他想,前方也许应该有一个平场。
然后他转过那个山嘴,当一片空旷的平场突然出现在他眼前时,他既感到有些惊讶,又觉得理所当然,一切似乎都落在他的意料之中。
在大山里能有这么一大块平整空旷的场地,更显得难能可贵,王建国猜测那是用来处理从山上运下来的毛竹和木材的,堆放在场边的毛竹和杉树也许正好给他的猜测提供了证据。向前方的大山望去,这时能看得更清楚了,大片大片的毛竹林、杉树林和板栗林汇成了绿色的海洋。毫无疑问,王建国在心里确信,眼前那些一眼望不到边的林海,肯定就是虎涧林场了。
在平场的边缘,有一位老人坐在石凳上,眼神呆呆地盯着前方,他的表情看起来僵硬麻木,他好像已经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他好像正在等待谁的到来。当他看到一个背着双肩包的身影,从山嘴那里慢慢出现,走在通向平场的小路上时,他的眼睛突然一亮。
你是三娃子吗?老人离得很远就迫不及待地向来人问道。
王建国没有说话,但他点了点头。
我们快来跳房子吧!我等了你很久了。
老人说话时像个孩童,抑制不住的兴奋和喜悦洋溢在他的脸上。
看着场地上用粉笔画的很整齐的房子,王建国就好像是跟老人约好了要来玩游戏似的,他急匆匆地卸下背包放在场边的石凳上,脱下西装挂在场边的树杈上,然后,他和老人玩起了跳房子的游戏。过了这么多年,游戏的规则他早已遗忘,但是没关系,老人极具耐心,一遍一遍地教他。
金色的阳光照耀着脚下平整的土地,看起来就像是撒满了黄金,那种美好近在眼前,触手可及。不远处的山腰上,有两三座白墙黑瓦的房子也沉浸在这无边无垠的阳光里,门是关着的,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住人。王建国想,那些房子也许已经被人抛弃了,也许里面还住着林场的守林人。
他们玩了一局又一局,身上流出了很多汗水。王建国贴身的衬衣早已被汗水浸透,脸上挂满了汗珠。时间过得真快,他们似乎玩了很久,但实际上又好像并没玩到几局。眼看夕阳亲吻着远方的山冈,王建国站在场边点燃了一根香烟,他记得他刚踏进这个场地时,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偏西的天空里。
王建国转过头时,刚好看到有一座房子的门开了,有一个中年人从屋里走出来站在门口。王建国看见了那人,那人也看见了王建国。两个人隔着老远互相望着对方,彼此都表现出了应有的惊讶。
是王建国率先打破了这种僵持的局面的,他一边迈步向那个站在门口的中年人走近,一边从兜里掏出香烟,向他做出了一个递烟的姿势。那人立即作出了回应,他迈开步伐,向王建国走来,伸手接了王建国递过去的香烟,嘴里问道,你是到林场来爬山的吗?对于这个问题,王建国不知如何回答,他很僵硬地点了点头。那人又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王建国随口回答说,从县城来的。
你走了那么远的路,肯定口渴了,进屋来喝口水吧。
不了不了,王建国连忙婉拒,他说,我不渴,谢谢!
那人返身走进屋里,不一会儿又出来了,一手提着一把老式的提梁壶,一手攥着三个茶碗。他走过来,把茶碗摆在场边的石凳上,倒了三杯茶。王建国连忙道谢。站在一旁的那位老人嘴里哆嗦着,也不停地说着谢谢。
这位老爷子,那人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向王建国解释说,他这里有毛病。他在这里呆了好几天了,他见到每一个人都问人是不是三娃子,要不要跟他一起玩跳房子的游戏。
他晚上是怎么过的?王建国问道
第一天晚上他住在我的柴房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柴房里有响动,我以为是什么野物闯进来了,拿手电筒一照,把我吓了一跳。随后的晚上,我都让他睡在我们的空房里,现在这里空房子多,都没人住了,人都搬走了,我在一张旧床上给他铺了一床破被褥,他一到晚上就睡在那张我为他特别安排的床上。
看到王建国对有关老人的话题兴趣盎然,那个中年人便不厌其烦地跟他详细叙述着老人的情况。
这老爷子,他接着说道,你可别看他现在有毛病,但是看起来很有气质的样子,以前也许是一位知识分子呢。而且他的精神好像是忽好忽壞的样子,有时候说的话你都分辨不出来他是有病还是没病,就比如说昨天晚上吧,我问他,你家在哪儿?要不要我送你回去?或者带信让你家里人来接你?他先是说他不记得了,后来他又说,他说——
说到这里那个中年人停顿了一下,他用手指搔着脸庞仔细地想了想,然后接着说道,他说他害怕有那么一天,他真的永远地走丢了,或者他死了,他的家人会太过伤心,所以他要提前预演一下。你听听,能说出这话的人,脑子像是有病吗?这像是脑子有病的人说的话吗?
那个中年人絮絮叨叨地说着,没有注意到王建国的反应。当他终于转过头来望向王建国时,他看到王建国呆呆地盯着天边的夕阳;他看到夕阳正在慢慢沉下山冈,余晖映红了半边天空;他看到泪水从王建国的眼角涌出,顺着脸颊慢慢地滑落,有一串泪珠在夕阳光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眼前的情景让他倍感惊讶,他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让他难以明白的是,他随口说出的几句话竟然让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潸然泪下。
【作者简介】李加福,男,安徽舒城人,现居北京。文学爱好者,作品散见于《鸭绿江》 《牡丹》 《中国铁路文艺》 《北方作家》 《爱你·教师文学》 《金田》 《三角洲》 《黄河三峡文艺》《核桃源》《大鹏文学》等文学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