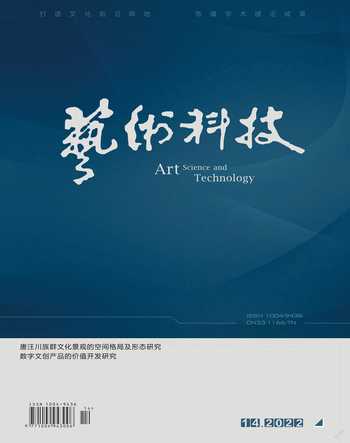运河线路中的清代戏曲业态流变
倪应丹 顾梓莹
摘要:中国戏曲的水路传播阐释了运河的文化意义。水路班“跑码头”的演出组织形式与“流动台”等运河戏曲舞台景观,呈现出戏曲传播受运河影响的特性。而运河文化的流动性也间接地推动新的声腔与表演风格的产生,形成了戏曲艺术的水文化特征。运河文化与戏曲艺术共同具备作为俗文化的包容性与市民性,充分体现运河线路对戏曲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线路;清代运河;戏曲业态;水路传播
中图分类号:J8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4-00-03
人类社会在跨区域与跨文化联通的过程中,形成了线路概念,即文化线路的形成过程是不同人群和不同文化基于道路的连接和流动,在空间上进行持续对话的过程[1]。作为水上道路的京杭大运河,不仅自身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景观,沿线戏曲业态流变过程也是其作为交通线路的价值所在。大运河不仅构成了盐业的漕运之路,而且其沿线城镇也为诸多剧种的形成发展、创作演出、交流演进等活动创造了条件。具有道路意义的中国戏曲传播的“商路即戏路”“水路即戏路”之说,凸显于盐商迎接乾隆南巡的戏曲活动中,而这也是“海派京剧”形成的动力,并不断推动中国戏曲艺术走向近代化。
1 运河影响戏曲“水路”业态形式
根据泰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的“时代、种族与环境”艺术发展论,运河沿线的地理环境必然衍生戏班“以船代车”“以船代步”等环境戏剧的活动方式。同时,运河沿岸人口密集、土地肥沃,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催生了独特的运河风土人情,这是运河对戏曲业态产生直接影响的社会条件。曹娅丽和霍艳杰提出,“大运河江苏段戏剧遗产,是维系运河沿线民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审美心理、民间信仰和民族情感的纽带,自古以来与民众的生存环境,包括生理特性、生活习性、生产方式、生养制度、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体现了戏剧遗产‘生生不息和‘天人合一的生态特性”[2]。作为古代经贸大动脉的大运河,对戏曲业态有着直接影响,而沿线城镇便成为戏曲活动与各戏曲流派交流的聚集地。
为了谋生,古代戏班常常坐船在运河沿岸的各城镇巡回表演,呈现极具特色的运河戏曲文化业态。据蒋柏连《京剧水路班的生存形态和当代启示》记载,每个戏班的人数都不固定,从一二十名到八九十名不等[3]。奔波于运河沿岸各码头之间的戏班流动演出活动被称为“跑码头”。由于这些戏班把行李和行头都放置在乌篷船上,以其作为外出表演的交通工具,因此也被称为“水路班”。丰子恺回忆童年时就提到,在乡间有一种被称为“江湖班”的戏班子,他们居无定所,演员们坐在船上在各个码头或村庄演出,他们的行头远不及城镇戏馆的精致,带的都是旧衣和旧背景,有些甚至没有背景,但是这些戏班子能让更多平民百姓欣赏到戏曲[4]。清代的戏剧文化下乡,不仅为花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也应和了戏曲艺术的通俗化风格。
水路班通常在乡下演出,所搭建的临时性舞台统称为草台,但受地理环境影响,他们的演出形式各具特色,草台类型也多种多样,其中里河东路的京徽班社自备的随班迁移的流动舞台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也被称为“行台”。运河本身具有自然景观性质,而戏曲需要以舞台为媒介展现其景观性,水路班的流动台便呈现出当运河与戏曲产生交集时的独特地域景观特性。
据学者严以健在《里下河草台及草台艺术琐谈》中的記载,这种舞台的安装和拆卸都很方便,一场表演结束后,台架和台板等就会通过船运输到下一处重新搭建[5]。除此之外,也有的戏班直接将舞台建在船上,人们称之为“船台”,观众在岸上或者游船到船台附近赏戏。这些独具特色的戏曲舞台形式的出现,与运河沿岸地理环境与人文气息所产生的地域文化氛围紧密相关,也与运河沿岸独特的戏曲活动方式相呼应。
2 运河传播促进戏曲“线路”形成
在“路学”理论中,道路延伸过程中的人口、物资、信息等要素的流动会在沿线产生新的社会空间。运河两岸的经济繁荣使戏曲以戏班巡演、演员流动、剧作家迁移等相互交流的方式实现充分发展,由此呈现开放性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戏曲艺术才能够做到跨区域发展。关汉卿、白朴等大量杂剧作家和演员沿运河南下,马致远等原本来自北方的剧作家开始创作南戏剧本也离不开运河对作家视野的开拓之功。同时,以杭州为中心的南方剧作家们尝试推动杂剧向南戏转型,例如,元代明初的《幽闺记》是以关汉卿的杂剧《王瑞兰闺怨拜月亭》为基础,由杭州剧作家施惠改编而成,将原本的四折扩充为四十出,被列为“四大南戏”之一。与元杂剧南移相对应的,明代昆曲逐渐北上。万历时期,昆曲甚至在北京的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昆曲传入北方后,由于受北方的风俗人情和审美情趣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豪放、刚劲的风格,故名“北昆”,而源于江南的风格柔和典雅的昆曲则被称作“南昆”。
位于江苏省长江以北、运河以东的里下河区域是戏曲表现为水路传播的集中地之一。清代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盐场众多,盐业发达,漕运兴盛,而盐商主要来自安徽,他们蓄养家班(即徽班),不仅方便自己听曲娱乐,也能用来社交应酬。乾隆年间,弘历六度南巡,扬州富商为了迎接圣驾,从各地调集戏班到扬州。在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徽班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学者邓小秋由此提出,里下河徽班的正式形成是在乾隆年间[6]。扬州盐商的戏曲活动推动了戏曲发展,诠释了戏曲“商路传播”的命题。除此以外,地域广阔的乡村集镇本就是戏班活跃的重要场所,咸丰至同治年间,里下河徽班广泛流动于苏中与苏北各地城乡,其演出的剧目因受众广泛而被称为“大戏”。与雅致的昆曲相比,在农村发展的里下河徽班更为通俗易懂、贴近民众。
太平天国运动促使里下河徽班成为推动“海派京剧”发展的动力。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扬州成为战场,遭到严重破坏,导致长期在此地演出的部分戏班向偏僻的运河东部的里下河各县转移。但是,由于后期苏北地区水患频发,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戏曲班社举步维艰,所以部分里下河徽班的优秀演员又选择南下进入上海。其实,里下河地区与上海及江南的大、中城市之间仅隔着一条长江,因而自清末民初以来,大江南北的戏曲演员就来往频繁、交往密切。在天灾人祸的影响下,里下河徽班入沪已是必然趋势。
有学者曾考察总结,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江苏的戏曲演员一部分选择逃到北京生存,另一部分则沿着运河向南,通过苏州吴江的甪直镇走水路到上海逃灾避难[7]。里下河地区的戏班来到上海后,他们在演出剧目和演出风格上采取广泛吸取策略,“兼容并包江南各地不同性质的唱腔乐曲和表演方法,唱腔不拘一格,剧目丰富多彩、文辞通俗易懂,尤其以真刀真枪的武戏见长”[8],深受上海观众欢迎,为上海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上海的里下河徽班引起“自徽班登场而文班减色”的局面,逐步颠覆昆曲主导的形势。由此可见,昆曲在上海式微的同时,里下河戏曲的综合性与上海海派文化的开放性相通,因此,其表演形式更迎合上海市民的欣赏习惯。里下河徽班在同治、道光以后,与北京京剧同台演出,经过“皮、梆合演”“京徽合演”,最终与京剧、直隶梆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京剧”,也称“外江派”或“南派”。与之相对应,北京的京剧被称为“京派”。
3 运河文化内涵诠释戏曲艺术特性
水上戏台能够营造戏曲观赏意境,正如《印象·刘三姐》的成功演出离不开桂林山水的自然舞台,即方圆两公里的漓江水域、十二座山峰和广袤的天宇形成的壮观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吴文化是水文化,水的浸润是江南物质和精神文化产生的条件。江南河沿线地区山明水秀、降水充沛,是昆曲演唱中最著名的“水磨腔”的诞生地。水也是戏曲表演的舞台元素之一,例如,没有运用任何扩音设备的北京恭王府戏楼之所以能使台下任何位置都能清晰听到台上表演的声音,是因为园林布局的巧妙设计。学者刘菁菁在《苏州园林与昆曲舞台的现代情感体验》中提出,恭王府戏楼的设计者利用戏台下九个装满水的大缸来代替音响,实现收音和共振的功能。只凭借水的扩音,就能让观众席的每个角落都能清楚听到台上的声音[9]。
在江南的水上戏台,观众与舞台之间有一面数米宽的水域,这也是一段审美距离,使观众在澄明心境中欣赏戏曲的婉转唱腔。江苏镇江西津渡的尚清戏台就是这样设置的,戏台被一片池塘三面环绕,每次有戏曲表演时,两旁的工作人员会使用干冰打造烟雾漫漫的朦胧美感,既可以在戏曲演出过程中起到切换场景的作用,又能够在审美体验上拉远观众与戏台的距离。江南戏曲追求悲、欢、离、合归于团圆的中和之美和劝人向善的教化倡导,也与传统水文化背景相关,如出自《老子》第八章的“上善若水”。由此,覃佳认为先秦时期以水作为譬喻的哲学思想与劝人向善、追求和谐的古典戏剧审美观念不谋而合[10]。可见,运河的水文化赋予江南戏曲独有的文化内涵。
族群交往与人口流动构成了文化线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永恒主题,“持续社会流动的本质是以道路为流动途径,开辟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范围,以获取更广阔栖居空间的过程”[11]。大运河作为连接南北的黄金通道,沿岸城市要发展经济,必须对外开放,敢于打破旧俗。扬州既是运河沿线城市,又是中外商人、学者、僧侣的集散地。唐代扬州大明寺的僧人鉴真曾六次东渡日本,这是大运河文化包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运河与海洋紧密相连,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国的本土产品通过运河运输到港口,从海外引进的玻璃、呢绒、洋钟等洋货,则通过运河到达东南沿海各港口,使运河沿岸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发生很大改变。在这样长期的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中,元末北杂剧中心南移、北方剧作家南迁,明代昆腔与清代徽班北上等戏曲活动形成了建立在不同戏曲种类互相融合基础上的综合性特征。
由于运河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运河节点城镇与沿线区域的普通民众,且戏曲的观众主体是平民百姓,因此,运河文化的市民性是通俗性的戏曲艺术得以沿运河传播的内在动因。宋以后的运河沿岸城市成为新的商业中心,随之兴起的市民阶层对文学形态有了新的需求,如《金瓶梅》《水浒传》的作者都生长在运河沿岸。除此之外,明清盐商对里下河戏曲的繁荣也起着推动作用。江南运河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明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背景下,推动了戏曲艺术“俗”文化风格的形成。
百戏兴旺,杂剧崛起,南戏昌盛,花雅争鸣,诸多戏曲门类与艺术风格的“螺旋式”发展之路诠释了中国戏曲发展过程中“雅”“俗”观念的变迁,帝王和权贵对戏曲的偏爱与扶持曾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某种戏曲种类的发展,但戏曲一旦进入以宫廷或文人为中心的上层社会就必然走向衰微。以昆曲的兴衰为例,早期昆曲因表现民众抗暴斗争的精神而深受百姓喜爱,但是当它被宫廷贵族尊为雅部并逐渐失去民间色彩时,就开始被花部取代。因此,戏曲艺术与运河文化都以贴近民众而著称,作为俗文化都具有市民文化共性。
4 结语
运河不仅为徽商的盐业商贸活动创造了条件,也为戏曲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丝绸之路成就敦煌文化一样,运河之路也是中国戏曲发展之路。今天,运河疏浚后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挖掘运河文化传统与戏曲景观特性,在二者各美其美的基础上实现美美与共,进而在物質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传统溯源及创造性转化中,实现优秀民族文化的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 方伟洁,袁英蕾,杜菲菲.文化线路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南方丝绸之路云南永昌段为例[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8,27(1):74-80.
[2] 曹娅丽,霍艳杰.生生遗续:大运河江苏段戏剧遗产生态人类学考察[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2):104-110.
[3] 蒋柏连.京剧水路班的生存形态和当代启示[J].艺术百家,1990(3):37-40.
[4] 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5.
[5] 严以健.里下河草台及草台艺术琐谈[J].艺术百家,1992(3):87-93.
[6] 邓小秋.里下河徽班发展始末试探[J].艺术百家,1992(3):71-77.
[7] 王珏.论京杭大运河江苏流域戏曲的发生与发展[J].艺术百家,2018,34(6):96-100,145.
[8] 吕承焕.京剧南来前后上海徽班演出活动考略[J].上海戏剧,2007(10):39-41.
[9] 刘菁菁.苏州园林与昆曲舞台的现代情感体验[J].四川戏剧,2013(6):62-64,71.
[10] 覃佳.浅析中国古典戏剧审美理想的水文化意蕴[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6(2):68-72.
[11] 方伟洁,高源.路学视野下文化线路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0(1):42-52.
作者简介:倪应丹(1997—),女,江苏无锡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戏曲史。
顾梓莹(1997—),女,江苏泰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