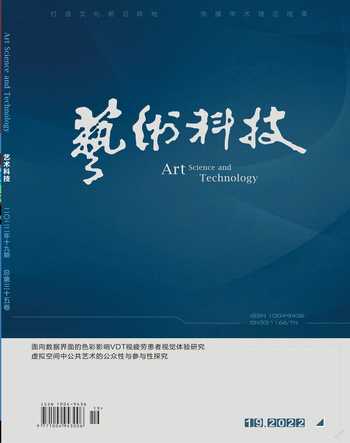先秦与古希腊音乐美学思想考辨
摘要: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社会性特征明显,表现为以礼为准绳,礼乐结合,乐从礼出。与先秦音乐美学思想不同,古希腊音乐美学思想带有较多的理性因素,哲学家们更多以形式结构为切入点,探寻音乐的内在规律。虽大体相异,但这两个时期的音乐美学观在对音乐起源、音乐审美准则及音乐功能的论究上具有明显的共性。“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文章通过研究以上美学问题,于回归传统中总结出音乐艺术的一般价值,并为现代音乐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先秦时期;古希腊时期;音乐美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9-0-03
1 音乐的起源——唯物主义模仿论
据《国语》《左传》等相关史料记载,我国音乐美学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初至公元前6世纪末。比之西方,虽跨越约200年,但音乐源于模仿的观点两者兼而有之。如“昔黄帝令伶伦作五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组考”“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1],这些古籍记载均表明先秦时期已出现音乐模仿观。
古希腊社会的音乐模仿学说已成为一种传统。德谟克利特认为,音乐产生于人对动物声音的模仿,“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的小学生的……从天鹅和黄莺等唱歌的鸟学会唱歌”[2],这与先秦时期的模仿论极为相似。
亚里士多德对艺术模仿论的阐述更为全面。他站在实践的角度看待该问题,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得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3]。此处需要说明,古希腊时期的音乐,与先秦时期“诗、舞、乐”三位一体的音乐概念相比,范围更加宽泛,涵盖了史诗、悲剧、喜剧、颂歌、器乐、舞蹈等众多艺术形式。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悲喜剧、颂歌采用节奏、语言、音调来模仿,双管箫乐、竖琴乐、排箫乐等具有同样功能的艺术则通过节奏和音调来模仿,舞蹈者则只需用节奏来模仿各种性格、感受或行动。由此来看,他已注意到不同体裁之间模仿的特殊性问题。此外,这种模仿并非机械的复制,而是在现实基础上注入创造性思维,使之“理想化”,达到优于现实,继而实现其教育和审美功能的最终目的。而对于艺术模仿的主要对象,亚里士多德则从客观自然物转向人本身,转向人的行动、生活、幸福,注意到了艺术与人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2 音乐的审美准则
2.1 寓杂多于统一的审美理念
在音乐领域,寓杂多于统一的美学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史伯的“和同说”,他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4],“以他平他”才能产生和谐,而“以同裨同”只能单纯引起数量的变化,这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另外,这种“寓杂”并非杂乱无序,而是有主次之分的统一体。聚焦到音乐问题上,史伯提倡“声一无听”“和六律聪耳”,即认为动听的音乐要由六律内的众多乐音构成。值得思考的是,在《国语·郑语》中,他又肯定了“和乐如一”。其实,这与“声一无听”的基本内涵并不矛盾,因为这种“一”已具有了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含义。之后,晏婴进一步发展了史伯的“和同”论,提出了不同事物之间相反相济的辩证思想。此外,在音乐“美”问题上,他既考虑到了音乐客体的节奏、旋律、体裁、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也注意到了作为审美主体——人的感情。而与史伯、晏婴相比,伶州鸠“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的命题更为深刻。在他看来,“平和”的音乐中所蕴含的是“至和”,而这种和谐更是一国之政应该效仿的关键内容。
寻找并发现和谐是古希腊哲学家们的审美追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万物的和谐见于一定数量的比例关系,他们通过对音程数量的比例关系的研究,提出了“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5]的认知观点,认为音乐的美来源于不同快慢、长短、强弱声音的对立统一。德谟克利特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基本一致,同样认为音乐的和谐源自对立面的斗争统一。不同的是,德谟克里特是从具体的感官知觉当中亲身体验,而并非从固定不变的尺度规范中得出的结论。
关于美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以事物本身为切入点提出“美在整一”的概念。他认为美的主要形式包括秩序(时间)、匀称(空间)、明确,“明确”通过秩序和匀称表现出来,这三种形式只能见于有机的整体当中。完整体所属的各部分内容密不可分,不能够随意删除或移动,否则就会拆散整体,这说明所谓的有机整体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对接到悲剧情节的设置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必须以“头”为始,以符合可然律与必然律的“尾”为结局,“身”则安排在两者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事物的美与体积大小也有直接关联,整体及各部分要符合人的感受阈限,过大、过小都不能称为美。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论世界》当中引用了德谟克利特关于“寓杂多于整一”的相关论述,并作出了自身对该问题“由一产生一切,由一切产生一”的辩證思考。
2.2 “乐以安民”的审美原则——以孔子、柏拉图二人为例
先秦时期,音乐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持一国稳定,从这点上来看“修礼以节之”,使乐成为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音”似乎成了必然。孔子之前的音乐审美观念已极为丰富,出现了众多美学范畴,如“和”与“同”、“中”与“淫”、“音”与“心”等,而这些范畴毫无例外都是因为“新声”的逐渐兴起。“新声”或称为“郑卫之音”,即以郑、卫两国为代表的各诸侯国的民间音乐,也包括某些外来音乐。这些音乐不同于雅俗旧乐的雍雍穆穆,不管是在演奏技巧上,还是在音乐风格上,都具有更强的观赏性,而这显然不合于当时的礼制规范。医和云,“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淫生六疾”,认为“淫声”会使人忘记平和,引发疾病。子产言,“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意在表明“淫乐”不利于安民成政,所以要把“新声”排除在国家之外,只保留“大不出均”的中德之音。
孔子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并突出强调仁,实现以仁辅礼。在音乐审美理念上,他将美、善加以明确区分,肯定了美的独立意义。“文质彬彬以质为先,尽善尽美以善为重”是孔子的审美理想,“思无邪”就是在该基础上提出来的。何为无邪?“思无邪”所指实际是就音乐内容而言,而“无邪”与礼同义,目的是要以礼约思,以礼约乐。一方面,个人要在其位,谋其事,所思所想皆要在礼制范围之内。另一方面,音乐情绪的表达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符合中庸之道。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稳民众情绪进而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但就音乐艺术本身来讲,是不利于其进一步发展的。孔子之后,孟子追求的“与民同乐”、老子推崇的“大音”、庄子的“天乐”观念等实则是对“乐以安民”审美原则的一脉相承。
古希腊音乐美学的研究角度更多是从哲学的自然观出发,哲学家们往往重视对音乐形式、内容、内在规律的研究。柏拉图作为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在有关理想国的论述中较多提及了音乐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虽然“理念论”贬低了艺术,但在他的理想国中,文艺尤其是音乐所承担的伦理道德职能极为重要。“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都重要得多,是不是为这些理由?头一层节奏与乐调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美的心灵。”[6]这表明,柏拉图注意到了音乐能影响人的心灵,进而也就肯定了音乐的伦理教育用途。此外,他否认一般人的“快感”,厌恶以满足人们“感伤癖”为目的的悲喜剧、史诗等传统文艺以及摧残理性的诗人,认为这都不符合治国标准,不利于国家的和谐稳定。
柏拉图的理想国度由三个等级组成:第一等级为懂政治的哲学家或懂哲学的政治家(卫国者或执政者),这些人代表着智慧和勇敢;第二等级为军事人员、武士(勇敢无畏、礼智坚定的防御者);第三等级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为国家生产物质财富),这部分人容易被情欲左右,所以最需要节制。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便是正义,而音乐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三个等级服务,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承担所属等级应有的责任,这样的音乐才是“真、善、美”。
3 音乐的功能——“音乐净化论”与“平和”之声
古希腊音乐美学的音乐净化论观点源于音乐情感力量的认同。在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首先肯定了音乐的“净化”功能。该学派认为,音乐是最能体现“数”和谐、秩序的艺术,并将在音乐实践中所得到的和谐比例推至宇宙天体以及人的心灵,当人内在的和谐与音乐外在的和谐彼此感应,就会欣然契合,便能以此影响人的灵魂。除此之外,他们还把音乐风格大体上分为“刚”“柔”两种,认为不同风格的音乐可以对人的性格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这种“净化”观点更多是从生理学的角度论述的,所以毕达哥拉斯也被看作是音乐治疗学的创始者。毕达哥拉斯关于音乐可应用的“症状”是十分丰富的,“用音乐,用某些旋律和节奏可以教育人,用音乐,用某些旋律和节奏治疗人的脾气和情欲,并恢复内心能力的和谐……他显然用这种净化的名称,称呼音乐治疗……有用来医治心中情欲的旋律,有医治忧郁和内心病症的旋律……还有别的:医治愤怒、生气、内心变化的旋律,还有一种歌曲可以治疗人的色欲”[5],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音乐艺术的重视程度。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当中也提到了“净化”一词,这种“净化”不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具有较多的生理意义,而是以获得心理健康为目的。正因如此,罗念生将其释为“陶冶”。对于“净化”与“陶冶”,笔者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意在通过某种途径宣泄或消除负面情绪,而后者更倾向于运用情感磨炼自身的情绪体验以应对现实。区别于柏拉图否定民众“快感”的哲学观,亚里士多德认为,欲望及情感需求是人性中的本能,因而有得到适当满足的权利。以悲剧为例,他认为艺术“净化”的理想功能就是利用由剧情引发的、受理性指导的怜悯和恐惧使人们得到针对性的锻炼,使人们在生活中看到或遭受苦难时生出适当的感情,避免过强过弱。同时,亚里士多德不仅将“净化”思想用于悲剧,还用以解释音乐。他认为音乐有教育、净化、精神享受三种社会作用,不同的作用与不同的乐调相匹配,如“要达到教育目的,就应选用伦理的乐调,但是在集会听旁人演奏时,我们就宜听行动的乐调和激昂的乐调”[2]。此外,亚里士多德也看到了音乐与人性格之间的联系,认为音乐之所以会对性格产生影响,是基于和谐,而这正是音乐和心灵共同拥有的美好品质。
先秦时期,医和、晏婴、单穆公等人较早注意到了作为审美客体存在的音乐与审美主体——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涉及用乐会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论题,这可以视之为我国历史上音乐养生学与音乐治疗学的萌芽。在他们看来,比之“耳所不及”“慆心乱耳”的淫乐,“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的平和之乐更适合修养身心。《左传·昭公元年》载医和言,“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淫声六疾”。可见,医和認为“淫声”会荡心塞耳,使人丧失平和之心,甚至会引发疾病。而平和之乐能使人护持平和的本性,由此得以健康长寿。单穆公曾在劝谏周景王铸钟时论及声心关系,“若视听不和而有震昡,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昡惑之明,有转易之明,有过慝之度”[1]。显然,单穆公认为听之不和会导致“震昡”,散佚元气,进而造成人民悖逆,是非不辨,滋生恶念。反之,平和之声会使人增长元气,人民归心,政事以和。其主要从生理与心理两个方面阐述了音乐对身心健康的陶染。另外,在《尚书》《周礼》等文史典籍当中也有相关论述论及了音乐的教育功能,如“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以乐语教国子”等。而这些思想无一例外都建立在对音乐即中和之音可以塑造心、促进身心和谐的高度认同上。
4 结语
抛开过去的时代局限,先秦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都看到了音乐艺术的重要功能——修身、治国,而这也正是新时代社会发展所需要和提倡的。国家的繁荣富强离不开包括音乐在内的文艺,为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要充分发挥音乐在美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以人民为导向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为人民提供正能量、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1]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45-46,225-238,50-51.
[2] 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43-44,123-124,127-128.
[3] 修海林.古希腊音乐美学思想概述[J].音乐艺术,1990(4):33-41.
[4] 陈静.先秦儒家艺术哲学思想:谈先秦儒家的“对立统一”音乐美学观[J].音乐创作,2014(5):150-151.
[5] 胡冬梅.音乐中的“和”与“德”:论中西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5(1):14-18.
[6] 王小丁.柏拉图的灵感说及影响论[D].西安:西北大学,2010.
作者简介:孙伟(1998—),男,河北保定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音乐史学与文化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