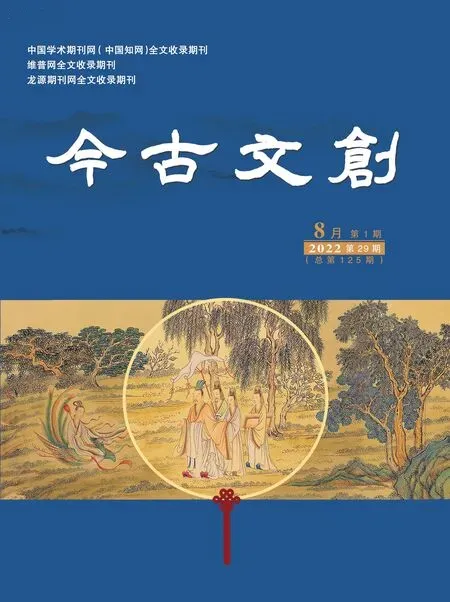从金钱 、 苹果 、 琴声看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人情冷漠
【摘要】 《变形记》以荒诞的故事反映生活真实,揭示了深刻的主题,在作家冷静客观的叙述中,蕴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思。卡夫卡用朴实细腻的语言,反映了人被挤压的生存状态和孤独感,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荒诞世界。本文选取《变形记》故事中三个不同阶段的典型意象——金钱、苹果与琴声,来展现主人公苦闷无奈的心理状态与其家庭这一社会缩影中的人情冷漠。
【关键词】 《变形记》;意象;人情冷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9-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9.005
一、前言
卡夫卡曾在手稿中写道:“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
所谓“一切”,到底有什么?或许可以从卡夫卡所处的社会背景与家庭背景中探得答案。并且这两点,都对《变形记》的成书起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是社会——战争年代,经济萧条、社会腐败,使得卡夫卡长期对于社会有着深深的恐惧,并且在创作时也展现出了极强的不确定性。他笔下大多是一些小人物,在扭曲的社会中看不见未来与出路,深陷迷惘与孤独。物质主义盛行的环境,金钱成为人们一心追逐的全部,每个人都是误入世界的精神漂泊者。
其次是家庭——父亲赫尔曼专横粗暴,使得卡夫卡一直生活在阴影中。而母亲以丈夫为中心的思想也使得她对儿子的爱难以表达。在这样家庭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卡夫卡,终身带着陌生感、异己感与孤独感。在卡夫卡1912年,也就是《变形记》完稿这一年的日记中,他写到自己被父亲责骂工作不够认真、不够上进,“父亲继续骂我,我站在窗边沉默不语。”[1]这一点和小说中格里高尔的际遇十分相像。加之种种高度相似的因素,《变形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作卡夫卡的“精神自传”。
此外,卡夫卡并未为对格里高尔的变形未做出任何解释,这一方面显示出这种境遇的超常性,是不可理喻的;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这一境遇具备某种“现实性”“普遍性”,无须解释。变成甲虫这件荒诞不经的事,格里高尔不会是唯一一个或最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里的所有人都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
人性虫形的格里高尔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是口袋里洗坏了的钱、是篮子里腐烂的苹果、是提琴上断掉的弦,是一切曾经很有用而如今已经失去价值的无用之物。恐惧、冷漠与厌恶被不断投掷,他渐渐变为人类社会的局外人,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和关爱,最终只能躲在沙发下难以见容于世。
《变形记》在引导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一切变得不一样,还是这个世界本就如此?
二、三大典型意象
(一)金钱——亲情淡漠的帷幕
爸爸的早报、妈妈的衣服、最亲爱的妹妹喜欢的小提琴,还有全家居住的大公寓、聘请的女佣……这些都是格里高尔坚持工作甚至生存下来的全部意义。父亲破产后,他“几乎一夜之间就从小伙计变成推销员”,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尽管内心非常诋毁这份“苦差事”,但是还是默默忍受。
在格里高尔变形的早上,当他还以为自己只是头脑不清醒而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只甲虫时,他想到的全部仍是繼续努力工作、还清家中的债务以及将开的火车。实际上他是非常苦于早起的,并且直接地认为这样的事情“真会让人发疯”。然而为了挣钱支撑家庭,格里高尔还是选择牺牲自己的时间、情感与快乐,日复一日地出差、顺应上级、做着不讨好人的工作。
他源源不断地将金钱带回家中,但从未想过金钱是连接他与家人的唯一绳索,这一点可以体现在家人对他的“注意”上。这种“注意”,不似家人之间的饱含爱意的关注,而更像是一种监视。[2]六点四十五时,母亲注意到格里高尔还未出门,但是当格里高尔回应时,她似乎只听到了那一句“我就要起床了”,而全然忽视了他声音里掺杂着的“痛苦的唧唧声”,便“踢踢跶跶走开了”。但是,这番对话使得家人都注意到格里高尔还未出门这一反常现象,父亲的拳头敲打在房门上,妹妹的担忧在侧门外响起。
不过,在他们听到格里高尔的回应,确定他安然无恙并且马上能够去上班后,一切又恢复了平常。是因为他们认为格里高尔仍具备工具性、实用性,马上就要出门为全家赚钱了。
然而,他们平静的心情以经理的到来而被迫结束。不仅家人如此,格里高尔自身也对经理唯命是从。本来无法接受自己变为甲虫的他因为经理的到来而慌乱,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甚至渴求证明自己并非怠工的愿望胜过了思考贸然出门的后果。并且这一渴望竟然能够促使已经变成甲虫的他站立起来、旋转身体打开房门,在笨拙的躯壳里绝望地挣扎。在经理被吓跑时还想着追逐他以使自己不会丢掉工作。此刻经理的心理是恐惧、行为是逃跑,那么家人做何反应?
母亲尖叫着投入父亲的怀抱。而父亲则大力地跺脚,要把格里高尔赶回房间。在格里高尔明白这一讯息、慌张地想要回到房间时,还因“担心浪费时间转身会让父亲不耐烦”,遭到父亲手杖的敲击,不敢转身,倒退着前进。直到他发现自己因难以控制方向而不得不转身时,也是“一边惴惴不安地不断斜眼瞄向父亲,一边伺机尽快掉头”,这足以见得格里高尔平日里对父亲的惧怕。然而,这场返回最终还是以父亲的敲击告终。
家庭应当是庇护之所,而为何此刻的家和公司别无二致?有的只是命令、压榨与漠视。敲击使得他“血流如注”,通过这一触目惊心的画面,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在这样一种突发的、毫无预兆的悲剧发生时,家人的行为更让人心寒与恐惧。
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的确生活在庞大而异己的家庭与社会中,但是没有变成甲虫的他就不是异己的吗?父亲经商失败后已休息五年之久,母亲安分做着家庭主妇,妹妹尚年轻,未从事过任何工作,只有格里高尔在全力为这个家庭奔波着。实际上,不是甲虫的他也早已丧失了正常人的生活,受到家人无形的压榨与损害。并且在家中都已如此,更不用说他在公司中、社会中的情形。
格里高尔沉溺在以往拿钱回家时家人的惊喜之中,那样不曾重现的美好时光,是自我的辉煌与家庭的温情的载体。他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于承担家计,丝毫没有想过父母亲与妹妹其实也有着工作的能力。以至于虫化后,他听到家人谈起赚钱的必要时,仍然会因为“羞愧、伤心而浑身发热”;知道家人拥有一笔他不知道的财产时,会认为“父亲的安排无疑更妥当”。这种情感以及格里高尔与家人之间陌生、对立的关系,更像是一个被控制了的人,早已习惯谦卑退让、委曲求全,毫无自我可言。同时也折射出家人之间微薄的爱意与匮乏的信任,更多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所以到后来,失去赚钱能力的格里高尔,必然成为家庭的累赘,沦落为一只众人都欲摆脱的丑陋甲虫。
(二)苹果——情感异化的纪念
苹果在《变形记》中象征着以父亲为首的情感异化。从苹果砸落开始,家人对他的态度就不单再是厌恶与恐惧,而更多掺杂了憎恨。一直以来,家人能接受格里高尔继续安然地呆在他的房间,怀着愧疚之心在晚餐时为他打开房门,前提都是他听话、安分,而一旦他有做出暴力行为的可能与倾向,就代表着其父子、母子抑或兄妹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立刻不由分说地对其进行袭击。
格里高尔因害怕房间里的画像被取走,自己作为“人”的过往会随之被遗忘,于是在母亲与妹妹清理他的房间时拼命保护墙上的画像。而从沙发底爬出来的他,第一次完整地展现在母亲面前,也由此吓倒了母亲。这一后果随之惹怒了回家后不明所以的父亲,使得他“下定决心要轰炸他(格里高尔)。”
从这一次攻击开始,苹果便代表着一种物质暴力形式,它们的抛出标志着家人情感的转变——变为一种对废弃工具的愤怒,而这一情节也推动故事走向高潮。陷入虫壳里的苹果,深深嵌入格里高尔的生存空间、身体和心灵,代表着空间的狭窄化、身体的残疾与心灵的钝伤。
成为虫形后只能以爬行为乐的他,再也不能灵活行动,“像个伤兵一样,不知得花上多少分钟才能从房间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而趴在天花板上看从未体会过的视角则更不可能,因为身体已经无法再承担“往高处爬”的任务了。格里高尔就因这颗苹果而招致形体破碎、乐趣丧失的命运,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里。
同人等比的甲虫和苹果,一虚一实,共同构建起《变形记》中荒诞的故事,揭露人性丑恶的真相。[3]昨天还是相知的亲人,突然被横插一道隔膜,并且在言语、思想、情感不通的情况下,对格里高尔充满敌意,全然忘记了变形前的他对家庭的辛勤供养,也不曾思考过变形本不是格里高尔的意志与责任。这一“思想改变”的过程其实也是对格里高尔命运做出的“改写”。他已经从家人变为了甲虫,又变为了“害人的怪物”,这是在对他的负面情绪与态度里,一个逐步推进、深化的过程,从无法接受他的变形、到渴望他恢复、再到想要将他清除的过程。
除此以外,“苹果”也像是家庭压在格里高尔身上沉重负担的象征。从一开始,格里高尔辛劳工作就是为了养活家庭,帮父母还债、赡养他们、送妹妹上音乐学院,他用金钱维持着仅有的温情,如一个宿主一般,怀抱着充盈的爱意去满足寄生虫的需求,并且认为这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情。
直到最后他选择死亡,也是因为听了妹妹冷酷的话语后,感受到了家人的冷漠、憎恨和排斥。他“带着满心的感动和爱想起家人,甚至比妹妹更加堅信自己应该消失”。为了不成为家人的负担,在凌晨的钟敲下第三声后,格里高尔呼出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背上那颗腐烂的苹果至死仍在,并且他已经完全习惯它的存在,变得麻木不仁。“苹果和周围蒙着柔软尘土的发炎部位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他就这样带着支撑家庭的压力而死,背着一生承受的艰辛与痛苦而死。
(三)琴声——自我终结者的独白
格里高尔一直为妹妹拉得一手好琴感到骄傲,不单如此,他放任妹妹无所事事的一大原因也是认为“她还要拉小提琴”,工作的目的更是一直包含着这一点。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让他骄傲的琴声、只有他能欣赏的音乐、他一心想要帮助妹妹实现的美梦,会把他推向何方。
当琴声再度响起,格里高尔似乎又能回忆起以往的幸福日子。靠近琴声,是他原有的、作为“人”的正常思维和正常感觉。家中妹妹是与自己最为亲近的人,格里高尔认为她“理应享受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穿得漂漂亮亮,睡到日上三竿,帮忙做点家务事,从事一些花费不大的消遣”。更为重要的是,拥有音乐天赋的她,本应在去年圣诞实现那个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前往音乐学院学习……
格里高尔在妹妹的提琴声中发出了自我疑问:“难道他是只野兽吗?音乐怎会对他如此有魔力?”琴声是他人形时的美好记忆,而习惯了虫体的他,在再次听到这一乐音时,作为人的记忆便被唤醒。
为此他不顾一切地向前爬去,并且感到对自己的莽撞已习以为常。他唯一想要做的,便是去听这场除他以外无人欣赏的演奏,去惊吓三个高傲自大、目中无人的房客,而这样出于保护和爱的心理,却将他引向最终的死亡——房客的恐惧、父亲的愤怒、妹妹的崩溃,刚租出一周的房子被退回……一切的一切,果真像是障碍一般,阻碍格里高尔爬入本该属于他的人类世界。
他只不过想再听一遍那悠扬的琴声,可他没意识到这琴声不再为他而生。他不过是那小提琴上意外断掉的一根琴弦,毁了整首歌曲,也没人想着他以往为那些曲子提供音符的日子。
这场闹剧以妹妹“上闩”的行为告终,展现出家人对他的极度拒斥,代表着彻底的弃绝。他们之间隔着的绝不是一道上了锁的门,而是整个冷漠的世界。在可以攫取他的工资与照顾时他们不曾推脱,在应当寄予他安慰与宽容时他们也不曾给予。无法上班的格里高尔,早像一枚无处适配的螺丝钉被社会遗弃,而现在连家中一方小房间都再无他的立锥之地——这样一种价值至上的畸形亲情关系,扭曲了原本该有的人情,余下的尽是刺人的冷漠。
“我们得摆脱这东西。我们已经尽力照顾他,容忍他,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想谁也不能对我们有半点指责。”妹妹的话语像是父亲砸来的苹果,用一种精神暴力的形式彻底敲碎了格里高尔的心,也消磨了他的生命意志。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才有些认清自己一直努力维系着的家庭关系,但他大概还是带着不会拖累家人的欣慰与满足死去。
琴声终于成为格里高尔生命的终曲,唤醒了他决定成为自我终结者的独白。在变为甲虫的那个清晨,他预想着的五六年后转运的好日子终究没能到来。
三、结语
小说最后,似乎新生命的迹象正在勃勃展开——萨姆沙夫妇和格雷特一同前往郊外旅行,在温暖的阳光洒落时,他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憧憬未来,而完全遗忘了几个小时之前,格里高尔才死于沾着厚灰尘、堆满弃用家具的黑暗房间里。
明暗对比、生死对比之间,格里高尔似乎从未存在。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此后格雷特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格里高尔?在十七岁的青春年纪,父母将为她找一位“如意郎君”,而丈夫的存在,只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崭新梦想”罢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世真实是唯利是图,是对金钱的顶礼膜拜,是对亲情的不屑一顾。格里高尔与格雷特生活在父母构建起的驯化体系之中,难以发现真相,亦逃无可逃、避无可避。
金钱、苹果与琴声,三个现实可感的物与甲虫这一虚构荒谬的物结合起来,使得虚妄之说有了真实之处,将格里高尔逐渐受到家人厌弃的过程展现得深刻而清晰。现代社会中人群丧失自我是普遍的、周围的人性扭曲是平常的、生存的痛苦是无法改变的……一切的信任都在不断崩塌,一切的人情都只剩冷漠,在挤压变形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人们只能如此微渺地活着。
参考文献:
[1]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日记[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0.
[2]戴春雷.从“敲榨”到“敲碎” ——由“敲门”细节透视卡夫卡《变形记》“吃人”主题[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02):113-120.
[3]李雪莲.解开“苹果”之咒——卡夫卡《变形记》读法一种[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7,(02):26-28.
作者简介:
郑云骢,女,汉族,四川雅安人,四川师范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世界文学、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