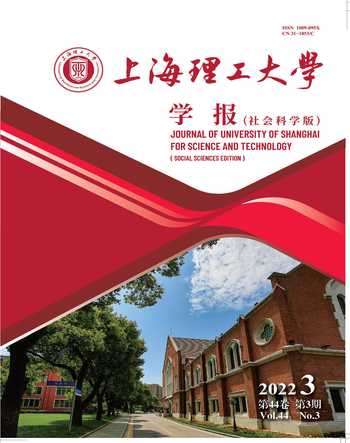乔叟对宫廷爱情传统的重写研究
胡英
摘要: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的乔叟是14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由于深受宫廷文化的影响,乔叟在早期诗歌中沿用了宫廷爱情传统,但为了反映英国宫廷的现实而对其进行了相应改写。随着文学视野的不断开拓,乔叟在宫廷爱情传统中融入了现实主义元素,对其中的贵妇和骑士的形象进行了革新。在后期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进一步超越了宫廷爱情传统的局限,以“婚姻”为隐喻表达了他对当时英国阶层矛盾的态度。乔叟在诗歌创作生涯中对宫廷爱情传统的不断重写不仅生动地反映了他个人风格形成的过程,还为后人了解中世纪末期英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关键词:乔叟;宫廷爱情;重写
中图分类号:I 1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 - 895X(2022)03 - 0264 - 08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2.03.009
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诗歌创作生涯一般被划分为早期的法国阶段、中期的意大利阶段和后期的英国阶段。乔叟在诗歌中对法国传统,尤其是宫廷爱情诗歌传统的运用一直以来都是乔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然而长期以来,以马斯卡廷(CharlesMuscatine)为代表的乔叟学者主要聚焦于讨论法国传统对乔叟的影响,较少涉及乔叟在创作生涯中后期对法国传统的超越[1],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但他们大多只对具体作品展开文本分析,缺乏对乔叟诗歌中宫廷爱情传统的演变进行的系统性研究。
针对这一不足,本文将结合乔叟所在的14世纪英国历史文化语境,讨论乔叟对宫廷爱情传统进行重写的三个主要阶段。在早期的诗歌《公爵夫人之书》与《众鸟之会》中,乔叟为了表现14世纪英国宫廷的现实而在沿用宫廷爱情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改写。在中期的诗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与《善良女子殉情记》中,乔叟在宫廷爱情传统中融人了现实主义元素,并对其中贵妇与骑士的形象进行了革新。在后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进一步超越了宫廷爱情传统的局限,以“婚姻”为隐喻表达了自己对14世纪英国阶层矛盾的思考。乔叟在诗歌创作生涯中对宫廷爱情传统的不断重写不仅反映了诗人通过融合不同文学传统和14世纪英国现实形成个人风格的过程,还凭借对“婚姻”“劝谕”“自由”“高貴”等主题逐渐深入的探讨为后世了解14世纪英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一、宫廷爱情传统与乔叟时代
宫廷爱情传统最早可以溯源至11世纪末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出现的新型抒情体诗歌。普罗旺斯抒情诗(Provencal Lyrics)的兴起与当时西欧的历史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在斯沃比(Fiona Swabey)看来,这一时期“无论在文化还是政治边界上,它都被认为是开放的,到处弥漫着宽容,自由和创新的氛围,充满了活力。这个高度流动的社会鼓励贸易,经济发展以及知识和思想的交流”[2]。普罗旺斯抒情诗通过歌颂贵妇与骑士的爱情,同时肯定恋爱中的骑士人格升华的可能,为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欧洲12世纪文艺复兴拉开了序幕。
普罗旺斯抒情诗兴起之后,一些教士、封建领主,甚至以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William IX ofAquitaine)及其孙女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为代表的法国贵族也参与了新诗的创作。在他们的推动下,普罗旺斯抒情诗中的爱情主题逐渐与法国骑士文学传统相结合。以克雷蒂安(Chretien deTroyes)为代表的宫廷诗人将宫廷爱情引入在欧洲流传已久的亚瑟王传奇,改写了普罗旺斯抒情诗中的爱情范式。著名中世纪学者刘易斯(C.S.Lewis)认为这一时期的宫廷爱情诗歌以谦卑(humility)、温文尔雅(courtesy)、私通(adultery)和爱情膜拜(religion of love)为主要特点[3]。随着圣母崇拜在中世纪中后期逐渐达到巅峰,玛利亚开始在一些著名浪漫传奇中作为最圣洁的贵妇出现,贵妇与玛利亚的形象逐渐合二为一。卡系尔(Thomas Cahill)在回顾这一现象时指出:“我们可以保险地说,无论是敬虔的室女崇拜,还是对领主夫人的桃式仰慕,都维系着该时期妇女地位的整体提升。”[4]宫廷爱情诗歌中爱情膜拜的特点进一步凸显,这一变化与埃莉诺及其女儿香槟的玛丽(Marie de Champagne)等宫廷贵妇对宫廷诗人的大力赞助,以及她们对宫廷爱情诗歌的积极推广密不可分。虽然她们大多没有直接参与诗歌创作,但是“她们都是艺术家灵感的源泉,又是作品的批评人和读者,从而为当时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175。
宫廷爱情诗歌虽然起源于普罗旺斯,流行于法国宫廷,但随着埃莉诺嫁给英王亨利二世,宫廷爱情诗歌也流传到了英国。在乔叟接触到的法国宫廷爱情诗歌中,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和莫恩(Jean de Meun)创作的《玫瑰传奇》(Rowian de la)Rose)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在皮尔索尔(DerekPearsall)看来,“《玫瑰传奇》是乔叟怀着满腔热忱阅读过的诗作;这部诗作成为了乔叟意识的一部分,在他个人经验中占的比重甚至超过了他的生活经验”[6]80。然而,乔叟的生活经验对他的个人经验,以及文学创作生涯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乔叟所在的14世纪是一个以斗争和变革为基调的时代。英法百年战争、宫廷内斗、农民起义、黑死病和宗教改革使得英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王室贵族对社会的控制逐渐减弱,教会对民众的影响也日趋没落,封建等级制度开始瓦解。劳作的人(laboratories)、祈祷的人(oratores)和作战的人(bel-latores)这三个传统等级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商贸阶层(the commercial class)在14世纪英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等级理论已不再能为日益增多的商人、公证人、银行家、律师等从事商贸及相关工作的人提供一个现成的位置”[7]172。当时英国社会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女性地位的提升。在漫长的中世纪期间,“妇女既无能力,也无必要,更无惯例在军事和其他方面为领主和国王服务”[5]11。然而14世纪黑死病和百年战争造成的男性劳动力短缺促使当政者放松了对女性就业的限制,普通英国女性有了更多机会参与社会生产。女性,特别是寡妇们外出就业的机会增多,经济也更为独立。多篇研究1300到1500年伦敦寡妇的文章显示,虽然女性无法进入伦敦最有名望和最盈利的公司,但在她们的丈夫死后,她们可以接替丈夫的行业,成为制革工人、剥皮工人、铸钟工人或造丝女工[8]。女性角色的变化给诗人乔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皮尔索尔指出:“乔叟不仅对新的商人阶层有所回应:他同时还异乎寻常地留意到了女性日益增多的对经济生活的参与……他对巴斯妇作为一个独立、成功的女商人的刻画并非荒诞的幻想。”[6]252
尤为重要的是,巴斯妇不仅以一个经济独立的女商人的形象出现,她还是企图通过参与圣母崇拜、罗拉德派运动和神秘主义运动来获得话语权的英国女性的一个缩影。在14世纪英国,圣母崇拜不仅帮助贵族女性、修女,甚至女神秘主义者巩固了她们的地位,还使得广大中间阶层女性通过家庭教育和对子女宗教活动的指导建立了在家庭中的权威[9]36。与此同时,圣母崇拜还促进英国女性积极外出朝圣,因为“朝圣之旅的经验为她们提供了与玛利亚更为 ‘直接的、个人的关系”[10]。除了参与圣母崇拜,当时一些英国女性还通过成为罗拉德派的成员获得了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权力,而这也是罗拉德派被教会斥为异端的原因之一,因为“让俗界人士能够接触到《圣经》已经够糟了,让女性也能做同样的事就更为恶劣”[9]166。此外,随着中世纪末期神秘主义运动在英国的兴起,以诺唯奇的朱丽安(Julian ofNorwich)和肯普(Margery Kempe)为代表的女神秘主义者开始著书立传,甚至在公众场合传经布道。虽然受到教会的极力阻挠,但这些女神秘主义者通过表达融入了大量女性经验的宗教理念打破了中世纪女性长久以来的沉默。虽然巴斯妇只是乔叟融合各类文学传统和英国社会现实虚构的一个女性人物,但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乔叟时代中间阶层女性经济地位和文化影响力的变化。英国中间阶层女性在家庭和公共领域发出的声音不仅呼应了贵族女性通过宫廷爱情诗歌改善女性形象的努力,还在一定程度上与希望提升文化和政治地位的中间阶层产生了共鸣,于是在14世纪英国转型期间,“女权”和“人权”产生了某种奇妙的交融,长期被父权社会边缘化的英国女性与难以在封建等级制度中确定自身位置的中间阶层男性在一些文化理念上不谋而合,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共同体”。创作生涯中后期的乔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现象,因此《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由位于上层社会边缘的没落骑士、来自中间阶层各行各业的男性,以及部分经济独立且行动自由的女性组成的朝圣者之间虽然争议不断,但却“找到了一条在现实的层面上和谐共处,搁置彼此间争议的办法,从而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取得了某些共识”[11]。
乔叟创作出《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样的诗歌绝非偶然。就个人经历而言,他出身富裕商人家庭,少年时人宫担任王室侍从,成年后成为王室官员,并曾作为王室特使游历欧洲,中年在海关等部门任职期间又得以接触众多英国中下层人士,因此较之同时代的英国诗人,乔叟对英国社会各阶层无疑有着更为全面的认识。就文学素养而言,乔叟在担任王室侍从期间深受法国宫廷文化影响,对法语诗歌非常熟悉,以至对于他,“法语可谓英国的另一种方言”[12]。在创作生涯早期,乔叟使用了大量的法语词汇,以便能够更为精确地描写爱情和骑士精神这样的高雅主题。担任王室特使之后,乔叟有机会出访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接触到了但丁(DanteAlighieri)、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和卜迦丘(Giovanni Boccaccio)等意大利诗人的作品并深受感染,从而开始将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用于丰富自己的诗歌语言。除了法国传统和意大利文学,基督教和古典文学传统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乔叟的创作。然而,乔叟在使用这些文学传统时,并不拘泥于对权威的尊重而恪守陈规,而是“凭借着日常生活的经验和对普通英国读者的了解去质疑‘权威会说什么”[13]136,因此能够将这些文学传统的精粹与自己对14世纪英国现实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也许正因如此,对他创作生涯早期产生重大影响的宫廷爱情传统才得以随着他对与14世纪英国中间阶层和女性密切相关的“婚姻”“劝谕”“自由”“高贵”等主题日益深入的探讨被不断地重写。
二、沿用与改写:《公爵夫人之书》
和《众鸟之会》
《公爵夫人之书》是乔叟早期梦幻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乔叟将这首诗歌献给了自己的保护人兰开斯特公爵,以悼念他的亡妻布兰茜。虽然现实中的兰开斯特公爵身居高位,但依照宫廷爱情传统,以兰开斯特公爵为原型塑造的黑衣骑士在爱慕的夫人面前无比卑微,并在痛失爱人之后丧失理智,成为了被爱神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弱者。与此同时,以兰开斯特公爵的夫人布兰茜为原型塑造的怀特夫人无论就外貌、品德和言行而言都可谓完美贵妇的典范。在与黑衣骑士的关系中,怀特夫人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由始至终都冷静而矜持地控制着两人关系的进展。在黑衣骑士急切的表白之后,她仅用一个“不”字便回绝了他的爱情。直至一年之后确认了黑衣骑士的真心,她才接受了他的感情,并从此承担起教导他的责任。黑衣骑士在回忆怀特夫人对他的教导时指出:“的确,我的甜爱,每当她纠正我过错的时候,总是和颜悦色,宽厚相待。同时,在我的青春多变的生命中,她严加督导,决不放松一步。”[14]26通过对怀特夫人的描述,乔叟强调了女性劝谕对男性成长的重要意义。在乔叟中后期的诗歌中,“劝谕”这一主题更是反复出现,成为解读乔叟作品的关键所在。
虽然在《公爵夫人之书》中描述黑衣骑士与怀特夫人的爱情时沿用了宫廷爱情传统,但乔叟根据英国宫廷的现实对其进行了改写,使之更为符合英国贵族保护人的审美趣味。由于兰开斯特与布兰茜是一对贵族夫妇,乔叟将宫廷爱情诗歌对骑士与贵妇之间“私情”的描述转为对夫妻之间的真挚感情的歌颂。肖明翰在分析这一变化时指出:“在中世纪诗人中,乔叟第一个摆脱私情巢臼,表现夫妻感情,从而向现实生活大大靠近了一步。后来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婚姻以及夫妻间的关系和感情成为突出的主题。”[15]103基特里奇(George LymanKittredge)在对《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众多故事进行归类之后,指出巴斯妇、托钵僧、法庭差役、牛津学士、商人、乡僧和弗兰克林等众多朝圣者都在各自讲述的故事,以及故事之外的对话中发表了对婚姻问题的看法[16]。他们讲述的“婚姻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创作生涯晚期的乔叟探讨14世纪英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隐喻。
除了《公爵夫人之书》,乔叟在梦幻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众鸟之会》中也明显沿用了宫廷爱情传统。这首诗是为了庆祝理查德二世击败法国理查五世的大王子,成功与卢森堡家族的安娜公主联姻而作。在自然女神主持的求偶大会上,三只雄鹰向高贵的雌鹰求爱,其中代表理查德二世的那只雄鹰承诺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对代表安娜公主的雌鹰绝对服从:“我完全归她所有,将永久为她服役,她尽可支配我的一切,控制我的生死;我要象尊崇主后一样的尊崇她,也照样向她请求恩顾与宽恕,如有违抗,我愿不惜一死为报……”[14]89-90此外,雄鹰还承诺给予雌鹰充分的自由:“既然谁都没有象我对她这样真心,即使她并未俯允,她也该以慈悲为怀,做我的终身伴侣。除此以外,我不敢给她任何束缚。不论如何痛苦,我决为她服役,不敢懈怠;天涯海角,我也不怕遥远。”[14]90虽然雄鹰沿用了骑士向贵妇求爱时固定的话语,但雌鹰的反应却有别于宫廷爱情传统中的贵妇。雌鹰并不为雄鹰的承诺所动,她拒绝挑选任何一只雄鹰作为她的配偶,恳请自然女神给她一年的时间考虑,一年之后再进行选择,因为“我还没有打算做维纳斯或可必德的侍役”[14]95。乔叟也许是希望借这一情节影射理查德二世和安娜公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姻过程,然而乔叟诗歌中的很多女性人物,如《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中的克丽西德和《武士的故事》中的爱茉莉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对自由的向往。在《伙食司的故事》和《自由农的故事》中,喬叟更是深化了对“自由”主题的探讨,并赋予了这一主题明显的政治寓意。
难得可贵的是,乔叟在《众鸟之会》中对宫廷爱情传统的改写不仅在于强调雌鹰对自由的渴望,更在诗中融入了英国其余阶层人士的身影。参加求偶大会的除了三只高贵的雄鹰,还包括虫食小鸟、水禽和靠植物种子为生的鸟类,自然女神将它们按照各自的秉性安排在自然花园不同的位置:“掠食猛禽坐在最高位,然后是那些虫食小鸟,他们当然还吃其他的东西,此刻我不详述;惟有水禽之类却排在山凹最低处坐下。至于那些靠植物种子为生的鸟类就坐在草地上,他们为数众多,叫人看去目眩。”[14]87《乔叟文集》的译者方重对众鸟的排位进行了解读:“这一段将鸟类分为不同的等级,代表着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坐得最高位的掠食猛禽应指贵族阶层而言,虫食鸟类乃中产阶层,水禽指市民商人,而为数众多的靠植物种子为生的鸟类则指农民。”[16]88与其他宫廷诗人不同,乔叟显然意识到中产阶层、市民商人和农民也是14世纪英国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借自然花园中众鸟云集的求偶大会呈现出英国各阶层的全景图。尤为重要的是,众鸟不仅参与了求偶大会,还得以在求偶大会陷入僵局时表达各自的意见。由于三只高贵雄鹰按照宫廷爱情传统向雌鹰的求爱极为冗长,迫不及待想要择偶的众鸟无法忍耐,开始叫嚷起来:“鸟儿们相互矛盾的观点和反驳瞬间爆发出来。各种方言、谚语和俏皮话此起彼伏,每一个都代表着和其他话语不同的世界观。”[17]众声喧哗之中,自然女神建议每类禽鸟选择一名代表发言,才得以平息众鸟的不满。乔叟也许意在通过求偶大会影射当时英国不断发展的议会制,自然女神对众鸟意见的尊重和妥善处理是求偶大会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相较于雄鹰和雌鹰高贵的身份,自然女神“高贵”的统治更值得赞颂。乔叟在《众鸟之会》中暗示了自己对“高贵”的看法之后,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更是借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朝圣者之口,从不同的角度对“高贵”这一主题进行了更为充分的探讨。
三、融合与革新:《特罗勒斯与克丽
西德》和《善良女子殉情记》
在创作《众鸟之会》时,乔叟便开始受到意大利文学的影响。随着乔叟对意大利文学的了解日益深入,他在创作《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和《善良女子殉情记》时更为明显地意识到宫廷爱情传统中的男女之爱与中世纪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两性关系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这两首长诗虽然在语言风格、叙事框架和故事情节上仍表现出若干宫廷爱情的特点,但乔叟通过对其中“贵妇”或“骑士”形象的革新,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中世纪父权文化的反思。
在《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中,乔叟重写了一个古典时期流传下来的关于爱情和背叛的故事。包括圭多(Guido delle Colonne)和卜迦丘在内的很多诗人在不同程度上均将故事中的克丽西德描述为贪生怕死、背信弃义的自私女子,但在乔叟的版本中.“克丽西德是以一个复杂、多维的人物形象出现的,她纠结反复的性格引发了乔叟评论家们无穷无尽的论述”[7]209。虽然乔叟笔下的克丽西德仍未逃脱悲剧命运,但她被塑造成一位有着细腻情感、丰富内心世界的女性人物。贝尔曼(Mary Behrman)认为克丽西德具有与命运抗争的英雄气概[18],达蒙(JohnDamon)则认为乔叟赋予了这个异教故事中的克丽西德以基督教精神,将她描述为一位“忠诚、富有同情心,心胸宽广的女人”[19]。
在这首诗中,特罗勒斯沿袭了宫廷爱情传统中的骑士形象。他虽然是特洛伊城地位最为尊贵的男子,但在爱神的惩罚下对克丽西德一见倾心,成为她卑微的骑士。然而,克丽西德却不再是宫廷爱情传统中沉溺于情爱的贵妇,她对两性之间真实的权力关系有着理性的认识。面对特罗勒斯的求爱,克丽西德反复权衡利弊,并曾吐露这样的心迹:“他喜欢我,又算得了什么稀罕的事?感谢上帝,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在我这地位我有相当优裕的生活,我还年轻,是花草繁茂的牧场上一只无羁无绊的羔羊,没有人忌妒我,我也不受任何牵涉;我并没有一个丈夫来向我夸口说我是他手上的败将!男子们不是忌妒,就是有统治欲,或是见异思迁。”[14]139在克丽西德看来,男女之间不可能存在平等的爱情,只有脱离男性以爱为名的掌控,她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过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生活。克丽西德的内心独白不仅呼应了《众鸟之会》中雌鹰对自由的渴望,还为雌鹰的心态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阐释。
乔叟不仅在这首诗中通过对克丽西德心理活动的刻画揭示了宫廷爱情传统与父权文化的冲突,还通过对克丽西德背叛的处理表达了自己对父权社会中女性命运的思考。与其他一味谴责克丽西德的诗人不同,乔叟拒绝对克丽西德的行为加以评判,相反却隐约其辞,使用了“古书上有记载”,“我还在其他书中看到”,“有人说——我却不知底细——”,“然而古书上说”等话语来保持自己与叙事的距离。此外,乔叟还将克丽西德称为“不幸的女子”,极为详细地描写了克丽西德对自己命运的哀叹,强调“她对特罗勒斯变心之际,曾经哭泣,据说天下女子没有一个能象她那样悲恸的”[14]249,从而隐晦地表达了对她的宽恕。通过这一系列的策略,乔叟无疑为未来的读者对克丽西德进行全新的道德评判预留了空间。
除了在《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中对克丽西德的形象进行了革新,乔叟还在《善良女子殉情记》中揭示了“痴情骑士”这一文学形象的虚妄。珀西瓦尔(Florence Percival)因此指出:“尽管乔叟一向尊重法国大师们的诗歌传统,但在《善良女子殉情记》的写作过程中,乔叟诗歌中的反叛因素更为明显。”[13]42这首诗中的贵妇大多在历史上以美德和对爱情的忠贞闻名,但也有以埃及女王克丽佩特为代表的少数贵妇因为离经叛道而饱受争议。虽然很多评论家将这首长诗视作乔叟的一部过渡性作品,然而科莱特(Carolyn P.Collette)却指出这部作品作为一个特殊文化时期的产物,不仅是乔叟作为一名经典作家的成长之路上极其重要的作品,同时也是使得“早期的人文主义与中世纪末期宫廷传统相遇的奇妙的文本”[20]。
依照宫廷爱情传统,《善良女子殉情记》将对爱情的忠贞程度作为评价人性的标准。”然而《善良女子殉情记》中的男性徒有宫廷爱情传统中“痴情骑士”的外表,却往往为了追名逐利而背弃贵妇们的爱情。在《菲丽丝记》中,乔叟对负心汉德莫逢作了如下评价: “他的面貌身材不亚于他的父亲,同时,在骗取爱情的手法上也是父子一脉相承的;真是天赋的才能。好比老狐狸莱纳做得巧妙,小狐狸自然也会照办;生来就懂得父亲的一套,用不着教,正象抓住一只小鸭在水边一放,它就会自动游去。”[14]322这首诗歌中的女性虽然高贵而富有,但受环境的束缚,大多只能在家宅或宫殿内虚度光阴,“以死殉情”便是她们所能取得的最大功绩;而男性则与“航海”这一意象紧密相连,他们永远在外飘泊不定,企图通过不断的冒险来提升自己在封建等级序列中的位置,“建功立业”才能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父权文化对性别角色的划分以不同方式对男女两性都构成了压迫,由于无法拥有共同的经历和成长,两性之间的爱情大多只能以失败告终。乔叟虽然在《善良女子殉情记》的引子里宣称这首诗是受爱神和雏菊花神之托而作,但他在诗中对“痴情骑士”形象的顛覆不仅意在批判背信弃义的男子,还意在揭示造成两性爱情悲剧的文化根源。
在对父权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乔叟还通过对“劝谕”和“高贵”的探讨表达了自己对封建等级文化的态度。评论家公认引子中爱神的原型是脾气暴躁的年轻国王理查德二世,而雏菊花神的原型则是他优雅的妻子波希米亚的安娜。安娜皇后性格温顺,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她曾试图去约束理查德二世某些过激的行为,但在很多已知的场合里,安娜曾为罪人们公开请求宽恕,例如她曾为1381年农民起义的造反者们求情,此事还耽搁了她到英格兰与理查德成婚[13]47。在引子中,爱神因为诗歌的叙述者杰弗里丑化女性而对他进行斥责,雏菊花神阿尔塞丝却选择为他辩护,珀西瓦尔因此认为:“她模仿了经常和圣母玛利亚联系在一起的女性仲裁者和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乔叟时代很多贵族女性认为在处理国内危机时需要充当的角色。”[13]92颇具深意的是,阿尔塞丝为乔叟辩护的长篇说辞与中世纪末期英国流行的文人用于向君主进谏,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明智地管理自我和国家的文体非常相似,从而使得自《公爵夫人之书》便出现的“劝谕”主题开始有了政治内涵。在强調“劝谕”的意义并拓展其内涵的同时,乔叟表达了自己对“高贵”的理解。在阿尔塞丝为杰弗里所作的辩护里,乔叟明确地借阿尔塞丝之口阐明了何为君王之道: “因为当个君王,顺天者昌,不可像乡间的地主一样不顾一切,残害良民。为主者必须为自己的臣民着想,他主要的职责就在乎使百姓沐其恩泽,随时随地听取民怨,及时注意民间的疾苦与呼吁。”[14]276阿尔塞丝告诉爱神,权力并不意味着专横暴戾,与之相反,权力的最高境界应是宽恕和感化,让臣下明白自己的过错并能从思想和行动上痛改前非。较之爱神的专权,阿尔塞丝对待臣下的方式无疑更为“高贵”,她不仅为爱神树立了如何处理阶层矛盾的范本,也让宫廷诗人杰弗里心悦诚服,感叹“此刻我是充分地感受到了她的福泽”[14]279。在《众鸟之会》中借求偶大会上自然女神对众鸟纷争的妥善协调暗示何为“高贵的统治”之后,乔叟又在此诗中将自己对14世纪英国阶层矛盾的思考融入了带有喜剧色彩的爱神、雏菊女神和杰弗里三人的对话,并通过阿尔塞丝的劝谕和杰弗里对她的赞颂含蓄地提出了自己对封建等级文化的质疑。
四、超越与重塑:《巴斯妇的故事》和
《自由农的故事》
乔叟作为一名中世纪男性诗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文化语境的限制,然而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增长,他对14世纪英国两性和阶层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后期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里,乔叟进一步超越了宫廷爱情传统的局限,故事的叙述者由宫廷诗人换作中间阶层男女,主题也由“爱情”变为“婚姻”。在这些“婚姻故事”中,《巴斯妇的故事》和《自由农的故事》最具代表性。
马西(Michael Masi)在讨论《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核心思想时认为巴斯妇是解读这部诗歌的关键所在,因为“所有在她之前或之后讲述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她的论点,或者是对她陈述的自身经历,甚至是对她成为主要由男性组成的朝圣者中的一员这个事实进行的回应”[21]。《巴斯妇的开场语》具有明显的法布罗文学的特点,然而《巴斯妇的故事》却具有浓厚的浪漫传奇色彩。在很多评论家看来,巴斯妇讲述的故事过于理想化,与其本人的身份性格并不相符。然而,也有评论家认为由泼辣剽悍的巴斯妇讲述一个以爱和宽容结尾的浪漫故事并不奇怪,因为“这个故事不仅让巴斯妇想要获得控制权和一个年轻、刚健的丈夫的欲望得到完全满足,还让她重获失去的青春美貌的欲望得以满足”[22]。想要同时满足上述欲望,巴斯妇必须对许多传统的文化理念进行革新,而何为真正的“高贵”便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
在巴斯妇讲述的故事中,骑士是一位身份高贵的男性,无论是在故事开头林中偶遇的仙女面前,还是在故事结尾成为他妻子的贫苦老妇人面前,都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在卡罗瑟斯(Mary Carruthers)看来,骑士的优越感源于“他有着明显的阶层意识”[23]。如果无法破除骑士的阶层意识,故事中身份卑微的老妇人与高贵的骑士绝不可能拥有一段和谐的婚姻。因此在两人的新婚之夜,老妇人对骑士进行了意味深长的劝谕。老妇人首先选择对骑士引以为傲的高贵身份进行消解,并告诉他何为真正的“高贵”:“但你提起家世富有,出身高贵,认为这就算有了地位,你这般自恃夸傲实在值不得半文钱。凡是那不论公私都以道德为,一心要做出高贵的事来的人,方可算得最可尊崇的人。”[14]469随后,老妇人又逐一革新了骑士关于“贫穷”和“年老”的认识。在骑士接受她的劝谕,并愿意将主宰权交予她之后,老妇人终于变身为美丽妙龄的女郎,使得两人都能体会到婚姻的幸福。这一场景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乔叟对婚姻中的两性之争,以及英国社会中的阶层之争的真正态度。消解传统的性别意识和阶层意识的目的不在于建立新的等级文化,而在于形成一种融汇了男女两性、以及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经验,更为平等、自由和包容的文化。
乔叟在《巴斯妇的故事》中借骑士和老妇人的婚姻对“高贵”进行全新定义之后,又在《自由农的故事》中借阿浮拉格斯与朵丽根的婚姻探讨了“自由”对婚姻和其他人类关系的重要意义。在《伙食司的故事》中,乔叟已对自由的重要性进行了初步的阐释。故事中贵族男子费白斯的妻子在丈夫为她提供锦衣玉食的生活,同时不遗余力让她快乐的情况下仍然设计出轨,乔叟以“笼中鸟”作比分析了费白斯的妻子背叛丈夫的原因:“以一只鸟来作比,把它关进笼,一心一意照护它,喂它饮食,想尽一切好东西给它享受,把它安置得清洁舒适,即使它的笼是金制的,十分美观,这只鸟儿还是万分情愿去吃它的虫,宁可在寒冷峻厉的树林中过它的生活。它永远要设法跑出笼去;这只鸟的心上只知道要自由。”[14]720-721与善妒的费白斯对妻子的严密监控不同,《自由农的故事》中的骑士阿浮拉格斯与贵妇朵丽根的婚姻是建立在给予对方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尊重的基础之上。阿浮拉格斯放弃了丈夫在婚姻中的控制权,而朵丽根则放弃了宫廷爱情传统赋予贵妇的主导权。自由农对此评价道:“这是一个融洽互让的表现,她所得的是一个顺从的侍者,一个可尊崇的主子——爱情上的侍从,婚姻中的丈夫;他得有权威,同时也受了束缚。束缚吗?——不,他仍掌有权威,因为他既取得了妻,又赢得了爱;他的夫人、妻子和一个接受了爱情律的配偶。”[14]559-560虽然自由农认为阿浮拉格斯与朵丽根之间的婚姻无疑是最符合人性的,然而有趣的是,在他这段评论中却出现了“侍者”与“主子”、“侍从”与“丈夫”、“爱情”与“婚姻”、“权威”与“束缚”、“夫人”与“妻子”等诸多相互矛盾的概念,从而预示了两人建立在宫廷爱情传统之上的婚姻在父权社会中可能出现的重重危机。在两人婚后,阿浮拉格斯离开妻子去武艺场求取荣誉,青年男子奥蕾利斯趁机向朵丽根吐露了爱意。作为宫廷爱情传统中的贵妇,朵丽根享有接受奥蕾利斯爱情,并驱使他为自己服务的自由,然而这一“自由”却让她陷入了僵局,最后唯有依赖丈夫和求爱者在处理此事时表现出的高贵品格才勉强摆脱了困境,朵丽根这才领悟到宫廷爱情与父权文化的格格不入。
虽然故事中阿浮拉格斯与朵丽根在平衡爱情与婚姻、自由与束缚、理想与现实的努力中遭受了挫折,然而考虑到自由农的身份,这个故事便显得别具深意。《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大多数男性朝圣者都从男性视角讨论两性关系,但自由农的叙述视角却在很多方面与朵丽根保持一致,只因为“他的社会等级与朵丽根的性别等级有着某种相似性”[24]。在中世纪中后期,随着庄园经济的瓦解和不同规模的城镇的兴起,农奴制逐渐消失,“领主和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消失创造了全新的社会文化。富裕农民和小贵族以及商人之间不再有法律规定的界限,社会地位不再取决于对土地的占有,而更多地依赖于个人从事的职业和拥有的财富”[25]。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富裕的自由农不仅满足于拥有足以与骑士阶层媲美的财富,他还选择讲述一个宫廷爱情故事来探讨“爱情”“高贵”“荣誉”等高雅的主题。虽然“他的行为显示他渴望的是担负一个骑士的责任”[26],但他的故事卻从对爱情的歌颂转为对婚姻的探讨,同时流露出强烈的掌控人身自由的欲望。自由农的故事对宫廷爱情传统的偏离无疑与他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虽然他解除了与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经济地位也有了较大提升,然而他在14世纪英国封建等级序列中的位置却远不如同行的骑士那般牢固。文化认同与现实地位间的冲突使得自由农一方面能对故事中贵妇朵丽根所受的性别等级文化的压迫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讲述阿浮拉格斯与朵丽根对理想“婚姻”的探索和因此遭受的磨难来表达自己对封建等级文化的质疑。因此在休姆(Cathy Hume)看来,“这个故事并未游离在它所在的文化环境之外。故事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和真实的人类生活的联系,以及对当时文化论战的贡献”[27]。通过选择自由农作为叙述者,乔叟完美地将自己对两性和阶层问题的态度融人了这个集“爱情”与“婚姻”于一体的故事中。
五、结束语
在乔叟所处的14世纪英国,无论是像《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学者那样捍卫传统,强调女性对男性、臣民对君主、人对上帝应绝对服从的一方,还是像巴斯妇和自由农那样,由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性别或封建等级文化的压迫而希望有所改变的另一方,都无法彻底地说服对方,只有在不断地辩论与妥协中寻求能够描述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全新语言。乔叟无疑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以不断赋予经典故事,现有词汇、传统主题以新的意义的方式参与其中。在乔叟的诗歌中,宫廷爱情范式在历经早期的沿用与改写,中期的融合与革新,以及后期的超越与重塑之后,逐渐转变为更能反映14世纪英国社会现实和新兴中间阶层情感解构的“婚姻范式”,而乔叟在此过程中对“婚姻”“劝谕”“自由”“高贵”等主题层层深入的探讨不仅使得他的诗歌成为14世纪英国社会变革的重要表征,还在两性和阶层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架起了一座不可或缺的文化桥梁,并促进了传统与现实,权威与经验的融合,从而在英国各阶层自14世纪起的连属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MUSCATINE C.Chaucer and the French Tradition:AStudy in Style and Meaning[M].Berkele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2] 菲奥娜-斯沃比,骑士之爱与游吟诗人[M].王晨,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3] LEWIS C S The Allegory of Love:A Study inMedieval Trad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1936.
[4] 托马斯-卡系尔中世纪的奥秘:天主教欧洲的崇拜与女权、科学及艺术的兴起[M].朱东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苏拉密斯-萨哈第四等级:中世纪欧洲妇女史[M].林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6] PEARSALL D The life of Geoffrey Chaucer:ACritical Biography[M]. Oxford and Cambridge:Blackwell, 1992.
[7] BISSON L M Chaucer and the Late MedievalWorld[M]. 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98.
[8] BARRON C M, Sutton A F . Medieval LondonWidows 1300 - 1500[M]. London and Rio Grande:Hambledon Press, 1994.
[9] WOOD D.Women and Religion in MedievalEngland[M]. Oxford: Oxbow Books. 2003.
[10] WAIIER G. The Virgin Mary in Late Medieval andEarly Modem English literature and PopularCultur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1] STROHM P. Social Chaucer[M].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89.
[12] BUTTERFIELD A. The Familiar Enemy: Chaucer,Language, and Nation in the Hundred Years War[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 PERCIVAL F. Chaucer's Legendary Good Women[M].Caru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喬叟,乔叟文集[M].方重,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5]肖明翰,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M].北:社会科科献出版社, 2005.
[16] SCHOECK R J, TAYLOR J . Chaucer Criticism: The Canterbury Tales[M].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Press, 1960.
[17] GRUDIN M P. Chaucer and the Politics ofDiscourse[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Press, 1996.
[18] BEHRMAN M. Heroic Criseyde[J]. The ChaucerReview, 2004(4) : 314 - 336. [19]
DAMON J. Classical Mythology and Christianity inGeoffrey Chaucer's Trolius and Criseyde[M].Huntsville: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2005.
[20] COIIETTE C P. Rethinking Chaucer's Legend of Good Women[M] . Suffolk: York Medieval Press, 2014.
[21] MASI M. Chaucer and Gender[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5.
[22] COOPER H. Oxford Guides to Chaucer: TheCanterbury Tal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89.
[23] EVANS R, JOHNSON, L. Feminist Readings in MiddleEnglish Literature: The Wife of Bath and All HerSect[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edge, 1994.
[24] CRANE S. Gender and Romance in Chaucer'sCanterbury Tales[M]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 BROWN P . Companion to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and Culture C. 1300 - C.1500[M]. Oxford: BlackwellPublishing Ltd, 2007.
[26] BERTOLET C E. Chaucer, Gower, Hoccleve and theCommercial Practices of Late Fourteenth-CenturyLondon[M] . Surrey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13 .
[27] HUME C. Chaucer and the Cultures of Love andMarriage[M]. Cambridge: D. S. Brewer,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