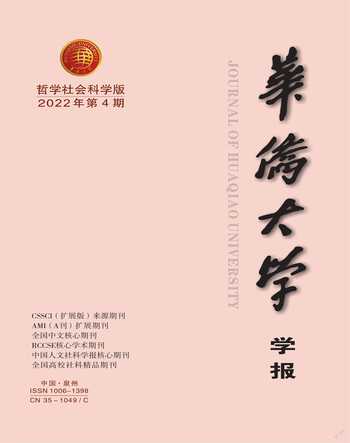台湾藏日本室町初年钞本《文选》述略
摘 要:古钞本是《文选》版本中的重要部分,它们的存在有其历史背景和独特性,对《文选》版本研究贡献很大。1884年杨守敬从日本访得两种并带回中国,此前学者多习惯将两种版本视为一体,并认为系杨守敬抄写本,其实乃两个不同版本,其中一卷本为镰仓本,二十卷本即室町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治《选》者难得一见。镰仓本确为杨守敬摹写,但室町本为原本的可能性极高。据格式、旁记、避讳等内容可以推测此本的底本年代应为唐代,其在保存萧统古式与亡佚文献、校正刻本错误等方面均有重要价值。《文选》写钞本的底本问题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焦点。但在研究时,虽应对写、刻本进行纵向的源流梳理,但也应明确写钞本与刻本分属不同系统,应先在写钞本系统内部进行一番深入研究后,再结合刻本作纵向地跨系统观照,或能离历史真实更进一步。
关键词:室町本;《文选》;日本古钞本;杨守敬
作者简介:王玮,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和古典文献学(E-mail:wangwei_6827@126.com;福建 泉州 362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尤袤本《文选》文献研究”(21FZWB068)
中图分类号:G256;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4-0151-10
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一帙《文选》,著录为“日本室町初年钞本”(下简称为“室町本”),此本为杨守敬1884年从日本访得并带回中国。室町幕府(1336—1573),是由日本足利尊氏在京都室町建立的武家政权。1336年为中国元朝至元二年,1573年为明代万历元年,故按其著录年代,此本大约抄写于元、明时期。该本为白文无注本,纸张厚实,字大潇洒,现存二十卷,分别是卷五至卷十、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九至卷三十,据其分篇可知为三十卷本,每半叶八行,每行十七字,正文间夹有大量旁记,部分卷目天头部分贴有若干浮签,上用汉字略记版本差异及李善注、五臣注、陆善经注、《文选钞》《音决》等内容。据屈守元介绍,武昌徐行可(恕)曾有一部据杨守敬室町本影写的卷子本,后黄侃从徐氏处借校并记有校语,向宗鲁又从徐氏借得校录,除原书的标记、旁注一一传录以外,又录了杨、黄两氏的校语,屈守元又从向氏处借得其详校本过临一遍。傅刚在北京图书馆发现傅增湘也曾两次以此本与胡克家本对校。由此足见此本文献价值之高。但因其藏于台湾,治《选》者难得一见。目前学术界对室町本的研究明显不足,大陆仅屈守元、傅刚先生据抄录本撰写过介绍文字,台湾地区仅何维刚先生据原本撰写过研究文章。(屈守元先生在《文选导读》、傅刚先生在《文选版本研究》中均有对室町本的相关论述。何维刚先生曾发表《试论杨守敬旧藏<文选>室町钞本的异文与来源问题》《杨守敬藏日本古钞<文选>之类目、注记与异文——以“赋”类为讨论重心》等文章展开对室町本的研究。)现结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见室町本,对其基本面貌、底本问题、文献价值等情况略加叙述。
一 基本面貌
(一)格式、类目、篇题等
室町本为三十卷白文无注古钞本,在格式、类目、篇题等方面有其特征,详情如下:
1.室町本卷五至卷九下,分别有“赋戊”“赋己”“赋庚”“赋辛”“赋壬”的题署。李善在卷一“赋甲”下明确说“赋甲者,旧题甲乙,所以纪卷先后,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题,以明旧式”,因李善将三十卷《文选》增至六十卷,故无法按照旧式排列,而室町本却保留了萧统旧式。
2.若某类诗文下,同一作者有连续多篇诗文,九条本、赣州本、尤袤本(九条本指日本九条家藏白文古抄三十卷本《文选》,现存二十一卷。赣州本属六臣本《文选》,即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尤袤本指南宋淳熙八年尤袤于池阳郡斋所刻《文选》,属李善注系统。)等版本的处理方式是该作者的第二首(篇)题目前空出若干字格再写篇名,而室町本则无空格,与集注本、北宋国子监本、明州本(集注本指周勋初所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北宋国子监本属李善注系统。明州本属六家本《文选》,即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等同。
3.《汉高祖功臣颂》开篇有三十一位功臣姓名,尤袤本或为节省版面,将人名逐一接续,而室町本、集注本等均为每人单列一行。《三国名臣序赞》“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吴志七人”的排列,赣州本、明州本、尤袤本等顺序有误,作“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吴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正确顺序应如室町本、集注本所列“魏志九人荀彧字文若……蜀志四人諸葛亮字孔明……吴志七人周瑜字公瑾……”(详情参见屈守元《文选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131—132页),此不赘述。)《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开篇的“祖太祖高皇帝”“父世祖武皇帝”,室町本每条单独成行,而尤袤本则是共居一行。《九歌》的《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诸小题皆在文后,而现存各本皆在文前。以上四处应为室町本保留萧统旧貌,由此可见其文献价值。
4.通过校勘发现室町本的卷目和篇目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讹误。如卷六卷目中作“王父孝”,篇目作“王文考”,卷目显误。卷目中《海赋》上写“江海”,篇目《海赋》上则题“海江”,篇目显倒。卷十卷目作《侍五官中郎将建帝台集》,篇目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帝”字为形近而讹。卷十五卷目中先题《斋中读书》,后题《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而正文中二篇顺序颠倒。卷二十三的卷目《解嘲》上写有“设论”,篇目中“设论”写在《答客难》上,卷目中的“设论”位置当误。第二,脱类目名、卷目名。如九条本卷十卷目《补亡诗》上有大类名“诗甲”、小类名“补亡”,而室町本仅有小类名“补亡”,无大类名“诗甲”。卷十卷目“韦孟讽谏一首”上无“劝励”小类目,而正文篇目《讽谏》上有“劝励”二字,室町本此处脱文。卷十五正文有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而卷目脱此条。卷三十卷目《吊屈原文》上写有“吊”,正文篇目《吊屈原文》上脱此类目名等。第三,卷名与篇名不符。如室町本卷十的卷名作《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而篇名则作《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再如卷十九卷名作《自解表》,而篇名作《解尚书表》等。第四,类目名称与其他版本记录不同。如室町本作“弹”,其他版本作“弹事”等。
(二)旁记
室町本同其他日本古钞本一样,在正文旁及天头、地角处多有旁记,但因笔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见并非原件,而是微缩胶卷,一律为黑白色调,故无法区分是否有墨、朱等不同注记。据笔迹推测当出自不同人之手,其中或有为杨守敬、黄侃等人所记者。
室町本旁记主要包括日语训点和汉字标识两部分。
日语训点为日本人阅读、学习中国典籍时的一种辅助手段,每卷数量大致相同,多集中于正文两侧,“左边是用于书写调整语序的符号的,而右边则要添加一些表示词尾变化或接续的假名,通常用片假名表记。”(刁克利:《翻译学研究方法导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7—348页。)由于汉语和日语的语序不同,日本人在学习汉语时,需要“给中国汉字配上日语读音,添加上一些训读符号”(陈端端、高芃:《汉日双向全译实践教程》,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4页。),如“一些表示助词、助动词、副词以及动词与形容词词尾变化的假名等”(刁克利:《翻译学研究方法导论》,第347页。),再颠倒汉文句子的主谓次序,即“把汉语句子的主语—谓语—宾语结构调整成日语的主语—宾语—谓语结构,因此在训读竖版汉文时为了明确句子的训读顺序,在回读词的左下角标注‘レ这一符号,这就是回读点。同时采用‘一、二、三……‘上、中、下‘甲、乙、丙等形式。”(蔡凤林:《汉字与日本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页。)这种颠倒主谓次序的方法称之为返り点,即回读符号。如《西征赋》“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室町本“有”字左侧写一“下”字,“明”字左侧写一“中”字,“中”字左侧写一“上”字,意味此句顺序应倒着读。蔡凤林认为“采用‘上、中、下形式是在平安时代后期,采用‘甲、乙、丙形式是在镰仓时代以后。……回读点起初标注在汉字正下方,十四世纪以后逐渐左移,十六世纪时固定于汉字左下角。”(蔡凤林:《汉字与日本文化》,第45页。)平安时代为794—1192年,室町时代为1336—1573年,室町本旁记中多见“上中下”字样,与蔡凤林所谓的“采用‘上、中、下形式是在平安时代后期”不符,然位置确在左下角,旁记或为十四世纪以后所记。
汉字标识多集中于天头部分,亦偶记于正文旁与地角处,每卷数量差别较大,由数条到数十条不等,内容主要包括异文、义注、音注三个方面。
异文包括四种。1.脱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为方便分类表述,故将异文分作脱文、衍文、讹误、记版本异同四类,其中脱文、衍文、讹误是站在室町本的旁记者角度而言,而非指室町本相对于《文选》原貌的脱文、衍文和讹误。)如《答客难》“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室町本脱“数”字,“胜”“著”两字间画一小○,于天头处补写一“数”字。考尤袤本“数”作“记”,《史记》《汉书》、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陈八郎本指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陈八郎宅刻本(下简称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指日本东洋文库藏朝鲜正德四年五臣集注本(下简称朝鲜正德本),此两种并为五臣注本。奎章阁本指韩国正文社于1983年据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明宣德三年活字本而影印之本(下简称奎章阁本),此本为六家注本。)等作“数”,九条本此处亦脱“数”字,却未补。室町本与九条本脱文一致,当非巧合,二者的底本应存在某种关联。至于室町本补“数”字,九条本未补,大概有两种可能,或室町本的抄写者在抄完之后进行复核时发现了问题,用其他版本进行补充,又或为后人所补。再如《马汧督诔》“嗟兹马生,位末名卑”,室町本脱“位”字,在“生”“末”两字间画一小○,于天头处补写一“位”字。2.衍文。如《东征赋》“知性命之在天兮,由力行而近仁”,其他本并无“兮”字,室町本天头处旁记“天下多兮字”。3.讹误。如《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辟玄闱以阐化”,室町本“辟”讹作“闱”,“闱”旁画一斜杠“\”,写一“辟”字,以此改正原本之误;再如《思玄赋》“水泫沄而涌涛”,室町本“沄”讹作“汸”,“汸”字左侧画一斜杠“\”,旁写“沄”。4.记版本异同。(记版本异同者分为两种,一种记于正文旁,这种情况并不多。一种记于天头地角处,数量相对较多。而部分天头处有浮签的卷目较为集中,如卷五等,浮签上多记版本异同,但应与正文旁记版本异同者非同时同人,如《长杨赋》“子墨为客卿以风”,浮签记作“以下风作讽”;同卷“帅军踤阹”,浮签记作“军下踤作萃”。)如:《西征赋》“鬼神莫能要”,室町本“能”字旁记“之五本”,即五臣本作“之”字,考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并作“之”。同篇“固乃周邵職之所分,二南风之所交”,室町本“职”“风”二字旁记“本无”,考现存各本均无此二字。同篇“而况于卿士乎”,室町本旁记“已上六字五有(‘有字简写为一横一撇)本无”,“五有本无”,应指五臣本有、李善本无,考北宋本无此六字,尤袤本作“况于卿士乎”,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作“而况于卿士乎矣”,陈八郎本作“而况于卿士乎”,但陈八郎本“乎”字下空一格,疑斲去“矣”字。奎章阁本注记:善本无而况于卿士乎矣七字。徐攀凤《选注规李》:“‘率土且弗遗,而况于邻里乎?正引起下文摹写旧丰一段情景。‘卿士句无著。袁刻六臣注云善本无此句。极是,宜亟删之。”(徐攀凤:《选注规李》,《<文选>研究文献辑刊》第6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201页。)胡克家《文选考异》卷二:“‘况于卿士乎,袁本作‘而况于卿士乎矣,云善无七字。茶陵本作‘而况于卿士乎,亦云善无六字。尤本此处修改乃取五臣五字以乱善,非也。”(胡克家:《文选考异》,《<文选>研究文献辑刊》第4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徐、胡并认为当无此六字为是,但室町本有此六字,室町本既不属五臣系统亦不属李善系统,胡克家所谓取五臣乱善的结论稍欠妥当。《景福殿赋》“纷彧彧其难分”,室町本天头处旁记“《钞》或作郁”。同卷“知治国之俟臣”,俟,室町本旁记“善本作佞”,尤袤本正作“佞”。尤袤本《高唐赋》作“九窍通郁,精神察滞”,室町本无“滞”字,天头处旁记“今(善)本察下有滞字,非。此与五臣合”,考九条本、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无“滞”字。尤袤本《答客难》作“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室町本无“修学”二字,“敏”上画两小○,天头处写有“李本无修学二字”。室町本《东征赋》作“历荥阳而过武卷”,孙志祖《文选考异》卷一谓“《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有荥阳县、卷县,无武卷县,疑‘武字因下文‘原武‘阳武而衍”。(孙志祖:《文选考异》,《<文选>研究文献辑刊》第4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96页。)“武”字,室町本旁记“亻本有”,考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并有“武”字,仅尤袤本无。“亻”为何意,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有过解释,“旁注倭文,又校其异同。其作‘扌者,谓折叠本,即折字之半,指宋刻本也。其作‘亻者,即作字之半,皆校者之省文,与卷子本《左传》同其款式。”(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台北:广文书局,1981年,第803页。)但“亻”当“作”字解,明显与此处意思不符。类似情况还有《西征赋》“俾庶朝之构逆”,室町本“庶”字旁记“鹿,亻本”,意为亻本“庶”作“鹿”,但考现存各本未有作“鹿”者,语意亦不通,或为误抄。再如“良无邀于后福”,室町本“邀”旁记“要,亻本”,即亻本作“要”,考现存各版本,北宋本、尤袤本作“要”,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并作“邀”,奎章阁本注记云“善本作要”。又如“然后陈钟鼓之悬”,室町本“悬”字左侧旁记“亻乍”,右侧旁记“乐”,当为“悬,亻本作乐”之意,考尤袤本即作“乐”。有的学者提出“亻”当异本之意,因“亻”是“异”的发音。作者的标记方式各有不同,现无法确知“亻”是何意,但应是某种版本的省文当无异议。至于杨氏所谓“作字之半”的省文并非“亻”,而是“乍”,通过上文“亻乍乐”即可知。至于“扌”,笔者并未在室町本的旁记中找到表刻本的“扌”字符号,但“亻”“扌”确实常见于九条本等日本古钞本旁记中。“亻”“扌”都应是某种版本的简称,但具体指代何本还未知。
义注包括两种情况。1.注明出处。如《北征赋》篇题下有旁记“善曰:《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作《北征赋》也”,考尤袤本确有此条善注,然“至作”作“至安定作”。2.未注明出处。此种情况较为常见,如《思玄赋》题上,室町本有旁记“玄,道也,德也,作此赋,以修道”,考奎章阁本此处有张衡注“玄,道也,德也。其作此赋,以修道德。志意不可……”可知其出张衡旧注,然尤袤本无此注。又同卷“张平子”名下,室町本旁记“张衡时为侍中,皆恶直丑正,作是赋,以非时俗”,考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等有五臣注“衡时为侍中,诸常侍皆恶直丑正,衡故作是赋,以非时俗。思玄者,思玄远之德而已”,可知旁记当节自五臣注。《风赋》作者“宋玉”名下,室町本旁记“宋玉,屈原弟子,郢人也,为楚大夫。襄王骄奢,故玉作此以讽之。《史记》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考现存各本,可知此段注文乃融合李善与五臣注而成。再如《北征赋》“何夫子之妄讬兮”,室町本“夫子”旁记“《钞》曰:谓蒙恬也”,此则引自《文选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知出处的注文,如《神女赋》“情独私怀,谁者可语”句,室町本旁记“失梦所在,求可语之人也”。考现存各本,未见此语,不知出处。综上所述,室町本旁记中的义注来源较为多样,包括旧注、李善注、五臣注、《文选钞》等,但多为节引,且大部分未注明出处,应为旁记者学习时所记。
汉字音注的数量较少,《登楼赋》《游天台山赋》两篇较为集中。如《登楼赋》“曾何足以少留”,曾,室町本旁记“在登反”。《游天台山赋》之“台”,室町本旁记“他来反”。以上两条,考现存各本未有注此字音者。其他卷目如《赭白马赋》“马无泛驾之佚”,室町本“泛”字旁记“方奉切”,与陈八郎本同。《幽通赋》“穷与达其必济”,室町本“济”字旁记“叶韵”,考陈八郎本音“跻,叶韵”。同篇“芊强大于南汜”,室町本“芊”字旁记“音美”,考陈八郎本、《汉书》颜师古注并音“弥”,尤袤本音“亡氏”,并与室町本异。《风赋》“被荑杨”,室町本“荑”旁记“徒奚反”,而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荑”并作“稊”,奎章阁本注记作“徒奚切,善本作荑字”,尤袤本李善注有“稊与荑同,徒奚切”。《头陀寺碑文》“耆山广运”,室町本“耆”作“山耆”字,右侧记“鱼衣反”,考现存各本并作“耆”,且无音注。《汉高祖功臣颂》“相国酂文终侯沛萧何”,“酂”,室町本旁记“在何反,或音讃,非也”。考《文选音决》正作“酂,在何反;又音讃,非”,室町本此条音注应自《文选音决》出。还有一种较为特殊写法的音注需要指出,《东征赋》“遭巩县之多艰”,室町本“巩”字旁记“六供”,“六”非指六臣本、六家本,而是“音”字上半部分的省写,形似“六”,即“音供”的意思,然此字李善音“居勇切”,五臣本无此字音注,室町本的“供”音不知何来。再如同卷“佑贞良而辅信”,室町本“信”字旁记“叶,六亲”,即叶韵、音亲,考五臣本音“申”。综上所述,室町本旁记中的音注来源也较为复杂,主要有李善本、五臣本和《文选音决》等,因《文选音决》残缺较多,旁记中既不见于善本又不见于五臣本的音注内容,或即出于《文选音决》。这些音注都将有助于古汉语研究。
(三)避讳
傅刚先生曾说“日本写抄本不会用中国的讳字,现存确定为日本的写抄本,如猿投神社藏弘安本、正安本及宫内厅藏九条本,均无讳字可证。”(傅刚:《文选版本研究》,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第367页。)但在室町本中发现了一些可能与避讳相关的情况,分列如下。通看全本,发现“民”有时径作“民”,如《长杨赋》“遐氓为之不安”,《东征赋》“忘日夕而将昬”,《劝进表》“齐民波荡”(尤袤本“民”作“人”)等;有时则作“人”,如《东征赋》“察农野之居人”(尤袤本作“居民”),《西征赋》“枚疲民于西夏兮”(尤袤本作“疲人”)等。除“民”字外,“世”字情况较为复杂。有直接作“世”者,如《西征赋》“绁三帅以济河”,《荐祢衡表》“前世美之”(尤袤本“世”作“代”)等;有作“俗”者,如《北征赋》“余遭俗之颠覆兮”(尤袤本作“遭丗”);又有作“代”者,如《西征赋》“当休明之盛代”(尤袤本作“盛丗”);又偶作“时”,如《西征赋》“谅遭时之巫蛊”(尤袤本作“遭丗”)。另外,发现一处或为避“渊”改字之处,《洛神赋》“指潜川而为期”(尤袤本“川”作“渊”)。“民”“世”“渊”三字同时出现以上现象,提示室町本底本年代是唐代的可能性较高。
除此之外,還发现“贞”字有6处缺末笔,即《荐元彦表》“则忠贞之义彰”、《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俾忠贞之烈”、《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建兴忠贞公壶坟茔”、《与山巨源绝交书》“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东方朔画赞》“肥遁居贞”、《祭屈原文》“贞蔑椒兰”之“贞”字。除缺笔外,还有一处似为改字:《后汉书·皇后纪论》篇,尤袤本作“简求忠贞”,而室町本“忠贞”则作“忠贤”,考现存各《文选》版本并作“贞”,惟集注本编者案云:“《钞》:贞为贤也”。又,北宋本、尤袤本《非有先生论》作“惟周之贞”,室町本“贞”作“桢”(不缺笔),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同。集注本、尤袤本、陈八郎本《褚渊碑文》作“不能害其贞”,室町本“贞”则作“身”,与九条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同,尤袤《李善与五臣同异附见于后》云“五臣贞作身”,奎章阁本注记云“善本作贞”。除“贞”字外,以“贞”字为构件的其他汉字并未发现缺笔或改字等现象。至于“贞”字的缺笔、改字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考证。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高薇在《日藏白文无注古钞<文选>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曾提及两个问题,其一,“杨守敬的二十一卷本,实际应严格区分为一卷本和二十卷本”,其二,“也有可能二十卷本是原本,杨守敬并没有对其进行影写”(高薇:《日藏白文无注古钞<文选>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献》2018年第4期,第108页。)。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卷古钞本《文选》,著录为“清宜都杨氏摹写镰仓旧钞本”,下文简称“镰仓本”。此本系杨守敬据上野氏旧藏《文选》卷一(温古堂旧藏)所抄,后带回中国,上野本现仍完好保存于日本。学界多习惯将一卷本之镰仓本与二十卷本之室町本合称为“日本古钞二十一卷本”,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明确将此二本分开叙述,分别题名为“古钞文选一卷(卷子本)”和“古钞文选残本二十卷”,显非同本,不应合称,更不能将其视为同一个版本进行探讨,亦不可将镰仓本的结论移作室町本的结论。另外,黄侃、屈守元等先生在提及该本时,并云“影抄”“影写”,(黄侃于《文选平点·文选目录校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中云“杨守敬影抄日本卷子本(后省称钞本或抄)有卷第一”。屈守元在《文选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126页)中曾说“杨守敬记录在《日本访书志》中的这个无注三十卷本的残帙二十一卷,曾由他并其旁注、标记一齐影写带回中国”。)学界因而普遍认为室町本与镰仓本一样,均为杨守敬影写回国。但据现存实际情况考察,室町本系日本古钞原本的可能性较大。1.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序》中云“藏在其好古家者,不可以金币得。属有天幸,守敬所携古金石文字,乃多日本所未见者,彼此交易。于是其国著录之书糜集于箧中。”(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第2页。)杨守敬当时曾以古金石文字与日本收藏家进行过交换,不排除曾收得室町本原本的可能。2.同系杨守敬从日本带回的古钞本《文选》,镰仓本明确被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著录为“清宜都杨氏摹写镰仓旧钞本”,室町本则被著录为“日本室町初年钞本”,若室町本也为摹写,为何著录中无标注?3.据字迹判断,室町本与摹写的镰仓本相差甚远。4.日本时至今日也并未发现室町本“原本”的蛛丝马迹。5.前辈学者们或因卷一(即镰仓本)为摹写本,而又误以为一卷本的镰仓本和二十卷本的室町本为同一版本,所以才认为室町本亦为摹写,殊不知两本并非一本。
屈守元说黄侃和高步瀛两位先生据室町本校勘过,并将成果体现在《文选平点》和《文选李注义疏》中。然《文选李注义疏》只完成了前八卷,其涉及的古钞本并非室町本,而是镰仓本。而黄侃《文选平点》确实保存了室町本的校勘成果,但存在四点问题。第一,校勘成果不全,仅见于《长杨赋》至《江赋》诸篇。屈先生怀疑“耀先先生(黄焯)所传壬戌平点本是校对未完的本子”(屈守元:《文选导读》,第134页。),其说或是。第二,《文选平点》卷首的《文选目录校记》中注明了每卷的古钞本(包括镰仓本与室町本)存佚情况,但与现存室町本相比,缺了两卷,即第四十六卷和第五十七卷下未标记“抄有”字样(黄侃平点、黄焯编次:《文选平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9、54页。),不知为何。第三,校勘不全。在《长杨赋》至《江赋》诸篇中,出校的异文只有小部分,绝大部分异文并未出校。第四,有校勘错误。如黄侃《文选评点·西征赋》“班述陆海珍藏,张叙神皋隩区二句,钞本海下、皋下皆有之字”(黄侃平点、黄焯编次:《文选平点》,第37页。),然检室町本,“皋”下确有“之”字,然“海”下并无“之”字。盖因“陆海”二字右侧恰为前一句正文“漕引淮海之粟”,黄先生或因看错行导致此校勘错误。虽然如此,黄氏的《文选平点》仍有其校勘价值。因某种原因,室町本中的部分地方现已模糊不清、甚至空白,而在黄氏校勘之时,这些地方尚保存较好,故可作校补之用。如黄侃《文选评点·西征赋》“有褰裳以投岸句,钞本有作或”句,检室町本,“有”字处已模糊难辨,但可确定不是“有”字,正可借黄氏校语知室町本此处作“或”。再如“想赵使之抱璧句,钞本抱作把”,检室町本,此处已为空白,可借黄氏校语补。然黄氏此书保留室町本内容有限,着实可惜。
二 室町本《文选》的底本探讨
关于室町本的底本问题,学界存在三种说法。(何维刚先生在《试论杨守敬旧藏<文选>室町钞本的异文与来源问题》(《汉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59页)一文中总结室町本底本来源时提到一种说法,即“森立之以为从李善本单录出正文”,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森立之此话是针对上野本(卷一),即下文所谓镰仓本而言,并非针对室町本,详情见下文。)1.六朝说,以杨守敬为代表。杨守敬可谓是我国最早研究室町本之人,其在《日本访书志》卷十二中依据纸质、字体,提出室町本是元明间钞本的说法。至于其抄写的底本,杨氏云“盖从古钞卷子本出,并非从五臣、善注本略出。何以知其然?若从善注出,必仍六十卷。若从五臣出,其中文字必与五臣合。今细校之,乃同善注者十之七、八,同五臣十之二、三,亦有绝不与二本相同,而为王怀祖、顾千里诸人所揣测者。又有绝佳之处,为治‘选学者共未觉,而一经考证,旷若发蒙者。……其中,土、俗字不堪缕举,然正惟其如此,可以深信其为六朝之遗”。(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第802—804页。)2.隋唐说,以向宗鲁、屈守元等为代表。向宗鲁认为此本“既不出于李注本,也不出于五臣本,那末,它一定源于隋唐旧本,即李善未注以前之本。”(屈守元:《文选导读》,第130页。)屈守元在《文选导读》中对此表示赞同。无论是六朝说还是隋唐说,其共同点都认为室町本是李善未注之前的本子,而非从某后世注本系统中摘出正文而成。3.钞自集注本说,以游志诚为代表。游先生因旁记中“间有日本注音及钞注”,认为其“盖钞自集注本者”。(游志诚:《文选综合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旁记中引用《文选钞》确实可以说明室町本的部分旁记是钞自集注本的,但并不能由此证明正文亦钞自集注本,此外游先生还提及邱棨鐊《日本宫内厅旧藏钞本文选出师表卷跋》一文作为佐证,但邱先生文中所记的日本宫内厅旧藏钞本并非室町本,因此“钞自集注本说”证据不足。
笔者基本赞同杨守敬、向宗鲁、屈守元等先生的观点,即室町本反应的是早期《文选》面貌,原因前人多已论述,在此仅补充若干条佐证。《射雉赋》“聿采毛之英丽兮”句下,徐爰旧注云“一本聿作伟”,考室町本正作“伟”,与李善前之旧注作者徐爰所见版本吻合。《高唐赋》“当年遨游”句下,李善注:“一本云:子当千年万世遨游。未详。”考室町本此句正作“姉当千年,万世遨游”,与李善当时所见之他本吻合。《祭古冢文》“水中有甘蔗节及梅李核、瓜瓣”,李善注云“一作辩字,音练”,考室町本“瓣”作“练”,右下角旁记“瓣”字,现存诸本无有作“练”字,室町本之“练”字,与李善当时所见之别本当有一定关联。《赭白马赋》“双瞳夹镜”,夹,室町本作“侠”,九条本旁记云“《决》作侠,古合反”。《求自试表》“此图圈牢之养物”,室町本“养”作“豢”,《文选音决》作“豢音患。或为养,非”。以上两条室町本所见均与唐《文选音决》同。类似之例还有许多,以上诸条均可说明室町本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的至少是唐时《文选》的面貌,有可能更早,但具体时代现在很难下定论。
与室町本底本密切相关的是其与李善、五臣系统的关系。杨守敬认为更近善本,而向宗鲁、傅刚、何维刚等认为与五臣本更为接近。(何维刚先生围绕此问题将室町本与陈八郎本、奎章阁本、明州本、胡克家本进行对照,详情可参看《杨守敬藏日本古钞<文选>之类目、注记与异文——以“赋”类为讨论重心》(《书目季刊》,2015年第3期)。)《文选》版本十分复杂,有写本、钞本、刻本之分,亦有李善、五臣、陆善经等注释本之别。不仅各个系统之间存在交织的内容,即使每个系统内部的各本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究竟谁能代表所属系统,莫衷一是。之所以同一个问题得出了不同结论,盖因杨守敬与傅刚等先生所用的校勘底本、参校本不同所致。如《答客难》“安敢望侍郎乎”句下,室町本无“《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其天头处有旁记“《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今按:《钞》、《决》、六臣有此二十七字,李本无。”然考尤袤本却有此二十七字,且奎章阁本注记曰“善本无菑字”(奎章阁本此句“无害”下有“菑”字,其他与尤袤本同。),并未云无此二十七字,奎章阁本为六家本,其中的李善注部分以北宋国子监本为底本,则北宋国子监本当亦有此二十七字。由此可见,室町本旁记者所见之李本与现传之李本已截然相反。那么楊、傅结论截然相反也就说得通了。在研究《文选》版本时虽应对写、刻本进行纵向的源流梳理,但也应明确写钞本与刻本分属不同系统,尤其是梳理某版本的底本源流之时,应先在该系统内部进行一番深入研究,再作纵向地跨系统观照。就室町本而言,它属于写钞本系统,首先应将其置身于写钞本系统中加以探讨,若其反映的确是隋唐时期的《文选》面貌,那接下去需要考虑地就不是它的底本更接近于善本还是五臣本的问题,而是善本、五臣本,何者受其影响更多的问题了。
三 室町本《文选》的文献价值
室町本中确实存在一些因抄写造成的讹误,如《为石仲容与孙皓书》“载籍既记其成败”,室町本“载”讹作“戴”;《出师表》“当奖帅三军”,室町本“帅”作“师”,但这并不影响其价值。黄侃先生于徐行可先生所藏室町本之卷子本卷六末有跋语云“逸珠盈椀,何珍如是!行可能藏,侃能校,皆书生之幸事也”。(屈守元:《跋日本古钞无注三十卷本<文选>》,《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33页。)向宗鲁先生也评此本为“一字千金”(屈守元:《文选导读》,第130页。)。由此足见室町本《文选》版本价值之高。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室町本虽为元、明时代之钞本,但其所据底本应为六朝隋唐时的本子,更接近萧统《文选》原貌,可与其他古钞本一起,共同助力于《文选》版本源流演变的梳理。
第二,室町本保存卷目数量较多。现存诸种三十卷本古钞白文无注本全系残本,且大部分仅存若干叶、若干卷,如上野精一氏藏卷第一、猿投神社藏正安本卷一、猿投神社藏弘安本卷一、宫内厅藏古写本卷二、冷泉家时雨亭文库藏卷二、静嘉堂文库藏卷第十、日本古钞本五臣注《文选》卷第二十、观智院本《文选》卷第二十六等,而室町本存二十卷,占全书之三分之二,存卷数量仅次于现存二十一卷的九条家藏本。
第三,室町本保存了部分亡佚文献。室町本旁记中保存了《文选钞》《文选音决》、集注本编者案等内容。如《北征赋》“何夫子之妄讬兮”,室町本“夫子”旁记:“《钞》曰:谓蒙恬也。”《对楚王问》“阳春白雪”,室町本旁记:“《钞》曰:白日,一名白雪……”可见《文选钞》此处作“阳春白日”。《石阙铭》,室町本卷名、篇名并作《阙铭》,旁记:“《决》曰:阙字上有石字。”《唐钞文选集注》今存部分无以上诸篇,室町本则将其保留下来,可谓弥足珍贵。
第四,室町本在典籍古式上保留了可贵的校勘资料。如《九歌》的《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诸小题皆在文后,而现存各本皆在文前等。前文已详述,此处从略。
第五,室町本可订正后世刻本的讹误,验证清代学者的校勘成果。如《与山巨源绝交书》,现存诸《文选》版本并作“少加孤露”,胡克家《文选考异》卷八谓:“何云:《晋书》作‘加少。案:‘加少是也。各本皆误倒。”(胡克家:《文选考异》,《<文选>研究文献辑刊》第44册,第445页。)孙志祖《文选考异》卷三亦云“于文义当从《晋书》”。(孙志祖:《文选考异》,《<文选>研究文献辑刊》第41册,第222页。)考室町本此处正作“加少”,可证现存版本误倒。再如《北山移文》,现存各版本并作“驰烟驿路”,黄侃《文选平点》卷五“先叔父尝语焯云:‘路或‘雾之讹。盖‘雾先讹作‘露,再讹作‘路。而驿路又属常语,遂莫知改正也。检《王子安集》,‘驿字每作动词用,则‘驿雾与‘驰烟为对文,非与‘山庭为对文也。”(黄侃平点、黄焯编次:《文选平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0页。)徐复《后读书杂志·<文选>杂志》亦引黄侃所说作“驿雾”,并引“影宋本《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引《金陵地记》,所举孔文首四句,正作‘驰烟驿雾,知宋人所见本,尚有不误者。”(徐复:《后读书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4页。)考室町本,此处正作“驰烟驿露”,黄侃先生推测极是。
About the Selected Works of Muromachi Edition from Japan Stored in Taiwan
WANG Wei
Abstract: The ancient manuscrip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elected Works edition, their existence has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uniqueness, and ha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study of edition of the Selected Works. In 1884, Yang Shoujing visited Japan and brought two editions of the Selected Works from Japan back to China. Previously, scholars used to regard the two editions as one, and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copied by Yang Shoujing. In fact, they are two different editions, one of which is Kamakura edition and the other is Muromachi edition. They are stored in the “Palace Museum of Taiwan” now. The Kamakura edition was indeed copied by Yang Shoujing, and the Muromachi edition is very likely to be the original. According to the format, side notes, taboos and other content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original of this edition must be in the Tang Dynasty,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in preserving the ancient forms and lost documents, correcting errors of edition.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the Selected Work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cademic discussion. However, in the research, although the source and flow of the written and engraved edition should be sorted out longitudinally, it should also be clear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ritten edition and engraved edition. We should first conduct an in-depth study within the writing edition, and then make a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ngraving edition, then we can go further from the historical reality.
Keywords: Muromachi Edition; the Selected Works; ancient Japanese manuscripts; Yang Shoujing
【責任编辑: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