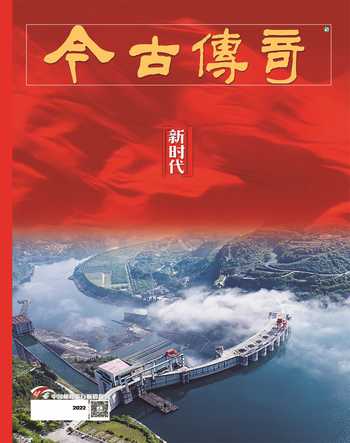一封来自345信箱9分箱的信
邓淑文
亲爱的哥哥、嫂子、姐姐、姐夫:
你们好!
我5月18日在武昌坐上去成都的火车,一路辗转,终于在22日的日落时分回到了家。一打开门,就看到单位同事给我送来的加急电报,它正静静地躺在我家的门缝里,距离它发出的时间却已经过去了整整3天。
看到电报,得知母亲在我离家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撒手人寰,前尘往事如繁星点点,一并涌上心头。我禁不住肝肠寸断,泪如雨下。
母亲出生于辛亥首义前夕,正是国家战乱频仍之时。她家境尚可,从小略读诗文,通晓礼义。奈何时运不济,命途多舛。20世纪30年代,卢沟枪声,惊醒神州晓月;日寇铁蹄,踏破鄂南山村。民无宁日,颠沛流离。日军强行占领了汀泗古镇,并逼迫父亲做维持会长。父亲不愿做日本人的走狗,偕同全家流亡。母亲怀抱8个月的弟弟也一同踏上了逃亡之路。
逃亡路上大家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本已苦不堪言,偏又遭土匪劫掠,财物被抢,父亲和弟弟被害。父亲死时年仅32岁,祖父、祖母年迈体弱,一家七口全系于母亲一人。寒蝉凄切,流水呜咽,我虽年幼,但此情此景仍记忆犹新。
疾風起而识劲草,严霜降而知红梅。母亲擦干泪水,结茅庐于废墟,卖茶水于车站,开小店于街市,摄影像于乡间。为生计之所迫,历人世之磨难,饱受欺凌,含辛茹苦,艰难度日。
在如此艰苦且战火不断的年月里,特别是身在“女子无才便是德”意识仍然浓厚的旧中国,母亲坚持送我们到学堂读书。有人劝母亲,家里困难,两个女孩子就不用送去读书了。母亲不为所动,说女孩子也要读书识礼,知道天下大事。
黄河九曲,滔滔东去;磨难千种,苦尽甜来。1949年,解放军来到了汀泗,古镇焕发新的生机。母亲深感共产党的恩情,经常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当年,我从武汉医学院毕业后,本已分配到北京工作。我想着,终于可以一解几年的相思之苦,好好和男友浩南团聚。到北京报到半月后,我才得知浩南被核工业部分配到甘肃去工作。当时,我国已经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作为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的毕业生,为了我国国防工业的强大,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遭受战乱分离之苦,他应该担负起这个光荣的使命。战场在哪里,他就应该在哪里。我虽然不是科研技术人员,但那里也需要医生。更何况我不想和他两地分居,于公于私都应随他一起去边疆。来不及和家里请示,我立马给单位写了请愿书,坚决要求到边远地区去工作。就这样,我和浩南在甘肃的戈壁滩上成了家。母亲事后得知我去了那么远的地方,而且是一个连通讯地址都保密的地方,虽然心里很挂念,但想着我们都是国家的人,是党的人,党让我们到那里去,那就一定要支持,再难也要去。
去边疆之前,在我的心目中,西部是那样的神秘,那样令人向往。明朗的天空,无边的绿毯。羊儿悠闲地吃着草,骏马在肆意地奔驰。草原上五颜六色的野花星星点点,生机勃勃。这种情境是多么美丽,如一首绮丽的小诗,又似一幅美丽的画卷。
然而,我并不知道迷人的西部还有着狰狞的一面——大戈壁。那儿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人烟,天和地的界限浑黄一体。住的是地窝子,睡的是自己用木板钉的床,吃的是窝窝头,但大家生活都过得很充实,工作热情极为饱满,人人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心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中国核工业能够自力更生而努力工作。
1968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小军出生了。当时,母亲已是近60岁的人了。得知我工作和家庭无法兼顾,她执意要到甘肃来帮我带孩子。一个小脚老太太独自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从汀泗到武昌到西安再到兰州,又坐了三天汽车,才到我们所在的基地——戈壁深处的一个小绿洲。
一到我们的宿舍,母亲来不及休息,就抱孩子、换尿布、煮米糊,忙个不停。从此,在这大漠深处,我们有了稳固的后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无论多晚回家,总有一盏明灯在我们心中闪烁,那就是母亲带来的温情。
母亲是一个非常和善且好学的人。我的同事们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而母亲则是一个说着咸宁方言的老太太,但她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和左邻右舍毫无障碍地沟通、交流。她甚至还向其他家属学会了做四川泡菜、山东煎饼。闲暇时,她会做棉袜、纳鞋底。因为识字,有一些文化,家里订的报刊杂志她期期都看,好的文章还读给孩子们听,督促他们学习。
就这样,母亲陪伴我们在戈壁滩上呆了整整10年。直到1978年,浩南奉调到四川,母亲又随同我们一起到了四川。这里仍然是人烟稀少,只有一座又一座连绵不绝的青山,但相比甘肃,无论是气候环境还是居住条件已经好了很多。母亲在四川只住了一年就决定回湖北,一是看我这里条件已经改善了很多,不需要再担心;二是年事已高,思乡情切;三是在外10多年,家里其他子女孙辈都没有亲自照顾,希望能够回家再续亲情。
母亲返乡这几年,日常的生活起居等都有赖于大哥、大嫂和姐姐、姐夫照料,我虽有书信问候和生活资助,但山高水远,无能为力,心中常怀愧疚之情。前年小军高考,在我的要求下,他考上了华中理工大学。我希望他毕业以后能够留在湖北,代我为母亲尽孝。
今年年初,我从大哥的来信中得知母亲病重,就计划着今年暑假带孩子们回咸宁一趟,到时候如果浩南工作不忙,也一起回去。但没有想到母亲病情变化太快,浩南身为项目技术负责人,工作丢不下。我请了15天的假,一个人赶到了咸宁。
母亲看到远方的女儿回家了,强打起精神,用干瘦的双手紧握住我的手,一边喘一边说:“你回来了,听说浩南前段时间体检查出肝不好,要注意啊!”我病中的母亲啊,哪怕是病得起不了床,心中牵挂着的仍然是儿女。
15天的假,去掉路途时间,只有短短的5天。这5天,我日夜侍奉在母亲床前,眼看着母亲的生命之火越来越弱,我心如刀绞。但我的假期已满,纵有万分不舍,也到了不得不分离的时候。
18日早上,我坐在母亲床头,久久不愿离去。因为疾病的折磨,母亲已没有力气再多说一句话。但她仍然努力向我微笑着,用手示意我赶紧走,不要误了火车,就像以往无数次我离家赶火车的时候一样。但这一次,母亲再也无法送我到车站,只有女儿带着无限的思念和哀伤踏上漫长的路程。
母亲已逝,但亲情仍在。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母亲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但她始终乐观、坚韧,恪守古训,奉养公婆,养育儿女,以柔弱之躯坚强地面对家庭变故,以一己之力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庭。子女孙辈都成了新中国的建设者,她的优良品质代代相传,融入到了我们的家风中。
路途阻隔,加之天气炎热,电话得知母亲已葬,随信附上现金500元,以补偿母亲丧仪所需。有劳哥哥、嫂子、姐姐和姐夫了。明年清明我们全家会回湖北为母亲扫墓。到时再见,一叙亲情。
妹新惠及浩南敬上
198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