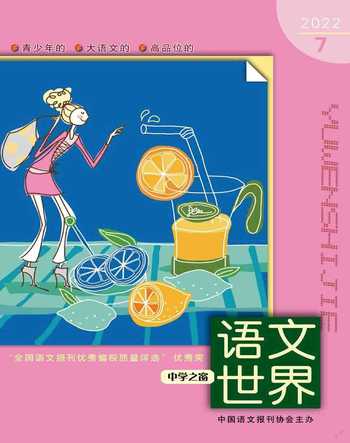情疏迹远只香留
南方的风总是不如北方的纯。正八月,山石上附的草还是青色的,灌木的叶子也同夏天一样,郁郁葱葱地堆叠在一起。唯有一阵西风拂过时,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桂花浓香,才提醒你秋天到了。
爸爸的故事不算长,却也不短,从哪里说起呢?
我的爸爸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湖北省咸宁市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母在山下有一小块地,爸爸很小就帮着大人和哥哥们打理田地,翻翻土,采采果子什么的。
爸爸上学时不穿鞋的,或者说整个乡村的人都不习惯穿鞋。一个春日,爸爸同往常一样,光脚走在土路上,春雨连绵,河道长了许多,连带路上都是些泥水坑。一脚踩进泥水里,突然一阵酥疼从脚底直插心底,整个人倒下去,几乎要晕过去。好一会儿才爬起来,往水里伸手去掏,又被刺了一下,才找到个去年的老黑菱角来。跌跌撞撞地半跑半跳到小河边,拿水把泥冲掉。脚心被菱角尖扎了个深深的眼,还冒着血,周围全是红肿的,几乎要肿成一个球了。好在这儿离家不远,爸爸又强忍着痛,一瘸一拐地回家。祖母给他找了乡医,每次换药像一次受刑的开始,一个多月仍不见好,反而肉越烂越多,越来越疼。直到后来去了城里的医院,才长出新肉来,渐渐好了。
爸爸在城里上的中学。学校在很远的山上有一片茶园,常常叫学生们去翻土,除草,也大抵算得上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实践”。六七月的早晨天亮得很早,爸爸和他的同学们却在太阳刚探出地平线时便出发了。一杆铁锹,两条腿,到十点左右的时候才将到茶山。夏日的太阳是最毒的,没有一丝云,没有一丝风,热气毫无遮挡地喷下来。连茶树叶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只有蝉喊得欢,叫人一阵阵头发晕。杂草交错在一起,根系发达牢牢地抓住大地。把手伸进灌木枝中,抓住草茎,不顾有多刺手,用尽全力,双脚蹬地,往后一扯,总算拔下几根来。等拔完全部的草,太阳已经快到头顶了。短暂的间隙之后还要翻土。一锹一锹地落下,重似千斤。许多男生都禁不住脱了上衣,继续卖力地干。回家之后后背红痒一片,有的甚至要脱了皮。
爸爸一边学一边干活,成绩也很好,考上了咸宁高中,后来又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京和咸宁就大不相同。爸爸先是被林立的高楼大厦惊掉了下巴,又极其不习惯冬天光秃秃的树和一点也不留情面的北方朔风。他第一次用北京的暖气就深深地“迷恋”上了。在南方,温度虽远没有北方低,但一阵阵的阴雨和湿冷总使人怎样都难受。北京屋外虽冷,但在屋里围着暖气一坐,整个人都是暖和的。
还有一个令爸爸一见钟情的东西,那就是图书馆。一排排素白的书架,摆满各种各样的著作和古籍。陈旧的油墨香气,浅浅的,沁人心脾。虽然大部分是土黄和青蓝色的,但在爸爸眼中就如彩虹一般五颜六色。从此,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图书馆,他还十分爱买书,买完之后要有仪式感地在扉页上写上自己的大名、买书的日期和书店。我曾问爸爸,问他买了这么多书都看了吗,又或者是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书。他也半戏谑地笑着告诉我:“大部分都翻过一遍吧,有些认真看过。小时候什么书都没见,过到北京来看见这么多书自然要使劲买了。当时生活费除了吃饭之外,我几乎都买书了呢!”
后来爸爸转专业去学马列主义,为了出国留学又从头学了德语。在德国一边学德语一边看《资本论》,孜孜矻矻,坚持不懈,读完了硕士和博士。
爸爸现在是个专门翻译校对马列著作的“译员”。工作可以大致概括为写稿子和审稿子两部分,却常常要写到很晚,或者周六周日自愿到单位加班。有一次他在家里看稿子,我悄悄过去瞥了一眼,是全德文的,还有爸爸在旁边五颜六色的德文圈画批注,比我语文书上的笔记还多不少。我曾问过他,又苦又累工资还挺少的,为啥要选择转专业干这一行啊,他十分平静地一边看着电脑上的文章一边对我说:“说来这也不完全算我选的干这一行,但是国家的这活儿总得有人干不是?我不干不也得有其他人干吗?”
爸爸是25岁干的翻译,如今也翻译23年了。爸爸自己近一半的年纪都奉献给了马列著作。他孩提时在生活中学会了坚韧,少年时在劳动中学会了努力,青年时在学习中学会了勤奋和热爱,这都是他能把这一份辛苦而重要的工作堅持下来的原因。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却又是不凡的。
顺着桂花的甜香再往山上攀去,桂花终于露出脸来。娇小的四瓣白金色花,一串一串地挂在枝上摇曳,却又有些羞涩地躲在油绿色的带齿叶片里。越往山上爬,桂树越多,桂花越密,桂香越浓。
爸爸常说,家乡咸宁是名冠天下的“中国桂花之乡”,今儿我看了,确实是多是美。您也不愧是咸宁人,同桂花一般将金子般的小花藏在叶子后,不骄傲,不张扬,不贪财图利,虽离着很远却能嗅到一缕醉人的甜香。

徐小墨,性格不算开朗,意志不算坚定,神经质心理。醉心京剧和昆曲,三年戏龄。钟爱古琴的古筝生。多少和体育有点仇的人。喜欢古诗文和那些先生文人们,尤其是魏晋和近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