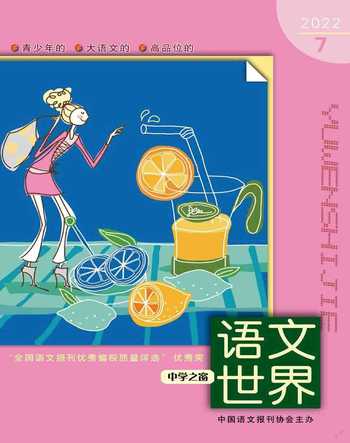相逢的会再相逢
丹飞
在讲述的河道里,故事在表情达意的淘洗下打磨掉辎重,缀以水流的形状,浣衣的倒影,过度的光华。现在掌握这枚卵石的,是一双剔透的小手。手伸展在氤氲的光里,光汰洗在潺湲的水里,水汪着这枚故事里的鹅卵。新的女孩到了家里,母亲总要演说一番我的光荣史的。一切历史都是光荣史,这条心理治疗上的金科玉律运用在我身上倒是恰如其分。当然,是在母亲的表述里。
在我的女孩跟前,母亲其实自然地变得寡言少语。母亲不是不想说话,只是怕说得对不到对方胃口,反坏了我的好事。“妈,往后跟她多聊聊,聊聊我的童年。”送别女孩,我这样宽慰母亲。母亲眼睛一亮,再面对“她”时,就多了许多话题。只是,隔三差五地,母亲面对的女孩会变幻一下面孔:头发短短长长,眼仁大大小小,笑颜深深浅浅。
她跟在我后面蹭到家里时,母亲正轻一下重一下地往上打水。母亲坐的井台历史不算久长,但也有些年头了。1991年,我與父亲一锹一锹地往下挖,钢管搭成的三角架上吊着滑轮,渐挖渐见湿润的土方一簸箕一簸箕地运到井台外面去。时还幼小,但还抱着信念,希望给离家数日就要回返的母亲一个惊喜,十指指根、指中、指肚打起水泡,旋即磨破,水迹未干,新的水泡又忙不迭在废墟上安营扎寨,疼和疲累都藏着掖着,在平和外表的成功伪装下,心里早疼得咧开血红大嘴。
青蛙好水,第二天晨起下井,总能见到井底三三两两的青蛙家族,格外安静地蹲伏着,鼓着一对金鱼眼,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这个从天而降的天神。其实,我比青蛙要胆怯,心里总悠着,生怕一个不小心,脚板或者手指触碰到哧溜水滑的寓言主角身上。坐井观天,青蛙的老祖宗早就遗下这样的笑柄,也算从另一个侧面记载了青蛙与人类的交好史:无论如何,青蛙很早就作为人类的审美对象存在着。
我不知道那些时赖在我家井底不愿远走的蛙们如何看小了天与地,我却是感激小小井口为我圈定的一角天衣的。平素心大,天宇空蒙,是闲不下心来望望头顶那片广袤的天幕的。“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白云苍狗,斯须变幻,却没有片刻心境留驻。井口取景,留出一方舞台任蓝天游走,雾霭流岚,真是不可多得的良辰美景。因为流连,常常耽误了手头动作频率,不用创可贴,蓝玛瑙束上寒冰玉,正好比伤口上敷了一剂夏日清凉,爽口也爽心。往日匆匆忽略的景致此时拥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甚至只有在此时,我才为自己平素的不察而脸红。
我家地势高拔,井址就选在后院一侧,富含铁质,土壤颜色格外红润,却板结而坚硬,天公作美,才挖到两米深,就有水源源不断地渗透上来,穿过土壤颗粒的缝隙,密密匝匝地浸润井壁,缘于此,青蛙才愿意舍广阔新天于不顾,而趋向这一方苦夏里的清凉宫。从这个意义来说,非但看不出蛙们目光短浅到哪里,反倒衬托出人类的武断和片面,见到风就是雨,猜不到青蛙坐井观天的个中缘由。当然,我们更可以窥透人类良苦用心的是:这一既定俗语的“约定俗成”又是人类表意策略的一次成功策动。动物界越懵懂痴傻,越是烘托出万物灵长的冰雪聪明。打井的我是想不到这些的,只有在疲累过后的夜里,躺在新絮的被窝里,做完了少年常做的好梦,完全放松了身体,悄然醒来后,才会有这样的奇思异想。当时的我正为发现水漫痕迹而欣喜不已。不可思议的是,那么高的地势,却只掘进不到三米,就有源头活水汩汩滔滔,清冽甘甜,润喉,养眼,还润泽心田。奇妙的是,三伏天气,方圆十里水枯,我家的水井却独葆甘泉,多少人家来取水,却总不见水井有浅下去的表情。那时候极喜欢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想不到,正是一口井,为我生动诠释了无欲、有容的哲学。
想给母亲惊喜,没有进门就脆脆叫一声“妈——”像往常常做的那样,等母亲一阵风似的抢过来拉着我的衣襟上下地看,“又瘦了!”母亲摩挲着我两颊,心疼不已,怜惜不已。牵着我进门,安坐着,看我水花四溅地择菜,听刀落砧板的合辙旋律,迷醉于我翻炒绿蔬红荤的恣意姿态,母亲的目光追着我的眼睛、脸颊、手脚,痴迷而忘我,全然忘却要帮手,而我身旁还有一个水灵灵的小女子。
知道母亲的忘情,我强忍着大颗大颗上涌的泪滴,情绪释放到洗择翻炒的行为举止间。洞察秋毫,却还要佯作不知,不忍母亲察觉我的知情,怕惊扰母亲对我一如既往的溺爱。
耽溺于情感的海毕竟不是多美妙的事,后来,我就要求母亲在我做菜时帮我一把,也请母亲放宽心,女孩子家既然爱您儿子,对您当然也热爱得不得了,您说什么话都不会得罪她,母亲这才宽了心,手没闲着,与她一起择菜递水。
一个是我深深爱的母亲,一个是我不知深浅爱着的她,两位女性头碰头,手不停地翻飞,口也闲不着,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不用担心冷场——因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兴奋点:我。想想如何欣幸,七尺男儿,扶不起家业,扛不起天下,却被两个好女人热爱着。
这一次我悄没声息地蹑足穿过客厅和走廊,她就紧随身后,站在母亲背后母亲才发现,撂下辘轳摇柄,忙不迭起身,握着她的手,宝贝一样端详着——然而不幸,内心深处还是聚焦在我身上。
母亲怪责我不曾打声招呼就回家,害得她没来得及整理家务,“团团糟”,母亲说。
她手小。不会家务,却总要在母亲面前表现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屡试而不爽。至于回头嘤嘤地哭娇嫩的肌肤因为择菜弄糙了也是必然的。我往往要一下一下地抚摸纤纤素手,一边柔情蜜意,劳动的手是最光荣的手,再劳动也无法损抑你的美,再粗糙也是精致的美,再说,过不了几天就又油光水滑了,这么一番拨弄,她总是耐不住要破涕的。我却窝囊透了: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女人这么做作,拎不起放不下的,却又不能重说,女人的眼泪比原则锋利多了,我的心脏虽然结实,也耐不起一再的刻画。
水井和辘轳总是她喜爱的物事。哪怕她是乡下人家出身,也要做出一副惊讶体态,呀,好好呀,她咋咋呼呼。一边身体力行,挽起袖子,鸦雀一般惊飞井水——落到盆里的水少,溅到身上脸上洒到井台上的水多。一边失败,却是一边越战越勇,神态夸张,动作夸张,不知道她心里是不是也夸张得吓人:不行,脸丢大了,水都打不好。然而,她总还知道掩饰得好,愈是怀揣肚子,愈是要装作若无其事。毕竟,不能虚怀若谷,总要藏掖小肚鸡肠。
母亲却是欣慰的,她再变化面容,总是好女孩模样。知冷知热,体贴儿子,也知道在自己面前勤加表现,这样的女子,总归是好的。儿子跟了这样的女子,吃亏也吃不到哪儿去。这么想望,不管带了谁家的女子回家,母亲都不意外,心境格外平和,我与她心里是不是深爱彼此,开始还是母亲关注的焦点,后来却主动放松了标尺,儿孙自有儿孙福,母亲想开了,知道再忧惧,儿子的爱情终归要儿子自己把握。母亲也明白,女子的好与女子和儿子的爱是两码事,自己完全可以认真享受好女子归家带给自己的愉悦,而把男女恩爱交给儿子和女子自己细细体味、好生咀嚼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