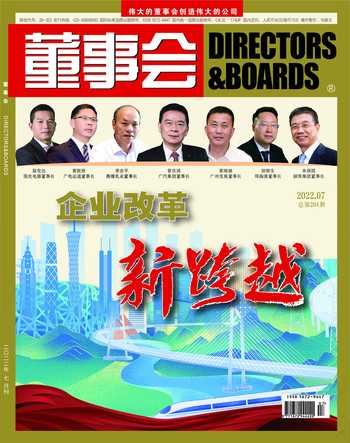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推动资本向善
王骏娴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制度是人类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宏观议题在企业微观主体的具体体现,并以信息披露的方式呈现。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是从道德层面对企业个体的約束,弥补经济和法律在制约个体利益损害公共利益所存在的不足。可持续发展信息具有经济外部性,以描述性、预测性信息较多,同时兼具全球共性和地域特点。可持续发展信息的外部性需从经济学层面解决。建议可持续发展报告独立于财务报告,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准则需给予各国家或地区一定的自主权。
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人类发展史
了解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渊源历史,才能明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
可持续发展并不是现代的产物,它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并发展壮大的智慧,只不过用现代的语言更易于当代人的理解。人类不断地通过与外部的自然环境以及内部的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得以可持续发展。在农耕文明时代,反复无常的自然迫使人们从本性上敬畏自然,使得古人善于观察、总结自然的规律并运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西方的经济思想史中重农学派也是将自然规律引入到经济思想中。在古代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则强调仁义,“利者,义之和也”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古希腊哲学重视内省,提倡正义与美德。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减少了对外部自然环境的依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启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但亚当斯密在早期所撰写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道德情操论》讨论道德的力量,同情和仁慈限制人的私欲,构建一个公平的社会,《国富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讨论个人如何受经济力量的引导和制约,竞争引导自我利益的经济趋向社会福利。《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共同协调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但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个人主义日益增长,农业文明基础的礼教受到挑战,新的道德共识伴随着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人类通过经济发展、道德伦理、法律制度等方式不断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信披推动资本向善
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环境、气候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将资本积累、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将环境、气候作为外部效应和公共物品的范畴。随着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生产引发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资源枯竭等问题,受到广泛争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生态阈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收入与环境状态的关系。经济发展初期,随着收入的增加,环境会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消费者收入的增加,环境会随之改善。但这里存在一个生态阈值的问题,若资源产权不明晰、环境成本的外部性没有内部化,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则经济的增长会使人类社会承受较高的环境成本,超过生态不可逆阈值,将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全球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就存在这样的危机。
无法内部化的环境、气候外部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气候问题可以采取外部性内部化的方式来解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外部性问题都可以采取内部化来解决。气候变化外部性影响范围广、时间长、不确定大,局部均衡分析过于简单化,且气候变化很多问题不能被市场化、货币化,例如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损失、公共健康影响、温升的厚尾效应等。
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及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类社会的内部还存在着诸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贫困等问题。联合国发布的2015年至2030年全球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涉及经济、环境、社会三个方面。这17个发展目标分别是无贫穷、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这些目标体现的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性问题,各个国家会根据自身可持续发展问题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NSDS)。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作用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根据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适用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通过信息披露促使企业践行联合国的SDG目标。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是从道德层面对企业个体的约束,弥补经济和法律在制约个体利益损害公共利益所存在的不足,如同《道德情操论》引导企业个体利益趋向社会福利,推动企业向善和资本向善。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多重特质
具有经济外部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大部分可持续发展信息具有外部性,无法被内部化。传统财务信息属于可以被内部化、货币化的信息,从而用于资产定价。被内部化的信息例如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已有较明确的会计处理规范。由于经济外部性,使得可持续发展信息难以通过会计处理和金融体系,对企业的账面价值或资产价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传统的经济和金融框架下,企业披露可持续发展信息无法直接促进盈利,会导致其缺乏内在动力。
描述性、预测性信息较多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主要是从道德层面对企业进行约束,可定量的信息较少,以描述性的信息居多。这容易导致企业力求披露对自身的声誉有利的信息,而避免披露使其声誉受损的信息,以及产生信息冗余的问题,影响决策有用性。另外一些可持续发展信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气候变化的厚尾分布、可再生能源价格、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政策监管趋势等。企业需要预测影响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因素的变化情况,而预测信息存在概率问题就会降低信息的可靠性及可验证性。这使得可持续发展信息更容易出现粉饰的现象。
既具有全球共性也具有地域特点
可持续发展可以是全体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例如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也可以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欧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欧洲绿色协议》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再如我国颁布的《生态文明改革总体方案》《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每个国家或地区都会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阶段性的社会问题等制定适合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定期进行调整。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是根据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制定的,它既具有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性,也具有地域特点。
如何做好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
可持续发展信息的外部性需从经济学层面解决
处理可持续发展信息外部性的问题,必须从经济层面解决,单纯的金融、会计原理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例如气候变化。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经济学外部性内部化已经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工业文明所倡导的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做法,产生的过度消费和过度生产对人类社会并不可持续。气候变化对生产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温室气体的排放权对发展中和欠发达地区来说是经济发展权;另一方面气候容量对生产力或资本回报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经济发展需要气候要素资产的高效利用而形成的零碳高生产力,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气候和生态友好的消费、技术、资本和生产方式。经济发展迫切的需要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進行转变,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原理(潘家华,2014)。这也是当前绿色金融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如何更准确地定义绿色资产,又如何针对绿色资产落实绿色金融政策,外部性内部化的理论基础已经不能满足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依托气候变化经济理论研究建立起新的绿色金融理论分析框架。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可独立于财务报告
基于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特点,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较难成为财务报告的一部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两者性质不同,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通过会计程序来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济成果的经济信息;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是在经济和法规之外对企业的道德约束,具有经济外部性。两者性质上有本质的不同,较难合并。二是财务报告的受众群体以资产所有者为主,而可持续发展报告是对企业道德层面的约束,受众群体主要以资产所有者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主。三是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要求其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且可验证,而可持续发展信息以描述性和预测性居多,无法达到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要求。可持续发展信息的质量特征多以重要性(实质性)原则为主,企业根据自身的商业模式、经营业绩、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来评估哪些可持续发展信息是重要的,进而对重要的信息进行披露。重要性原则决定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可给予企业一定的灵活性。若要将财务信息和可持续发展信息合并则可能会影响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影响可持续发展信息的重要性。
国际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需给予各国家或地区一定的自主权
从可持续发展信息的特征来看,建议国际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在制定过程中参考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而同时给予各个国家或地区一定的自主权。如同联合国制定SDG,每个国家再根据SDG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NSDS)一样,由于文化背景、经济发展阶段、政治体制等因素的不同,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各不相同,需要根据各自国情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