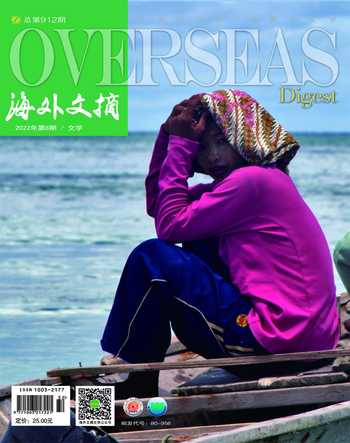我的非典型母亲
邱仙萍

母亲和父亲同岁,今年88 了,双双这样高龄一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人,在农村并不多见。
难怪,小时候我跟在父亲后面,大家都很奇怪:“老邱,你怎么还有这么小的女儿?”我悄悄告诉他们:“我是捡来的。”
我家有四个孩子,哥哥、大姐、二姐彼此间只相差了一岁,母亲一年一个接连生下了三个。而我,和他们竟然相差了七、八、九岁。我的出生对高龄的母亲来说是个意外,但肯定不是惊喜。据说是医生之前没有给母亲结扎到位,等到发现怀上后,孩子太大已经没法流产了,有点买三送一的意思。母亲总回答不上我的生日,不是说成大姐的,就是说成二姐的。生辰更加不记得,一会儿说是傍晚,一会儿说是凌晨。不过老太想起了一件事情:“你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家里着了火,几个孩子玩木屑刨花。老房子火苗蹿得很快,黑烟马上到了二楼窗口。我一把抱起你就往外跑,一路跑到村口银杏树下面才敢停下来。”“那后来呢?”老太说的话差点让我背过气:“我停下后低头一看,哎哟我的妈呀,我手上抱的不是你,是一个荞麦枕头。幸亏,后来你被荣仁叔给救出来了。”
五六岁的时候,村里来了几个耍杂技的,驻扎十几天后,我和大家混得很熟了。我会劈叉呈一条直线,会后弯腰用嘴把地上的花叼上来,会侧翻倒翻筋斗。他们觉得我资质很不错,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去耍杂技,会让我牵猴子,我兴高采烈牵着猴子就跟他们走了。一直到十几里外,父亲他们才追上来把我截回去了。我常想,如果没有给我弄回去,说不定,我可能早就在什么根的大舞台上表演二人转了。
在我们眼里,母亲是个干大事的人,不喜欢儿女情长,类似古代的花木兰。爱猪爱狗爱猫爱鸡爱鸭,远远多于爱她的孩子,我带回去的草莓,说先给她养的狗来福吃,还说来福这狗子是天才,知道草莓哪个部位最甜。母亲喜欢上山打虎、下河捉鱼,不喜欢在家绣花洗衣做淑女。聊到过往,说有一次和大伙去溪里抓鱼,三岁的我半夜醒来,“蝌蚪找妈妈”般赤脚走了三里地,幸亏没有被蛇给咬了。
母亲读书读到十三岁,这在农村算是识字比较多的女性了。早年外公外婆家境富裕,上面有三个哥哥,家里对母亲自是宠溺。和父亲结婚后,她自己考进了邮政局,后来又随父亲去了兵工厂。自然灾害那年,父母响应国家号召回老家,父亲当上了公社书记。考虑到家里孩子多,两个人都是居民户口的话,这点工资难以养活全家,母亲的户口就耽搁下来留在了农村里。原来漂亮温柔的母亲开始学着山上砍树、下地种田,学着和粗壮的男人比拼体力挣工分。在一个个点着煤油灯的黑夜,母亲和奶奶还要看管三个差不多大的孩子。一个哭闹,另外两个也跟着咦里哇啦凑热闹,经常忘记给哪个洗过脚,哪个还没有洗。
对于家里没有男人的女人来说,这一天天的操持、煎熬和长夜漫漫,想必,再柔软的心也会变得无望和暴躁粗粝。
对于年少的我,是不会去研究母亲这些心情的。两个姐姐对我的照顾已经超过了母亲,我对母亲的感情也没有那么亲昵和依赖。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喜欢读课外书,在那个唯有高考才能农转非的年代,看课外书的性质估计和现在玩网络游戏差不多,是被大人呵斥和限制的。我和二姐常躲在楼上看《飘》《茶花女》,看金庸和琼瑶的小说,母亲就在楼下大呼小叫安排我们活计。有一次,她还真的把二姐藏在木头箱子里的几本书烧了。我心里恨得要命,恰巧老师布置了一篇“我的妈妈”之类作文,我写得非常生动感人,把妈妈写得很高大伟岸,结尾是妈妈和我一起上山拢猪草,山洪暴发,为了救我,母亲被洪水冲走不见人影了。老师看得热泪盈眶,把它当作范文贴在墙上。后来家访时,才发现我母亲好好着呢。
从小我就习惯了半夜醒来母亲不在身边。她是乡里的赤脚医生,夜里我家楼下经常有人来喊我母亲。她一边穿衣服收拾药箱,一边让人准备好木盆和热水。方圆二三十里地,母亲接生了上百个孩子,竟然无一失手。每次去学校给孩子打疫苗,她就把我从窗台上揪下来先扎上一针做示范:“你们大家看,一点都不痛的。”
后来不当赤脚医生了,我家装上了村里第一个电话。母亲每天不是喊东家接电话,就是给西家带信,像是一个村的新闻中心。尤其到了冬天,事情特别多,经常四五点钟有电话打来:“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去某某家,让他们好烧水了,我一个小时后就来了。”干嘛呢,是杀猪的人打来的。我妈趿着拖鞋穿上棉袄,一溜小跑。还有妇女生孩子的,老人上医院的,学校读书的,外地做生意的,可忙活了,就差没在家里按个广播站。
12 岁时候,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初中,是全校个子最小的女生。老家和学校有几十里地,没有通车。交通基本靠走,带路基本靠狗,吃饭打冲锋般吼,穿衣基本靠姐姐们留。有一次周六回家和高年级学生扒卡车,結果他们上去了,我个子小上不去,一直被挂了两里地。到了高中,父亲给了我一辆28 寸永久牌自行车。我骑在车上,像是一只鸟停在了树枝丫。有一回去学校经过一段田塍路,我和一头黄牛相遇,它威风凛凛地对我怒目圆睁。我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那头牛箭步上前一个挑角,把我和自行车挑到了旁边池塘里,幸亏水不深,但车上驮着的米和一周吃的梅干菜,全被牛给顶没了。
这些事情,我是不会说给父亲听的,更不会讲给母亲听。反正觉得自己可能是捡来的,衣服脏了自己洗,感冒发烧了自己被窝里捂着,父亲给我十元钱我往往只拿五元。曾经我很想得到一条像同桌女生那样的小花裙,母亲就说:“能给你读书已经不错了,你看村里的女孩子,哪有你书读那么久的,她们早早就出去挣钱嫁人了。”
为了不让母亲以后随便把我许配给村里的什么王木匠啊李铁匠的,我能选择的就是好好读书,自谋生路。以至于到后来,父母和别人说起我,就说:“家里最小的这个,是最不需要我们操心的。”
母亲和我的非常规母女沟通方式,导致我对母亲,也是不按常规出牌。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吵架,母亲晚上收拾东西,絮絮叨叨要回娘家舅舅那边,说明天就去办离婚,她早厌烦这个家了,大不了去街上卖茶叶蛋,给别人当保姆。
父亲坐在凳子上沉默不语,把头放进两只膝盖中间,像只鸵鸟。哥哥姐姐们惶恐不安,着急劝架,拉着母亲不让她走。我这个老幺一步上前,和母亲说:“你走吧,赶紧离婚。我告诉你,你一离婚,我爸立马娶个大姑娘。他为了你提早退休,每个月工资交给你,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的,这么好的男人肯定是外公外婆家祖上积德,你才找到的。现在的男人可不比你们那个年代老实厚道,非但不赚钱,还家暴,外面的世界有你想的这么好这么美吗?”
母亲停下脚步,愣住了,后来哇地哭将开来:“有你这样的女儿吗,这样说你娘,吵架不来劝和,还让我们离婚。”
父亲和母亲在八十岁那年,倒是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把老房子拆了,用了一年时间盖了新房,父亲每天和工匠们一起在工地上忙碌。本来是外包活,不用管饭管烟,但母亲还是按照农村老底子建房习惯,每天中午张罗两大桌饭,每顿都有十几个菜,炖猪脚、烧鸡鸭什么的。房子造了挺大的三层,哥哥、二姐、我和父母,每户人家各分到两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是木地板,有单独卫生间、空调。我的房间比较特别,多了个露台,说可以给我写写东西、喝喝咖啡用。母亲的总结发言像是发表就职演说,说有房子就有归宿,有父母就有家。平时大家即使散得再远,节假日回来了,还能住在一个屋子里,像是小时候一样整整齐齐。
在英国读书的我女儿,假期回来看外公外婆。看着眼前这个两年未见就蹿成高个、正值青春好年华的女孩,母亲竟然显得有点拘谨和局促。孩子临走前,她塞过来一个很大红包:“去这么远的地方读书,一定要自己当心哦。”眼底里,竟呈现出之前对我少有流露的母性温柔。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那个村,名字就叫作“百岁”,居住在那里的人,都是百岁老人,都是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