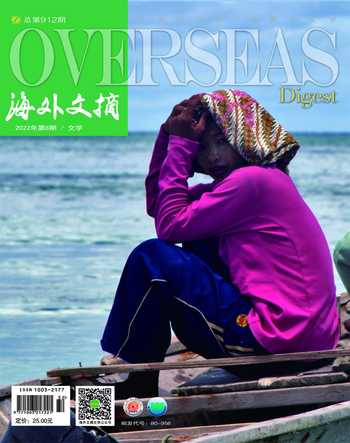我爹

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我知道人应该是有个爹的,但我是没有爹的孩子。
那时村里有诸如婚丧嫁娶的活动,别的小伙伴都由爹带着去,他们可以跟在自己的爹身后肆无忌惮地奔跑嬉闹,而我被自动排除在他们之外,一个人默默坐在人少的角落,一言不发,低着头,看他们捧着鸡腿、炸鱼大口吞咽。
还记得学前班的时候,村里的一个大爹家腊月间宰猪,爷爷被邀请去帮忙,到了饭点,那个大爹喊我也去吃饭,当时小不懂事,也就跟着去了,奶奶可能觉得小娃娃跟着去吃一顿饭也没啥,故而没有拦我。
从我家到那个大爹家很近,只隔着两分钟的路程。他家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三间砖头混凝土结构的平房(当时村里还都是土砖和泥巴混合的房子)。
到他家门口,那个大爹一进去,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大我四五岁的两个堂哥,他们拦在门口,不让我进,两条腿撑开,把门堵得死死的。我灵机一动,从堂哥的裤裆底下钻了过去,当时的我可能还很得意。当我渐渐知晓人事,一回想起来心就疼,就恨不得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丢人,真的给我死去的爹丢人了。
在村子里,我像是一个“明星”,全村的人都认识我。不是因为我有多优秀,也不是我长得多好看,而是因为我是村子里两个没有爹妈的孩子中的一个。
走在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能叫出我的名字,换作别的小孩也就是亲近的几个邻居知道,远一点的同村人是不知道的。
我最常去的是大奶奶家,关于我爹妈的很多信息也是从她口中得知的。她说,你长得和你妈更像,你爹的脸盘子比你大。从大奶奶口中我知道爹是村里读书最厉害的人,妈是村里做豆腐最好的人,当时我们家是全村人都羡慕的殷实之家,一辆三轮摩托车就能证明了。
从大奶奶那里我了解到我爹的些许信息,在一天傍晚,爷爷在火炉边吸着旱烟,那天天气有点冷,十月以后的乌蒙山是渐冷的季节了。
我冷不丁冒出一句,爷爷,我爹是不是读书厉害得很?他没有回答我,而是起身爬上二楼,下来的时候提着一个红色的木箱子。与其说是红色,不如说是红黑色,原本红色的箱子已经让烟熏成了不红不黑的模样。
爷爷打开挂在箱子上的锁,从里面抱出一摞书放在板凳上。我凑过去看的时候他拿起一本数学,是一本初中的数学,上面写着我爹的名字。此前我看见我爹的名字是在墓碑上。
爷爷说,这是你爹的课本,你看上面的字写得多好看,你看这些都是红勾勾。爷爷又拿起一本笔记本,他翻开第一页,我看见一个大大的“奖”字。这是我爹学习优异的证明,也是爷爷引以为豪的存念,他捧着这本笔记本的时候是多么开心,当年我爹把笔记本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也是这样高兴吧。
在这些陈旧的书堆里,我看见一本小小的笔记本,笔记本外壳上的字已经看不清,翻开第一页写着一些字,当时我是看不懂的。但看着那些用水笔写得工工整整的字,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这是我爹写的,比我们老师写得还好看。
读大学后,有一次翻东西无意间又看见这本小笔记本,我马上就有把它收藏起来的冲动,这或许是我与爹进行交流的一种媒介。但具体是什么媒介,我讲不清,但我明白,它对我很重要。
笔记本的第一页写着一句话:敢于拼搏,忠于心中的道路。原來初中时爹就有这样远大的抱负,回想我的初中,每天只关心打饭的时候食堂阿姨能不能多给我打上一点。第二页写着第二句话: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把青春虚度。越往下读,我越羞愧,臊得脸红。想想同样年龄的爹思考的是何等高远的问题,同样年龄的我却只知吃喝玩耍,从来没有思考过未来,哪怕是接下来几天的事。
我没有和爷爷提起过我收藏了笔记本的事,更没有告诉他我抄写了笔记本后两页上的两首歌。一首是《小芳》,另一首是《青青河边草》。这两首歌我只在一些影视剧中听到过,它们离我太久远了,它们是属于我爹那个年代的。正因为它们是我爹喜欢的歌,我才抄写,不是想学会唱,只是单纯想抄了感受一下其中的意味。
那本承载着我爹青春记忆的笔记本被我继承了,也可以说,我继承了我爹的精神财富,里面有我爹写的字,我还会想,会不会我爹身上的一些气息也残留着。我会长久地保存它,让它一直陪在我身边,就像我爹在我身边一样。
十八岁,成年,到了出门远行的年龄。这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成了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也是第一个考上一本的人。当我把高考成绩拿给爷爷奶奶看时,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奶奶站起身去烧火做饭,爷爷抱着一捆草去喂牛。
之后一个晴朗的下午,家里来了一个收破烂的人,爷爷喊我和他去抬东西,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值得把收破烂的人特地喊来。他带我走进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我知道这间房子是我家的,但我从来没有见打开过一次门。爷爷拿一根棍子把缠绕在房间里的蜘蛛网搅下来,拉开一张落满尘灰的花油布,下面竟是一辆三轮摩托,我从来不知道。
细看后确实是一辆三轮摩托,只是没有现在的大,说来与一辆三轮脚踏车差不多大。爷爷问收破烂的人值多少钱,人家说,老样式,而且已经报废了,就是废铁的价格。我也不称了,估一估,给你150 块钱。爷爷说,不可能才给这点嘛,这可是我们村第一辆车。收破烂的人一口咬定只给150 块钱,多一分钱都不要。
爷爷看人家不松口,150 块钱也就卖了。接着他又把家里的黑白电视抱了出来,问值多少钱,人家只给20 块钱。爷爷让人家往上再加点,给加了5 块钱,两笔买卖加起来,卖了175 块钱。这台黑白电视我见过,一直在角落里放着,坏了好些年了。
收破烂的人走了以后,爷爷说,这是你爹当年买的,是村里的第一辆三轮摩托车,第一台电视。爷爷说这些话的时候是自豪的,也是悲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辆车和这台黑白电视是我爹遗留下来的,爷爷保管了十八年,最终又回到了我手里,算是爹给我的遗产吧!
从家出发读大学的前一天,我去了爹的坟前,一个人悄悄去的,不想让人看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做一件不想让人发现的事,总是选择在傍晚或者晚上。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人少,一个是黑夜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
我爹没有埋进祖坟,在我们村想进祖坟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年满六十岁,二是死的时候留有后。爹死的时候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他出门打工的时候只知道我妈怀孕了,没想到去了就没有回来。
他出门一定是想多挣点钱,等我妈生我的时候就能安心在家陪着,等我满月还能办一场体面的满月酒席。只是我爹死了,我爹死后一百零三天我出生了,时间相隔那么近,以至于我满月的时候没有办酒席。
我爹死的时候是那么年轻,和我现在一般大。和爹一起死去的还有我小叔,他才十九岁,还没有娶媳妇。这一年,村里和爹一起死去的人有好几个,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按理说这个年纪是人一辈子最好的时候,敢闯敢拼,意气风发,可是他们却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罪魁祸首是一次特大瓦斯爆炸。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问爷爷奶奶下葬爹和小叔时是什么样的场景,怕爷爷奶奶又再次感受丧子之痛,那我将是多么不孝。爹和小叔都葬在祖坟旁边的地里,只隔了两百多米。
坐在我爹坟前,我注视着墓碑上刻着的名字,嗣男——范庆奇。多么单薄,薄得只要一滴眼泪就能刺穿。我应该有很多话要说的,可我一开口只说了一句:“爹,我考上大学了,我要去甘肃读书了。”就再没有多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