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往ZOOM岛
DAVID KUSHNER
清晨的劳作很快就要开始了。阻塞的交通,拥挤的火车,电梯和自动扶梯将上班族们送到他们专属的格子间里。但是,在亚热带马德拉岛(Madeira)的古老村庄——蓬塔杜索尔(Ponta doSol),一天的工作却不是这样开始的。它始于日出时悬崖之上的瑜伽。
“吸气,向着大海伸展,”去年10月的一个清朗澄明的早晨,林赛·巴雷特(Lindsay Barrett)——一位姿态灵活、有着金色沙发的瑜伽教练这样指导着六七位“千禧一代”的学生。他们所在之处是距离大西洋海平面几百英尺以上的一座悬崖边的石板露台,海浪在下面不停撞击着火山岩礁,发出阵阵轰鸣的噪音。粉橙色的阳光从绿色的梯田山脉和层叠的瀑布上远远延伸出去,一直铺洒到广袤的蓝色海平线上。
但这些人并不是来度假的信托基金受益人。他们是在疫情期间从世界各地移居此地生活和工作的专业人士。31岁的巴雷特曾经在纽约的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任职,但2019年,她订了一张单程机票,到这里重新发现自己。“我想努力工作,”她说,“但我也想享受人生,我不想为了竞争而疲于奔命。”

她有同好。沿著附近蜿蜒的鹅卵石街道,在咖啡馆外,在公园里,有大约200名使用笔记本电脑和iPad通过无线网络体验未来工作方式的“小白鼠”,遍布在这个古老的小镇。在所有的漫游爱好者中,他们这一类人被称为“数字游民(Digitalnomads )”。他们是Zoom世代的早期探索者,依靠技术和不断变化的规范而得到解放,可以在任何有无线网络的地方工作。比如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城(Kansas City,Missouri)的自由撰稿人约翰· 韦丁(John Weedin),这个留着一头长发的30岁年轻人一边卷起他的瑜伽垫一边说:“我想一直旅行,真的。人们正在让这种工作方式成为可能。”
没有一个地方能像马德拉岛这样更能让其成为可能。从阿鲁巴岛(Aruba )到格鲁吉亚(Georgia )等等很多国家都在努力吸引这些“游民”来提振他们被疫情破坏的经济,但马德拉这个位于非洲西北部海岸的小岛却独领风骚。巴雷特和这里的其他游客都是“马德拉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 Madeira )”项目的成员,这个独特的项目专为满足他们的需求而设置——帮助他们寻找出租住所,在市中心为他们配备最先进的协同工作空间,并通过一个名为Slack的私人网络频道组织各种社交活动,比如今天的瑜伽课。
这些都是该项目创始人贡萨洛· 霍尔(Gon?alo Hall )雄心万丈的愿景。霍尔是个34岁的高个子,来自里斯本,他跟我说他“总是穿着沙滩短裤”。霍尔是这个新生游民群体的主要布道者之一。在马德拉岛的旅游经济急剧下降后,他用当地政府提供的仅3.5万美元的资助,于去年2月推出了“马德拉数字游民”项目。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游民项目就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社群——并帮助重振了当地经济。政府支持下运行的商业孵化器“初创马德拉”公司的项目经理米凯拉·维埃拉(Micaela Vieira)说,游民们每月创造的收入大约在150万欧元。“这些对我们是极大的帮助。”她说。
游民们是如何促成这个项目的?如果说他们也舍弃了一些东西,那会是什么呢?我来到马德拉岛寻找答案。但是,正如霍尔所说,让一群当代游民安居在一个古老的渔村,这既是一项社会实验,也是一项经济实验。并且,像任何实验一样,它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我们是一个社群,”他笑着说,“但我并不控制每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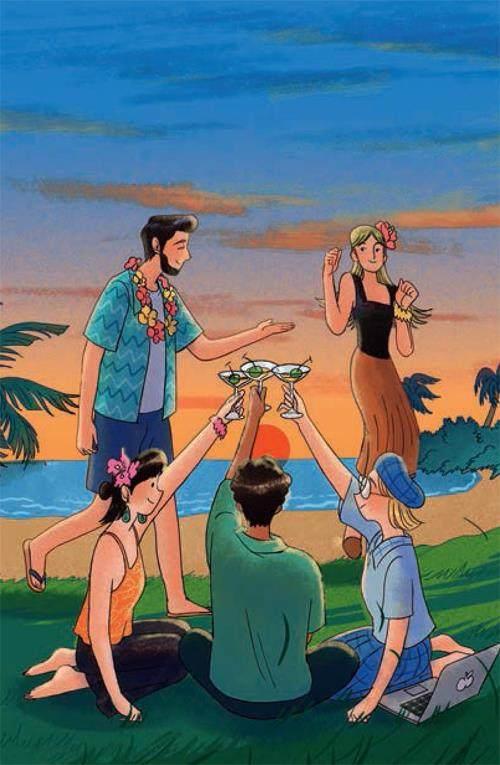
马德拉岛位于摩洛哥城市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Morrocco)以西约550英里,是濒临北大西洋的一个僻静角落,也是你能想到的距离办公室格子间最远的地方。对于从小就经常来这里的霍尔来说,这个地方是创建游民岛的完美地点。
本身就是游民的霍尔对于告别安定生活所要面临的挑战有着切身体会。4年前,他还在德国的一家体育博彩公司工作。“我那时很开心,在约会,薪水也很不错。”他说。但是到了30岁,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悲惨之处。“像是当头棒喝一样,我突然明白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他说,“我不想待在某个漂亮的德国城市里过安稳日子。我想环游世界,我想冒险,我想开始我自己的事业。”
他辞了职,和他的女友、用户界面设计师卡塔琳娜(Catarina )一起环游世界,从波兰到巴厘岛再到越南。他成为游民生活方式的早期倡导者——他推出了自己的播客《远程工作运动播客》,组织关于远程工作的研讨会,并就如何推动远程工作方式向各个公司提供咨询。他的热情不仅是为了享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更在于帮助那些想在蓬塔杜索尔这类偏远地区隐居的人们从网上找到有成就感又能挣到钱的工作。“远程工作是一种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工具。”他说。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地球上突然到处都是远程工作者了。与此同时,旅游业崩溃,那些重度依赖旅游业的地区收入大大减少。马德拉岛就是其中之一。疫情前,该岛平均每年接待150万名游客;疫情后,占国民生产总值约20%的旅游业缩水了很大一部分。蓬塔杜索尔很受欢迎的“牛排与太阳”餐厅老板玛丽莎· 弗雷塔斯(Marisa Freitas )像很多当地的永久居民一样,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我当时在想,我可能会失去这家餐馆。”她告诉我。
霍尔看到了一个可以帮到弗雷塔斯这些人的机会。2020年9月,他向经济部长提出了一个计划:吸引游民,让他们来支持本地的商业,甚至或许还能激发新的生意。“我们的兴趣在于让村子保持强大,”他说,“必须让当地人获益。”听完霍尔的提议后,“初创马德拉”公司与他达成了一项协议,支持并资助他的计划,在蓬塔杜索尔创立他们所谓的全球第一座“数字游民村”。他们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的。“我们希望一共能收到500份入驻申请,”维埃拉说,“结果我们每天都能收到200份申请。”

随之而来的是一项艰巨挑战:把一个人烟稀少的15世纪村庄带入21世纪。首先要找到一个能够改建成协作空间的场所。在蓬塔杜索尔的镇中心靠近餐馆酒吧一条街的地方,有一座专为美国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设立的文化中心,这座建筑有着玻璃墙和花园景观,还有一个空闲的展览厅,可以当作共享办公空间使用。他们与通信公司NOS合作,通过室内和室外的路由器,在这里覆盖了下载速度达到每秒500G的无线网络。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苏珊娜· 佩斯塔纳· 席尔瓦(SusanaPestana Silva)帮助房东们改造了他们的出租公寓,好为数字游民提供服务,他们增加了办公桌,改善了网络连接,她还帮他们以较低的价格吸引租户,有时的折扣幅度能达到50%。
但是,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互联网和居住环境。游客们是为了享用海鲜才到蓬塔杜索尔来的:比如用新鲜的橄榄油和大蒜烹调的鲜美多汁的大虾和美味的石斑鱼,此外,当地烤羊肉的美味程度也堪称一绝。但是,由于大约四分之一的游民是素食主义者或纯素主义者,所以餐厅必须要提供豆腐和蔬菜。在“牛排与太阳”餐厅,弗雷塔斯在菜单上增加了素食菜式,她给这类选择起的英语名字是“背叛肉食”。
现在是游民村的上午10点左右,我来上班了。潇洒欢快的数字文人们正从他们的公寓里出来,沿着鹅卵石小巷漫步,准备找个地方办公。一个年轻的英国在线营销人员戴着飞行墨镜在一处露台上轻松地打着电话。一个来自俄罗斯的邋里邋遢的计算机程序员霸占了户外的一张桌子工作,他那几个在家受教育的小孩则在他身边用画笔涂颜色。
虽然他们习惯了四处奔波,但这个群体中有一种亲密无间的气氛。我在寻找位置的时候,他们会对我露出微笑或做出友好的姿态,感觉他们都在开着同样一个宇宙玩笑,那就是——他们真的能够在这里工作。33岁、来自埃及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Egypt)的软件开发人员艾哈迈德·哈穆达(Ahmed Hamouda)辞去了在亚马逊的工作,和女友一起来到这里。他告诉我,成为一个游民虽然会有些折腾,但是值得。“因为这里的天气,因为这个社群,”他说,“我们想要以这样的方式生活。”
在我采访的那一周,島上包括哈穆达在内有大约1000名远程工作者,他们来自50多个国家,分布在几个主要的地点:此处这个叫作蓬塔杜索尔的小海湾,距离这里约45分钟路程的马奇科(Machico)市,以及附近繁华的首府城市丰沙尔(Funchal)。一些人租公寓住,价格通常很公道,还可以俯瞰郁郁葱葱的香蕉种植园。其他人,按照霍尔的描述,会分租住进周边遍布的老农舍,那些农舍地下室的酒窖都有200年的历史。如果需要把某个项目完成,或者需要上网用Zoom开会时,他们就会抄起笔记本电脑,溜达到随便哪个协同工作空间去。

但是,对于最早抵达的那批人来说,这个实验进行得并不顺利。斯佩拉· 特扎克(Spela Tezak )当时一心想离开。这位33岁的旅游经理原本在她的家乡斯洛文尼亚(Slovenia)生活,新冠疫情让她的工作陷入停顿。起初,特扎克花了很长时间四处奔走,与旅行社和年轻的旅行者们一起奋斗。然后,突然间,她干不下去了。“我有了一些时间思考自身。”一天晚上,把一头金色长发梳成马尾、讲话速度非常快的特扎克在丰沙尔的一家露天咖啡馆告诉我:“我想为自己的精神健康做点事情。”
她读到了关于“马德拉数字游民”项目的报道,并认为那个岛似乎正是适合等待疫情过去的地方。像她的诸多同龄人一样,只要有网,她就可以继续工作,所以住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许多游民完全不富裕——他们只是勉强维持生计。而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就是能让人负担得起。她在蓬塔杜索尔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公寓,并在2021年3月买了一张前往该岛的单程票。她抵达后只遇到了一个问题,眼前的蓬塔杜索尔死气沉沉。“看起来像个鬼村”,她说。
尽管在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工作很有诱惑力,但现实终究无法逃避:学习当地语言,跨时区工作,以及,或许也是最关键的,寻找社群。霍尔从自身多年的游民生活中深知,仅仅帮助这些新移民获得签证延期和找到高速互联网是不够的。“社群是关键,”他说,“这就是其他人在吸引数字游民方面彻底失败的原因。他们错失了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游民们是在不同的社群之间旅行,而不是在不同的地点之间旅行。我旅行是因为我的人、我的群体、我的朋友们和我的部落都在那个地方,而我想和我的部落在一起。”
2021年冬季开始抵达该岛的游民们也是如此。“游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其中之一就是,我怎么样建立社群?”去年3月从荷兰来到这里的可持续发展顾问帕梅拉·斯米特(Pamela Smit)说道。按照斯米特的说法,“如果所有人一直埋头苦干,只顾做自己的事情,我怎样做才不会感到孤单呢?”
霍尔并没有对新人们放任自流,而是创建了一个Slack频道作为他们的网络中心。他谈到,培育一个社群就像在《模拟人生》游戏中创建一个繁荣的城镇一样。“不要试图强迫它,”他说,“你必须创建基础设施,但你并不拥有它们。你必须尽快把权力交到游民们手中。”霍尔通过提供日落远足和午后游泳等等活动来推动社群的发展,最终,新人们开始利用这个频道来组织他们自己的活动。不久之后,霍尔说:“就是游民们在自发管理游民们了。”
来自德国吕贝克(Lübeck, Germany)的24岁大学生梅尔· 马科本(Merle Makoben )在今年1月之前一直担任蓬塔杜索尔游民社群的经理。她发现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个人发展。这是霍尔在企业家蒂姆· 费里斯(Tim Ferriss )的人生修正(LifeHacking )理论中发现的一个特性,也是激励着许多人开始上路的重要因素。他们安排了瑜伽、萨尔萨舞课程、音乐即兴表演等等活动。“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在寻求自由和自我成长。”马科本说。
豪尔赫·弗雷塔斯(Jorge Frietas)是蓬塔杜索尔主街上不多的几家酒吧之一——“小房子(The Small House)”的第二代侍者,对于那些点了几杯野格(J?germeister)之后就开始不停滑手机的世故的年轻游客,他的看法很复杂。有些人是好客人,另一些人则表现得不那么好。而且,镇上的人担心他们可能会把新冠病毒带来。为了防止病毒传播,马德拉在2021年1月实施了工作日晚7点之后的宵禁令。“但一些旅行者仍然违反规定。”马科本说,于是警察对他们进行了“训诫”。
事实证明当地人的担忧不无道理,霍尔说,春天时,一个游民患上了新冠肺炎,之后又出现了3例。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游民们决定进行自我隔离。“把我们自己与当地人分开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感染其他人从而对他们造成更大危害 ,”马科本说。但是后来,随着病例的减少,游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目的感。“我们从想隔离以确保大家的安全突然转变成想与大家融合在一起,”她继续说道,“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你们的家,我们不想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单独的泡泡里面。”
“我们想出一份力,”特扎克说,“我们想给予这个美丽的村庄一些回报。”他们开始在镇上做志愿者:组织带领清洁海滩的活动,绘制壁画,给当地人提供各种课程,比如来自德国的游民教大家跳萨尔萨舞的课程。不久之后,蓬塔杜索尔又开始拥有了活力。“牛排与太阳”餐厅的老板弗雷塔斯说,游民们对于餐厅的复苏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对我们非常非常有益。我要说‘他们是我的天使。”
虽然霍尔正在蓬塔杜索尔建立他的社群,但他并非马德拉岛上唯一一个有事业心的游民。从这里向东半小时路程的丰沙尔一家五星级酒店和度假村里,一个为不同类型的旅客所提供的不同类型的社群脱颖而出,占尽风头——它与霍尔的理念截然不同。“我有我自己的原则,”霍尔委婉地说,“我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很了不起,但那与我的愿景不一致。”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来到奢华的萨沃伊皇宫度假村(SavoyPalace resort),登上了酒店的全景式屋顶泳池平台,与创建了这个不同愿景的竞争者见面:他叫博格丹·丹丘克(Bogdan Danchuk),他的游民同伴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博格·迪(Boggy D)。丹丘克32岁,是个和善的年轻人,一头金发在脑后梳成一个男式发髻,穿着牛仔裤和牛仔布的纽扣衬衫。他向路过的酒店员工挥手,好像他是这儿的摇滚明星。“我想念这个地方。”他叹了口气说。
正如霍尔在蓬塔杜索尔领导着游民们一样,丹丘克也在这里组建了自己的团队。但是,他们的愿景是完全不同的。霍尔以小村庄为核心,力求保持本地特色和公共性;丹丘克则走起了企业化和光鲜亮丽的路线:当地新冠病例数激增之时,他自己和他的168名游民朋友达成了一项协议,一起搬进了这个豪华度假村。6个月间,这家酒店专供他们享受之用,他们沉浸在一种颓废的、反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与酒精、狂欢和加密货币为伴。
“我仍然无法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他若有所思地告诉我,他的目光越过无边泳池,凝视着下方的海洋,“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丹丘克生长在乌克兰,家境贫寒,有时晚餐只能靠洋葱和一点面包充饥,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他从未梦想过的。随家人移居以色列后,他成了一个有进取心的孩子——他当上了受大家欢迎的班长,并发誓再也不做穷人。丹丘克18岁时创建了自己的数字营销公司,一年后作为游民开始旅行。从那以来,他去过的国家超过36个,从美国到越南,他会在某个地方待上几个月,然后继续走。
但有一个地方讓他想留下:那就是马德拉岛。“这个地方让我惊叹,你在人生中渴望拥有的每一件事,这里都有,”他说,“这里让人有身处大城市的感觉,但它又被大自然所围绕。”缺点只有一个:陈腐、呆板的游客。“来这儿的都是,差不多从70岁到行将就木那个年龄段的人,”他说着笑了起来,“对于游民来说,这是这个地方唯一的缺点,但这里的一切都在吸引着那些人来。”
新冠疫情暴发后,他听说了“马德拉数字游民”项目,并构想了一个竞争计划。他想找一家酒店,好让他和其他游民在那里过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他的理由是,酒店可以提供大学宿舍般的体验,而且各项设施更为成熟。“你可以去酒吧,去餐厅,展开社交,”他说,“你们本质上是一栋大楼里的室友。”丹丘克给岛上的各家酒店发出了电子邮件,提出游民套餐的想法。他一不做二不休,也给萨沃伊皇宫度假村——他认为那是岛上最豪华的酒店——的拥有者萨沃伊特色酒店集团(Savoy Signature group)发了邮件。原本他的计划是让游民们入住位于岛屿西海岸卡莱塔(Calheta)的另一家萨沃伊酒店。
但后来,随着疫情持续,萨沃伊酒店联系了他。由于缺少游客,其他的萨沃伊特色酒店会保持关闭状态,但该品牌的旗舰酒店萨沃伊皇宫会继续开放。丹丘克的游民们可以帮助酒店灯火长明。萨沃伊皇宫是他们的了。“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个疯狂的进展,”丹丘克说,“但同时我也有点害怕。”在全球疫情暴发期间,让100多个千禧一代游民们涌入一家五星级酒店,会出什么岔子呢?
丹丘克在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和Slack上的游民信息中心放出了消息。入住皇宫酒店没有任何要求——只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但有很多人想住进去:大约1000人在争抢仅有的168个名额。霍尔的游民村蓬塔杜索尔用公寓生活和小镇气氛吸引着仍在奋斗中的年轻一代,而丹丘克提供的豪华生活方式则让那些被他形容为更年长、更具企业家风范的远程医疗医生、加密货币交易商和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们着迷。
洛蕾莉·迪扬(Lorelie Dijan)是去年2月最先抵达的那批人之一,33岁的她来自菲律宾,时髦又爱玩。疫情暴发时,迪扬是德国法兰克福一家汽车公司的信息技术项目经理。她告诉我,当她走进萨沃伊酒店金碧辉煌、有着水晶吊灯的大堂时,简直不敢相信。“就好像是,哇,好吧,这也太惊人了。”然而,除了几名正在等候迎接她的员工之外,酒店里几乎空无一人,这又让她觉得很不真实。“那里真的没有人住。”11月,她在德国的公寓里通过Zoom告诉我。
32岁的蒂姆· 蒂里坎恩(Teemu Tiilikainen )是芬兰一家信息技术咨询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和他的妻子、软件工程师索菲娅·赛格(Sofia Seger)来到这里,不仅希望能够暂时躲避疫情,还希望能够找到经常被年轻专业人士忽视的一种东西:新的朋友。“到了这个年纪,你的大部分生活都围绕着你的工作或者爱好之类的,”他说,“我实际上并不经常结交新的朋友。但我们都来到了这里,一起聚到了这个泡泡罩里。”
由于疫情的缘故,这个泡泡罩是确实存在的。游民们必须提供新冠病毒检测的阴性证明,才能进入马德拉岛。由于马德拉岛严格实行宵禁令,这些自称“萨沃伊人”的游民下班后也必须留在酒店。当然,被关进一座豪华的高楼也有好处。游民们把萨沃伊酒店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梦想宿舍。据丹丘克描述,他们靠客房送餐服务过活,并在雪茄房的电视上安装了PlayStation游戏机。他们去健身房锻炼,享受按摩,并且在酒店的一个酒吧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Poncha——一种酸甜口味的鸡尾酒,是岛上的招牌酒饮。丹丘克说,他们甚至还说服酒店让酒吧24/7保持开放。(萨沃伊皇宫说,之前他们的酒吧从未在午夜之后还开放。)他们开始通过Slack频道相约结伴游玩,从自助早餐厅到棕榈树旁的泳池,还有岩石嶙峋的海滩。他们安排了瑜伽课,会议室里的卡拉OK,以及一种叫做“打圈(circling )”的自我提升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他们会在草坪上围坐,分享彼此的思想、感受和恐惧。这些游民正在设计一种新的社群生活——有客房服务的那种。“过了大约两周后,这里感觉就像一个亲密的大家庭了,”迪扬说,“因为每天晚上我们都有活动,周末我们也有活动。”他们变得如此亲密,以至于她开玩笑说,“混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乱伦一样。”
“看到这一切在我眼前诞生,感觉很超现实,”丹丘克说,“看到这个社群在同一屋檐下蓬勃发展,我一直在掐自己来证明这不是梦。”人们只能独自并孤单地困在自己家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通过社交网络,人们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创建自己的社群。而现在,他们甚至可以真的搬到这些社群中居住。“如今,你可以在Facebook上找到让你感觉有归属感的群体,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现实,”丹丘克说。在疫情中应运而生的马德拉岛和萨沃伊酒店仿佛完美风暴一般证明了这种改变生活的方法是可行的。“它已经来临,”丹丘克说,“不过这是我们第一次得以亲身经历。”
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仍然面临限制和隔离的时候,萨沃伊人陶醉于他们奇怪的反乌托邦乐园。“我称之为马德拉岛的魔力,”迪扬说,“人们不断延长他们的旅程或取消他们的航班,而且越来越疯狂。”大部分的疯狂源于马德拉岛神奇风暴的另一部分:加密货币的一发冲天。丹丘克说,酒店里全都是加密货币的当日交易者、对冲基金经理和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负责人,他们一边灌着poncha酒,一边用笔记本电脑上买卖加密货币,并互通关于新发货币的行业情报。丹丘克称,有两个游民用酒店里的人们提供的200万美元投资创办了自己的加密货币对冲基金,还有一个人用两千美元的投资赚了20万美元。“我们这儿有些人凭借他们得到的忠告重建了他们全部的职业生涯。”丹丘克说。
卢卡斯·布劳恩(Lucas Braun)就是其中之一(他希望在本文中使用假名来保护隐私)。布劳恩过去是柏林的一名销售经理,2020年底,他和朋友一起来马德拉岛打网球度假。他入住萨沃伊酒店时,只带了一个装满衣服的网球包,随后就深深地陷入了加密货币的世界。不久之后,他就开始整天从事加密货币交易,并拓展自己的认知。
“一旦涉足加密货币,你就必须放开思想去面对新的想法和新的领域,”布劳恩说,他把加密货币交易比作服用迷幻药,而这个圈子里的一些人确实也实践过。“迷幻药非常有利于开拓你的思路,让你的想法四通八达。你没有那么多的疑问,你实际上一下就明白了。”他最终辞去了之前的工作。“那是一个改变人生的时刻,”他说,“它让我醍醐灌顶。我放弃了自己过去墨守成规的思维模式。”他在岛上住了一年之久。
纸醉金迷,阳光明媚,“加密货币酒店”——萨沃伊酒店的昵称——的居民们出海坐游艇,出行坐出租,豪华晚餐上有新鲜的鲷鱼和马德拉葡萄酒。丹丘克说,有一天晚上,萨沃伊酒店的首席执行官经过大堂时,游民们正在用吉他弹奏《迷墙》(Wonderwall )。他们举办了极致癫狂的跳舞派对,在完全黑暗并且搬走了所有家具摆设的空房间里沉醉,还在海滩派对上看到了日出。
然而,他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代价都是丹丘克承担的,他说是他处理了所有来自酒店的投诉,包括一台被砸坏的电视。“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看到一百条WhatsApp信息。”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重新入住酒店,他声称酒店方面已经让他好好看着点儿他那些萨沃伊人,包括一个穿着怪异的鞋子在大厅里踱步的邋遢游民。“你能不能告诉他一下,他不可以穿着烂拖鞋在五星级酒店里走来走去。”他说酒店对他有过这种提醒。
最终,是新冠疫情的减弱给这场疫情时期的狂欢派对画上了句号。去年5月起,由于新冠病例数持续下降,马德拉岛的旅游业开始复苏。满头银发的退休者开始乘着旅游大巴一批又一批重新涌入这个小镇。对萨沃伊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甜蜜套餐和他们短暂的梦幻生活将在6月前结束。与霍尔在蓬塔杜索尔营造的氛围所不同的是,这里从未想要长久。
丹丘克看着不止几个钢铁大汉在离开酒店前与他拥抱时泪流满面。“这些事业有成的人突然找到了一个社群,突然共同参与了一些事情,突然有了这种住在交换生宿舍里的经历,当然条件要好得多,”丹丘克说,“这成了他们的新常态,成了他们的家庭,成了他们的人生。这件神奇的事情被创造出来并真的发生了,人们真的不想离开。”
迪扬就是其中之一。“在法兰克福,我一个人生活,”她说,“我有朋友,但我并不是每天晚上都能和朋友们见面。然后,在那里,突然間,你有了一个社群。即使有人只住两个星期,也会产生某种亲情。所以每次有人要离开时,感觉都是,‘哦,别走!每次都有点伤心。”一个萨沃伊人告诉索菲娅·赛格,在这样的泡泡罩里他们很容易与现实世界失去联系,赛格回答道:“不,实际上这才是现实该有的样子。这样才应该是正常状态。”
“ 嘿,哥们儿,”阿卡迪·希尔弗曼(Arkadi Silverman)一边滑着手里的iPhone一边跟我说,“看看我新买的这套公寓的照片。”
这是蓬塔杜索尔的一个星夜。32岁的以色列人西尔弗曼一身珠光宝气,懒散悠闲地和其他一些游民聚在悬崖顶上的一间酒吧,这是每周一次的“紫色星期五”邀请制派对现场。这个派对因为从舞池中可以远眺壮观的紫红色日落而得名,海水冲刷着下方的火山岩,让人心潮澎湃。正如某个在线活动名单中所解释的,这个私人派对的目的是“专业人脉社交、聚会和跳舞”。
西尔弗曼自称是一名退休的职业扑克玩家,现在从事加密货币投资组合管理和NFT交易的相关工作——这些NFT也包括他刚刚用价值约400美元的以太币购下的“公寓”。他在手机上向我展示了一个有桌子、椅子和窗户的卡通客厅的图像。这位数字游民已经买下了一座数字公寓。“相当不错,是不是?”他说。
10月,我再次上岛采访时,岛上已经恢复了繁荣的景象。夜店重新开业,酒庄的品酒会也开放预约了。随着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开始返回办公室,被游民们称之为“与地点无关”的生活方式的梦想也变得越来越真实。根据Digital.com最近的一项调查,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企业永久关闭了部分或全部办公室。疫情之前,只有不到6%的美国人远程工作。现在,预计会有将近25%的全职劳动者在今年开始远程工作。到2025年,估计将有3620万人在家工作——当然他们也可能会在海滩上、蒙古包里或任何其他他们梦想中的非常规的工作地点办公。而那些一意孤行地希望在疫情消退后吸引员工回到办公室的公司正面临着所谓的“大辞职”浪潮,从2021年9月到今年1月,有2160万员工辞去工作,创下了历史纪录。
与此同时,在马德拉岛上开创的“数字游民”生活方式仍然在继续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有一些关于游民的书籍出版,比如《游民资本家》(Nomad Capitalist )、《数字游民生存指南》(The Digital Nomad Survival Guide),以及蒂姆·费里斯所著、被很多人奉为该风潮经典之作的《每周工作四小时》(4-HourWorkweek )。还出现了一些游民播客节目,比如游民乌托邦电台(Nomadtopia Radio)、游民正火(Nomad on Fire)、游民执行官(The Nomadic Executive)等等。此外还有游民大会、游民约会网站,以及一条(按照他们的宣传,“为了激励和分解在环游世界的同时开展网络业务所需的基本要素”而设立的)横跨大西洋的游民游轮航线。
更多的政府也开始参与其中,比如葡萄牙政府。该国议会于11月批准了新的劳动法,以保护和吸引更多的游民。其中包括一条规定说:除非情有可原,否则该国的雇主如果在下班时间与远程工作的员工联系,有可能会被罚款。“我们认为葡萄牙是世界上最适合这些数字游民和远程工作者选择的居住地之一,”同月,该国的劳动、团结和社会保障部长安娜·门德斯·戈迪尼奥(Ana Mendes Godinho)在里斯本举行的网络峰会上说,“我们希望能吸引他们到葡萄牙来。”
对于远程工作这个陌生的新领域来说,过去几年的发展会像宇宙大爆炸一样被载入史册。马德拉岛的社会实践经验已经开始被输出。丹丘克也希望把他的“远程天堂酒店”模式带到东京、波士顿和夏威夷等等更多地方。霍尔则会继续监督“马德拉数字游民”项目,该项目仍然为来到蓬塔杜索尔和岛上其他村庄的远程工作者提供一如既往的服务。他还在努力将马德拉模式带到其他国家。我最近通过Zoom与他联系时,他正在马德拉岛以南约一千英里的佛得角(Cape Verde)岛链上创建一个新项目。“这里非常酷,”他笑着告诉我,“白沙滩,和海龟一起游泳,到处都是现场音乐。”
随着游民生活方式逐渐流行开来,阻止人们加入部落的唯一障碍是恐惧。“让人们远离游民生活的只是安于现状和恐惧,”他接着说。
“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他们会说,你能做到是因为运气好。我不行是因为——此处会有各种借口。但我认为我只是打破了现状,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困难,安于現状是非常舒适的。这也许就是游民社群如此有趣的原因,因为社群中的每个人都不得不打破现状。每个人都不得不说,“我要辞掉这份工作。我不要在这里定居,我不要买房,我不要养狗,也不要买车。相反,我要环游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