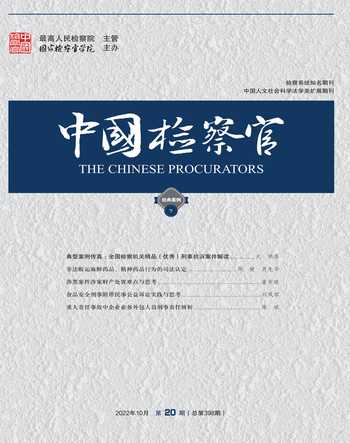私放卖淫嫖娼人员行为的司法认定
刘文钊
一、基本案情
贾某系某派出所社区民警,主要负责辖区内的治安工作。2017年至2020年,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王某请托,为王某在辖区内经营足疗店提供帮助,多次收受王某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6万元。其间,王某多次在经营的足疗店内容留他人卖淫。贾某对此知情。
2020年9月11日晚,群众报警举报王某足疗店附近出租房内存在卖淫嫖娼行为。当夜适逢贾某值班,其带领3名辅警出警处理,在现场查获卖淫嫖娼人员李某、陈某,遂将二人带上警车,准备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回程时,贾某想到事发地点离王某的足疗店较近,便主动联系王某,得知陈某系王某足疗店的失足妇女。为防止处理卖淫嫖娼案件时陈某供出王某足疗店容留卖淫的情况,进而暴露自己的受贿行为,贾某将李某、陈某私放,以未发现卖淫嫖娼人员为由结案。同年10月,王某足疗店内容留卖淫行为被发现,王某因犯容留卖淫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
二、分歧意见
贾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王某经营足疗店提供帮助,收受王某贿赂,毫无疑问构成受贿罪。本案争议在于贾某私放卖淫嫖娼人员行为的定性问题,存在属于受贿罪谋利事项、构成徇私枉法罪以及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三种不同观点。
持受贿罪谋利事项的观点认为,一是卖淫嫖娼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出警处理的贾某没有刑事侦查职权,因此不能归入徇私枉法罪或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范围;二是贾某私放卖淫嫖娼人員的行为也不属于为犯罪分子提供住所、财物等帮助其逃匿或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不构成窝藏、包庇罪。故该行为无法单独评价为犯罪,只能认定为贾某受贿罪的谋利事项。
持徇私枉法罪的观点认为,一是徇私枉法罪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在主体上是相互排斥的,本案中贾某符合徇私枉法罪的主体要件,便不属于具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刑事立案是司法行为的一部分。发现容留卖淫犯罪线索后,贾某为了徇私利,私放证人,故意包庇王某免受立案,属于典型的有案不立,符合徇私枉法罪的客观要件。贾某符合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同时还构成受贿罪,根据刑法规定,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又根据本案案情,徇私枉法罪可能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重于受贿罪,故而应当认定为徇私枉法罪一罪。
持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观点认为,一是根据某派出所关于社区民警的职权分工,贾某具有查禁辖区内犯罪活动的职责。二是虽然私放行为发生在处理卖淫嫖娼活动过程中,但结果是帮助王某逃避刑事处罚,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同时,其还构成受贿罪,应当数罪并罚。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本案定罪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区分徇私枉法罪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从立法目的上看,徇私枉法罪前身是1979年《刑法》中的徇私舞弊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在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9条基础上增设、修改而成[1]。前者的立法目的在于防范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的故意枉法行为;后者在已有徇私舞弊罪(徇私枉法罪)的基础上增设新罪的目的是杜绝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查禁犯罪活动中的包庇行为。两罪的立法目的存在扩张、补充关系。从犯罪构成看,两罪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一是主观上都要求明知帮助的对象是犯罪的人而枉法不追诉[2];二是帮助的对象都要求是犯罪的人,但不必须是经法院判决有罪的人,只要有证据证明实施了犯罪行为即可;三是客观行为都可能表现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等隐瞒事实的手段。然而,两罪还是存在着明显区别。
(一)贾某同时符合两罪的主体要件
徇私枉法罪的主体要件为司法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94条的规定,主要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为具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适用时,首先要明确两罪主体要件的关系。对此存在着排斥论和包容论的争议。持排斥论的学者认为,两者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即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中的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人员不包括具有追诉、审判等司法职责的人员,进而认为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使其不受追诉的,一律构成徇私枉法罪[3]。与之相对,司法实践中通常持包容论的观点,认为两者存在交叉重合[4],较为典型的是2006年《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立案标准》),明确指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包括具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司法工作人员。
笔者支持包容论观点,理由为,一是查禁犯罪的主要路径是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认定犯罪,并判处刑罚,与刑事诉讼的目的一致。即查禁犯罪活动职责与刑事司法职责具有目的上的统一性、逻辑上的延续性以及常识上的重合性。在刑法没有明确区分的情况下,人为割裂二者关系,不仅有悖于社会一般认知,在逻辑上也难以自洽。二是排斥论观点还可能造成不当的处罚空隙。排斥论的问题在于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与徇私枉法罪的区别完全寄托于主体身份和实施渎职行为时所处的诉讼阶段,却忽略了此罪与彼罪区分的关键——客观行为。根据刑法规定,两罪客观行为并不相同,如果完全贯彻排斥论必将人为造成司法工作人员实施通风报信行为无法定罪处罚的不当漏洞,典型案例是承办民警将抓捕计划告知犯罪嫌疑人家属造成嫌疑人逃跑的案件[5]。按照排斥论的观点,承办案件的民警属于司法工作人员,不符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要件。客观行为上,该民警只是通风报信,没有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施加直接影响,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的客观要件。同时,其也没有提供处所、财物帮助藏匿,亦不符合窝藏罪的客观要件,只能认定为无罪。显然,这样的结论有悖于两罪的立法初衷。与之相对,包容论不存在此类问题,该承办民警同时符合两罪的主体要件,仅实施了通风报信行为,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另外,持受贿罪谋利事项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才具有查禁相关犯罪活动的职责,也是不能成立的。查禁职责的规范表现就是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的针对犯罪行为的查处、惩治义务,如《人民警察法》第2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义务之一就是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这项义务并不因工作内容变化而改变。本案中,贾某身为社区民警,负责辖区内的治安工作,具有查禁相关犯罪活动的职责。同时,根据其所属公安局的职权划分,派出所对于一般刑事犯罪具有侦查权,贾某也属于司法工作人员。
(二)贾某私放卖淫嫖娼人员的行为符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第399条的规定,徇私枉法行为包括徇私和枉法两个方面。徇私指的是为徇私利、私情;枉法指的是歪曲事实和法律,包括明知无罪而追诉、明知有罪而包庇、在刑事审判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裁判三种类型。根据刑法第417条的规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行为是指采用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方式,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追究。两者的最终目的都包括使犯罪的人免受处罚,但行为方式存在两点区别:
一是实施渎职行为时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徇私枉法行为只能发生于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即只能在刑事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诉讼流程中实施包庇等枉法行为。需要说明的是,刑事立案指的是诉讼程序,而非立案结果。在立案初查过程中,承办人员明知符合立案条件故意不立案,使他人不受追诉,也可以认定为徇私枉法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则没有诉讼阶段的限制,既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中,也可能发生在犯罪分子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时。在区分两罪的客观行为时首先需要判断实施行为时所处的诉讼阶段。如果实施包庇等行为时犯罪分子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那么一般应当认定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如果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则需要根据渎职行为的性质进一步分析。关于认定犯罪行为已经被司法机关发现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应当以犯罪线索能否被其他司法工作人员发现为标准,比如控告、举报人向其他司法工作人员报案、案件线索被录入办案系统等等。因为无论是徇私枉法罪还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都要求行为人明知是犯罪的人。如果将行为人本人知悉的犯罪行为理解为已经被司法机关发现,则是以主观认知认定客观行为,属于主观归罪。本案中举报线索指向的卖淫嫖娼地点并非王某的足疗店,而是陈某自己的出租房。经事后查证,陈某当晚也并非在王某的容留下卖淫,而是自行寻找到李某。不能否认陈某的落案可能牵连出王某的足疗店,但是公安机关收到的线索并非直接指向王某容留卖淫。贾某私放卖淫嫖娼人员时,王某容留他人卖淫的线索尚未被司法机关察觉,不符合徇私枉法罪成立的诉讼阶段要求。
二是渎职行为的本质特征不同。根据《立案标准》,徇私枉法行为包括6种情形,主要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等手段,明知是无罪的人追究其刑事责任,明知有罪的人包庇其免受追究,故意使他人受到不当追诉,故意使他人受到不适当的强制措施,故意枉法裁判以及其他徇私枉法行为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行为则包括5种情形,即泄漏查禁犯罪活动部署,提供隐匿便利,泄漏案情,帮助、示意犯罪分子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翻供,以及其他帮助逃避处罚的行为。通过对比可知,在包庇有罪的人逃避处罚时,两罪的行为方式存在交叉重合,即均可采取示意或帮助犯罪分子伪造、隐匿、毁灭证据、串供、翻供等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该行为方式并不能完全体现两罪实行行为的本质。“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的核心在于“枉法”,即通过歪曲事實、法律的方式利用司法权掩盖犯罪行为,而单纯的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并不能达到该目的,还要对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作出司法上的判断,如故意不予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故意挂案不查、违法撤销案件、不采取强制措施、变更强制措施,故意有罪判无罪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行为的核心在于“提供便利”,“通风报信”的结果也是提供逃避处罚的便利。通常情况下,只要行为人泄漏侦查部署、进展,或实施了帮助、示意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串供、翻供的行为,就达到了为逃避处罚创造条件的目的,实施了该罪的实行行为。由此可知,两罪客观行为的本质区别在于对逃避处罚结果的作用力不同,前者是直接决定免受处罚,后者间接帮助免受处罚,个案认定时需要把握行为人是否利用职权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司法判断。如果存在错误的司法判断,一般应当认定为徇私枉法罪。如果仅是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翻供,提供了逃避处罚的便利,没有歪曲事实、法律的枉法行为,则应当认定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比如甲系刑侦支队队长,办理了乙涉嫌故意伤害案。立案之初,甲和乙共同协商如何逃避刑事处罚,甲负责拖延侦查,乙尽快赔偿被害人损失,并指示被害人作有利于乙的假证。获得矛盾证据后,甲报请抓捕乙,并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不批捕,乙被释放。之后,甲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乙因证据不足被不起诉。在该案中,甲实施了通风报信、拖延侦查、指示作伪证等行为,但其最终侦查认定的结果与故意伤害案件真实情况一致,并未歪曲事实,也提请批捕、移送起诉。最终作出不逮捕、不起诉决定的是检察机关。甲没有实施枉法行为,而实施了帮助逃避处罚行为,应当认定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本案中,贾某处理卖淫嫖娼举报时查获了李某、陈某,属于治安案件,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如果私放二人的目的仅是为了帮助二人逃脱行政处罚,那么仅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但在得知查获的失足妇女系王某容留的卖淫人员后,贾某担心在处理治安案件时王某容留卖淫行为被公安机关发现,遂决定私放卖淫嫖娼人员,以达到包庇王某的目的。此时,公安机关尚未发现王某的容留卖淫行为,也未针对该行为进行初查,虽然在行政处罚案件中实施了枉法行为,但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的客观要件,本质上属于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行为。
(三)贾某的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应当数罪并罚
贾某明知王某实施了容留卖淫犯罪行为,为防止其被公安机关发现,在处理关联行政处罚案件时私放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为王某逃避处罚提供帮助,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同时,其利用担任治安民警职务上的便利,为王某在自己辖区内经营足疗店、逃避处罚提供帮助,收受王某的贿赂人民币6万元,构成受贿罪。一人犯数罪应当予以并罚。最终,贾某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因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本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GJ2021C19)阶段性成果、天津市人民检察院重点课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21TJJY0802)阶段性成果。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三检察部一级检察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300000]
[1] 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3-651页。
[2] 徇私枉法罪实行行为还包括“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两种情况。本文涉及的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与徇私枉法罪的关系,故而以“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展开论述。
[3]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0页;郭立新、黄明儒主编:《刑法分则适用典型疑难问题新释新解》(第三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967-968页。
[4] 参见张军主编:《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第9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第9版,第2184页;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6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601页。
[5] 张懿:《办案人员向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应如何定性》,《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