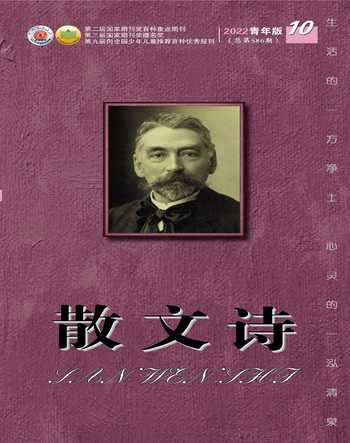一杯时光
花盛[藏族]
一杯时光
橘黄色的灯光,穿过窗户拉长时光的影子。
酒杯很浅,却装满空寂的语言和近乎苍白的日子。
饮一口,就有鸟鸣、麦香和炊烟从杯子里晃出来,像故乡的田野上斑斓的野花和深夜闪耀的群星。
再饮,就有月亮落下去,晨曦升上来,牛羊的蹄印里,生活,像打开的书页,长满葱郁的文字。蝴蝶像一个象征词,需要反复斟酌,它们不同于杏花桃花梨花间追逐的蜜蜂。风吹花落,就有一只小手握住青涩的果实。
再饮,杯子就见底了,里面有校园的钟声、溪流的奔跑和父母的叮嘱,还有那个沉浸在童话故事里,无法自拔的小女孩儿。
不能再饮了,得留下最后一滴,留下无尽的空,盖一座房子,房子周边修一畦菜园,栽上篱笆和桃树。让鸟儿在暮霭里归巢,让余生和亲人住进来,让一只猫守住洞口,让月光缝住漏洞和缝隙,只为萤火虫让出一条道路。
看 雪
把孤独分成无数截,雪花,就有了具体的情节和分量。
空旷的部分,像呼出的白气,遇风成光。
将迷茫的白挪开,泥土就露出褶皱的语言和湿润的深渊。
石头和枯草,在更高处,相拥而泣。
而在风中晃动的,是生活的一截,也是生命的一截,它们——
像细碎的光,在日子的版图上蔓延着刺眼的光芒。
羽 毛
从天空落下,残存着飞翔的温度,雨滴的湿润,雪花的冰凉,也残存着冰雹的坚硬。
而闪电,是黑夜难以驯服的狮子,它出没于深夜,吼开一条短暂的路;像静默的花瓶,突然跌落,破碎。
道路布满荆棘,生活一片狼藉。短暂的明亮,在漆黑的夜色里,羽毛般抚平时间的波澜。
剩下的日子,以静制动,以平淡替代聒噪,以细腻替代粗糙,以光泽替代灰暗。
夜 晚
刨开一层一层的雪,就有一只手从雪下面伸出来,递给你一块月亮,蓝色的光,潮水般涌动腐朽的味道。
银质的骨骼是一棵棵会说话的草,告诉你,也告诉我,这漫长的命运和短暂的美感。
语言顿时虚空如竹,坚强直立。但内心辽阔,将山川入怀。
驱散眼里的灰烬,我打开自己,像打开另一扇门,窥探夜晚的慈悲和未知的深渊。
雪已停,风已歇。天空返还深邃的蓝,露出深夜里梦的笑靥。
一个人踏雪而归,肩上落满时光的银屑。
照亮黑夜和道路的,不一定是星火,但一定是内心的执念和梦想。
一个人月下独酌或等待,此刻,不要说出你的伤口,它只是月光为你留出的一扇门。
依门静听,大坪梁的风,正在把月光磨细,磨出清澈的水流,从心头流过。
落在地上
云落在地上,便以另一種身份与你产生关联,比如雨滴、雪花和冰雹。
叶落在地上,就是一张被遗忘的契约,不再谈论甲乙丙丁的责任,也无谓成败得失。
梦落在地上,有跌落谷底的绝望和绝处逢生的力量。
你我,还有他们,皆为世间渺小的存在,万物般陷于一种无形的轮回。
人落在地上,所有你在乎和不在乎的,包括金钱、名利和地位,包括生活的刺和内心的涩,都抵不上时间的视而不见。
语言落在地上,如影随行,一半白,一半黑,要么归于一言九鼎,要么归于尘土沦陷,更多的时候,黑白不分。
大坪梁
老家迁徙到大漠深处后,我时常坐在大坪梁的风中,俯瞰党家磨河,像一缕桑烟,被时光不断扶住,又被风不断吹皱。
大坪梁上,开满苏鲁花——
她们,没有因村庄的消失而悲伤,像一只只快乐的鸟雀,在鸟鸣里为我打开一扇明亮的窗。
河流远去,云朵下的大坪梁岿然不动,像在等待什么。
当我掩面转身时——落日,是一张孤独的脸。
谷 雨
一片片浅浅的云在山顶萦绕,被一对对羽翼划开梦幻的弧线。
小草探头,努力生长,以赴春天之约,而洮河畔的桃花,又红过一次了。
风吹花落——
落在原地,被小草轻轻接住,藏在心灵里;
落在书页上,被小女孩藏在时光里;
落在水面上,被浪花簇拥着远去。
等小草长大,人面沧桑,桃花不再。沉睡于书页的花瓣,守着内心最后的墨香。
洮河,始终没有停止流动。我们,像浪花走在一条没有回头的路上。一场细雨淋湿风所传递的消息,回首,春已尽。
我们的人生终究赶不上一次阑珊的春光,唯借谷雨,作为与春天的一次诗意告别。
初 夏
一棵树守住一块地,就有一朵花守住一个梦。
低矮的云雾掠过脸颊,一丝冰凉和清醒,汇聚成头发、睫毛,和鼻尖上微明的秘密。
细小的雪粒,被风簇拥而来,在初夏的大坪梁,在高原一隅,像一朵洁白的花,羞于表达自己的心思。
来不及说再见,就落于碎石和草丛间。
那一地的白,是你为自己留出的一块无字碑——
也为未知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