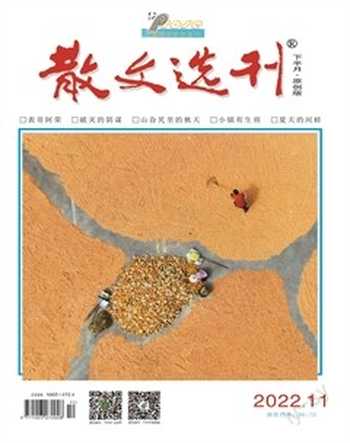猴子酒壶
吴显为

酒壶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念想。
酒壶扁方形,七八寸高,四五寸宽,一两寸厚。壶身是盘腿而坐的老猴子,像一尊弥勒佛笑视前方,憨态可掬;左手抱着小猴子,右手弓成壶把。小猴子蹲在老猴子的盘腿上,靠在老猴子鼓鼓的肚皮上,两只小毛手在老猴子的肚皮上挠着痒痒,透着忍俊不禁的天真可爱。釉面光滑,黄里泛红,密布着毛茸茸的细纹,触摸起来有温润的毛刺感。父子嬉戏妙趣横生,表现出率真的灵气和调皮,再戴着橘红色的大檐帽,颇有沐猴而冠的味道,既幽默滑稽,又贻笑大方。
猴子酒壶盘坐在条台上,光亮照人,满室生辉。我小时候就翘着食指说,这是花果山上请来的孙悟空和小猴子,惹得小伙伴扑闪着眼睛,啧啧称赞。有个小家伙上去要摸,我奔过去一把拉下:“不准摸!宝物,神得很,是你这样的脏手能摸的吗?”
猴子为我家带来了欢乐。正月春饮,母亲精心烹制的六盘大菜,喜盈盈地登上餐桌,筷子酒盅齐整整地站好队伍,眼巴巴地等着主角——猴子出场。我和弟弟欢蹦乱跳,一步不离地尾随着父亲,从条台上慢慢请下早已净身的猴子,把从供销社打来的八角二分钱一斤的散酒,小心翼翼地往壶里倒。酒壶里立刻唱着呵呵的音乐,散着浓浓的酒气,屋里充满着轻松快活的空气。倒满酒,哇塞,酒桌上欢声一片,笑语连篇,一个个睁大了滚圆的眼珠,盯着活灵活现的老猴子小猴子。老猴子精神抖擞,抓耳挠腮,嘻嘻地笑视着母舅姨父;小猴子也激动万分,歪头斜肩,一边眨眼瞟着大家,一边挠着父亲的肚皮……
父亲回忆:“两岁时,我伯我妈,就先后走了。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外闯荡。听说挑瓷器赚钱,就奔到景德镇。一担竹篮,装着满满的瓷货,从景德镇往回挑,边挑边卖。渴了,用手捧起塘里的水;饿了,就从包里掏出烧饼;累了,就靠着大树吸几口黄烟。最受罪的,是遇到流氓土匪。我学过打,也只能把扁担舞一舞,舞得呼呼叫。有时倒能吓跑几个蟊贼,总有不要命的。不能伤人,伤了人,就收不了场。只能苦求,只能护卫。瓷货是易碎品,不经碰。有一回一篮子的瓷货,碰得一下子碎了一地,稀里哗啦。我急了,扁担往下一戳,戳进了一尺深,双手按在扁担头上,双脚离地,在扁担上慢慢平展,昂着头,瞪着眼。歹徒一见吓得一哄而散,逃得比兔子还快。人是吓跑了,可一地的碎片,还是让我泪水直流。含着泪蹲下来,用小棍子划拉着碎片。咦!有件好的!双手捧起,用抹布擦掉泥土碎片,用稻草裹着放进包里,带回了洪镇吴花屋。”
猴子酒壶,就这样进了我家。
猴子见证了父亲的磨难。1943 年娶了马氏,不到两年病逝了。1946 年再娶冯氏,不到两年又病逝了。1949 年发大水,用两担米娶了小金洲漂落至马蹄冲的一家童养媳——我的母亲。1951 年,母亲生下我大哥,分得了土地。1958 年,我家闹饥荒,迁到了小金洲。痛苦时,父亲看看猴子,摸摸猴子,心里就有一丝慰藉。70年代,我家极度困难,收文物金银的几次上门,母亲卖掉父亲送的银耳环,又打起猴子的主意。
“干脆把我卖了!你可晓得,猴子比你还早来我家呢!”
猴子就是父亲的命。临终时,他还是念念不忘猴子酒壶,把我们召集床头,留下了遗嘱:“猴子酒壶,是我一生心血的代表。是传家宝,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弟兄分家,传家宝传给了我。像父亲一样,我每天抹得光亮,供在三脚架上,打躬作揖,阿弥陀佛。家有贵客,就讲父亲艰苦奋斗的故事。
忘了“家宝不可示人”。
又忘了人心不古。
猴子酒壺失踪了!
猴子宝座一直空着,等着它就位。等了十几年,还在等。永远等。有时瞅着瞅着,顿觉失魂落魄,揪心撕肺。我怎么,怎么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呢?我问妻子,妻子说父亲原谅了我。
佛家禅语,我也用之劝人,这一回却劝不了自己。酒壶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流于心间的血液,叫我怎能放下呢?
恍惚间,猴子酒壶飘然而至。定睛细看,老猴子长得像父亲,小猴子长得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