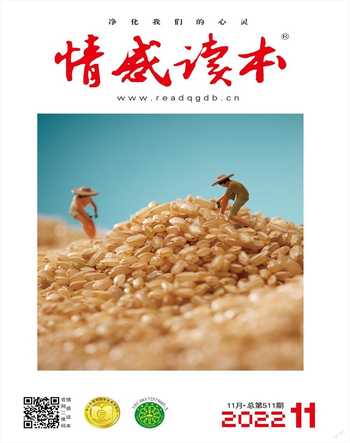母亲的食物
赵瑜
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以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进行评论,而唯有与母亲相关的东西,比如母亲的食物,我们无法评价。
每一个有乡愁的孩子,都有一个饮食习惯固执狭窄的母亲。比如我的母亲,多年以后,她曾经在海口生活过数月。不论我请她吃海南的任何食物,她都是拒绝的,本能地觉得不好吃。
母亲素不喜欢吃鱼,而海口的饮食,以鱼为鲜。母亲的饮食口感是以盐味重为上,而整个南方的饮食皆以素淡为主。母亲不理解海南人为什么会吃得如此的简陋。她自然不知道,在海南人的理解里,那么好的食材,任何过度的烹饪都是对食物味道的破坏。而从物质贫乏时代里走过来的母亲会觉得,那么好的食材,不好好地用各种调料加工一下,岂不是浪费了那食物的珍贵吗?
这不只是对食物理解的差异,这几乎是一种处世哲学的差异,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
这不是母亲的错,她的饮食习惯是个人生活多年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是她的舒适区域,是她多年人生妥协的结果。她喜欢吃的每一种食物,都有一个远大于食物本身的故事。
我的母亲所做的食物,大都和时间、力气有关。母亲几乎是一个村庄的代表,我记忆中的村庄里,有数不清的平原上的炊烟,属于母亲的空间极小,院落——田野——菜地。这空间宽阔且狭窄,方圆六里地盛放了母亲的半生。
在旧年月里,一个村庄,就足以安放一个人的一生。我的母亲,在40岁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我出生的村庄。所以,一说起母亲,就会打捞出以下的折叠——我出生的院子、村庄,以及村庄外属于我们家的几块麦田。这些劳作和生活的场景,就是母亲的全部内容。
母亲煮的粥,是我出生的那个村庄所有女性煮的粥的味道。母亲做的馒头,是我们村庄里所有麦子的味道。不能简单地用“好吃”来形容母亲的食物。我18岁出门,以后的30年,吃过全国各地的面食,却很少能吃到母亲做的手擀面的味道。母亲的食物,与其说是“好吃”,不如说是母亲在一碗面里,传递了爱。这既是哲学的,也是属于内心的。
一个人最初的胃部记忆十分繁杂,很难准确梳理。在年纪尚幼的时候我就知道,村子里许多孩子的母亲做的食物比我母亲做的好吃。我的母亲不会做很多花样翻新的菜肴。然而,母亲做的蒸馍,对我来说,是对食物最初的启蒙。
从种麦子开始,一直到麦子收割,母亲全程参与了麦子的成长过程。她珍惜每一粒麦子,面粉打出来以后,母亲会用一种规格极细的箩再次对面粉进行细筛。这样,粗的面粉被做成一种馍馍,供父母和我们兄妹吃。而细箩筛过的白面做成的馍,是专门给爷爷吃的。
食物的贫乏,让面粉也有了身份的差异。那时的乡村,强调长幼有序,尊老才会获得社会的认可。所以,母亲的做法为她挣得了不错的名声。随着年龄的增长,麦子不再紧缺,我们这些小孩子渐渐也能吃到专供给爷爷的细面馒头了。以后的时间里,只要吃到馒头,都会以母亲手工做的馒头作为参照。母亲的馒头,成为一个地址、一个标签。
母亲的食物是众多颜色中最清晰的白色,大雪的白,馒头的白,面条的白以及米粥的白。母亲的食物,是众多河流中最宽阔的那条,是一年四季中最为舒适的秋天,是秋天的树叶落在地上后的沉醉,是我不论走多远都洗不掉的黄河的底色。母亲的食物,其实更像是一幢关于爱的碑刻,一刀一刀地刻在我的味蕾上,是魏碑,是汉隶,也有可能是酒醉后的一纸行草,不论我离家乡有多远,都能在瞬间接到食物的信息。
作为一个中年人,在外面漂泊多年,饮食习惯早已经改变了最初的狭窄。然而,母亲的食物对我来说依然有效。很难解释,人的身体记忆为何如此固执。如果说母亲的食物是一种文化的铺垫,那么,我们的一生中总有一天,将超出母亲的认知范围。然而,食物的记忆却会打破这样的循环。食物打破身份的限制,我们对母亲的接受,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包含着食物味道的捆绑。吃到母亲的食物的那一瞬间,我们被时光遣返回多年以前,我们复又变得柔软而单纯,我们成为一个陈旧的自己。
母亲,有多么具體,便有多么抽象。在城市生活多年,大多数时候,我已经成为一个说普通话的人,然而,一旦回到县城回到母亲的生活圈子,我立即又开始使用母亲的方言。那些字词,像一道道的食物一样,既养育了我,又温暖了我。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以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进行评论,而唯有与母亲相关的东西,比如母亲的食物,我们无法评价。它是我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最初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我将成为另外的人。
母亲的食物,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比喻,它和温饱有关,和爱相关。实际上,它大于文化,也大于审美。母亲的食物是一种植物,时光越长,长势越好。中年以后的我,自然而然地开始喜欢朴素简单的东西。而这样的喜欢,和母亲的食物是多么一致。
原来,人生就是这样循环守恒。疏远和回归,需要时间需要距离,我们离开故乡,是为了确认自己已经不再单一。当我们足够丰富时,最初的简单的食物却又渐次清晰。
离开才能丰富,丰富才能回归,回归才会简单。人是如此,食物也是如此,故乡呢,也是如此。
吴忧摘自《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