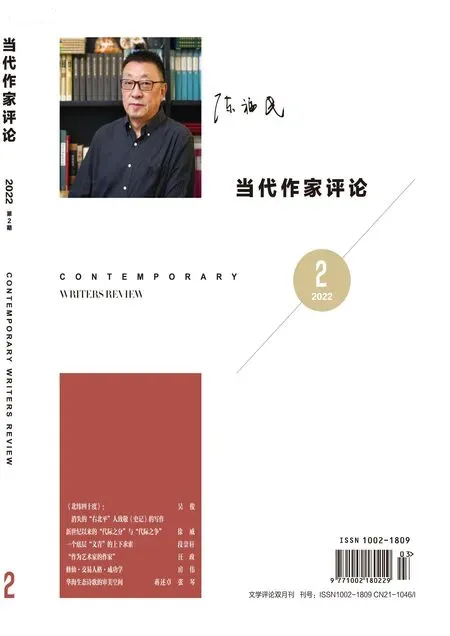从“主人公”到“英雄”
——从一首译诗看当代翻译诗学的面向
李 昕
2018年10月,诗人王家新翻译的阿赫玛托娃诗选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定名为《没有英雄的叙事诗》。这一书名出自阿赫玛托娃晚年的同名代表作,一首被誉为20世纪诗歌经典的三联叙事长诗。对于熟悉王家新诗作和诗论的读者而言,这是意料之中的命名。多年来,王家新在不同文章中多次提到“没有英雄的诗”,认为这不仅是阿赫玛托娃诗歌创作更本真的写照,也是深入中国当下诗歌的重要隐喻。他甚至说:“我要这样来‘读’,哪怕是一种误读。”
在此之前,该诗已有4个全译本,分别是:陈耀球的《没有主人公的歌》(1985)、汪剑钊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2015)、乌兰汉(高莽)的《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2016)、晴朗李寒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2017)。此外,在众多介绍、评述文章中,该诗多以《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之名被广泛提及。就汉语表意逻辑而言,《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或《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表意明晰,清楚地说明了该诗不含某一类型的人物,不存在任何语言歧义。而在《没有英雄的叙事诗》中,译者舍弃了“××人物”或“主人公”(作为人物类型)和“叙事诗”(作为文体)之间顺畅的逻辑关系,将“英雄”一词置于语义的核心,凸显了其分量。相比其他译法,这一翻译制造了一定程度的生涩感和语义复杂性。此外,王家新还通过译注,提示了“英雄”一词有其历史脉络和现实意蕴,从而使这一诗名的翻译成为颇可琢磨的问题。
为了探究该译名出现的原委及其背后的诗学动因,笔者通过词源学、概念史、文学典故上的钩沉稽考,结合原文本意与译者诗学,尝试发掘这一译名背后耐人寻味的翻译意图,并由此带来对诗歌翻译和当代诗学的一些思考。
一、词源学、概念史及文学典故稽考
据王家新介绍,他的译文是从英译转译的。在多位英译者笔下,该诗的标题均为“Poem Without a Hero”。英文单词hero的复义性为多元阐释提供了的空间,也在汉译中构筑了难度。基于其英文释义,该诗题至少有三种可能的含义:(1)没有主人公的诗;(2)没有英雄的诗;(3)既没有英雄也没有主人公的诗。那么阿赫玛托娃的原题究竟何意?是二者居一,还是兼而有之的一语双关?
该诗的俄文标题为“Поэма без героя”。其中,Поэма大致对应英译本中的poem,但不尽相同。俄语中表示“诗”的词汇并不唯一,Поэма有其具体的语义所指,即“长诗、史诗,叙事长诗、史诗性巨著”,这也是为什么多数汉译本将其处理为“叙事诗”;第二个单词без表示“没有”,对应英文中的without,语义清楚明确;最后一个单词героя对应英文中的hero,在俄文中它同样是个多义词,既可表示“英雄”,也可表示“主人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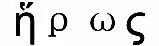
以上三种释意互相区别,又紧密相关。在此后漫长的语言演化进程中,hero的语义被不断地附加、推衍,逐渐出现了“主人公”的语义。考察西方文学的历史,不难发现,“肇始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学中的主角其实最初就设定为英雄”。这不仅包括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或希腊悲剧中的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抑或中世纪文学中的宗教英雄、圆桌骑士、绿林好汉,即便自文艺复兴至18世纪,普通人日渐成为文学的主角,他们也往往代表了人性中优秀的品质,如高尚、纯洁、善良、勇敢、坚毅等等,所以仍然延续了“英雄”的某种属性。
文学史上英雄神话的真正动摇是在19世纪。华兹华斯主张以普通人的语言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而堪称浪漫主义英雄最强音的“拜伦式英雄”,则带上了撒旦一般的负面力量。此后,现实主义小说大师萨克雷更直接以“没有英雄/主人公的小说”作为自己的名著《名利场》的副标题。英雄主义在文学中的全面坍塌出现在20世纪。这不仅表现在主要人物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更表现在代表勇气、信念和统一价值的英雄精神,逐渐让位给对存在之困境和抗争之虚妄的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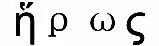
二、原诗本义与作者诗学
《没有英雄/主人公的叙事诗》(为免歧义,下文在分析原著时简称《没有》)是阿赫玛托娃深植于自己和同代人的命运悲剧而孕育出的苦花。自1940年开始创作,至作者去世前一年,这首诗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作者持续修剪添补,使这首诗变得日益深邃,“没有一只火把投进去能照亮它的底部”。不能不说,阿赫玛托娃是深怀抱负的。为了这部标志着她“创作的峰顶”的作品,她阅读了赫列布尼科夫、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巴格里茨基等几乎所有同代人的长诗,甚至还同布罗茨基讨论过“构思的宏伟”。在一代人以及一个城市的悲剧命运面前,她曾经“沉默了三十年”(《第七哀歌》)。这首长诗,是她以全部的生命记忆为命运“加冕”,为那个城市和那一代人“送葬”。强烈的悲悯、历史的沧桑和深切的命运意识,支撑着诗人把这部作品写成了史诗。
除了史诗般的架构和意蕴之外,诗人亦调集一生的诗艺,充分吸取本民族及世界诗歌的养分,创作了一部在艺术手法上极具创新性的作品。有研究说,《没有》让人想到了艾略特的《荒原》,这毫不奇怪。长诗中丰富的象征、隐晦的指代、繁复的叙事视角、毫无预设的人物转换、多种诗歌体式的交融、叙事与抒情的高度浓缩和杂糅、大量的引文和典故、明显的“元诗”性写作等,无不表明奉行传统诗观的阿赫玛托娃其实是站在西方现代诗歌的总体成就上创作了这部杰作。
一诗之名,往往是诗歌要旨所系。诗人曾自陈,她是用“隐形墨水写作”,她的“盒子里有着三重底”,那么,《没有》这首诗的诗名,是否也体现了长诗对隐晦、复义和创新的追求呢?
《没有》的诗名首先指向诗中人物。作者在长诗的第二部“硬币的另一面”,对“主人公”做出了具有元诗性质的解释:
我回答说:“他们是三个人——
其主角扮成了里程碑,
另一个的穿着像是恶魔——
他们的诗都在那里,
会确保他们在世纪扬名……
第三个只活了二十岁,
……
结合长诗的内容,这三个人物的原型分别为勃洛克、库兹明和科里雅泽夫。此外,长诗的主要人物还包括女舞蹈家奥尔嘉·苏杰伊金娜。但诗中的人物形象都是诗人运思之后的艺术形象,带有特定的象征意蕴。
勃洛克是长诗的灵魂人物。作为阿赫玛托娃眼中的“世纪初的纪念碑”(《诗三首》),勃洛克被作为白银时代诗歌精神的最高象征。在这首诗里,作者将勃洛克虚构为奥尔嘉成功的追求者,优雅高贵,如同坠天使。但作者很少用叙事性的笔墨,更多的是通过与其诗作相关的引文,将勃洛克刻画为过去时代的精灵,在长诗里出没无定,配合着诗人完成了关于那个时代最悲怆的叹惋。
如果说勃洛克是理想诗歌的明媚光影,库兹明则化身为黑暗王子,在长诗里投下恶魔般的阴影。库兹明是阿克梅派的前辈诗人,被称为彼得堡的“唯美派王子”。作为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及特立独行的唯美主义者,库兹明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在长诗中,库兹明被作为享乐、轻浮、放荡的代表,作者借此表达了对历史及彼得堡文化中轻浮、冷漠一面的反思。
科里雅泽夫是长诗中线索型的人物,发生在1913年的科里雅泽夫自杀事件,和俄国的历史变迁交织在一起,在作者的心底激起的回响远大于事件本身。在阿赫玛托娃眼里,1914年才是新世纪真正的开始,开启了战争的、革命的、动荡的20世纪,“一个真正的——而非日历上的——/二十世纪向我们走来”(《没有英雄的叙事诗》)。而科里雅泽夫自杀事件,似撬开一战前彼得堡城市文化及诗歌风尚的杠杆,被作者作为核心事件加以描述。青春、单纯、脆弱的科里雅泽夫,成为先后罹难的一代诗人的代表,其身上叠合着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叶赛宁等多人的影子;而女主角奥尔嘉则被作为“时代的肖像”,因为她“哪怕连手指尖都属于那个时代”。Nancy K Anderson, ’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2004,p.211.本文英译汉为笔者译,不另注。但长诗中的她,“只是表面上的奥尔嘉,而实际上也是我,也是安德洛尼科娃”,也是舞蹈家安娜·巴甫洛娃。
如前所述,这首叙事诗并未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它以强大的内力,将叙事和抒情压缩、打乱、糅合。故事中的人物也由此成为群像,成为“一大群纠缠的影子”,轮廓不清,彼此投射,无法真正区分和辨识。作者所倾力表达的,并非一个或几个人物,而是一代人的命运,一种文化的挽歌。
那么,这首诗又是否与“英雄”有关呢?
最早建立这一关联的是苏联时期的学者,他们认为这一诗题借鉴自拜伦《唐·璜》的开篇:“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虽然阿赫玛托娃未曾明言,也没有直接的证据为之证明,但文本内外有大量的资料可资参考。
就文本外而言,阿赫玛托娃对拜伦不可谓不熟悉。这不仅是因为拜伦曾在19世纪的俄语诗坛引起旋涡般的影响,甚至出现了“拜伦主义”的说法,也因为阿赫玛托娃倾后半生之力所研究的普希金将拜伦视为“另一个天才”“另一个主宰”(《致大海》)。此外,在个人的散文及诗作中,阿赫玛托娃多次提及拜伦及其名著《唐·璜》,1946年长诗中的“来自未来的客人”以赛亚·伯林到访,阿赫玛托娃除了跟他分享了《没有》之外,还专门朗读了《唐·璜》中的诗句。
其次,阿赫玛托娃个人的生活及创作亦与浪漫英雄主义不无关联。个人小传里,她这样概括自己的创作:“我写诗,是以我的国家英雄的历史为主旋律的。”按照《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说法:“她接受、并分担了俄罗斯的悲剧命运。”她不仅以坚忍高贵之姿承受了命运矢石的交攻,更以悲悯和博大超越于个人遭遇之上,发出一代人的咏叹和悲吟。
就文本而言,该诗也多处与拜伦或《唐·璜》有关。第一部第一章的第三个题词“我的火焰般青春——当乔治三世为王”就出自《唐·璜》;第二章开头散文部分“小黑奴们在打雪仗”及第二章开篇“梅耶荷德的小黑奴”,均为彼得堡上演的莫里哀的喜剧《唐·璜》中的情景;而在第二章中,作者化用勃洛克描写唐·璜的诗歌《督查骑士的脚步》中的诗句,建构起了“勃洛克—拜伦”和“奥尔嘉—安娜”的关联,由此,勃洛克被比拟为一个拜伦式的人物;第二部,诗人提到了拜伦为雪莱举行火葬的情景,高擎着火炬的拜伦成为诗人诗歌理想的化身。
而作品中的人物,亦具有鲜明的“非英雄”或“反英雄”的特点。阿赫玛托娃曾在相关笔记中写道:“可怕的是‘所有人’都参加了假面舞会,但没人表示懊悔。”Nancy K Anderson, ’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2004,p.204.假面舞会是时代的隐喻,“没人表示懊悔”则可引申为“没有英雄”的一种具体说法。世纪末的狂欢文化裹挟了一代人,但无人警醒或担当,由此形成的悲剧底色,一直绵延至全诗终了。以主要人物论,勃洛克虽是一代精神之高标,但在生命末年受抑郁症困扰,忧郁消沉;库兹明一直以反面形象出现,代表了末世浮华;年轻诗人科里雅泽夫身为骠骑兵少尉,本该坚强骁勇,却脆弱到为情自戕;奥尔嘉艺高貌美,却是时代里“困惑的普绪克”。传统叙事诗中的焦点型主人公并不存在,传统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亦不存在,甚至自信而昂扬的英雄精神也不存在。
由是观之,作为复义单词的героя在这首诗中不乏双关之意味。但两种含义一显一隐:一为本义,一为联想义。“主人公”之义,从文本即可自证;“英雄”之义,则需基于原诗主题、语境及作者诗学深挖得出。译成汉语时,由于天然的语言差异,两种含义无法兼顾。译者的考量和取舍,则不仅关乎对原诗的理解,还与其诗学主张和翻译理念深刻相关。
三、译者诗学与翻译理念
事实上,对于“主人公”这一本义,王家新心中是了然的。在《没有英雄的诗——纪念阿赫玛托娃》一文中,王家新提到他曾询问过有关俄文翻译家,得到的答复是应译成主人公。但他接着写道:“我仍倾向于把阿赫玛托娃的这首长诗,甚至她一生的创作置于‘没有英雄的诗’这样的命名之下。我宁愿这样来‘读’,哪怕是一种‘误读’。”
王家新的这种坚持,与他对原诗的理解不无关系。在《没有英雄的叙事诗》的译者注里,他写道:“该长诗有多个人物,包括叙事者自己,但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主人公,故译为《没有英雄的叙事诗》。”可以说,原诗的潜在含义为王家新最终确定这个译名提供了依据。但这并非最关键的因素。他所以这样翻译,更多的是基于对阿赫玛托娃创作的理解,或者说,是基于一种诗学意义上的辨认。
在王家新的诗学及翻译理论中,“辨认”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自己的一生,就是一个对诗歌、对自我、对命运的辨认过程。……人生是一种辨认,写作是一种辨认,翻译更是——这至少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和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辨认,到最后,这成为一种对生命、对诗歌本身的最深刻的辨认。”王家新在阿赫玛托娃身上辨认出了一种同时含蕴着承担精神和反讽眼光的诗学品质,一种现代诗歌和诗人的真实命运。
王家新非常看重阿赫玛托娃的承担精神,他在包括《没有英雄的诗——纪念阿赫玛托娃》《承担者的诗——俄苏诗歌的启示》《1941年夏天的火星》等多篇诗论随笔中谈及阿赫玛托娃的承担精神。他曾说:“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一个柔弱的女诗人告诉了我怎样以诗来承担历史赋予的重量,她就是阿赫玛托娃。”他惊异于后者“对苦难历史的承担、在地狱中的冒胆穿行及其反讽品质”,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洞察一切的目光”及“安于命运的沉静”;他赞赏在苦难面前她不失控,不失态,更不沉沦,“不允许自己因与现实的过深纠葛而妨碍了对存在的全部领域的敞开”;他认为她在苦难里发展了诗艺,生长出“反讽”的品质和才能,掌握了极好的艺术辨别力和分寸感,从而“把不堪承受的历史化为了诗”,“把诗写到了让人惊心的程度”。在王家新看来,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属于“从来不是那种想当‘英雄’的人,但他(她)在巨大压力下所做出的一切,却使我们的内心至今仍不能不受到震动”。
而阿赫玛托娃式的承担精神不能不在王家新的精神世界里激起强烈的共鸣。在中国当代诗坛,王家新早就被放到了“承担者”的位置上。程光炜通过对其90年代创作的分析认为:“他将时代的遽变融入个人的思考过程,然后又将个人命运的苦难置于时代这个特殊的历史空间,从而成为真正有勇气承担起历史重量的诗人。”
促使王家新如此翻译的,除了他的“承担诗学”,还有一种深入存在本质的深切意识和诉求。正如诗歌创作不是为了“美学或道德上的正确,而是为了接近存在的奥义”,诗歌翻译亦然。虽然诗歌翻译的文本是过去之物,但译者却有义务把它带回当下,让它与此在的现实产生摩擦,如此或者可以获得希尼所谓的“诗歌的纠正”的力量。因而他认为“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译法过于因循传统,“带有一种五六十年代的色彩,而‘没有英雄的诗’却能指向一种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诗学实践相关的话语”,才与诗人和诗歌的当下命运发生对话。
这是一种诗人不再是世界的“立法者”(雪莱语)的时代,是诗人不再身居文化中心,或者被视为“酒神的神圣祭司”(荷尔德林语)的时代。资本的冲击、消费主义的流行、文化样态的变化,如此种种,使文学退居边缘,而诗歌则退居边缘的边缘,“生逢这样一个时代,如果说我们曾有那么一种诗歌精神,那我也感到了它无望的告辞。我们的想把它挽留下来的一切努力似乎也都是徒劳的”。这就是王家新和他的诗人同辈们面临的现实。王家新的老朋友,德国汉学家、诗人、翻译家顾彬深解“没有英雄的诗”的况味,写下“世界太昂贵/诗律太便宜”和“诗行不是英雄/它寻觅轻巧的形式/犹如鱼寻求柔和的火”这样的诗句送给他。
在这样一个时代,“诗歌何为”“诗人何为”不仅是诗学命题,更事关诗歌与诗人的存在本身,愈到危急时刻愈是如此。王家新无数次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说“没有英雄”构成了客观现实,“无需英雄”则体现了诗人倔强而明智的坚守。“这是诗,已无需英雄的存在;或者说,这种诗里没有英雄,没有那种英雄叙事,但依然是诗,而且是苦难的诗,高贵的诗,富于历史感的诗。正是这样的诗在今天依然保持住了它的尊严,或者说,在与历史的较量中,正是它替我们赢回了属于我们个人的精神存在。”王家新如此说,他后来的诗也的确如此,没有英雄叙事,诗歌也不再是英雄的舞台。当代诗人们面对这样的命运,不辍坚守,默然承担,以此对抗住流俗的吞噬,守护着诗歌的尊严。虽然在这之中,分明也有一种英雄主义的回声。
回到翻译本身,“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译名或许体现了原诗在诗歌类型上的特征,但“没有英雄的叙事诗”则指向了存在的基质,指向了一种写作的品格和精神,甚至也是一种诗歌理想。它以一盏从阿赫玛托娃手中接过来的灯,刺透了历史和当下的幽暗。
而从翻译诗学的角度看,这样的翻译所以成立,也与王家新对翻译的理解有关。王家新认同本雅明的翻译观“翻译是(文学的)一种样式”。Walt Benjamin,,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69,p.70.译作并非附丽于原作,而是在延续和拓展原作的过程中获得独立的价值;译者的翻译活动不只得到了原作的授权,更得到来自文学本身和他自身时代的授权;译者所追求的忠实亦不局限于对原作字面的忠实,而应在更高的维度体现对诗歌本身的忠实。
王家新是不惮于袒露译者个性和创造性的。但他对诗歌翻译中的“精确”同样有着执着的追求。他认为翻译就是要找到“那个唯一的词,因为诗歌就是语言唯一的绝对性”。这唯一的词不仅透露出诗歌创作的关键所在,如果可能,还应力图抵达存在的隐秘。在这首诗题的翻译里,“英雄”就是那个唯一的词——它和原作形成互文,和当下的诗歌境遇产生深刻关联,它本身即构成了一个诗学的命题,带着历史的纵深感和对现实的关切。
四、诗歌翻译的面向
译事本就复杂,方家各有其道。但王家新的译诗理念及策略,揭示了诗歌翻译面向的几种可能:面向差异,面向开放的文本关系,以及面向译者显身的翻译。
将翻译作为跨越不同民族文化的手段和方式,使其工具化、透明化,最大限度上实现“再现”和“对等”,是传统译论所秉承的基本准则。这种译论,面向意义的确定性、文化的交融性,以及语言间的共通性,但回避甚至遮蔽了翻译中的差异。而面向差异的翻译,则承认存在于文本、语言、文化及参与主体等层面的差异,认为翻译无法完全穿透这些差异,实现对原文本的等值复现。因其如此,翻译及翻译批评更应在充分尊重并直面这种差异的前提下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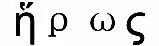
就具体翻译而论,语词一旦开始了它跨越语言与文化的旅程,就必然有所“丢失”,又有所“获得”。以“英雄”一词为例,面对其多义性所带来的难以分割的多维内涵,汉译者必须做出取舍,是译为“英雄”还是“主人公”,相信不是一位译者所面临的难题。而从文化上看,这个词又带有希腊文化、圣经文化、西方文学的历时积累等多重因素所赋予的文化负载。首先,这些文化负载是无法经由翻译全然传达的,在中西不同语境中,“英雄”一词所激发的想象必然不尽相同;其次,我们也无法要求这个词不与译语接受语境发生新的摩擦,产生新的语义。可想而知,源语语言与文化本身在不断地变化,译语亦然。
及至参与主体的层面,即译者层面,差异更是无法避免的。文学翻译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文学活动,创作主体对作品本身必然产生影响。永远不存在和原作等同的译本。不论自觉与否,每一位译者所呈现的,都只是个人意义上的译本。承认译本间差别的合理性,承认个性化译本的必然性,才能形成健康的翻译批评语境,为个性化翻译留出空间。可以说,“差异”本身即是生产性的,会促进文学翻译展现更充沛的活力。
王家新的翻译不仅创造了有意义的“差异”,重要的是,他的这种翻译深刻介入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进程。对此,已有多位论者在文章中予以阐发。当代诗人、评论者张高峰在一篇书评中这样说:“《没有英雄的叙事诗》不仅是一位中国诗人‘爱的产物’,也深刻传达出因命运相共而唤起的‘周身战栗’。正是在一种全然发自骨肉沉痛般的灵魂连接中,王家新以他对‘口授者’的生命领受,以他坚实而隐忍的汉语和卓越的译写,‘把她的时代带入到我们的时代’:‘一个真正的——而非日历上的——/二十世纪向我们走来’。”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足见译名之重要。多年来,阿赫玛托娃的“Поэма без героя”一诗以《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为中国读者所知,王家新的翻译,以《没有英雄的叙事诗》刷新了对该诗的读解。此一名之立,彰显了译者与原作者诗学理念的深度交互,它激发了原作的新生,同时也必将在汉语诗歌中引起持续的反响。这一切,如同王家新所译的这首长诗“第一献词”中所写下的:“不,这只是坟墓上的/松针,在沸腾的泡沫上/临近,更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