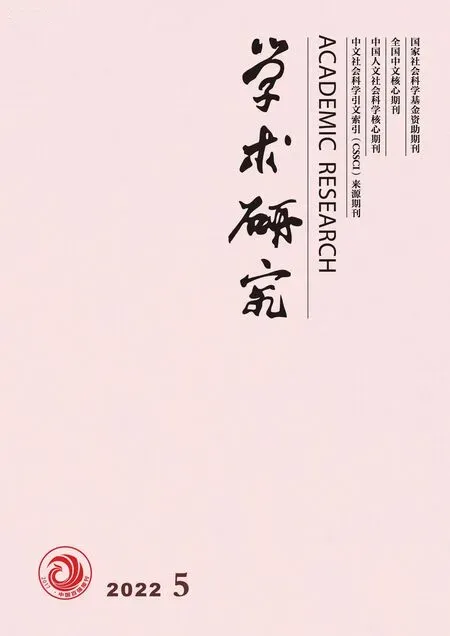论休谟的道德动机及其与道德感的关联
李 薇
究竟是什么原因激发人们做出那些被我们称为德(virtues,如正义、仁慈等)的行为?这一问题关涉道德动机(moral motive)的本质。18世纪英国道德哲学家休谟在坚持道德源自情感的基础上,将道德动机理解为人的心灵中某种具有推动作用的情感,①Norman Kemp-Smith, The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Don Garret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2.认为它是我们判断某一行为是否为德的必要条件。因此,道德动机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②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David Fate Norton, Mary J. Norton(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p.307-308.当前,以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迈克尔·A.史密斯(Michael A. Smith)为代表的休谟主义者几乎都分享了一个基本观点,即欲望在休谟道德动机中发挥着更为根本的作用。③Donald Davidson, “Actions, Reasons, and Causes”,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Michael Smith, “The Humean Theory of Motivation”, Mind, vol.96, no.381, 1987, pp.36-61; Michael Smith, The Moral Proble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Bernard William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Moral Luck: Philosophical Papers 1973-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面对反休谟主义者对休谟动机理论的批评,④反休谟主义的代表有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M.普拉茨(Mark de Bretton Platts)等,他们认为道德动机与欲望无关,信念可以直接激发道德动机。参见Thomas Nagel, 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John McDowell, “Non-Cognitivism and Rule-Following”, Wittgenstein:To Follow a Rule, Steven H. Holtzman, Christopher M. Leich (ed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1, pp.101-113.史密斯又进一步将动机解释为在欲望和手段目的的信念中获得其来源,试图为休谟的动机理论做辩护。目前,学界围绕休谟动机理论中关于欲望和手段—目的的信念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技术处理,⑤参见徐向东:《欲望的本质和休谟式的动机》,《道德与文明》2015年第5期;杨松:《道德动机的来源——当代休谟主义与康德主义的争论》,《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王奇琦:《论休谟主义者的道德动机》,《世界哲学》2015年第1期;文贤庆:《休谟式动机理论的本质》,《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4期等。本文则准备从情感框架内部来深入分析和论述休谟对道德动机的理解。因为,无论是欲望还是手段—目的的信念,它们在休谟的道德视野中都属于情感范畴,其本质就决定了它们始终无法超越主体经验,也很难对这一关键问题做出有效回应:人们为何会摒弃主观差异而自觉凝聚道德共识?我们知道,发现并建构一套始于人性自身的、普遍有效的原则谱系才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论宗旨和基本任务。①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367.其实,如若我们仔细考察休谟的道德哲学,就不难发现他还着重强调了效用的道德功能。②参见[英]弗雷德里克·科普勒斯顿:《科普勒斯顿哲学史第5卷·英国哲学:从霍布斯到休谟》,周晓亮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9页。国内对“utility”的翻译并不统一,有时译为“效用”,有时译为“功利”“有用性”等。因此,本文对这几个术语的含义不做详细区分。休谟表示,这一原则能有效约束人的欲望、信念等情感因素,从而更好地指导和规范人的道德实践。休谟道德动机的这种内在张力使其本身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特性,这亦是他努力追求道德哲学科学化的结果。
鉴于此,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论述休谟对道德动机的一个重要的前提预设,即道德动机是激发德的真实存在的原因;第二部分将讨论休谟道德动机自身包含的客观性、社会实践性和社会现象性等固有属性;第三部分将考察道德动机的这些属性在仁慈、正义两种主要的社会德性(virtues)中的具体展现;第四部分将论述道德动机与道德感的关联。如此一来,休谟关于道德动机的理解将会得到较为完整的呈现。
一、道德动机是激发德的真实原因
休谟明确表示,当人们做出被称为德的行为时,他们心中必然存在激发这些行为的原因,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动机。但是,人们往往只重视外在行为,而忽略了心中被标识的那些情感对象,即激发行为的真实原因或理由,它们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③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307.休谟认为,道德动机是我们判断某一行为是否为德的必要条件:“离开了有别于道德感的某些动机或者有推动力的某些情感,就没有任何行为是可以赞美的或可以责备的,所以这些个别的情感对那种道德感必然有一种巨大的影响。我们的责备或赞美,都是依据这些情感在人性中的一般势力。”④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311.休谟也因此被称为动机论者。但是,人们内心的情感往往是隐匿的,并不能被我们直接感知和把握。它们真的存在吗?它们又何以成为我们的考察对象?对此,尽管休谟并没有直接言明,但从他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答案,即道德动机是真实的而并非虚构的对象,这也是休谟设计道德动机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预设。因为,尽管情感隐而不显,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与之对应的各种外在标识和表现(如语言、表情、行为等)对其进行考察和剖析。换言之,这些能被感知的外在标识和表现就是反映我们心中情感的具体符号,通过它们我们就能间接地探察内心的道德动机。正如休谟所说:“当我们赞美任何行为时,我们只考虑产生行为的那些动机,并把那些行为只认为是心灵和性情中某些原则的标识或表现。外在的行为并没有功。我们必须向内心观察,以便发现那种道德的性质。我们并不能直接发现这种性质,因此,我们只能专注行为,将其视为外在标识。尽管这些行为仍被视为标识,但我们称赞和赞许的最后对象仍是产生这些行为的那个动机”。⑤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307.
简言之,道德动机是通过其外在标识而变得真实的。这些标识是道德主体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人们总是可以通过各种语言进行交流,也会看见对方的不同表情、行为等,因此它们就可以被视为一种既有的事实。由此,激发这些行为的道德动机也就是真实存在的。它存在的事实就在于,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总会向他人表明或反省我们自己做出德行的原因或理由,而这些原因或理由在通常情况下也的确是有所指的。比如,当我们询问一个人为什么要向难民施以援手时,他极有可能给出的理由是“他们是我的同胞”或者类似的其他答复。
此外,休谟还讨论了真实的道德动机可能被遮蔽了的情况。受某种原因的影响,善的动机可能被遮蔽了,并没有立刻被察觉,但当实际情况得到澄清后,我们仍会由起初的责备转为敬重,并依然对激发这种善的动机表示赞许。①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307.休谟在此想表达的意思是,当我们指责某人没有及时做出德行时,总是在心中预先设定了处于某种情况下的人们应当持有善的动机或者承担善的义务。如同上述情况,人们之所以会对救助行为表示称赞,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心中原有的救助动机。如果某人因阻力没能及时行救助之举,我们起初或许会责备他缺乏善心,但了解实情后,我们还是会对他的善心表示赞许。质言之,即便我们受干扰没能及时做出正确判断,也绝不会影响道德动机的真实存在。总之,无论是出于同情,还是出于仁慈,又或是出于多种理由或动机的混合,也不论我们是否会对行为的真实原因或理由做出错误判断,道德动机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客观事实。对此,麦金泰尔做出了很好的诠释:“每一种道德哲学都或隐或显地对行为者与其理由、动机、意向和行为的关系作出至少是部分的概念分析,而这种做法一般又预设这样一种要求:这些概念被具体化或至少能够被具体化在现实的社会世界中”。②[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还需说明,休谟这种分析道德动机的理论方法与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当时,不同领域的哲学家都倾向于将心灵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由心灵产生的情感就可以作为客体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其也就自然带有了“客观属性”。③Alexander Broadie(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2.休谟对心灵的探讨也遵循了这种自然主义的路径。对此,我们可以从诺曼·K.史密斯(Norman K. Smith)对休谟哲学的自然主义解读中得到一定的理论支撑:“史密斯提出了对休谟哲学的一个新的看法:休谟哲学的主题不是怀疑主义的,而是自然主义的。这里的自然主义是指一种理论方法,它要求将人看作自然物,对人的感觉、思想和行为等的实际状况作如实的、自然的描述,这一描述可以用自然科学的观点和语言进行解释。”④转引自周晓亮:《休谟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绪论第11页。概言之,当休谟谈论道德动机时,就已经为其设定了一个客观性维度。但他还必须应对的问题是:既然道德哲学研究的是那些普遍的、确定的、共同的对象,那么道德动机就应该具有同样的属性。不过,这种具有推动性的情感究其本质仍然属于感觉,因而其必然具有主体差异性,那么它又如何引导人们自觉并自发地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如果道德动机缺乏这种普遍效力,就只能沦为零散的、个别的意见,绝不可能帮助人们凝聚道德共识。但倘若道德索然无味,既不令人向往,也不遭人憎恶,那么它就不会对人的行为产生任何影响。休谟认为,道德动机本身必定蕴含着某种能吸引人的特性,从而持续地激发人们追求它、实践它,而这也将我们引向了休谟道德动机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即社会实践性。
二、道德动机的重要特性及其相互关联
休谟反复强调,道德哲学是一门实践学科,而我们做出道德推理的最终目的就是行动。⑤参见[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周晓亮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3-4页。因此,道德动机的实践性是指道德情感自身就能转变为能动的行为准则,对人的道德交往起到规范作用。但是经过上述论述可知,道德动机的本质是心中真实存在的情感,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那么应如何规范人的日常行为,使之弃恶扬善、克己利他?若道德动机的实践性得不到有效说明,休谟所建构的道德知识就只能流于被动的、静止的形式。换言之,在休谟那里,激发德行的情感必定会受某种强有力的原则控制和约束,促使人们自觉地遵守一致的道德规范。因此,除了客观属性之外,休谟认为道德动机自身必然包含一种实践性,否则在社会生活中就不会出现诸如见义勇为、慷慨捐助的道德现象。其实,休谟在设计道德哲学体系时,就已经将这种实践特性纳入考量。道德动机的实践性源自何处?对此,休谟的回答非常清楚,它的实践性就是来自社会效用或社会功利。“在一切道德决定中,社会效用这个条件是人们所主要考虑的。”⑥[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第11页。即在休谟那里,社会效用就是人们衡量一切道德决定的主要因素。进而言之,如果要使道德具有规范作用,我们就必须对激发人们做出德行的那些情感有所规定,即它们并非任意的,而必须具有共同的、一致的特征:这些情感以及由此激发的行为必须给他人或者整个社会带来有益的后果。正如休谟所言:“公众的便利对道德起规范作用,它不容违背地建立在人性中,建立在人所生活的世界的本性中”。①[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第35页。实际上,休谟在考察道德起源时,就已经提前将效用融入与道德情感相关的论述中。他认为,在人性中总有一种倾向,即把效用带来的情感和道德的情感相互混淆,使两者难以分辨。更重要的是,效用原则有着最大活力,它能完全控制人的情感。休谟将其比作牛顿力学中的重力定律,认为它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②参见[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第30页。能影响并改变心灵世界中的情感方向,使其朝向公共利益。质言之,休谟所建构的道德哲学之所以能成为实践的、规范的学科,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功利。但是,休谟更关注这种社会效用激发道德行为的心灵发生机制。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切实有效地指导人的道德生活。
首先,休谟认为,激发人们做出道德行为的并不是某一种单纯的情感,而是某些相互融合的情感。他指出:“情感虽然是各自独立的,但当它们同时存在时,就会自然地相互融合”。③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270.只不过,道德动机并非各种情感和利益的随意融合,它必定遵循某种心灵秩序,最终形成具有主导作用的情感或利益,否则,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道德世界就是混乱无序的。其次,这些自发融合的情感和利益应当以社会效用为根据对自身做出甄别和排序,在合理利己的基础上,通过影响、改变其自身的方向,使那些对社会整体有利的情感(如仁慈、正义等)成为指导行为的主导原则,进而使道德动机的合力始终朝向公共福祉。而且,社会效用是被人们真实感觉到的。因为,不论是出于自爱,还是出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情感,效用总能直接给人带来愉悦感,并自然得到赞许,再借助同情的感染力传递至社会更多领域。由此,休谟道德动机的社会实践性也总是包含着客观性的,并通过一种获益的真实感觉来激发人们做出德行。
但是,这里还需要阐明休谟是如何有效调节利己和利他的。笔者认为,休谟是通过在道德动机中赋予利己一定的道德功能来应对这一问题的。他明确表示,利己也是激发道德的动力之一。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我们不能彻底将其根除,唯有改变这种情感的方向来做出补救,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通过同情的传递实现从利己向利他的过渡,“公益若不是由于同情使我们对它发生关切,对我们也是漠不相关的”。④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394.总之,同情使每位社会成员脱离自己的圈子,实现利益情感的分享和传递,使对他人利益的关切成为对我们自己利益的关切。⑤参见[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第46页。此外,为了巩固那些高尚情感作为道德基础的效力,休谟认为还需进行一些人为干预。比如,通过缔结协议、履行责任、实施教育、颁布法律等方式鼓励人们持续地行善弃恶,假以时日将其循序渐进地转化为日常的生活习惯,就能形成道德实践的自觉。⑥休谟认为,习惯对心灵有两种强大的、原始的效果:其一,可以使人们在完成任何行为或想象任何对象时畅通无阻;其二,使它以后对这种行为或对象有一种倾向。参见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p.271-272.然而不论采取何种形式,社会效用对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决定性贯穿始终。
凭借休谟道德动机的社会实践性,我们就可以有效回应反休谟主义对休谟主义道德动机的批评。前者认为,休谟主义关于动机源于欲望的观点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在道德生活中,人们为何会经常选择做一些他们自己并不欲求的事。在笔者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道德动机的社会实践特性发挥了约束效力,要求人们的行为朝向社会功利,驱使他们克己利他,尽管有些行为并不是他们自己所欲求的。
同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道德动机的社会实践性必须借助被我们称为德的那些外在标识才能彰显出来,如一些语言表达(如正义的、仁慈的、慷慨的)、表情(如高兴、愤怒、悲伤)、肢体行为(如鼓掌、奋不顾身)等。而且,只有当这些标识向我们清晰地、明确地显露出来时,它们才能发挥相应的道德效力,因此它们可以被看作内心情感转化为能动准则的外在现象。对此,弗雷德里克·科普勒斯顿(Frederick Copleston)做出了恰当评论:“根据休谟所言,动机与行为之间的结合与我们所见到的物理活动中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结合,具有同样的恒常性。”①[英]弗雷德里克·科普勒斯顿:《科普勒斯顿哲学史第5卷·英国哲学:从霍布斯到休谟》,第321页。由此,我们就引申出了休谟道德动机的第三个重要属性,即社会现象性。更确切地说,这些标识必须通过人的社会交往而外化为一种能被感知的现象,但它们不是通过单独的、偶然的现象呈现出来的,而是通过那些具有恒常特性(令人愉快的或有用的)的现象呈现出来的,并得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赞许。在休谟那里,这些特性凝练为一种人格价值或精神品质为人们交口称赞,这就是通常被称为正义、慈善、友爱等等的社会品德。值得一提的是,休谟设计让道德动机激发的社会现象被多位旁观者所观察和经验,而且这总能给他们带来效用或愉快的感觉。因此站在旁观者的视域,这些社会现象就可以被看作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从而具有了客观性。②参见周晓亮:《休谟哲学研究》,第276-277页。正如亚历山大·布罗迪(Alexander Broadie)曾经说:“休谟更倾向于接受旁观者而不是亲历者的判断”。③Alexander Broadie(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p.64.此外,休谟还诉诸语言考察了反映道德动机的那些社会现象中附着的客观性和实践性。语言是人们为了生活便利而发明的用以沟通交流的工具,它是人们了解彼此心中情感观念的外在标识和符号,其自身就蕴含了一定的公共性和共识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脱离个体经验成为更广泛存在的事实。而且,休谟十分清楚地发现,道德语言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语义的二值性,即一种是善的、值得称赞的,另一种是恶的、应当被憎恶的。正如他在考察了心灵的属性后说:“这些属性要么使人成为尊敬和爱戴的对象,要么使人成为憎恨和蔑视的对象”。④[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第5页。由此休谟得出结论:我们通常用来形容道德品质的词都会有一类褒义词和与之对应的一类贬义词。与可敬的品质相反的就是可憎的品质,与勇敢的品质相反的就是怯懦的品质,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道德语义的这种二值性其实就已经暗含了一种道德判断,即要么是善的,要么是恶的。而我们凭借这些与道德相关的术语、概念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几乎无误的道德判断,由此其对人的言行也就具有了实践范导性。⑤[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第5页。
综上,休谟道德动机的客观性、社会实践性和社会现象性彼此关联、相互包含,它们在激发德行时一起发挥道德功能。当我们根据客观性将道德动机理解为推动外在行为的内心情感时,这些情感就借助可感的标识具有了真实性,从而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此外,休谟通过效用原则约束了道德情感,使道德动机具有规范和引导人们朝向社会善的实践特性,而道德动机的真实性和实践性又借助那些具有恒定特性的外在标识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我们还注意到,这些固有属性又都指向了普遍性,因为它们对所有人都适用,并为人们一致认可,这就与休谟道德哲学的根本任务完全契合了。道德动机的这些特性如何在具体的道德行为中发挥作用?下文将以仁慈和正义为例来论述这一问题。
三、仁慈与正义的动机
仁慈与正义是休谟主要考察的两种社会品德,并被他视为我们了解其他社会品德的入口。道德动机的客观性、社会实践性和社会现象性如何呈现于仁慈和正义的动机之中,来激发人们做出仁慈和正义的行为?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我们就可以验证休谟道德动机的这些固有属性是否对其他社会品德同样适用。
休谟在《论仁慈》中明确指出,在日常的道德交往中,我们一般会使用“善交往的”“温厚的”“人道的”“仁慈的”“感恩的”“慷慨的”等形容词,及与它们相关的词汇来形容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其实,这些概念实则指向了仁慈动机的社会现象性,这也是休谟将仁慈称为社会之德的原因,因为它是人们通过社会交往表现出来的。当我们使用这些概念时,心中就已经存有一个信念,即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一种仁慈的动机,由它就能激发人们做出仁慈之举;而仁慈的社会现象性从根本上又与外在行为相关联,因为“善交往的”“仁慈的”等概念,实际上都是我们对救死扶伤、慷慨解囊等具体行为做出的抽象概括,目的在于对相应品行做出道德判断。同时,在休谟那里,仁慈这种德的一部分价值至少源于它有助于人类获得利益,给人类社会带来幸福的倾向。①参见[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第7-12页。由此,社会效用的普遍性使仁慈动机在激发德行时具有了一定的目的,即总是为利他和利公做出考虑,因而其自然能够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
我们再来看正义。在论述正义时,休谟首先通过历史溯源考察了这种德的起源。在黄金时期和战争时期都不需要正义,但我们所处的社会往往是这些极端状态的中间状态。尽管我们会存私心,自然偏向自己的亲友,但我们的确感知到正义会带来更多益处。由此,我们称赞正义,并引导自己去做正义的行为。这同时也隐含着一个事实:在社会生活中一定存在激发人们做出正义行为的动机。而且休谟发现,正义动机最终指向了维护社会普遍利益,这就是它的社会实践性。“我们应当认为正义和非义的这种区别有两个不同的基础,即利益和道德;利益之所以成为这个基础,是因为人们看到,如果不以某种规则约束自己,就不可能在社会中生活;道德之所以成为这个基础,则是因为当人们一旦看出这种利益之后,他们一看到有助于社会安宁的那些行动,就感到快乐,一看到有害于社会安宁的那些行动,就感到不快”。②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342.显然,在休谟那里,利益和道德是激发正义的两个基础。社会利益对应的是正义动机的实践性;道德源于人内心真实的情感,对应的是正义动机的客观性。这两种特性在休谟看来是凭借全体成员共同缔结协议这种普遍社会现象表现出来的,它就是正义动机的社会现象性。这种协议的本质是一种“感觉”,一种人们“对共同利益的普遍感觉”。当社会成员将这种感觉表现出来并相互了解时,他们就会产生“适当的决心和行为”,③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315.以此矫正自身言行,在将利己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同时朝向利他。即正是这种“对共同利益的普遍感觉”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强有力的约束,促使人们形成了一致的正义感。正如努德·哈孔森(Knud Haakonssen)所言:“在休谟的理论中,正义是一套自发出现而又受到规则约束的行为惯例,人们遵守这些惯例并将其逐渐内化形成正义感。”④Alexander Broadie(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p.217.这一协议带给全体社会成员的感觉是真实的,同时又能使社会成员都获利,即它同时关联着正义动机的客观性和实践性,并很好地将两者融贯起来。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休谟道德动机的客观性、社会实践性、社会现象性在仁慈、正义的动机中也能得到清晰展现,因而对于其他社会之德同样适用。但是,休谟论述道德动机的这些特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就关涉道德动机与道德感之间的关联。
四、道德动机与道德感
休谟在《人性论》中表示,道德是能被我们感觉到的,这种知觉善恶的特殊情感就是道德感,它是我们做出道德区分的根据。但他又进一步补充道:“人性中如果没有独立于道德感的某种产生善良行为的动机,任何行为都不可能是善良的或在道德上是善的”。⑤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308.休谟之所以强调道德动机的作用并将其视为激发德行的必要条件,与他从哈奇森那里继承了道德感概念密切相关。⑥哈奇森认为,道德感是一种内感觉,具有被动性。为了使内心情感在实践中变为能动准则,他引入了动机概念(哈奇森将动机理解为一种情感,认为它是由外界对象或行为作用于人的心灵而产生的一种情感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人选择一种行为,避开另一种行为)。后来,哈奇森将动机进一步解释为人们从一个对象那里得到某种利益的意愿或倾向。欲望会让人产生不安,直到获得欲求的利益。同时,这种获得利益的倾向具有普遍性,可以指向自己的利益,也可以指向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动机或欲望可以出自仁爱,也可以出自自爱。但是,道德动机只能出自仁爱。质言之,哈奇森将人的行为解释为主观感觉和外界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旨在试图从一定程度上克服道德感的被动性,使其具有主动性和自发性,从而也强化了道德的实践性。尽管哈奇森对道德动机做了论述,但这一论述仍然缺乏系统性和严密性。关于哈奇森对休谟的影响,参见Stephen Darwall, The British Moralists and the Internal ‘Ought’: 1640-17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86-287; Norman Kemp-Smith, The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Don Garrett, pp.23-44.除了使道德感具有能动性之外,休谟还有两个目的。其一,休谟引入道德动机是为了有效弱化道德感的主观性。根据休谟,道德感是人们做出道德判断的主观因素,它源于感觉经验。倘若道德感缺乏可靠的客观根据,这种理论就无法为道德知识奠基,更不用说推演出能动的道德准则。笔者认为,这里的问题可以从道德动机呈现的特性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以上讨论可知,道德动机的每重特性都包含了客观性,这就会使其整体表现出一定的客观倾向。但是休谟又并未使其脱离情感基础:道德动机的客观性源于情感;道德动机的实践性是通过令人愉快的社会功利实现的;道德动机必须借助一些外在的社会现象显露出来,因而它们必定属于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概言之,休谟是在维持道德源自情感逻辑的严密性的同时,试图通过情感自身克服道德感的主观性。在他发现道德感自身存在的问题时,有意识地转向对道德动机的深入考察就显得尤为必要,其目的在于给道德寻找更可靠的基础。其二,休谟引入道德动机旨在更科学、更理智地解释道德的来源。以正义这种社会的基础德性为例,休谟详细论述了这种德产生的社会环境,阐明了它是人们出于交往便利的目的而人为发明的产物,是“人为的德”(artificial virtues)。但正义并不会因为它是人为的就不稳定,这有赖于休谟在考察正义起源时做出的两重考虑。第一,他将自利情感巧妙地引入正义动机。休谟发现,人的利己情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我们根本不可能依靠心灵的自然原则去控制利己,只能通过改变这种情感的方向来约束它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由自然得来,而是由人为措施得来,或者,更恰当地说,自然通过判断和(非正式)的协议作为一种补救措施来抵消情感中的不规则的和不便利的条件”。①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314.而在休谟看来,只有人们彼此间的这种协议才能给予我们遵守正义的原始动机,而这种协议的本质在于使每位社会成员都有了一种获益的感觉。为此,休谟得出结论:“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②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p.320-321.第二,休谟敏锐地察觉到,自然的正义是不可能具有充分约束力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抵抗眼前利益的诱惑而着眼于未来,自觉去遵守正义规则。为此,我们还必须通过发明法律法规、教化等人为方式不断去强化正义体系,于是就产生了政府。政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赋予人们政治义务,强制人们遵守正义法则。但无论是自然义务还是政治义务,“履行这两种义务的最初动机,都只是私利”。③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348.再借助同情,休谟将对利己的关注过渡到了对利公的关注:“对于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正义——引者注)所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④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p.320-321.简言之,休谟认为,对自己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共同关切才是我们确立正义的基础。⑤休谟以此对哈奇森的道德感做出了改造和修正。在哈奇森那里,只有仁爱才是激发德的唯一动机。在休谟那里则不同,道德动机是利己和利他情感的综合,它在社会效用的指导下使情感秩序朝向利他。质言之,休谟并未将利己彻底排除在道德动机之外,而是赋予了它相应的道德功能。由此,休谟对正义动机做了更符合人性的描述,也对道德起源做了更具说服力的论证。
可见,尽管道德感和道德动机的功能不同,但它们并非各自独立、毫无关联的,而是休谟道德评价机制的一体两面,在道德判断中共同起作用,进而使道德判断的结果呈现出了普遍性和客观性。
综上所述,我们将休谟的道德动机理解为一个情感事实,即人们做出道德行为时总会存在激发这种行为的原因或理由。进而,我们分别探讨了休谟道德动机包含的客观性、社会实践性和社会现象性等重要属性,又分析了它们对于仁慈、正义之德同样适用。最后简要论述了道德动机与道德感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看出,道德动机的这些特性始终都以情感为根据,被休谟巧妙地设计进了一个融贯的道德原则谱系之中,或许还会由此引申出更多其他有待我们发掘的属性。尽管休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弱化或稀释感觉的主观性,但用情感为道德奠基就必然会带入主体因素,这是一个始终难以摆脱的问题。由此我们也就不奇怪随后的边沁为何对道德感理论进行彻底批判,摒弃情感,而激进地只择取功利作为道德基石,从而引发了19世纪英国道德哲学的功利主义转向。但是,休谟的道德动机仍然是当代休谟主义和反休谟主义讨论的议题之一,说明它本身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空间。因此,我们应更开放、更多维地看待休谟关于道德动机的理解,才能深入挖掘它对当代道德哲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