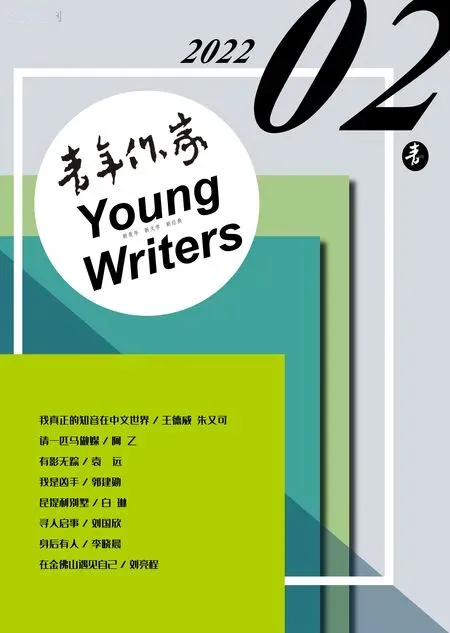我该给你献上什么
叶浅韵
我上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列火车上。他说,要赶去曲靖血站给一个临产的孕妇献血。我把献血这件事想得太过平常。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故事。下了火车,在凛冽的寒风中,一个倔强而温柔的背影匆匆而去。
今天,他来找我,带着六岁的女儿。女儿像只脱兔,与我并不见生。一会儿在我怀里,一会儿在他怀里,一会儿又不知所踪。他的脸是被太阳光常年照射过的土地的颜色,手臂上的血管凸起,青筋像一个愤怒的中年男人在咆哮。
数年前,我大舅被牛抵伤,送往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五脏六腑全无好处,腹腔里充满了积血。医院要求患者亲属立即献血,以补充血库输血的用量。家里的年轻人赤膊上阵,迅速去了曲靖的血站献血。
病危通知书下了一张又一张,大舅终是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了。那个产妇肚子里的孩子也快十五岁了吧。他说,如果不是他及时赶到,两条人命也许就没有了。生产大出血像夺命连环套,套住一大一小两个在鬼门关上的人。时间是生命,鲜血是生命。好在,她们摆脱了魔鬼的追索。大舅与别人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没有我姐姐家这些娃娃,我坟头上的荒草都长许多年了。
当时的凄惨,还像一本不能撕去的老历书。表弟拿着一把刀,疯了似的要杀了那头老黄牛,为报父仇。一边是失去理智的儿子,一边是生命边缘的父亲。我母亲和她的妹妹们用尽力气顶住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柱子,浑身地紧箍上去。牛,被牵到街上卖了,充抵得一些医药费。母亲说,要知道,自己养的牛啊狗啊猪啊鹅啊,通常不会伤害自己的主人,若是它们这么做了,必然是家里有怪事了。
用宿命论来解释一切灾难,是乡间算命婆婆最灵验的招式。她们会说,如果不遭遇此劫数,会有更大的劫数。比如说,丢失些钱财就免了灾祸,小灾小难就抵了大苦大罪。人们在比较之间获得安生的心理。我母亲深谙此法。血脉相连的亲情在一场重大灾祸面前,像石榴籽那样紧密地抱在一起。
有过这一次有惊无险的亲情大营救后,献血就成为家里人的常态。连续好几年,他们争抢着去。为了达1600ml的献血量后,配偶和直系亲属都能享受终身免费用血的权利。像是我的亲人们在维护一个大家庭的完整而尽力,伤痛之后的觉醒显得很平常。每当我说要去参加义务献血大军时,家里人却要阻止我。除了血管细这一说,我肥胖时,他们就说我太胖了,我纤瘦时,他们就说我风都吹得倒了。我始终是一个没有献血小红本本的人。
后来,义务献血就成了众识。没有人觉得伸出臂膀献血会与崇高和奉献这些词汇有很亲密的联系,无非是几个红糖鸡蛋就能产生的能量。没有经过生命与时间赛跑的人,一切都可以说得轻松。有一次,同事的女儿意外受伤严重,她守在医院几夜未合眼,亲眼看着血液流进女儿的身体。女儿终于活过来了,她才深深懂得献血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几乎每一次单位有义务献血的宣传时,她都撸起袖子第一个上。每一次她讲自己的经历,大家都听得很沉重。但是,沉重了一会儿之后,每个人又进入自己的生活里,以为疾病和伤害都还离自己很遥远。
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故,被时光发酵成为故事。我们有太多时候活得昏碌。当他告诉我,他献的不是普通人的血,而是世界上的稀有血型时,我睁大了眼睛。我悄悄看向他的手臂,几条看得见的经络里,正在生产着这世界上的稀有血型——Rh(-)o血型。这种血型可与任何Rh(-)血型匹配,属于稀有血型中的万能血型。他像一个资深的医生,仔细地向我普及关于稀有血型的知识。生怕我弄错,还必须要写在纸上。至此,我才知道,屏幕上那些剧情里,两个人互相输血的方法是错误的,医院的操作不可能这样,需要严格检测。
血缘这种东西在两个无干的人身上,被一种奇妙的东西排斥着,又吸引着。我们是自己,我们又不仅仅只是自己。忽然想起一个少年在班级里演讲时的哽咽,他说他的身体流淌着另一个民族的血液,他的生命是第二次生命。那时我太年少,并不能理解他的痛。如今忽然就懂得了他那双慈悲而深情的大眼睛,他始终是一个愿意多付出的人,默默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有时,他离群索居,引人误会,有时,他也谈笑风生,让人开心。这一时刻,我明白了,那是一个少年对生命的礼赞。
他告诉我,这些年连续不间断的义务献血,已经献出好几千毫升。我又睁大了眼睛。这一次,我再也不能克制自己。冒昧地问他为什么愿意把身上流淌的鲜血无私地献给别人,如他的亲人担心的那样,你这是为了什么。他的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他说他为自己没有成为一具遗体而流泪。这是幸福的眼泪。死亡曾与他擦肩而过,他庆幸自己还活着。
汶川大地震前一天,他与朋友住在都江堰附近的一个酒店里。当他坐火车抵达昆明时,看见大街小巷都在募捐。他把身上的一万多块钱全部捐了,又撸起袖子捐血。他恨不得匍匐在地上,为苍天眷顾自己的生命敞开胸怀:把我拥有的都拿去吧。活着,是上天额外的恩赐,他愿意为此而献出身上的一切——钱、物、鲜血。那是他第一次献血,他并不知道他的血型。
开车到曲靖收费站时,才发现自己连过路费也不够了。他只好停下车来求助,一再告诉收费的姑娘:我是一个好人,我绝对是一个好人。但“好人”这两个字没写在脸上。站上的负责人来了,看了献血证书,听了他的故事,“啪”地敬了一个礼,放他通行。并对他说,这费用如果不能免去,他就自己替他交了。多年以后,讲起这些故事,他的眼睛里还闪着光芒。他说,你看,人世间终是好人居多吧。
当他再一次回到都江堰时,那座坍塌的酒店,再次确认他还活着,不是一具遗体。这些年,他做志愿者、公益人,他觉得他不是自己,他属于需要他的人。他曾捐助过几十个贫困大学生,其中的一些人现在成了他的帮手,延续着爱的希望。如果他是一个富裕的人,或者我可以用达则兼济天下的标签赠予他。事实上,他手里拿着一个屏幕裂了一条长纹的手机,身上的穿着与一个普通农民无异。他与我说起献血联盟志愿者的事情时,仿佛打开一个手机百宝箱,让我确认他正在做了不起的事情,并不是孤单的。他们有一群人,在点燃生的希望,延续爱的温暖。人间值得。
知道他是熊猫血型这事,很离奇,太像小说家设计的情节,为巧而成书。四十四岁的妻子呕吐、乏力、嗜睡,像是早孕的症状,然而医院给出的结论却不是早孕。妻子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被当作肿瘤来医治,甚至都请来了神婆仙家。碎碎念叨的咒语没能阻止一个新生命的正常发育,她长成了我眼前这个活泼聪明的孩子。
当时,他拿着B超检查的单子询问医生时,还被当作愚昧臭骂了一顿,而当他出示从前在同一医院检查的单子时,医生有点尴尬,说那是实习医生的检查结果。接下来,他知道了妻子的血型是稀有血型。高龄产妇的稀有血型,让他很紧张。为防万一,他得到处寻找匹配的血型。他筛查了妻子家族的几十号人,没有一个是Rh-血型。这是一种血型的变异,在汉族人中很少出现。他最后一个筛查自己,不抱任何希望,纯粹是为了知道自己的血型。神奇的是,他居然是Rh(-)o血型,可以匹配任何Rh(-)血型。有了这个强大的保障,一家人的心就放在了肚子里。
妻子生产时顺产,没有用上他的血,而他的担忧却从对妻子的担忧,转移至对同类人的担忧。更巧合的是,他们的三个女儿都是稀有血型。后来,他就有了组建稀有血型献血者联盟团队的念头。现在,已发展到两百多人的团队,为确保这一血型的人急需用血提供了保障。万物以稀为贵,他们却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稀有的珍贵,用鲜红的血液传递着无疆大爱。
他说,每隔半年才能献血一次,少一天也不行。除去老弱病残孕,以及女人的生理期,大概就只有十几个人能随时赤膊上阵。他们是同一种命运的共同体,像一大家人一样,关注着彼此的安危,在生命面前毫无保留地付出。我曾看过一封感谢信,一个老人接受过献血联盟的几十次帮助,离世后,他的孩子们匍匐在地感恩一次又一次的生命献礼。
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每多一些,就发现自己的渺小和浅陋更深一层。可我终将做不了别人。在抽血的窗口,我不只一次被护士嫌弃过。不久前的记忆,还在眉头上徘徊。
这是一次单位的例行体检。年轻的小护士戴着手套的手轻按在我的左手臂上,来回游动,找准一个位置,用棉签消完毒,熟练地把针头戳进去。尖锐的痛在我皱眉头之间舒缓了几分,却不见红色的液体流进管里,她轻微地偏离了一下针头的路线,还是不见血流的迹象。她拔出针头,重来。到第三次的时候,终于见到针管里的回血,她浅笑了一下说,你的血管也太细了。
她的话让我突地生出几丝羞愧,好像一个大个子长了小力气,干活时被人看不惯的窘迫感。在抽血的窗口,我受过许多次这样的质疑。我怕疼,却一时想得有点宽大,幸好这左一次右一次的实验针法,不是戳在我的孩子或是其他孩子的身上。
针管里的血液流得很缓慢,她让我做握紧拳手的动作,握紧,打开,握紧,再打开。好不容易才抽够了三管血。我按着一根棉签,像只晃动的鸡蛋,小心地离开窗口。下一个,大概是她的老师换了她。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看我。会害羞的姑娘很好看,我迅速就忘记了刚才的痛。
检查结果除了血液的黏稠度高之外,各项指标正常。额外加了一项血型的检测,A型。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血型。路过广场时,有一些人在排队献血。志愿者在宣导,说血库的A型和O型血告急,200ml的血就有可能挽救一个生命。我撸起手臂,摇了摇头,为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利他的人而失望。
这种失望在每年的义务献血宣传时,都短暂地冒出过。这一次献血,单位里的那个姐姐病了,她显得很遗憾,像是自己欠别人什么似的。几个生龙活虎的姑娘和小伙子去了,献血回来,跳脚麻手地享受单位休假的福利去了。他们没有说献血的荣光,而是很现实地说,用鲜血换来的小自由。对于爬泥啃土的基层工作人员,我深知其中的况味。
没有经过亲人在生死线上挣扎时惨烈的人,都可以在谈笑之间完成某些义务或是使命,并用一些生存的小智识,把自己放在生活的小平面上,且愿意低些、再低些,哪怕低到平庸里。就像我们彼此举起的酒杯,为了显示对方的尊贵,愿意往下、再往下。这对于生活,无伤大雅,亦不落大俗。或者说,大雅与大俗在生活里,没有太过明显的边际。大多数人都这么庸常地活着,并以能有这样的生活而自足。
他伸出手臂,对我说,再有半个月,又可以去献一次血了。这些血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接着,他向我讲述了一个沉痛的故事,他为自己没能挽救她而感到难过。千里迢迢的救援路上,他抵达了,唯独这身边人的妻子却不能。他要说的她,是一个我并不熟悉的人。他说得有点难、有点痛、有点慢。
女儿像只小蜜蜂一样飞进来的时候,他的眼泪正在飞。稚气的世界里没有沉重这个词汇,她笑得很甜蜜,像是爸爸不是在哭,而是在笑。她坐在我的腿上,立即对我身上的气味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我却像抱着一只珍贵的熊猫,生怕一放手她就爬到树梢去了。我知道,等她长大了,她也会像她的父亲那样,在需要她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膀子。这么想的时候,我把她搂得更紧了。我知道,她刚成年的姐姐已经加入献血联盟大军了。这不是使命,不是责任,而是一种选择。她们的身上有着相同的生命质地,是因为她们有一个这样的父亲。
小城的血库里没有产妇的匹配血型。产房内外乱成一锅粥。有人说,快发条朋友圈求助吧。丈夫用颤抖的手在屏幕上敲打出一行字:跪求Rh(-)血型,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妻儿吧!一长串的回复,没有一条是有效的,在生命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爱莫能助的安慰和祈祷比冷漠更让人焦心。他想起了电影里的许多剧情,巴不得自己的血型能立即变异为妻子的血型,从一只手臂输到另一只手臂,他的妻儿就能得救了。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妻子失血过多,已经昏过去了,医生和护士在忙碌着进进出出。没有人有时间来关心一个心碎的中年男人,他瘫在椅子上,又从椅子上滑跌在地板上。他一声声地悲鸣,如果可以,让我来代替你受罪吧,我亲爱的妻子。说好不生了的,可这政策就像一个重大的福利,失去了多可惜呀。你说,有了女儿,农村人传统,家中又是独子,就再生一个吧,万一就生出了儿子呢。即使是女儿,互相有个伴也好呀。
在身边许多人怀不上二胎时,他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而自豪,为妻子肥沃的土壤而开心。他每天陪着怀孕的妻子散步,幻想中年得子的种种幸福。他笃定地以为妻子怀的是儿子,因为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个老神仙拉着一个小男孩来找他,说是他家丢了的孩子,嘱咐他以后要好好看护。
胎儿的性别鉴定在医院里是严格保密的,但给妻子做B超检查的医生是好朋友,只冲他说一句,这回你家就圆满了。他的脸上顿时笑出了一万两黄金,感觉自己的人生就要到达顶峰了。他没有想过,妻子正走在危险的路上。羊水栓塞,这四个字就像夺命的利剑,劈开妻子的身体,他的身体,还有他们的儿子的身体。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在这一道残酷的选择题面前,他真希望能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让妻子活下来,再不要冒险去做什么。他更不想听见医生说,我们尽力了。可是,医生无奈地向他摊开两只手。他眼前一黑,不知道在哪里。醒来,只有一个念头:亲爱的妻子、儿子,带上我一起走吧。
爸爸,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女儿扑进他的怀里,撕心地大哭。眼泪的苦海里,两颗泅渡的心,无着无落。妻儿的后事,是亲人们帮忙处理的。他像个受人指挥的机器人,拨拨动动。让他清醒的是,眼前十一岁的女儿,她把他拉进一个残缺的现实里,让他必须打起精神来修补这破碎的家。
后来的日子,他像游荡在人间的鬼魂,被女儿的需求支使着,接送她上学,管她的吃喝拉撒,擦去她脸上的泪花,轻抚她思念妈妈的伤痕。除此,他疯狂地在网上查询羊水栓塞的资料、案例。他曾听人说这座城里就有一家人与妻子的血型是一样的,他甚至还认识那个男人呀,为什么当时就没想到呢。
有一天,他试着拨打了一个电话。两个男人的哽咽,让电话无法进行下去。挂掉电话十分钟,他们就在一杯酒里相遇了。后悔和责备,是酒的主题。但他们都无法挽回两条生命了。喝醉了的男人,重复着同一句话:我该给你献上什么!一个面对妻儿,另一个面对生命。血,鲜血,我该给你献上鲜血。一个无能为力,另一个一无所知。无能为力的人在痛哭,一无所知的人在地里劳作。生命的通道就这样被关闭了。
他责备他,你就不能找到我的电话吗?按人际交往的现代法则,想认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最多通过6个人就能找到呀。说得越多,他越觉得对不住死去的妻儿。后来,干脆就不说了。酒,一杯杯见了底。今夜,酒是他们共同的仇人。
这是一场事故。这是一个故事。但凡不在自己身上的生死,都可以像往日的炊烟与白云,飘飘荡荡就过去了。然而,也总是会有人深切地记住。那个人,也许不一定是亲人。但必须是他从鬼门关前打过转儿,了悟了活着的意义,知道生命的价值,有着强烈的共情力,才能真正地做到感同身受的那个人。他们用一杯杯酒水和眼泪来祭奠逝去的人,痛悔失去的机会。
不久前,从地里劳动回来的他,灰尘未拍干净,又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因为他献血的周期未到,他就打起了刚成年女儿的主意。女儿明白父亲的心,打了一个出租车就去了另一个城市。车费自理,安全自负。这些年,他一直是这么过来的。有人说,这是一种崇高,他说,他真没有想那么多,只希望地里的庄稼能长得更好一些,女儿们的学业更进步一点。
前面的事故已经变成故事了,日子总是要继续的。他在我面前复述这个故事时,还是没能管住他的眼泪。像是他辜负了兄弟的幸福,没能替他挽住两条生命。愧疚让他不能自已,我也戚戚然然。为别人的生命而流的眼泪,沉重而慈悲。
Rh-血型,千分之三的稀有血型。我眼前这一对父女的血管里流着与别人不一样的血液。他们脸上的悲喜与别人并无二致。对于血型的医学常识,我只局限于一些ABO的字母。为此,我查询了一些资料,再一次明白了“稀有”和“熊猫”的意思。正因为这些,在临床医学上才具有重大意义。
他曾经在去重庆旅途中接到血型求助的消息,数百里远的路上,打上出租车直奔医院。重大交通事故中的危重病人需要他,出租车司机被感动了,坚决要把收了的钱退还他。病人得救了,他像是自己的生命又得到一次重生。他清瘦的身体,没有一点熊猫的憨态可掬,我无法想象每一次从他的血管里抽取300cc--400cc鲜血时,他应该是怎样的状态。他说,除了喝白开水,我不大相信红糖水能有更大的作用。你看,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献血对身体健康完全没有影响。
他挽起袖子,手臂上的血管暴露在我眼前,像是一台生命的救援仪器。注定,我成不了一个崇高的人。但我能确定我是一个敬畏崇高的人。所以,他与我,必然要因某种方式坐在一起,说一说关于血脉相连的故事。
我常常在一些强大的能量场里热血沸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致力于有用,便也成了我对生活实践的一种常态。即使到了今天,我也还认为我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一名作家,一名老师,一名医生,甚至一名战士。生而为人,我终将为有用而活着。
特蕾莎修女说: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即使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不管怎样,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他或许并不知道特雷莎修女的存在,但他们是走在同一条道上的人,想把最好的东西献给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