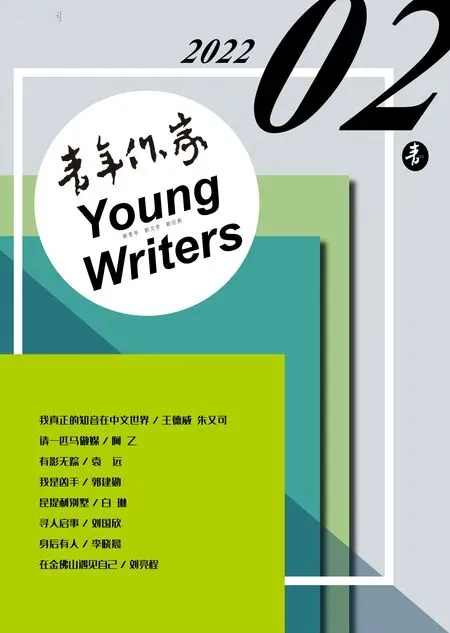评论者说 从极狭窄的角度拓展开阔深沉的体验天地
列文
库雷希在他的小长篇《虚无》里,释放了这样一个主题:老年就是一轮崭新的童年。它以衰朽多病的老去的大导演的视角,重构了老年人与现实之间那一层排斥与介入的关系;大导演以近乎孩童的、窥探的方式,固执地想要重新找回挂满欲望果实的生命之树。《虚无》所连接个人与现实的叙述桥梁,是疑似的相较而言更年轻的伴侣的出轨,围绕“出轨”与“捉奸”冲动,库雷希构建了心理与行为这种“年龄差”的张力,以及被现实所排斥与不甘心地想要重新介入其间的张力。在本期“新力量”栏目《树洞》这篇小说里,这种张力的构建同样是新奇和有力量的:目标明确的来自现实的欺诈与个体投身于现实的纯粹。作者许桂林构建此种张力的叙述桥梁,是爱情。爱情是俗套的、过于宽泛的主题,但作者处理得很好,给予了爱情一种新鲜的角度,它拒绝了有关爱情的社会属性的那一部分而紧紧扣住爱情的一方,“我”的爱情的种子的萌动与抽芽的过程。
在世俗的爱情里,我们很容易能观察到恋爱双方通常的行为、语言,所以我们对此很难产生新鲜感,但《树洞》的角度,抛弃了正常的媒人、家庭、旁观者和双方的关系定位、现实地位以及相关的诸如道德、价值观等等因素,它专注于“受害人”产生“爱情状态”时的心理展示,这样一来,整篇小说的视野实际上也就脱离了爱情的狭窄,使得个体与现实的关系有了一层更为抽象以致具备了普遍意义的想象空间。
剧情构成上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小说的精心打磨,“我更好奇了,一个大男人,干嘛在树下哭啊”,同样,读者也对此产生了好奇,有迫不及待想读下去解密的冲动,进而读到最后,我们才发现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浪漫邂逅”,我们不禁对女主人公感到惋惜。读者对女主人公的轻信、单纯、善良、“一根筋”、胆小而渴望激情等感受,都可以成为小说剧情成功的佐证。
《树洞》开篇作者营造的种种“不寻常相遇”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残雪的“梦境”小说。《树洞》的叙述就给人一种类似的现实与梦境交错进行的奇妙的阅读体验,但它控制住了滑向超现实的那一根叙述之弦,避开了更晦涩的抽象表达,比如略显诡异的“树洞”书柜,房间内的摆设,“老人机”等等,虽然这些布置都可以看成是作者对“他”的身份所埋的伏笔,但在阅读过程中,依然给人以奇异的感觉。
读完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树洞”以及“树洞”当中那个虚假的“双胞胎姐姐”,我们很难不去联想到作者是在对女性意识进行一种充满象征意味的表达,它是在说女性的爱情、价值观在现实当中的胚胎性展示,还是在说,人性中纯粹那一面的被囿于,就留待不同读者的不同理解了。
不过,在语言方面,《树洞》也有略显平庸之嫌,语言给人的新鲜感还须加强,另一方面,作者对细节的处理也有待讨论。细节过于单薄,则会使小说失去一种真实可信任感,进而使得阅读体验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如果说《树洞》立足于心理展示,那么李晓晨的这篇《身后有人》就侧重于人物的行为展示,但不同于表现主义手法,《身后有人》加入了大量的类似旁白解说的叙述进去,像并行的两条线,同时把心理与行为呈现出来,这样一来,也就方便读者更为直观地对小说人物进行人格侧写。无论怎样的人格,都必须有一个安放的环境,在这篇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环境成为点睛之笔,或者说,成为那个“诗眼”。
当代有一句名言,“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句话极其形象地展示了个体以及个体的命运与“时代”这种大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讲述“时代”的宏大的文本已经够多了,甚至于,我们讲述时代之中的小人物命运的文本也已经够多了,我们迫切需要一些新鲜的角度,来重新生成两者之间的对立张力,而《身后有人》似乎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角度。
小说把故事放置于“拆迁”这样一个不可抗拒的环境下,而“拆迁”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个戏剧性的舞台,换句话说,一个足够揭开个人生活那一层隐纱的公共事件。而《身后有人》新颖的一点在于,它让主人公大年回避了与“拆迁”的交锋,小说不直接呈现个人与时代的对抗,小说更为微观地去呈现环境之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冲突:大年与邻居义武的有关小厨房产权的冲突,大年因二年而产生的与租户明月的冲突,大年与前妻因可能的拆迁款的分配的冲突。在这些鲜明的冲突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平庸、善良的主人公大年,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主人公大年对复杂环境的主观的排斥。也就是说,大年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被动形象的象征。他只看着邻里在计算拆迁面积时的小动作而不去作为,他面对义武的诉求只是生气而不去思考解决之道,他面对前妻要求分拆迁款时的复杂难辨的怀旧心理,以及他一方面难以拒绝二年的请求,一方面更难以面对明月的租住着落,这一连串的被动,被作者放置在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拆迁所引发的背景下,立即使得文本具备了更为立体的想象空间。然而更加戏剧性的是,拆迁忽然被终止了,被十分随意与轻描淡写地终止了,这样随意的开头和结尾,与在过程中涌现出的带给大年巨大感情冲击的各方面事件之间,构成了最具讽刺意味的个人与时代之间那一种如颤琴弦般的张力效果,读来令人唏嘘不已,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小人物命运的荒诞与沉重。就像“身后有人”这个题名所影射的,这样一个微不足道、不懂“上进”的小人物,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总会有一种令人心有悸挂、背脊发凉的不自在感。
从叙述语言上看,小说《身后有人》写得平稳有力,张弛有度,在矛盾冲突的各个场景上,也不见有新人常见的慌张的感觉,足可见作者的写作功力沉稳扎实。但有一点似乎值得商榷,在围绕大年行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类似旁白的心理状态的“补充说明”,这种写法虽然不被认为是妨害性的,但就角色而言,略微显得有作者本人的人格植入之嫌,以致可能会给阅读增加一些障碍。
本期最令人惊喜的文本当属刘国欣的中篇《寻人启事》。我们回顾文学历程,从乔伊斯的经典化作品到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都不断地在回答这样一个命题:小说可不可以这样写?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并由此引发了一个反问:小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写。于是经大量优秀作者的写作实践,我们观察到许多突破性的文本,旨在从真实和虚构的基于现实的角度,去追寻一种更加饱满的阅读趣味。其中,散文的小说化,以及小说的散文、随笔化,便是成功(难以否认有失败的例子)的尝试之一。刘国欣的这篇《寻人启事》,即是在散文化的叙述碎片之中,完成了具有极强感染效果的小说文本呈现。
《寻人启事》的叙述,通篇建立在看似毫无章法、时空逻辑混乱的碎片似的内心独白之上,但这些碎片其实全都包含在一个明确的时间集合之下,那就是“我”给“父亲”上坟烧纸的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么一个短短的现实时间集合里,小说完成了跨以多年计的时间呈现,这样对比强烈的时间差产生的张力,让人从另一方面想到博尔赫斯的名言:“毁灭一个人就是毁灭一个宇宙”,在时间对比中,我们看到了那个丰沛饱满的情感“宇宙”,看到了隐藏在微小事物、微短时间里的,无限庞大的可能性。
“出轨”、“抛妻弃子”,这些都是有鲜明道德色彩的行为,但作者并不在乎“道德”,因为这种社会约束性的指认并不能更清晰地表达个人在这些事件中的最真实的感受,所以作者对文本进行了大胆的后现代的处理,不讨论宏观,不讨论价值、意义,把对事件的关注,突降至与心灵的第一视角触碰上面,并彻底打乱时空逻辑线索。
不知道是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寻人启事》的叙述,不断地在相同场景(比如吃饭,比如散步)之间反复交叉跳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跳跃所带来的情感共情效果,是令人震撼的,它甚至在某种程度的诗美学的能指角度,在形式上强烈展示了因“出轨”和“抛妻弃子”的冲击而造成的个人内心情感上的混乱不堪与破碎,从而有效地抵消了时空散乱所带来的阅读体验的不适。这种类似个人精神病历的呈现,令人想到自白派干将普拉斯唯一发表的长篇小说《钟罩》,《钟罩》的自白式游历方式,相当于把精神列车安置上了轨迹清晰的铁轨,将整整一代自白派诗人的精神世界,娓娓勾画了出来,而《寻人启事》有着几近相同的展现效果,这样的“病历报告”对我们进行精神与情感的省察与自省,起到了重要的启发性作用,并且往深处拓展了我们的阅读体验。
另外,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类似“有——没有”这种干脆果决不留余地的句式,也可以成为事件冲击之下,“我”的内心混乱的佐证。“我”不断穿梭在过往的温情与事件之后痛苦的撕扯之中,仿若在惊涛骇浪中行舟,抑或是飞翔于峻岭险峰之间,比起许多的“大”而不当的小说,刘国欣这篇《寻人启事》,从极狭窄的角度入手,拓展出了一片开阔深沉的体验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