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传递研究
陈杰 常雪 钱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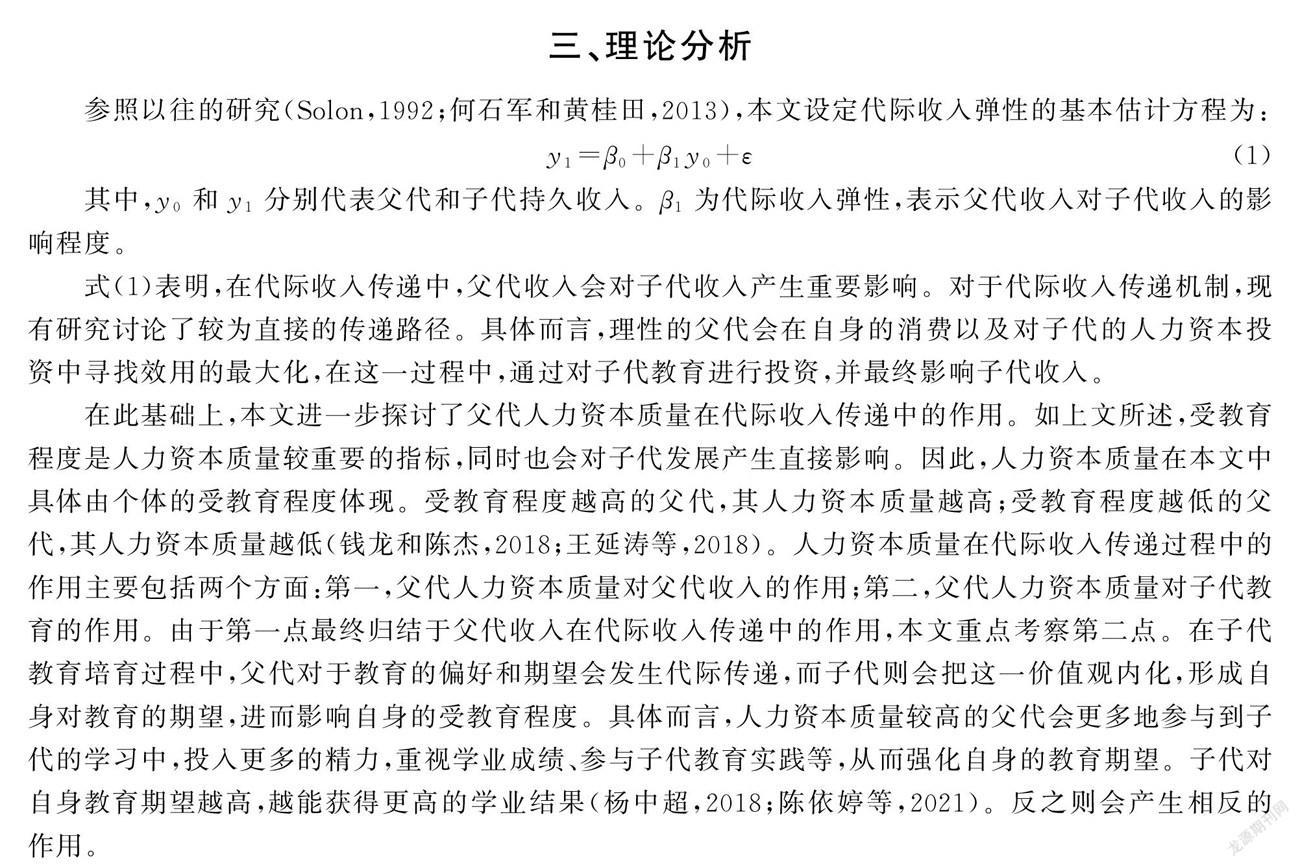
摘 要:通过构建一个加入父代人力资本质量的代际收入传递分析框架,对比分析父代收入与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可以拓展提高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相关公共政策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CHNS调查数据,实证结果显示,与父亲类似,母亲收入与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同样重要,而且对儿子与女儿的影响均存在差别。具体而言,一方面,父亲收入对女儿的影响比对儿子更为重要,而母亲收入对儿子的影响则要高于对女儿的影响;另一方面,父亲人力资本质量对儿子的影响比对女儿更为重要,而母亲人力资本质量对女儿的影响则要高于对儿子的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或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父代教育约束”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已经高于收入预算约束的作用。
关键词:代际收入弹性;人力资本质量;教育;工具变量
一、引言
“三农”问题,核心在农民,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在中央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支持下,农民收入持续增加。2000年以来,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其实际增速的峰值分别为2010年和2011年,均较上年实际增长11.4%。此后,尽管实际增速有所放缓,但是,2016—2019年,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仍达6.5%(姜长云等,2020)。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相关影响因素,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非农就业(蔡洁等,2020)、农村金融(温涛和王佐滕,2021;李波和张春燕,2021)、土地要素(栾健和韩一军,2020)、农村产业发展(王玉斌和李乾,2019;张林等,2021)等因素。除此之外,近两年探讨最多的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即农村贫困人口的增收(周玉龙和孙久文,2019;徐舒等,2020;汪三贵等,2020),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电子商务(唐跃桓等,2020;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互联网(孙华臣等,2021)、数字乡村(齐文浩等,2021)等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在对农民增收展开研究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探讨农民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李实等(2018)利用国家统计局及CHIP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7年的0.37上升至2013年的0.41。姜长云等(2020)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趋于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呈不断扩大趋势。农民收入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实际反映了同一代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收入分配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传递问题。Becker 和 Tomes(1979)最早建立了代际收入传递的经济学框架,在此框架中,代际收入传递一般用代际收入弹性来表示。该弹性越高,说明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越大,代际收入流动性越低。现有文献重点测算代际收入弹性,以及探讨代际收入传递机制(Qin 等,2016;Fan,2016;杨沫和王岩,2020;邓悦等,2021),对于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绝大部分讨论了较为直接的传递路径,即父代收入通過对子代教育进行投资,并最终影响子代收入。但是,除了收入,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亦有重要作用。人力资本,亦称“非物质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如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健康状况等,属于一种质量概念(李唐等,2016),其中,教育是其最重要的体现。基于此,在本文中,人力资本质量主要由个体受教育程度反映。不同人力资本质量的父代,其对于子代的教育期望、教育参与均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影响子代的教育结果,并最终影响子代的收入。因此,在探究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除父代收入这一较为直接的影响,父代的人力资本质量也应该考虑在内。基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加入父代人力资本质量的代际收入传递分析框架,比较分析父代收入与人力资本质量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相较于以往研究,通过对父代收入与人力资本质量展开对比分析,可以拓展提高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相关公共政策的思路。这对于农村居民,尤其是人力资本质量较低的群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此外,以往的文献或是笼统地分析父代与子代,或是仅仅分析父亲与儿子之间的收入关系,对母亲角色的作用关注较少。然而,在拓展后的分析框架中,母亲人力资本质量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因此,有必要针对父亲和母亲人力资本质量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均展开分析。
二、文献综述
对于代际收入弹性的测算,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利用收入的追踪数据,计算父代多轮收入的平均值作为持久性收入(何石军和黄桂田,2013;陈杰等,2016);第二,将父代的持久性收入视为内生变量,利用父代的教育、职业等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展开分析(Lefgren 等,2012;Lefranc 等,2014)。表1汇总了最近几年对于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在配对方式上,现有研究主要估计父亲与儿子、父亲与子代(儿子与女儿)的代际收入弹性。相关估计结果显示,中国代际收入弹性总体处在0.4左右,且城镇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要略高于农村地区,但估计结果仍未形成一致结论。
估计代际收入弹性只是代际收入研究中最基本的一步,更值得关注的是父代收入是通过何种机制传递给子代的。Becker 和 Tomes(1979)的理论模型认为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禀赋的遗传是代际收入的主要传递机制。对于禀赋遗传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最初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计算并比较兄妹间以及社区内样本的收入相关性。其基本思想为,如果个人未来的收入与社区和家庭等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与其他随机抽取的人群相比,在同一社区和家庭成长的子代之间会表现出更大的收入相似性。由于对兄妹和社区收入相关性研究并不能区分禀赋遗传和后天培养的作用,在接下来的文献中,研究者们把总体收入的方差分解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基因、家庭环境和个体因素。Bjrklund 等(2007)使用瑞典的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获得如下结论:基因遗传对总体收入方差具有重要贡献,其贡献达到了10%(女性)、20%(男性);而家庭因素的影响相对比较小;个体因素的影响很大,占到总体收入方差的6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选择采用收养者的数据来探讨代际收入传递的机制。在领养为随机过程且养子如亲身子女一样被照料的前提假设下,被收养者与其养父母之间不存在基因相关性,通过比较不同样本组,研究者们就可以得出基因、家庭环境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的作用。Sacerdote(2007)利用HICS数据,得出亲身子女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32,收养子女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09。
除了禀赋遗传,人力资本因素对代际收入的传递同样重要。Qin 等(2016)构建了一个“三代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教育与健康)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并用CHNS1989-2009的数据进行了验证。Hérault 和 Kalb(2016)探讨了教育在劳动收入(工资)代际传递中的作用,并分儿子与女儿进行了讨论。Fan(2016)认为代际收入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对单位的所有权进行传递,并通过相同的方法,得出改革开放前,社会资本是高收入群体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后,教育是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方式,社会资本依旧是高收入群体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方式。Bevis 和 Barrett(2015)利用菲律宾农村的面板的数据,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分解,主要从健康、教育、土地以及配偶教育等方面探讨代际收入的传递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过程在儿子与女儿之间的差异。近年来,学者们主要对教育这一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细化,比如Blandenau 和 Youderian(2015)将儿童教育时期分为早期、中期及晚期,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对晚期儿童教育几乎没有作用,但是增加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早期教育能够有效提高流动性。
综上所述,以往文献对代际收入弹性与代际收入传递机制均做了深入探讨,特别是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启发性。但是,以往研究很少涉及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忽略了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加入父代人力资本质量的代际收入传递分析框架,比较分析父代收入与人力资本质量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以期对以往研究做出一些补充。
三、理论分析
参照以往的研究(Solon,1992;何石军和黄桂田,2013),本文设定代际收入弹性的基本估计方程为:
y1=β0+β1y0+ε(1)
其中,y0和y1分别代表父代和子代持久收入。β1为代际收入弹性,表示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
式(1)表明,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父代收入会对子代收入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现有研究讨论了较为直接的传递路径。具体而言,理性的父代会在自身的消费以及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中寻找效用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子代教育进行投资,并最终影响子代收入。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如上文所述,受教育程度是人力资本质量较重要的指标,同时也会对子代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人力资本质量在本文中具体由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体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代,其人力资本质量越高;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父代,其人力资本质量越低(钱龙和陈杰,2018;王延涛等,2018)。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对父代收入的作用;第二,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对子代教育的作用。由于第一点最终归结于父代收入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本文重点考察第二点。在子代教育培育过程中,父代对于教育的偏好和期望会发生代际传递,而子代则会把这一价值观内化,形成自身对教育的期望,进而影响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具体而言,人力资本质量较高的父代会更多地参与到子代的学习中,投入更多的精力,重视学业成绩、参与子代教育实践等,从而强化自身的教育期望。子代对自身教育期望越高,越能获得更高的学业结果(杨中超,2018;陈依婷等,2021)。反之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对于上述分析内容,本文借鉴Lefgren 等(2012)的研究,假设两代人的收入都由人力资本质量和市场运气两部分组成,即:
y0=γ0+HC0+η0(2)
y1=γ1+HC1+η1(3)
其中,HC0和HC1為用等额市场价值表示的两代人的人力资本质量,η0和η1表示两代人的市场运气(与人力资本质量无关的、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偶然性收入)。
进一步假设子代的人力资本质量由父代的收入和人力资本质量共同决定,且二者的边际影响相互独立(Lefgren 等,2012;陈琳,2016),即:
HC1=α+π1y0+π2HC0+φ1(4)
上述两代人的收入决定方程和子代的人力资本质量决定方程构成了模型的基本组成部分。把式(4)带入式(3),得:
y1=π0+π1y0+π2HC0+ν1(5)
其中,π0=α+γ1 ,ν1=φ1+η1。在该式中,π1衡量了在控制父代人力资本质量的情况下,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π2衡量了在控制父代收入的情况下,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对子代收入的影响。
进一步地,把式(2)带入式(5),得:
y1=π0+π1γ0+(π1+π2)HC0+π1η0+ν1(6)
式(6)显示,父代的人力资本质量既可以直接影响子代收入,也可以通过其收入间接影响子代收入,而父代的市场运气则只能通过其收入影响子代收入。
从理论上讲,由于存在个体能力等遗漏变量以及单年收入的暂时性波动,对式(5)或式(6)进行回归,直接识别π1,π2非常困难。对此,Lefgren 等(2012)提出了一个间接界定π1和π2的方法。具体而言,在上述分析框架内,若针对父代收入采用工具变量Z0估计代际收入弹性,可以证明得到该IV估计值满足:
βIV=π1+π2cov(HC0,Z0)covHC0,Z0+cov(η0,Z0)=π1+π2ζIV(7)
在式(7)中,若找到只与父代的收入运气(η0)相关而与父代人力资本质量(HC0)无关的工具变量,则βIV,LUCK=π1;若找到与父代人力资本质量(HC0)相关而与父代收入运气(η0)无关的工具变量,则βIV,HC=π1+π2。进一步,获得π2=βIV,HC-βIV,LUCK。通过上述方法,可以分别获得父代收入与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的贡献率。
四、数据与估计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1989至2015年之间10轮的数据,该数据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的追踪调查项目。2011年以前的调查范围覆盖了9个省(区)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包括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和黑龙江省,2011年上海、北京和重庆3个直辖市加入,2015年进一步加入云南、浙江及陕西省。CHNS数据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数据中包含家庭中个体特征、职业类型、收入等各方面信息。
为了得到本文所需要的数据形式,首先对所有家庭样本中父代(父亲与母亲)和子代(儿子或女儿)的信息进行分离,然后将同属一个家庭的父代、子代数据进行合并,从而获得两代人的数据。其次,从对子代劳动力数据初步统计结果来看,不少劳动力甚至是未成年。由于使用较低年龄段子代的收入会带来较大的测算误差,所以本文剔除子代年龄低于18周岁的样本。依据法定退休年龄,将父亲劳动力的年龄上限设定为60岁,母亲劳动力的年龄上限设定为55岁。此外,根据以往关于生命周期偏误的研究(Haider 和 Solon,2006;Bhlmark 和 Lindquist,2006),父代处于40岁以上年龄段可能是生命周期偏误最小的年龄段,本文进一步设定父代年龄不低于40岁。最后,本文利用CHNS数据提供的2015年消费价格指数对父代、子代收入数据进行了平减[2015年消费价格指数已按照当地的情况进行了调整,具体计算过程见CHNS数据库中的“Individual Income Variable Construction”和“Household Income Variable Construction”。]。本文共得到农村样本中父代-子代有效配对样本数为2364对,其中,父亲-儿子与母亲-儿子配对样本数为1509对,父亲-女儿与母亲-女儿配对样本为855对。
(二)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表2汇报了农村配对样本中父亲、母亲、儿子以及女儿主要变量的统计结果。从农村样本来看,对于父代而言,无论是收入、年龄、受教育年限还是职业的分值上,父亲均高于母亲。对于子代而言,儿子的平均收入为9749元,比女儿的收入高约1/3。儿子的平均年龄与受教育年限要略高于女儿,但是,女儿的职业分值的平均值却略高于儿子。与此同时,在对数据分析时发现,父亲、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分别占总样本的61%、92%,职业分值子代平均值要高于父代。
(三)估计方法
如上文所述,代际收入弹性的基本回归方程如式(1)所示,在具体估计中,一般使用单年收入作为持久收入的替代。但是,由于单年收入与持久收入往往有较大偏差,使用单年收入来估计代际收入弹性会带来向下的偏误(Solon,1992;Zimmerman,1992)。对此,Solon(1992)认为,基于个人一生实际收入一般为单峰型的基本事实,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对个体的年收入水平用年龄及其平方项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方程为:
y1t=β0+β1y0t+β2age1t+β3age21t+β4age0t+β5age20t+μ(8)
式(8)中,y1t、y0t分别为子代、父代在t年的收入的对数,age1t、age0t分别为子代、父代在t年的年龄,μ为随机扰动项。通过式(8)的调整,可以优化单年收入对持久收入的替代效果。
本文的重点在于剥离出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需要分别估计出π1+π2,π1。现有研究在估计代际收入弹性时,通常使用父代自身的教育和職业作为父代收入的工具变量(Lefgren 等,2012;Lefranc 等,2012)。有鉴于此,本文进一步使用父代配偶的教育和职业作为其收入的工具变量,具体而言,本文使用母亲的教育和职业变量作为父亲收入的工具变量,使用父亲的教育和职业变量作为母亲收入的工具变量,从而得到估计结果βIV,HC=π1+π2。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来自于:第一,受教育年限和职业是影响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而且,由于可能存在婚姻匹配效应,婚姻双方的受教育年限、职业分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比如,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分值较高的女性有更大概率嫁给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分值较高的男性,反之亦然,符合有效工具变量相关性的条件。第二,若使用配偶教育、职业因素作为工具变量,则不会与自身一些不可观测因素,比如能力等相关,符合有效工具变量外生性的条件。与此同时,本文职业分值是按照Erikson 和 Goldthorpe(2002)的职业等级分类表来设定,职业分值一方面与受教育程度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人力资本质量无关的运气相关,与陈琳(2016)的研究一致,本文同样使用父亲(母亲)职业对父亲(母亲)教育年限回归的残差作为与父亲(母亲)收入运气相关而与人力资本质量无关的工具变量,得到估计结果βIV,LUCK=π1。
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两阶段估计办法进行估计,其中,第一阶段的估计方程为:
y0t=γ0+γ1Z0t+γ2age1t+γ3age21t+γ4age0t+γ5age20t+ν(9)
其中,Z0t为一系列工具变量,若y0t为父亲收入的对数,则Z0t包含母亲教育、母亲职业或父亲职业对父亲教育年限回归的残差;若y0t为母亲收入的对数,则Z0t包含父亲教育、父亲职业或母亲职业对母亲教育年限回归的残差。
估计式(9)得出y^0t=γ^0+γ^1Z0t+γ^2age1t+γ^3age21t+γ^4age0t+γ^5age20t,代入式(8)替代y0t得到第二阶段估计方程为:
y1t=β0+β1y^0t+β2age1t+β3age21t+β4age0t+β5age20t+μ(10)
为了获取正确的标准误,本文一次性估计两个阶段的回归方程。通过对不同类型工具变量展开估计,估计出的β1即可代表π1+π2,π1。
五、实证分析
(一)代际收入弹性估计
表3汇报了农村样本父亲与儿子、父亲与女儿、母亲与儿子以及母亲与女儿最小二乘法(OLS)和工具变量法(IV)的估计结果。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采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出的代际收入弹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采用单年收入估计时存在的向下偏误(Solon,1992)。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首先,大部分子样本估计结果的F统计量均远高于10,仅有母亲-儿子配对样本中,以母亲职业对教育的残差作为工具变量估计时,F值为8.7,但是也已非常接近10,因此基本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其次,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发现其p值均大于0.1,即无法拒绝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原假设。以上结果保证了本文工具变量选取的有效性。
如上文所述,本文利用配偶教育和职业变量作为父代收入的工具变量,用以估计βIV,HC=π1+π2,利用父亲(母亲)职业对父亲(母亲)教育年限回归的残差作为与父亲(母亲)收入运气相关而与人力资本质量无关的工具变量,用以估计βIV,LUCK=π1。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与理论预期一致,βIV,HC>βIV,LUCK。由于βIV,LUCK=π1考察了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对比以往关于代际收入弹性的研究结果(Lee 和 Solon,2013;Deng 等,2013;Li 等,2014;Qin 和 Wang,2016;Palomino 等,2018;杨沫和王岩,2020),除了母亲-儿子估计出的结果略高之外,其余結果均处在0.2-0.8的范围内。这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较为合理,同时也表明中国农村地区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较大。进一步地,父亲收入对儿子的影响略低于父亲对女儿的影响,而母亲收入对儿子的影响则高于母亲对女儿的影响。此外,父亲收入对儿子的影响要低于母亲对儿子的影响,而父亲收入对女儿的影响则略高于母亲对女儿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这里尝试改变工具变量,主要是针对π1+π2的估计。利用不同工具变量组合估计出相应结果,若父代收入与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影响的相对大小未发生变化,则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如上文所述,现有研究通常使用父代自身的教育和职业作为父代收入的工具变量(Lefgren 等,2012;Lefranc 等,2012)。基于此,无论是估计父亲与子代样本,还是母亲与子代样本,本文进一步采用父亲与母亲教育和职业的所有信息,即利用母亲受教育年限、母亲职业、父亲受教育年限以及父亲职业的组合作为工具变量,用以估计π1+π2。表5汇报了相应的结果,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回归的F值均大于10,所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同时,对
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发现其p值均大于0.1,即无法拒绝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原假设。对于估计结果,本文发现,父代的收入影响依然是较为重要,且父亲对儿子的收入影响低于女儿,母亲对儿子的收入影响高于女儿,这一结果与上文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检验不同受教育程度下,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以更深入地考察这一作用的异质性。结合样本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本文将父代样本分为初中以下样本与初中及以上样本。表6汇报了相关结果,可以发现,在父亲-儿子,母亲-儿子,母亲-女儿样本中,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父代,其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要高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父代。尽管在父亲-女儿样本中,初中以下父代人力资本质量的作用低于初中及以上的父代,但其贡献率也已达到了44.1%,并非是一个较低的数值。以上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代,其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反而较大。对此,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代,获得经济资源的能力较弱,其收入一般也较低。较低的收入会产生收入预算约束,影响对子代的教育投资,最终影响其成年后收入;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代在对教育的认知,在对子代教育的直接影响上相对较弱,同样会影响到子代的受教育程度,这一作用过程可以称之为“父代教育约束”。与此同时,本文发现,对于代际收入弹性π1,无论是父亲与子代还是母亲与子代,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群体,其代际收入弹性较高,表明对较为弱势的群体而言,其子代更有可能继承其不利地位。结合上述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结果,本文认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会同时产生收入预算约束与“父代教育约束”,使得其对代际收入传递产生较大影响,并最终导致这一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与此同时,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而言,其“父代教育约束”对子代的影响在父亲-儿子、母亲-儿子、母亲-女儿样本中已经超过收入预算约束的影响。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对于生活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人群而言,其经济行为也会有所差异。对此,依照一般的划分方式,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以及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山东、辽宁;中西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南、湖北、广西、贵州、黑龙江、重庆、云南、陕西。],以考察不同经济环境下,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表7汇报了相关的估计结果,首先考察不同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值,不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平均值显示,在父亲-儿子,父亲-女儿样本中,东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要略小于中西部地区;在母亲-儿子,母亲-女儿样本中,东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则略高于中西部地区。该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父亲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在东部地区,母亲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较大。其次分析不同地区父代收入与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表7中父亲与儿子、父亲与女儿、母亲与儿子以及母亲与女儿的结果均显示,中西部地区父代收入的影响要低于东部地区,甚至在父亲与女儿、母亲与儿子以及母亲与女儿的样本中,中西部地区父代的收入影响占总影响的比重要低于50%。这一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较大,甚至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过了父代收入本身。
以上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的作用要高于东部地区。一般而言,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要低于东部地区[由《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第二部分各地区乡村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规模可知。]。这一发现进一步佐证了表6的估计结果,即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其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相对较高。
六、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富二代”、“穷二代”等词汇频繁见于媒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到代际收入传递,特别是对代际收入传递机制展开研究。现有文献重点讨论了较为直接的传递路径,即父代收入通过对子代教育进行投资,并最终影响子代收入。但是,鲜有研究进一步探讨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加入父代人力资本质量的代际收入传递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年至2015年共10轮的农村居民数据,使用配偶的职业和受教育年限以及父代自身职业对受教育年限回归的残差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在其中的作用。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重点在于剥离出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并与父代收入作用的强弱展开对比。本文的主要发现为:总样本估计结果显示,父亲收入对儿子和女儿收入的影响在总影响的占比分别为65.5%以及86.2%,母亲收入对儿子和女儿收入的影响在总影响的占比分别为94.8%以及61.6%,父代收入的影响均高于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但是,父代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特别是在父亲对儿子以及母亲对女儿的影响中,其贡献率分别达到了34.5%与38.4%。对比以往研究,以往文献重点探讨了父亲与儿子、父亲与子代(儿子与女儿)之间的收入传递,对于母亲的讨论相对较少。本文在对父亲、母亲、儿子以及女儿展开分析后,发现尽管均是代际收入传递,但是,父亲对儿子与女儿收入,母亲对儿子与女儿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具体而言,一方面,父亲收入对女儿的影响比对儿子更为重要,而母亲收入对儿子的影响则要高于对女儿的;另一方面,父亲人力资本质量对儿子的影响比对女儿更为重要,而母亲人力资本质量对女儿的影响则要高于对儿子的。这一结论表明,尽管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父亲掌握一个家庭大部分经济资源,对子代影响较大。但是,本文利用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母亲收入与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同样重要,且对儿子与女儿的影响存在差别。
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代,其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反而较大。此外,不同地区的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父代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在中西部地区,父代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较大。一般而言,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要低于东部地区,不同地区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教育异质性的结果。综上,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或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父代教育约束”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已经高于收入预算约束的作用。异质性结果进一步表明,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不容忽视。若将父代收入看作“硬”实力,那么,父代人力资本质量这一“软”实力在弱势群体代际间阶层跨越上可能更为重要。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应加强宣传引导,特别是针对农村人力资本质量较低人群,需要为其提供易于接受的方式理解“知识改变命运”,帮助其家庭,特别是下一代提高教育预期。此外,政府应继续增加在农村教育领域的补贴,帮助农村家庭降低教育成本。与此同时,不断优化农村教育财政支出结构,比如,可以实行性别差异化的支出政策,特别帮助农村家庭中女儿获得受教育机会,保障其至少完成义务教育阶段,有效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最后,尽管本文剥离出父代人力资本质量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并与父代收入作用的强弱展开对比。但是,本文对人力资本质量的定义仅仅局限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对此,后续的研究可以以此为基础,做进一步拓展,比如纳入健康因素,从而更为清晰地展现代际收入传递的路径。此外,在代际传递中,子代的反馈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比如善于学习的子代可能会引导父代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入,对于这一代际间的双向互动同样值得后续做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杰、苏群、周宁,2016:《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传递机制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
[2] 陈琳,2016:《中国城镇代际收入弹性研究:测量误差的纠正和收入影响的识别》,《经济学(季刊)》第1期。
[3] 陈依婷、陶阳、杨向东,2021:《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教缺失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机制:父母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链式中介作用》,《全球教育展望》第10期。
[4] 蔡洁、刘斐、夏显力,2020:《农村产业融合、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六盘山的微观实证》,《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2期。
[5] 邓悦、郅若平、王俊苏,2021:《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6] 何石军、黄桂田,2013:《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2000~2009》,《金融研究》第2期。
[7] 李波、张春燕,2021:《农地经营抵押贷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对湖北省50个縣(市、区)的实证研究》,《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8] 李实、岳希明、史泰丽、佐藤宏等,2018:《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变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V》.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9] 李唐、韩笑、余凡,2016:《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10] 欒健、韩一军,2020:《农地规模经营能否实现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的趋同?》,《中国土地科学》第9期。
[11] 姜长云、李俊茹、王一杰、赵炜科,2021:《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特点、问题与未来选择》,《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2] 齐文浩、李明杰、李景波,2021:《数字乡村赋能与农民收入增长: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农民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13] 钱龙、陈杰,2018:《依靠教育还是依靠健康:两类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及分化效应》,《新疆农垦经济》第2期。
[14] 邱子迅、周亚虹,2021:《电子商务对农村家庭增收作用的机制分析——基于需求与供给有效对接的微观检验》,《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15] 孙华臣、杨真、张骞,2021:《互联网深化与农户增收:影响机制和经验证据》,《宏观经济研究》第5期。
[16] 唐跃桓、杨其静、李秋芸、朱博鸿,2020:《电子商务发展与农民增收——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考察》,《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
[17] 汪三贵、孙俊娜、王琼,2020:《如何提高金融扶贫质量:基于贫困村互助资金收入效应的经验研究》,《宏观质量研究》第6期。
[18] 王延涛、李心雅、蒋海舲,2018:《职业资格证书收入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人力资本质量的视角》,《宏观质量研究,》第4期。
[19] 王玉斌、李乾,2019:《农业生产性服务、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财经科学》第3期。
[20] 温涛、王佐滕,2021:《农村金融多元化促进农民增收吗?——基于农民创业的中介视角》,《农村经济》第1期。
[21] 徐舒、王貂、杨汝岱,2020:《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经济研究》第4期。
[22] 杨沫、王岩,2020:《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机制研究》,《管理世界》第3期。
[23] 杨中超,2018:《家庭背景与学生发展:父母参与和自我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教育经济评论》第3期。
[24] 张林、罗新雨、王新月,2021:《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生活质量——来自重庆市37个区县的经验证据》,《宏观质量研究》第2期。
[2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6] 周玉龙、孙久文,2019:《瞄准国贫县的扶贫开发政策成效评估——基于1990-2010年县域数据的经验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第5期。
[27] Becker, G. S. and Tomes, N., 1079,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6): 1153-1189.
[28] Bevis, L. E. M., Barrett, C. B., 2015, Decomposin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The Gender-Differentiated Contribution of Capital Transmission in Rural Philippines, World Development, 74: 233-252.
[29] Blankenau, W., Youderian, X., 2015,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xpenditure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Income,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8(2): 334-349.
[30] Bjrklund, A., Jntti, M., Solon, G., 2007, Nature and nurture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Evidence from Swedish children and their biological and rearing parents,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7(2).
[31] Bhlmark, A. and Lindquist, M. J.,2006, Life-cycle Variation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urrent and Lifetime Income: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for Swede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4(04): 879-896.
[32] Deng, Q., Gustafsson, B. and Li, S.,2013,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in Urban China, 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9(3): 416-436.
[33] Erikson, R. and Goldthorpe, J., 2002,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3): 31-44.
[34] Fan, Y.,2016,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41:299-314.
[35] Gong, H., Leigh, A. and Meng, X., 2012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Urban Chin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8: 481-503.
[36] Haider, S., Solon, G.,2006, Life-cycle Variation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urrent and Lifetime Earning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4): 1308-1320.
[37] Hérault, N., Kalb, G., 2016, 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 of Labor Market Outcome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4(1): 231-249.
[38] Lee, C. L., Solon, G.,2009,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4): 766-772.
[39] Lefgren, L., Sims, D. and Lindquist, M. J.,2012, Rich Dad, Smart Dad: Decompos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0(2): 268-303.
[40] Lefranc, A., Ojima, F. and Yoshida, T.,2014,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Japan among Sons and Daughters: Levels and Trend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7(1): 91-134.
[41] Li, Z. D., Liu, L. and Wang, M. J.,2014,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nd Public Education Spending: Evidence from China,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40: 89-97.
[42] Palomino, J. C., Marrero, G. A. and Rodriguez, J. G.,2018, One Size Doesn’t Fit All: A Quantile 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S. (1980-201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16(3): 347-367.
[43] Qin, X. Z., Wang, T. Y. and Castiel, C. Z.,2016,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Human Capital and its impact on income mo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38: 306-321.
[44] Sacerdote, B., 2007, How Large are the Effects from Changes in Family Environment? A Study of Korean American adopte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1): 119-157.
[45] Solon, G.,1992,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393-408.
[46] Zimmerman, D. J.,1992, Regression Toward Mediocrity in Economic Stat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409-429.
A Study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Transmission of the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The expansion of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based on the parents
Chen Jie1, 3, Chang Xue1, 3 and Qian Long2, 3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Institute of Food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By constructing a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transmission analysis framework with the input of the quality of paternal human capital,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role of paternal income and human capital i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transmission,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ideas of public policies related to improvin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CHNS survey data, the relevant empirical test results show that mothers’ income and human capital quality are equally important i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transmission just like fathers’, and different effects have been observed on sons and daughters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on the one hand, fathers’ income is more important for daughters than for sons, while mothers’ income is more important for sons than daught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quality of fathers’ human capital is more important for sons than for daughters, while the quality of mothers’ human capital is more important for daughters than for sons.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test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paternal education constraint o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transmission has been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income budget constraint for groups with lower educational level or in the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instrumental variable
責任编辑 郝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