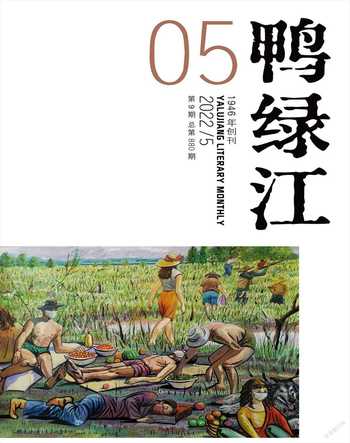秦岭之东的傍晚(组诗)
秦岭之东的傍晚
秦岭之东的麦田正在接近天空
看麦娘、麦家公、麦蒿、麦瓶草
像一群乞儿,在垄间、埂上
相互挤搡,抢食阳光
山谷,一万年都在
开花和准备开花
雨水上门之前,穿上自家织就的春风
秋天弯下腰,伸手抓起一把果实
送给每个过路的人。她是
别人家的姑娘或祖母
总会听见尘埃翻身
有时在清晨,有时在午后,每次都有
不一样的声音。据此
区分孤独与空虚
此刻饲养它的一桌、一椅、一门
来自一棵砍倒的树
倒下的树,还能叫作树吗
天将黑的时候
一步步挨下冈来,摇动两边的云
风却那么静
比秦岭的一万年还要深
临寒食帖
不只是这样清寒的早晨,才回忆
一个叫作余集的小镇
每每在城市的餐厅,靠窗的桌边坐下
就会油然想起,那家小吃店
和一碗叫作神仙饺的馄饨
驼子老板,少言寡语
独自站在临街的长案前
十指翻飞,从不回头
转身时,必是恰到好处
笊篱一抖,添料,加汤
一只手端着碗,一只手在前面轻摇着
像是拨开灌木林,把滚烫鲜香的早晨
递给从枝叶间伸出双手的人
还有窄窄的石板路
和小店周边的日杂店
布店、药店和铁器店,以及台阶下
一长溜摆放着的小葱、蒜苗、菜瓜
蹦蹦跳跳的河虾
很多早晨,只要一想起
千里之外也能看到
竹筐和秤盘上明亮的露痕
这时,我总是低着头,默默转身
曾经无数次想过,再沿着短短的老街
走进那家小店,浪费一个早晨
可终究不肯
因为一碗神仙饺
耽误远山沧海,或守夜掌灯
——就这样,浪费了一生
挪威森林
多年前读《挪威的森林》
记住了那片森林
多年后的初秋,北欧山谷
下午五点的阳光穿过冷杉
照着小小的野湖、我的手掌
一棵挂着几粒硕大果实的黑莓
另一本同名的书
多么喜欢那湖面上的一片云
像一张刚刚精心洗过的桌布
坐在黑莓旁,就想到
壁炉、罩子灯、黑面包和小麦啤酒
星空下,一声声牛哞
将木椅变成旷野
那干草上,正在落雪的旷野
就让我觉得人生多有意义
可以因一个书名热爱陌生的一切
因一束阳光裹紧无边的寒夜
并且,明知自己的无知
还假装比一本书更能洞见它的隐喻
斯卡布罗集市
一到秋天就想写下一些东西
如同一到时候就抑制不住地怀念
今天,路过斯卡布罗集市
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
欧芹、鼠尾草和百里香
每一缕风都从几百年前吹来
让人看到秋天,看到旷野
以及越老越不可名状的告别
走过陌生的人群
如同走入森林
听到各种生命的开谢
没有一个人问我来自哪里
一阵又一阵迷向的风
出入古老集市
突然发现所有的努力
都不过是让期待变得可有可无
当我在一座桥上回望
听到水声洞穿风声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疼痛
丹江 隐隐作声
你跃出水面,我在人群里
你的背影,依旧清且涟漪
我也知道,不是每条船经过
你都会翩然并行
必定是凌晨乍醒,听到
浩茫的岁月,隐隐作声
江风如刀,人们躲进舱里
我特地站在船尾
你会望见,夹岸的芦花镂空了守候
我的背影,还是百无一用
注定不能与你在水下永生
一直游走于江湖,投水容易
如何收拾一路的土与尘
我此番就是为了打捞八千里的暮色
让人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
写着你名字的月和云
十万花海
我有一方小院,高黎贡山下
门朝十万花海
春天油菜花,秋天万寿菊
夏天,十万云朵,朝朝暮暮
最爱十万雪花
围拥火炉上的铜瓢,喝酒吃肉
后山黑胡子道士打着铜鼓,彻夜唱歌
十万花海都在灯下
沉默不语的时刻
看着自己的影子模仿余生
愿我每一个清晨
有所信,有所爱,有所恨
烤龙河
一条河在这个世界流淌了很久
除了我,没有人会一再写下它
——烤龙河。多么奇怪的名字
曾经以为只流经小小的村庄
然后在视线落地处消失
常常想对每一个认识的人:
多么干净,多么平缓,从不喧哗
哪怕在盛夏的暴雨之后
也只能在深夜倾听它的奔腾
冬天,小鱼在冰下
一口一口地吮食阳光
便觉得整个世界
都在融化
但我總是欲言又止
这与它奇怪的名字没有关系
有些事,如今只想让它
从回忆中流过
从小小村庄的眼角流过
浅草青黄的河谷,结下
一颗颗能叫出我名字的露珠
问路
今晚,去圣塞巴斯蒂安。窄窄的街道
一扇扇草绿的门。一盘伊比利亚火腿
我们的手势,让灯光一惊一乍
桌子那头,大西洋正在酣睡
滋贺的琵琶湖,为温泉宽衣解带
用信乐烧的杯子喝酒。你们载歌载舞
我鼾声如雷。你们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龙江大桥,等一场浩荡的落日
繁星填平河谷,小酒馆的火塘才说
失望和希望,都是这里的常客
骑着五彩的森林上山,川主寺是一枚
纪念章。我们没有更广阔的胸膛
只好用背影驮着那一场风雪
和风雪之后,不会消融的白和空白
走到天尽头,大风劫走语言
还想剥去白色的衬衫
拿起一张明信片,风就停住
终于没有写下地址。让它自己问路
今晚,哪里也不去。大雪纷飞
——我们,以及我和你们,都是谁
作者简介:
薄暮,河南商城人,公务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莽原》等,著有诗集《北中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