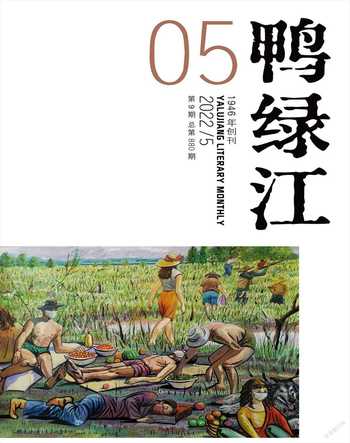成长隐痛、现实焦虑、爱与希望
90后作家已然成为国内文坛一股新势力,在80后开始怀旧的今天,90后写作差不多已经成了青年写作的同义词。最近几年,国内多家刊物先后开办了90后栏目或做过90后专辑。《鸭绿江》杂志曾在2019年第9期推出“辽宁90后作者小辑”,沈阳市作协在2021年9月推出了一本《盛京四俊——沈阳90后新锐作家作品集》,这些举措,对培养辽沈本土青年作家来说如春风拂柳,恰逢其时。
成长母题 现实关注
每位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母题,往往一生都在对其进行书写,而成长却几乎是所有作家都要面对的共同母题。尤其是在初涉文坛时,差不多每个写作者都会把焦点对准成长,在对往昔岁月的回望和书写之中,完成从一个文学青年到一位青年作家的成人仪式。在“盛京四俊”的作品里,成长小说占据了很大比例。王图和卓尔的大部分作品以及王冠楠的某些作品,都可以归入成长小说之列。述怀的作品不能简单定义为成长题材,但在她的小说里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成长始终与笔下的故事纠缠在一起,那些故事影响并伴随着“我”的成长。在对往昔故事的回想追述中,“我”重建了自己童年的成长环境,完成了自我溯源般的追忆似水年华。
从某种角度上讲,成长就意味着伤痛,没有伤痛的文字似乎从来都不值得书写。在四位作家的成长小说里,主人公普遍伤痛、贫困、孤独、惶恐,处于生活的苦难和边缘境地。王图的《风从低处来》里受家暴威胁的张小康只身逃到外公外婆家中避难,遇到同样生活在苦难之中的跛子小黑,并由此结成了友谊。他的《火车经过》可以看成是《风从低处来》的姊妹篇,小說里的黑小子马永昌与跛子小黑不仅精神气质相通,而且形象也很相近。卓尔《黑书包狂奔》里的刘福来家境贫困,买不起智能手机,没有女生喜欢,从小学到大学不断遭受嘲笑和打击,黑书包成了他的倾诉对象和生死之交。《北京屋檐下》中的得利和刘福来一样出身农村,在他人眼里是身上散发着“炕洞子味儿”、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低端人口”。《丑狗》里的主人公因为出身贫寒而备受欺凌。王冠楠《黄鹤传》里的黄鹤同样是个身处底层的边缘人,出身农村,家境贫寒,努力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却成了有钱子弟焦富的替考工具。《吃饭》里的刘北泽父亲身亡,母亲改嫁,和爷爷相依为命。《傻子》里的主人公是个傻子,父亲凭空消失,被迫打三份工维生的母亲又遇到了车祸。《苞米地里的艾丽丝》里的艾丽母亲不知所终,父亲又因伤人入狱。她在发廊打工、卖小吃努力养活自己,但父亲出狱当天身亡,相互温暖的男友张汉文也出了意外。
在他们笔下,成长小说的主人公还有另一个特点:父爱缺失,母爱无力。这种缺失非常彻底,在大多数作品里,父亲的形象模糊不清,呈现出来的只有粗鲁、无知、蛮横和暴力。王图的《风从低处来》里,张小康父亲的出场方式充满了暴力和威胁——“伴随着砸门声,传来爸爸断续而含混不清的声音:‘……开门!快,快开门,不然,我就……你们!’”卓尔的《黑书包狂奔》里的父亲是个文盲加酒鬼,对儿子动辄打骂,把儿子的书包扔进火里——“他连我买个新书包也气得要杀人,他大字也不认识几个,连我学的什么专业都不曾知道,此时却吹嘘起来自己教子有方,别人问起什么方子,他就会说就揍他,揍到他哭,揍到他只能跑。”她的《丑狗》里的父亲同样简单粗暴,对儿子缺少温情。王冠楠《苞米地里的艾丽丝》里艾丽的父亲是个欺行霸市的流氓,后被送进了监狱。这类小说里,母亲的形象则大多懦弱无助,终日生活在父亲的淫威之下,对儿女的爱也显得苍白无力。王图《风从低处来》里的母亲除了把儿子送上火车逃走,想不到任何更好的办法。《火车经过》里马永昌的母亲经常遭受丈夫打骂,看不出什么反抗迹象。卓尔的《黑书包狂奔》里的母亲在丈夫的淫威下胆战心惊,连儿子送的礼物都不敢接受。面对苦难,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习惯的做法就是逃离。在王图笔下,逃离已经成了一个意象,与卓尔小说主人公的狂奔遥相对应。有意思的是,在王图和卓尔的小说里,主人公逃离的目的地同是外婆家,或许在两位作家心中,那里也是温暖安全的地方吧。
这样设置情节和人物关系,我想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前辈作家的影响(比如王图的作品似乎有余华的影子),还有为增加情节性和矛盾冲突刻意为之的因素存在。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更多的则是出自作家内心的苦难意识。对几位青年作家而言,这种意识或许还没有从自发转入自觉,但已经成为他们作品坚实而可贵的底色。对苦难的关注与书写,透露出作家的境界和情怀。这一特质从他们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中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印证。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说的成长题材和关注现实题材之间并无明确界限,两者还有许多交叉和重叠。在四位作家笔下,成长题材也在关注现实,关注现实题材同样包含着人物的成长。之所以分别讨论,是因为我觉得两类题材对应着写作者两个不同的创作阶段。
卓尔的《丑狗》《北京屋檐下》,王冠楠的《一个故事的N 种讲法》《傻子》《一个普通朋友的葬礼》《苞米地里的艾丽丝》,述怀的《偷眼》《孔雀开屏》《格色》,都是写得很实很接地气的作品。较之成长类题材,这部分作品向生活扎得更深,手法更朴素,质地更坚实。把人物从狭窄封闭的空间里解放出来,放到了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小我由此变成了大我,小说的主题也随之变得更加开阔。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到作家对现实的关注,也能看到他们脚踏大地仰望星空的写作姿态。与充满想象的成长类作品相得益彰,恰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让他们在写作的道路上行进得更加踏实。我想这类作品可以解读为成长小说的延续。卓尔的《黑书包狂奔》中的刘福来毕业后就是《北京屋檐下》的得利。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人物的成长,也能看出几位年轻作家的进步和成长。从《风从低处来》到《我们去西宛城》,我们看到了王图的构思更加宽广开阔。从《黑书包狂奔》到《北京屋檐下》,卓尔迈出了从小我向大我跃进的坚实一步。从《鞘》到《苞米地里的艾丽丝》,同样能看出王冠楠的进步。从《木头人》到《孔雀开屏》,也能看出述怀的成长。从题材上看,述怀的小说多取材于老工业基地的故人往事,但我不想把她的作品归入工业题材、后工业题材或者目前很火的铁西叙事,关于她的作品,我想在下面一节集中进行讨论。
跳跃性 非理性 碎片化
四位作家的小说构思都有独特和出人意料之处。王图和卓尔的小说情节丰富饱满,比起中老年作家,在面对故事和人物时,他们显得更加自由不羁、挥洒自如。卓尔《九个故事》里的一句话准确地描述出这种自信的写作状态:“我能够杜撰无数的故事,把假的说成真的,或把真的说成假的,我越来越享受这个过程了。”
王图的小说故事情景转换迅速,有自己独特的时间线索。《诺曼不曾死去》《风从低处来》《火车经过》《我们去西宛城》几篇小说虽然都是线性展开的,但人物和情节的跳跃让小说结构变得丰富多元。王图擅长用细节推进情节,写得扎实,贴近人物,给人一种高度真实感。一些创造性描写又让小说呈现出难得的飞翔姿态。《诺曼不曾死去》写了一段散发着诡异气息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之间纠缠扭曲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对峙,隐约交代的双方家庭背景让我们看到这种虐恋并非毫无依据。小说的力量来自两个人物之间主动与被动关系的扭转,这也是小说能够起飞的翅膀。《风从低处来》里的张小康给外公丈量身高的细节就特别令人难忘。卓尔的《九个故事》结构别出心裁,实验意味很强,用八个各自独立的故事构成了完整的文本,讲了一个爱与孤独的故事。第九个故事又从文本中跳脱出去,对前面的八个故事进行了解说。这个实验小说成功与否并不重要,作者展现出的勇气令人敬佩。
从构思上讲,王冠楠的小说往往出人意料,显示出作者独特的构思方式。他善于由虚及实,从看似凌空蹈虚的故事中透视出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一个故事的N种讲法》是一篇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用几个不同的视角对乡村发生的一件命案进行了反复讲述。故事与故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让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也让事情的真相变得愈发扑朔迷离。《鞘》里的武林至宝名剑变成了封在剑鞘里的碎片,让人看到名利之争有如云烟。《孤独日》建立起一座虚拟城市和一套虚拟规则,折射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品里为取消孤独日而做的努力和抗争,也正来自生活中人们渴望理解和交流的美好愿望。《一场牌局》用天使和恶魔打牌的方式,对濒死之人一生的善举和恶行进行了总结,也对善恶的界限和标准进行了思考。他的几个短小说《傻子》《三个人的晚餐》《相声》也各有独特之处,字数虽然很少,却如钢针般锐利,刺痛读者的某丛神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小说情节上看,几位年轻作家的小说往往具有很强的跳跃性,有时候甚至呈现出一种非理性。比如王图的《我们去西宛城》里东北风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拿枪的日本兵毫无来由地闯进来又被逃兵黑泽杀死。卓尔的《苹果》里画家莫名出现又莫名死去。在王冠楠的《鞘》《黄鹤传》《苞米地里的艾丽丝》中,情节的行进也有着相似的特征。但我并不觉得这么设置多么突兀,反而能感受到一种不羁的自由和活力。作家苏童在一篇访谈中说过,青年作家特有的心态“就是要以天马行空的姿态让别人吃惊”。不过我觉得,如果青年作家的创造力能和现实结合得更紧密些,作品会变得更加坚实有力。这是我在阅读时的一种期待。
在四位作家里,述怀的小说显得尤其与众不同,叙述视角、人物设置、小说结构、写作手法更加复杂和多样化,有着浓烈的实验意味。她用独特的方式讲了时间的力量、神秘的力量,讲述了发生在沈阳这座老工业城市的故人旧事。《木头人》用童年视角写了多年前发生在工厂区的杀人和裸奔两件旧事,情节淡化飘忽,虚虚实实,通篇弥漫着一种奇异的不确定性。在《无稽之谈》里,她用“拼贴”“并置”“碎片化”等后现代手法,先后用“我”“员外”“我爸爸”“老奶奶”的视角,共同讲述了生活在一隅之地的药婆的故事。《盲刺》里的谈智慧因为偶然淘到一本老旧日记,和太姥爷鲍十斤的人生发生了交集。他千方百计不断追寻,终于解开了太姥爷身份之谜,但随之而来的疑惑更大了。《循环》则充满了神秘的不可知性,李卫东的咒语不仅在追求钱晓丽的男人身上应验,甚至连他自己都成了被诅咒的对象。在《孔雀开屏》里,先是通过出租车司机的嘴讲述了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工人临危受命维修机器的故事,紧接着又由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爸爸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格色》用第一人称视角,从铜先生的外在特征入笔,跨越时间和空间,经过不断补充和重述,一层层抵达故事的核心,揭开了一个遭受情感失败的伤痛者封闭孤独的内心世界。
在述怀的作品里,故事和情节已经被打散成碎片,有如朦胧的梦境若隐若现,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心理感受以及故事遗留的气味和拖痕被着重突显。她似乎对情节和人物形象有着独特的警惕,一旦某个情节或人物固定下来,就会感到某种不安,紧接着就会进行解构和擦除。她不断地把人物和情节建立起来,又不断地推倒,在记忆和事实的缝隙间,在虚构故事和真实生活的裂纹里,不断进行“镶嵌”“贴合”“解构”“建立”与“擦除”,最终达到了一种奇异的艺术效果,让小说散发出“一股子神秘诡异的味道”。这应该是述怀持有的一种创作理念,正像她在《动物园》里说过的一句话——“一切讲得太明白没意思”。《无稽之谈》结尾处这段话或许更能透露出她的构思方式和写作感受——“人和时间是不能够做对儿的,这是互相伤害的方式,对于看起来像是那么一回事的瓜,里面的脉络,你不细想还可以,要是真的想细了,仔细地追究起来,这里面,都是会被说成无稽之谈的”。
锋芒和锐气 想象与动感
我还要格外说一说几位年轻作家的语言,这也是构成90后写作诸多元素里较为闪亮的关键词之一。四位作家的语言风格不同,同一位作家在处理不同素材时语言也有差异和變化,但他们的语言无疑都有着锐利的锋芒,挟裹着青春的风雷和强大的冲击力甚至是破坏力。我想,作家的语言一方面来自天赋,另一方面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另外也是创作理念使然。语言透露出作家的情感方式,是作家与世界交流沟通的窗口,也是作家的气质和面对生活的态度。从某种角度上讲,作家的语言也是他的世界观和文学观。换个角度讲或许也能说得通,小说的语言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最终能走多远。
王图的语言联想丰富充满动感,在叙述时充分调动起了各种感官,让人阅读时见其形、闻其声、嗅其味。
张小康无聊时就会躲在这里,随手捡起岸边的石片,一抬手,那石头就躲闪跳跃着奔向远方,激起一串串的水花,张小康想,我就是这样的石头,叫人一丢,蹦跶几下,就不在岸上了。(王图《风从低处来》)
她双手扶住我的脸颊,我们额头相抵,我们的眼睫毛似乎都缠绕在一起,我看着她瞳孔里的深渊,她离我近在咫尺,又似乎是相隔整片银河,这感觉让我呼吸急促。她的手抚摸着我的脸颊,又拍拍我的颈背,像是说悄悄话一样:“你要好好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咱们都是。”我用力点点头,她笑颜如花。(王图《诺曼不曾死去》)
她从破旧的铁门里走出来,嘴角带着笑,经过我的身边,有一股香气飘过来,像是味道甜甜的大白兔奶糖,我挺起鼻子贪婪地吸吮着,心中想到,原来这就是婊子的气味啊,真好闻!我长大了也要当婊子!(王图《火车经过》)
他那苍白的脸和画家乌黑的脸黏在一起,他们在我的眼前飞速地旋转着,转得我都看不清了,随后两张脸又慢慢地融合在一起,“啪滋”一声,变成了一块牛奶加巧克力味硬糖。(王图《火车经过》)
模糊中,我看见了铁皮盒子里的东西,那是一张张画着铅笔画的纸片,还有一个小照片,一家三口,被撕去了一半,所以只剩下六只腿,四条大腿,两条小腿。盒子的角落里,放着一只死去的红腿蚂蚱,我轻轻地拿出来,那只蚂蚱像是纸片一样脆弱地破碎了。(王图《火车经过》)
卓尔的语言诗意浪漫,意象简洁有力,有如剔透的冰凌,让人寒冷并印象深刻。
天上落下白色的呕吐物,我想,老天爷服下了大量牛奶,这会儿正在呕吐。(卓尔《黑书包狂奔》)
事实上从来没有人爱过我,我对爱只有激情式的想象,但却像冬天里的棉裤裆一样,空捞捞的。(卓尔《黑书包狂奔》)
我心里突然憎恨起大自然来,它曾经在我的印象里是绿意盎然的春天,是神秘的山脉河流与可爱灵动的小动物。而如今它是一个冰冷的词语,丧失了所有美好的属性。(卓尔《丑狗》)
天女在那里向他告别,只见她身体轻盈柔软,摇摇曳曳飞到月亮上去了。(卓尔《北京屋檐下》)
王冠楠的语言相对平实,但偶尔闪现的火花也足以带给人惊喜。
人是变化多端的,像云彩或是浪花,不像动物。(王冠楠《孤独日》)
吴倩倩说话的语气和她身子的扭动在同一个频率上,她一说话就像一条见了雄黄酒的白蛇,或者青蛇更贴切些。(王冠楠《苞米地里的艾丽丝》)
“砰!”充满了气的篮球在火光中炸开,溅起黑色的灰尘。隐约中我看到了快乐的尸体。(王冠楠《一个普通朋友的葬礼》)
我没想到这个世界变化来得如此快,人在一瞬间变成尸体,要好的朋友在一瞬间变成罪犯,本来是欢天喜地的年节,在一瞬间变成了漫天飞雪的葬礼。真是无常。(王冠楠《一个故事的N种讲法》)
述怀的小说语言如音符般跳动,像乐曲般悦耳流畅,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时时感到吃惊。她的语言和创作手法紧密贴合,也带有某种调侃和解构的意味。读她的小说时,甚至可以忽略人物、情节、故事这些传统的小说元素,而单纯地沉浸在语言带给人的愉悦和美感里。
我已经心不定了二十多年,也不差再多个几年。这种特质随着年月增长越发凸显,像是老茧,磨出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皮。(述怀《木头人》)
这里面还有些事情,能归纳到传奇小说的素材,我爸说,让我好好记着别忘了,以后如果写出来,这些故事都能拿去换钱。我不知道,换钱这些个事情,我是不是能够做得到。(述怀《木头人》)
在这里,一切都像苞米地里的杂草一样,疯狂地交缠撕咬冒出尖牙,滋滋地伴随着风声,野蛮生长。(述怀《循环》)
象征隐喻 爱与希望
在四位作家的作品里,象征和隐喻有如散落的珍珠不时闪现出光芒。象征和隐喻的运用拓展了小说的容量和空间,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作家的胸怀和抱负。逃离是王图小说里常见的意象,非常准确地映射出人物所处的逼仄苦难的处境。就像马尔克斯最后让一场飓风吹走了马孔多一样,王图似乎也对风抱有某种理想的期望。从他小说的篇名《风从低处来》就可以看出他对风这个意象的喜爱。他还有一部中篇名叫《狂风席卷一切》。在《风从低处来》里,垂死的外公象征着某种无法说清的结束,《火车经过》里的马永昌一心要找到的蝴蝶则象征着希望。卓尔和王冠楠对象征和隐喻的运用也很熟练。在卓尔的《黑书包狂奔》和《丑狗》里,黑书包和丑狗都是鲜明的意象,既是沉重的负担,又是保护的铠甲和知心伙伴,与人物的命运相互勾连扭结,撕扯不清,难以分开。《苹果》里鲜艳的苹果和烂掉的苹果象征着生活的不同形态。在《北京屋檐下》里,卓尔用隐喻和象征的方式设置人物,得利身处底层却爱好诗歌,他身上兼具浪漫和现实的特征。与他对应的,住主卧的天女象征浪漫,住隔间的黄发女象征现实,两个形象照出了浪漫的无助和现实的残酷。象征和隐喻是卓尔小说走进现实的入口。
王冠楠的《孤独日》,全篇建立在一个隐喻之上,虚构的城市和虚构的规范与现实世界一一对应,虚构世界里两股势力的对抗,正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折射。《一场牌局》象征着人生的善恶博弈。《一个故事的N种讲法》的结构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隐喻,通过对一个案件的不同讲述,告诉人们世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述怀《孔雀开屏》里的出租车司机,眼角如孔雀开屏般的皱纹,象征着岁月的沧桑和美丽。《木头人》的篇名就是个明确的象征,准确地定位出小说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这些象征和隐喻的运用,见证了四位作者的才华和勇气,从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作品的内涵和空间,让他们笔下的文字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有了一种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到的“轻盈”的姿态。
在阅读四位作家的作品时,最让我感动的是有关爱与希望的描写。在他们的小说里,总能看到令人温暖心动的细节。尽管人心险恶,世界支离破碎,但王图仍然努力给笔下的人物以希望。在《火车经过》的结尾处,赵小琳伴随着疼痛来临的初潮,昭示着女孩的成长,也是象征着希望的一抹明媚的亮色。《诺曼不曾死去》里男女主人公虽然彼此折磨,但仍然难舍难分。即便是在战争题材的《我们去西宛城》里,王图也通过姐姐李香儿和日本兵黑泽这对人物关系的设置,向读者传达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卓尔的《黑书包狂奔》的主人公刘福来受尽嘲弄和屈辱,仍然心怀爱意,省吃俭用给妈妈买雷锋帽。卓尔的《北京屋檐下》里的得利推着电瓶车艰难行走在北京街头时,还能够大声朗诵诗词,仿佛自己站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即便面临露宿街头的窘境,仍然“梦到自己站在流光溢彩的大舞台上,下面都是他崇拜过的大诗人,李白和苏轼笑着指给他看”。王冠楠的《一场牌局》里的主人公“我”虽然时时对人心怀恶意,但最终得出的结论还是“但是我爱他们”。这大概也是他最终能够闯过鬼门关苏醒过来的原因。《傻子》里的主人公小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把车轮下的图钉捡起来。《苞米地里的艾丽丝》里的艾丽,尽管生活充满苦难,却默默地喜欢读书写作。述怀《盲刺》里的太姥爷身份不明,刺杀日伪行动无人认可,但那种民族气节却昭然于世——“总有一腔热血,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挺身而出,哪怕就是盲刺,也要把自己化作一支冲天的后羿之箭,虽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谈智慧在小河沿放飞龙形风筝祭奠太姥爷的细节格外令人感动,也让人读出了爱与希望。在《孔雀开屏》里,虽然将老工人维修机器的故事解构掉,但小说里的爸爸仍然发出了“对上一个年代,对青春和家国”怀念和留恋的感叹。
文学是个复杂多义的门类,很难用一个笼统决断的定义进行总结。但从對人类心灵和精神关注的层面上来讲,在文学诸多定义里一定有一个是:从孤独苦难的废墟上开出的爱与希望的花朵。我一直觉得,爱与希望也是文学甚至是人类能够存在下去的理由。爱自己,爱他人,爱家,爱国,爱世界,有爱才会有希望。正因为此,文学作品才能流传百世,抚慰和震撼一代又一代读者心灵,在人类前行的路上点亮温暖的灯火。
【责任编辑】陈昌平
作者简介:
安勇,1971年生。毕业于地质学校,现居锦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2004年开始写作,近年来有小说发表于《山花》《天涯》《芙蓉》《上海文学》等刊物,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曾获第八届、第九届辽宁文学奖。短篇小说《铁屑》进入2019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