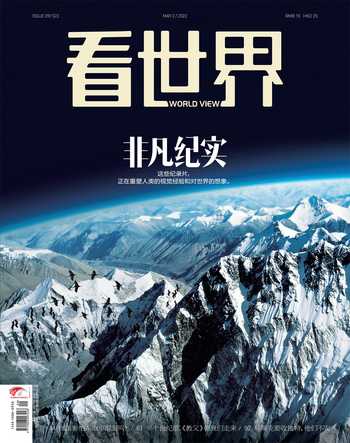从《多古拉之歌》到《何处是我柬埔寨的家》
郭力昕

柬埔寨吴哥窟
这是我第一次去柬埔寨。从曼谷出发,长途巴士过了泰国边界、进入柬埔寨之后,窗外的景观也产生了些变化。
传统房舍虽有味道,但乡间村镇的经济条件似乎比泰国乡村再差一截。這条路线上的地形地貌平坦,景观上也稍嫌乏味。缺乏公共投资的公路品质不佳,尘土飞扬的道路两旁,常有瘦骨嶙峋的白牛,纹风不动的或坐或立,有如雕塑或某种静物,时间似乎在此静止。
但那是乡间景观。
走进柬埔寨
当我随各国的背包客青年抵达被外来观光人口占据的暹粒市后,无论白天在附近吴哥各寺庙穿梭寻找自拍背景的游人,或者晚上在暹粒市中心觅食饮酒的各国观光客,市场店家的噪音,取代了安静与缓慢—虽然柬埔寨人的生活节奏,大抵还是舒缓从容的。

柬埔寨街头,瘦骨嶙峋的白牛
进入金边,景观与经验又不一样。这个首都城市,现代和传统杂陈,发展与原状并置。混乱中自成章法的交通,与严重欠缺公共建设的市容,反映着多数东南亚国家某种类似的历史进程与当代情境。当然,每一个东南亚国家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
12世纪前后臻于顶峰的高棉帝国,于逐渐衰落之时先后被暹罗与越南侵入版图,在19世纪又被法国殖民近百年,于二战期间再被日本占领三年。独立建国为柬埔寨之后,这个不幸的国家在1970年代初,因美国发动的越战而遭池鱼之殃,被美军轰炸到人无立锥之地,为“红色高棉”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入21世纪的柬埔寨,政局与社会渐趋稳定;尽管贫富差距、贪腐问题和卫生水平等诸多问题严重,这个国家靠着旅游业与其他传统产业,还是让经济逐渐成长起来。
金边市里,来自各国的建设投资项目,随处都是。在满地灰沙、处处成堆垃圾的街道巷弄里,小资品味的精致餐馆、咖啡店、法式糕点店、服饰精品店,纷纷在观光客聚集的地区冒出。
在当年“红色高棉”集中执行酷刑的地点之一“S-21集中营”,金边将它保留为大屠杀博物馆,让国人与世人不忘历史;同时,柬国人民已经在经济诱因下,重新学习中文与英文,以迎接更多的观光经济收益。
被法国殖民的记忆已远,而美国为现代柬埔寨带来的巨大灾难与噩梦,似乎也因经济利益而被快速遗忘。美金是与柬币共用的货币,且更受欢迎。
文化偷窥者
作为一个短暂停留的观光客,我想起一部令我反感的法国影片《多古拉之歌》。
这部在2004年被选为“金马影展”开幕片的创作型纪录片,从一出管弦乐加上合唱的大部头音乐作品出发,以金边、暹粒和一些乡村为猎取影像的场景,没有旁白或任何文字,甚至没有现实环境里的声音;少部分的现场声音,以压低的音量混杂在既有的音乐作曲中,配置成一种气氛或情调。
导演勒贡(Patrice Leconte)将所有搜集到的柬埔寨城乡影像,编辑、镶嵌在先谱好的音乐旋律、节奏或氛围中,制作成一部对柬埔寨/东南亚之东方主义想象与异国情调消费的西洋古典音乐大MV。
这个不幸的国家在1970年代初,因美国发动的越战而遭池鱼之殃。
来自柬埔寨现实处境或街头景观的《多古拉之歌》,一切材料都被去脉络地、支离破碎地,转为视觉化、美感化、趣味化、奇观化、神秘化的影像拼贴:水稻田、贫民窟;五彩气球、废弃轮胎;传统舞者、工厂女工;柔焦处理的黄衣和尚、静坐发呆的三轮车夫、各种萌态的街头儿童……
影片一开场,就花好几分钟的连续篇幅,以舞曲风格的音乐,或气势磅礴的合唱与管弦乐,不厌其烦地拼贴都市里的混乱交通,尤其是与多人搭乘或满载各类货物的摩托车骑士,好像这些摩托车骑士都不顾危险、喜欢表演特技。
但许多仍依赖摩托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人都知道,摩托车充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街道、无所不在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政府长期不建设或规划公共运输系统,而不得不然的生存之道。勒贡这类法国导演,显然毫无兴趣了解或反映这些政治社会历史脉络,今天摩托车满街的金边,只是他贩卖亚洲视觉情调给欧洲观众的材料。
影片里所有画面的在地意义都被取消,均质化为视觉趣味与影音剪接的拼贴游戏。在听似庄严浩荡如“史诗”般的合唱与乐曲、实则为一种另类煽情之西洋古典音乐陈腔的催情下,音乐与影像的共构,成为一种悲悯柬国贫穷处境的“人类普遍情感”,一种悲剧式“净化”或“升华”的自我感动的想象。

年轻电影导演Neang

《多古拉之歌》剧照

《何处是我柬埔寨的家》剧照
片尾的奏乐部分,故意以糊焦影像处理的西方白人儿童合唱者,唱着悲悯动人的曲调,画面叠影着柬埔寨的贫穷儿童脸孔,让1955年纽约现代美术馆“人类一家”(The Family of Man)超大型摄影展的“普世”意义梦魇,于半个世纪后重现。
法国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一个世纪的掠夺、搜刮之后,现在这位法国电影人又以哀伤的腔调,歌咏人类一家式的陈腔滥调。此种名曰悲悯、实为恩赐与剥削的影像语言,是非常经典的、一再重复于某些西方影像创作者的极为伪善的“艺术创作”话语。
可叹的是,被剥削或被同样如此凝视的地区或社会,常常毫无自觉,还供奉着这些西方“艺术大师”们,引为上宾。
拒绝剥削与凝视
对照着文化偷窥者的《多古拉之歌》,有几部柬埔寨导演的短片,特别值得关注。
除了《邊界》这部泰国导演关于泰柬边界冲突的作品之外,柬埔寨当代艺术家Vandy Rattana的《炸弹池塘》(2009)与《独白》(2015),以及Neang Kavich的《何处是我柬埔寨的家》(2013),都涉及这个国家现代历史经验中被“红色高棉”或西方国家蹂躏的历史重述。
当美国于越战期间,在柬埔寨11万多个轰炸点扔下的270多万吨的炸弹,今日变成长满了生物的池塘时,《炸弹池塘》引我们注视美国过去与今日在全球各地从未停歇的恶行。《独白》则是艺术家追忆“红色高棉”时期,对自己未曾谋面的亲人的亲密呢喃,让历史梦魇成为一种细腻而复杂的视觉和心理再现。
《何处是我柬埔寨的家》是另一位年轻电影导演Neang入选多项国际影展或得奖的纪录短片。此作的制片人是柬埔寨知名导演潘礼德(Panh Rithy),其名作《消失的影像》(The Missing Picture, 2013)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 “一种注目”单元的首奖。
《何处是我柬埔寨的家》跟拍一位18岁、皮肤黝黑的柬埔寨青年San Pattica。他在流离失所的无家无父状态里,努力抵抗周围人对其肤色与贫穷的歧视言行,并希望寻找从未见过的父亲。
因为家庭贫穷,Pattica自幼被送进孤儿院,母亲靠捡拾垃圾为生,父亲则是跟随联合国维和部队于1992—1993年到柬埔寨“维稳”的喀麦隆人。
Pattica同母异父的妹妹,则是另一个来自加纳的非洲维和士兵一走了之的产物。他们在柬埔寨随处与当地妇女发生关系,留下一堆后患,包括制造了大量的孤儿、性工作者,并带来了艾滋病,让柬国的艾滋病患暴增。
在影片中,金边的景观与现实,不是支离破碎的视觉观览物,而是柬埔寨当代社会具有历史重量的某些真实的缩影。Pattica的故事虽然沉重,但同时也让人鼓舞:一位处境如此困难的柬埔寨青年,对自己的尊严与才能仍有坚持,依然努力要做个正直的人。
这样的案例,无论是片中的青年,还是这部纪录短片本身,对柬埔寨的青年世代,应该都有激励的作用。《何处是我柬埔寨的家》由位于金边的Bophana Center制作,潘礼德导演作为创办者之一,希望努力建立起柬埔寨的电影档案资料与本土的制作能力。
对观众而言,既不能以任何剥削的、审美的凝视眼光,看待这样的影像作品,也可以在观影之余反思:历经巨大内外创伤,曾经灰头土脸、经济困顿至摇摇欲坠的柬埔寨,尚能有影像艺术家奋发勇敢地以影像书写,检视自己家园无可言喻的痛苦历史,那些繁荣富裕的国家,有没有足够的影像生产,在深刻地省思自己的土地?
———走进去,就感到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