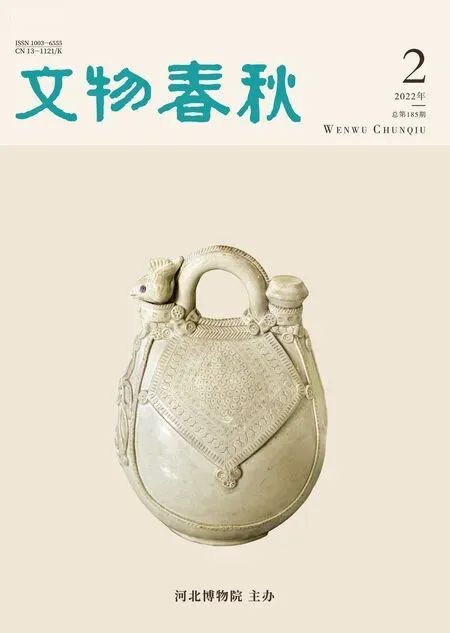考古视野下的二里头文化韧性、社会转型与社会崩溃
葛 韵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加利福尼亚 里弗赛德 92507)
作为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一直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有关二里头文化衰落与崩溃的研究却付诸阙如。当今社会的复杂状况为考古学者考察历史时期之前的社会崩溃提供了一手的观察材料,包括社会崩溃的原因与过程,社会重组所展现的韧性,以及相应的社会转型。本文尝试摆脱“文献—考古遗存相缀合”的研究模式,回归考古学本位,以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的物质遗存为基础,结合社会崩溃理论和政治人类学相关理论,探讨二里头文化转型与衰落的成因。
一、相关定义及其局限性
有关社会崩溃的研究,自美国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Collapse: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问世以来,引起了西方诸多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广泛关注,其中不乏质疑与批判,但在中国考古学界却并未引起相应的重视。因此,在本文展开前,有必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简单介绍与界定。
(一)社会崩溃
“社会崩溃,往往表现为政治实体的碎片化和文化传统的中断,如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信仰体系,甚至语言、文字系统的消失。”社会崩溃尽管不一定导致人群的灭亡,但往往伴随政治实体的解体与分裂,人口随之减少,政府角色弱化,宗教活动衰减,此外,相关的公共设施、象征权力地位的纪念碑式建筑停建,甚至被破坏、废弃,各种精致手工品也会停产。上述描述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并非所有复杂社会的崩溃都会如此。
广义而言,社会崩溃可以理解为社会政治复杂性的迅速衰落(几代人之内),或一个特定政治体系的消亡。伦福儒先生曾提出社会崩溃有四个表现特征:国家中央行政组织的崩溃,传统精英阶层的消失,集权经济的崩溃,聚落迁徙和人口锐减,而相对应的可辨识的考古学现象有“宫殿、公共建筑、精英居址甚至是整个聚落的废弃;高等级传统墓葬的消失,以及向更小型聚落呈分散分布的转变”等等。因此,社会崩溃应指的是一个特定政治机构或实体的分裂、分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被整合、分离和重建。但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的社会分裂或分离,抑或是消失,才算是社会崩溃,一直为学者们所争论。例如所谓的玛雅文化社会崩溃,虽然社会上层统治消失,精英阶层的居址被废弃,纪念碑等建筑物停止修建,但是平民阶层依旧居住在各个城市附近,家户组织的文化与祭祀传统依旧传承了下来。因此,在分析社会崩溃时,我们不得不引入另外一个概念——社会韧性。
(二)社会韧性
以往的研究常将社会视为被动的实体,认为其从衰落开始即一落千丈,直至消失。然而对社会崩溃模型的研究显示,社会崩溃过程不仅存在多样性,甚至衰落过程还可能出现周期性的波动。在这一过程中,正是社会韧性发挥了重要的缓和作用。
韧性常常被模糊地概念化,往往与描述一个特定单位的脆弱性相联系,而其所面对的压力则被分为急性的变化(如海啸、军事入侵等)和慢性的变化(如环境退化、长期干旱、经济停滞等)两种。但明确而言,社会韧性可分为政治韧性和文化韧性:前者是“在面临挑战时保持或迅速恢复的能力”,属于一种维持或恢复平衡(equilibrium)状态的短期能力;而后者是“在经历社会政治复杂性衰落的文明中,涉及文化方面的维持,如世界观、亲属关系和语言”,也就是在面对重大破坏无法维持或迅速恢复到平衡时,通过转型或适应维持其存在的长期能力。
此外,将韧性的概念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结合,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实体在转型期间所选择的不同轨迹。文化大传统代表国家与权力,是由城镇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文化传统;文化小传统则代表乡村,是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换言之,文化大传统具有国家权力、官方意识形态等上层文化色彩,文化小传统则具有区域文化、民间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大众文化色彩。其中,大传统与政治韧性联系更为紧密,精英阶层的垄断往往与政治统治有关;而小传统则与文化韧性相关,社会实体(如乡村或城市人群、宗族和民族团体)与几代人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有更广泛的联系,例如家户内部的习俗与传统的延续。正如弗希博士所言,社会上层的“政治领导人主要采用短期策略(如对自身合法性的投资)来应对内外部压力,以维持他们的控制机制的均衡”,而以社会下层文化为代表的“社会制度包括长期战略(如习俗和传统),旨在加强群体认同以及适应和忍受政治变革的共同愿望”。
因此,理解特定的社会和政治实体如何与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相联系,对于研究社会崩溃乃至社会转型非常重要。
(三)社会转型及其动因
相比于“崩溃”这一特定的带有负面情绪的词汇,“社会转型”被更多学者所接受。后者纳入了当遇到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环境压力等内部和外部问题时,社会实体所做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反应,以及相应产生的社会现象,如社会繁荣、重组、衰落甚至是复兴等,从而强调结果的多元性和替代性,而非单一的社会崩溃。换言之,同样作为人群对内外部压力所做出的选择,社会转型包括社会崩溃,因为社会崩溃本质上也是社会实体的一种适应,只不过是失败的转型。如前文提到的玛雅文化的社会崩溃,让我们认识到灾难后社会结构中的连续性和文化韧性的存在。因此,在研究古代社会的衰落与崩溃时,有必要进一步细化、理清社会实体经历的更多轨迹与可能性,而非直接判定为一落千丈式的崩溃。
社会转型的动因很多,总体来说分为内因和外因两类。就衰落与崩溃而言,贾雷德·戴蒙德总结为以下5类因素:(1)人类对环境的无意破坏;(2)气候变化;(3)强邻在侧;(4)友邦援助的减少;(5)社会所做的反应。尽管这些观点曾被诸多学者批判,但其创见性的总结也为公众理解社会崩溃提供了一些视角。若按内外因分,其中(1)和(5)皆为内因,剩下三点为外因。徐良高先生对此也曾做过具体的区分:“外因包括自然灾害,如长期的干旱,持续的洪水,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的流行性疫病,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的过度增加导致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比如土地贫瘠化、盐碱化等)。战争,包括外敌入侵、战败或过度扩张,过度适应于特定的环境或依赖于特定资源而缺乏适应的弹性与灵活性,特定资源的枯竭导致文明的崩溃。内因包括能导致政治体自我弱化和分裂的不同统治群体和机构自我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比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然而如前所述,社会转型还包括其他轨迹,因此以上提及的内外因素,同样也会对社会的发展与繁荣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社会转型绝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种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样无穷尽地罗列社会转型的动因,并不足以解释特定社会转型的具体原因及其机制。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依据特定社会实体所面对的内外部压力来进一步研究这个社会是如何适应或因这些压力而转变的。当然,无论内因、外因如何变化,社会的内部动力才是决定这些社会发展与衰落轨迹的首要因素。
二、重建二里头文化的社会转型与崩溃模型
在梳理了有关社会崩溃、韧性与转型的相关概念后,本文将对东亚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的社会转型与崩溃及其成因进行分析,以考古学为本位,结合人类学、社会学相关理论,梳理并探讨二里头社会在面对内部、外部压力时所做出的决策及其影响。
(一)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的转型
二里头时代是中国史前时期向原史时期过渡的重要节点,在这一时段,中国史前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所以,以中原地区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国三代时期乃至中国历史一体化的滥觞。根据最新的测年数据,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750—前1520年。
正如李旻教授所言:“二里头的兴起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龙山社会崩溃后的再生特征,从中既能观察到龙山文化因素的适应力,又能看到新传统的创新性。”其中,四级聚落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表一),遗址中心区大型宫殿基址与宫城的建造,围垣作坊区的出现,明显的墓葬等级差异,在二维实芯铜器制造技术基础上创造出的铸造三维礼器的块范法技术,以玉器、绿松石制品与铜制酒器、响器和白陶及漆器组合成的二里头文化礼器的核心,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礼制制度,都显示出二里头文化在龙山时代之后由多元走向一体,也因此奠定了其在国家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处于关键的质变地位。

表一 洛河流域内二里头文化聚落数量统计
在二里头时代,考古学可见的二里头都邑转型发生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许宏先生称之为“二里头都邑的第一次礼制大变革”。转型的标志包括:中心遗址宫城城墙的建造;宫城内3号、5号宫殿的废弃,1号、2号、4号宫殿的建造,使得宫城内由二期的东部一组建筑群演变为东、西两组,且建筑格局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复数单体建筑纵向排列;与宫殿数量增长呈反比的则是水井和窖藏坑的数量锐减;铸造技术上,二期仅能制作铜铃,至三期开始铸造复杂的三维铜礼器;自三期开始玉礼器数量与器类出现大的发展,与铜器、陶盉、漆觚的组合成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礼器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白陶礼器地位下降,数量锐减;箭镞的数量则明显增加,有学者研究三期箭镞数量大约是二期的10倍,可能与二里头文化追求战略资源的控制从而进行对外扩张有关。
根据环境考古的研究,二里头文化二期的温度要高于四期,而湿度方面,干旱程度则不断加深,至四期才有所好转。此外,水井的深度也旁证了这种趋势——二、三期的水井深度均在距地表9~10米以下,而四期的水井深度只有7米多。显然,发生于三、四期之间的气候变化与发生在二、三期之间的社会转型的时间并不相符,所以二里头文化的社会转型应与自然环境变化的关系不大。
相应地,二里头文化其他等级聚落也同时出现变化(图一)。次级聚落中心望京楼城址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早段开始修建,而大师姑城址很可能修建于二、三期之交,或三期早段。宽大的城垣与城壕,显示出这两座城址重视防御的功能,而其分布在与下七垣文化交错的地带,说明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时,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这也是随后二里头文化所面对的主要外部压力。

图一 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图
三级聚落则因地理位置及战略资源分布的区别出现了不同的兴衰情况。南洼遗址应是一处以生产白陶器为主的手工业中心,随着玉礼器的流行,该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时出现衰落之势。王城岗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三期进入兴盛期,在利用龙山文化的护城壕基础上修建了带有防御色彩的壕沟,很可能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据点。东赵遗址由二期进入兴盛期,该遗址依地势而建,并建有环壕,其功能应与大师姑、望京楼遗址类似。南关遗址则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出现并进入兴盛期,借用南部的河流与西部、北部的壕沟形成的带有防御功能的环壕聚落,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表明,其很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开发铜、盐的战略据点。东下冯遗址与南关遗址类似,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仅为小型聚落,至三期时进入兴盛期,双重壕沟的出现则说明聚落规模与等级发生了变化。而最近发现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很可能也是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进入兴盛期,但碍于资料稀缺,有待下一步的具体研究。
综上,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二里头都邑宫城城墙的夯筑及内部大型基址等礼制建筑的调整,使得宫城核心区由原来的“空间”(Space)变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排外的“场所”(Place),闭合的宫城具有独占性和秩序性特征,以隔绝公众参与,日常生活遗迹的减少说明这一场所的功能趋于专业化,也反映出礼制的进一步规范化与系统化。另一个表象是礼器组合的转变与丰富化,尤其是运用块范法铸造的青铜礼器,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经济力量的象征。而结合外来的铸造技术创新出块范法铸造技术以铸造复杂的三维铜礼器,本就是以礼制文化为内核的礼制需求的体现,即礼制是“以青铜容器和兵器为代表的青铜礼器的原动力”,正如梅建军先生所指出:“礼仪活动的社会需求很可能是范铸技术诞生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代的青铜礼器主要发现于二里头遗址,“说明二里头的统治者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垄断了青铜礼器的分配,并为社会地位最高的统治阶层所有”。
再看二里头文化与同时期其他文化的互动、交流情况。以陶器为例,诚如秦小丽先生所言,二里头文化三期,“伊洛系陶器进一步向周边地区扩大,特别是西北和北部的山西省西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地区成为其扩大的重点,两地区均出现了伊洛系陶器凌驾于地方系陶器成为主体因素的状况。甚至在山西省中部的晋中地区也可看到伊洛系陶器的影响”。这与前文梳理的二里头文化不同层级聚落的兴衰情况相吻合。而二里头文化的陶盉、陶鬶或陶爵的分布,向北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南到安徽江淮地区、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向西达甘肃、青海一带(图二)。以牙璋为代表的玉礼器,则“经南阳盆地到达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分西南与东南两支扩散”,西南直抵越南红河,东南到达湖南、福建与两广。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已经形成的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络,到龙山时代形成了跨区域的礼仪知识共享的局面,而此时则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统一的礼制传统格局。

图二 二里头时代出土有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的遗址分布图(摘自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34页)
美国考古学家Blanton曾运用双重过程理论对前西班牙时期的中美洲文化进行研究。简言之,双重过程理论探讨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统治策略:一为排他性的个人倾向的政治统治策略,一为合作倾向的集体政治统治策略。分析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的社会转型情况,显然其对内统治策略有集权化、排他性的倾向,如:都邑内与平民阶层划分出互动边界,以此建构出绝对的政治身份与权威;有规划的宫室布局,体现了统治阶层的设计方案甚至是宇宙观;政治斗争和社会不平等体现在对知识和仪式的控制上,所以进一步完善、系统化已有的礼制制度,并垄断复杂的青铜礼器铸造技术;加强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尤其是对涉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青铜器制造的资源控制——这一系列举措都旨在巩固个人倾向的统治地位。就对外策略而言,纵观二、三期之交,二里头文化统治阶层对不同地区采用的是不同的外交策略。对西北方向的经略,尤其是突然出现带有防御性的西吴壁、东下冯、南关等矿冶、盐业聚落中心,说明二里头文化对盐、绿松石以及铜矿等战略资源的控制,是该文化对此地扩张的动力。与此同时,在东部边缘地区开始筑造带有壕沟的次级中心和一般聚落,以保护周围地区的居民,显示二里头文化与分布在其东方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以致成为主要的外部压力。但在该阶段,以礼器为象征的文化、权威及礼制思想更是向外辐射的主流。
(二)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社会转型的动因简析
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二里头文化对社会内部和外部压力所做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反应导致了社会转型的出现。而该现象发生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走向繁荣的基础之上。外来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大麦、羊和黄牛等,以及本土的水稻、粟、黍和大豆早已成为普遍的食物来源。食物的多元性提高了人们所摄入营养的丰富程度,并为都邑人口的增长提供动力,从而于第三期达到人口高峰,而都邑周边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也进一步促进了二里头文化的扩张,三、四级聚落数量的增长印证了这一点。
但人口的增长也可能加剧了社会内部的不稳定性。如前所述,面对这一情形,统治阶层选择加强集权来为生产与分配的集中控制提供保障,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分化。具体地说,是通过完善礼制文化以应对这一社会内部压力,尤其是通过发展新兴的冶铜工业以实现集权。相比于制陶手工业,冶铜业从原材料获取到铸型制模、熔炼浇铸,再到铸成之后的修整和加工等,都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此外,对铸造技术与知识的垄断,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一方面通过此类“炫耀性消费”行为,可以凝聚并彰显统治阶层的权威与能力;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将礼制思想的体现从以白陶器为代表的礼器组合,转向、融合至以外来的铸造技术与本土发达的制陶术相结合而创造出的复杂块范法铸造技术制造出的青铜礼器以及玉器为主,既是一种技术的在地化(Glocalization)过程,也是追求“文明以止”思想与礼制文化韧性的体现,并以此来强化统治阶层的身份地位与意识形态。
在对外联系上,二里头文化也主要依赖于礼制文化的扩散与传播,尤其是加强与其他文化社会上层的联系,而非直接地武力压迫与征服。如内蒙古敖汉旗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遗址的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的陶爵、鬶、盉。这些酒器与宴飨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宴飨将不同网络中距离更远的、处于不同社会和环境的群体联系在一起。“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的价值越高;从地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的价值越高”,用这些陶酒器随葬,表明当时这两种文化的社会上层之间建立了一种互惠关系,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局。此外,特定的陶器风格也被用来标示彼此的社会认同感。当然也存在例外,如二里头文化与同时期东方文化的关系较为紧张,故不得已在其文化东部边缘地区筑城。总体来看,二里头文化陶礼器(图二)与玉牙璋(图三)的广泛分布表明,二里头文化以礼器为象征的礼制思想的向外辐射为其文化扩张的最主要手段。但同时,笔者认为,这种以“软实力”扩张的外交政策,也是二里头文化崩溃的根本原因。

图三 二里头时代前后玉石牙璋的分布(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彩版二四)
(三)二里头文化的崩溃
有关二里头文化的崩溃,《国语·周语上》有“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记载,而根据环境考古对二里头遗址周边环境的复原研究,此说显然不成立。这种记载应是后代在天命观与德治思想的指导下来解释王朝更替与“天”易其命关系的论述,与《尚书·汤誓》中的“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大同小异。而学界多数学者则将二里头文化的崩溃与商夷联盟势力以武力推翻夏王朝的历史记载相联系,在考古学上则表现为:下七垣文化因素成组地沿东、西两条线向南的传播路径很可能是拥有这一技术—文化传统的人群的迁徙路线,而最终漳河型先商文化因素和岳石文化特征器物进入郑州地区和洛阳盆地,成为导致二里头文化终结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一推进过程存在时间差,所以“各地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不尽相同,豫东杞县最早,郑州商城稍晚,二里头遗址最晚”。
根据对二里头都邑废弃情况的相关研究,二里头文化的消亡发生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第2阶段,表现为“除了绿松石器制作作坊和铸铜作坊仍在使用外,上述主体要素(二、三期建成并开始使用的“井”字形道路、宫城城墙、1号基址群、2号基址群)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叠压或破坏而废弃,尤其是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器物成组、大规模出现于二里头都城中心区,破坏包括1号基址建筑群在内的多处重要遗迹”。这些都是二里头文化政治统治彻底崩溃的象征,也意味着统治阶层政治韧性彻底崩溃。但其政治遗产却作为文化韧性被二里岗文化继承并发扬。就消亡后的二里头遗址而言,一些遗存并未被直接废弃,如铸铜作坊的继续使用与新绿松石作坊的投入使用,以及6号基址和10号基址的兴建,此与周灭商后利用殷人的铸铜作坊和生产技术制作青铜器的情形相似。
与此同时,洛阳盆地的四级聚落体系也随之崩塌。洛阳盆地中东部可确认为二里岗文化早期的聚落相比二里头文化四期减少了近60%(表二),如此大规模的聚落被废弃,说明二里头文化的文化韧性在此时几乎消磨殆尽。

表二 洛河流域内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文化聚落数量对比
但如前所述,笔者认为社会的内部动力才是决定这些社会发展与衰落轨迹的首要因素。有学者结合边际收益递减模型研究二里头文化的衰落:宫殿的建造、奢侈品的投入和人口的增长导致生产资源和生存资源需求的扩大,以致资源紧张,尽管对外扩张获得资源可以暂时缓解这一内部压力,但同时也耗费一定的资源和劳力,实际上反而加重了资源的短缺情况,此外也加剧了与当地人群的矛盾,最终因统治者个人意识的强化,导致平民生存压力骤增,宗教系统也无法再维持对民众的精神制约,权力对民众失去约束,政治系统日益脆弱,自然无法应对外来力量的攻击,因此导致社会崩溃。此说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因资源需求开始向外扩张,符合二里头文化二、三期转型时的情况,但是在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并没有发现宗教系统多元化的证据,也未见其控制的资源区出现“反叛战乱”情况,相反,中央集权趋势则进一步加强,文化依旧处于兴盛期。所以纵观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政治韧性表现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礼制文化的不断完善与向外辐射,尤其是以礼制文化为核心的外交策略。笔者认为这是二里头文化在百年左右便由二、三期之交的兴盛转为四期晚段的衰亡的根本原因。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更强调祭祀功能。就现有发现而言,青铜器皆以酒器为主,即使是陶礼器也是以酒器为主。该文化统治阶层重视饮酒,一方面共同饮酒可以改善与其他文化贵族共同进餐之后建立的还不足够亲密的关系;另一方面,根据研究,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玉柄形器为瓒,圆陶片为漆觚底,是与爵一起在祼礼中成套使用以祭祀祖先的,此举既可以强调共同祖先的血缘关系,亦可增强自身的正统性。尽管也发现了青铜戈、钺、斧和箭镞,但就其材质与刃部使用情况而言,除箭镞外,其他近战武器均应属礼仪用器,所以青铜器的军事功能在二里头文化中并不突出。这也表现在二里头文化的聚落等级体系,即二里头文化的社会边界上。在都邑地区,只有宫城建立了城墙,且宫城内两组建筑基址几乎都是临墙而建,而非位于城内正中位置,所以城墙的意义更多是划分身份边界,防御功能为辅。二级聚落以望京楼和大师姑遗址最具代表性,但两座城址皆位于今郑州地区,所以对二里头都邑而言,其防御意义更像西周时期“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前沿重镇,而且这种情况仅限于东方。而三级聚落中,带有防御功能的城址主要以东下冯、西吴壁、南关等分布着丰富资源的地区为主,更像是控制资源生产、储藏与转运的中转站。
就二里头文化的文化边界来说,二里头文化的统治阶层似乎更偏好跨文化系统间的交流,以彰显其影响力与地位。作为定居农业文化系统的核心,二里头文化与半农半牧文化系统诸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半农半牧文化系统的聚落为多中心模式,如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石城在不同流域以不同比例出现,说明各个团体之间存在着冲突,也意味着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因此以大甸子遗址为代表的团体与二里头文化的紧密联系更有利于其在竞争加剧的团体环境中脱颖而出。但对于二里头文化而言,这种松散的政治联盟性质的互惠关系并非稳定可靠的同盟关系,尤其是对方仅是地方社会中的某一团体,而非统一的政治实体。
但对于同一文化系统内部的其他地方文化,二里头文化似乎并未通过这样的礼制文化外交策略建立互惠关系,这很可能与龙山文化崩溃后二里头文化作为“月明星稀”格局中的唯一强势存在有关。如与下七垣文化南部类型,“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在北到磁县以北、洛河附近的内丘南三歧遗址,南到漳河以南的安阳大寒遗址、西到祀县鹿台岗遗址漳河型先商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器。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安阳梅园庄和杞县鹿台岗遗址漳河型先商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器,似乎表明二里头文化影响波及的范围向南回缩”,这样的文化渗透应是社会下层人群的迁徙与移动造成的,而非统治阶层所建立的政治联系。
因此根据现有材料,可以将二里头文化统治阶层采用的外交策略归纳为“亲远疏近”,即远交牵制近邻,但其形式是一种基于互惠的软实力文化扩张,而非武力压迫。这种松散的远交策略并没有对二里头文化产生实质性的保护作用,在二里头文化遭受侵略时,半农半牧文化系统的诸文化非但没能为二里头文化起到牵制作用并提供保护,反而很可能是逼迫下七垣文化南迁的动因,从而最终导致二里头文化的崩溃与灭亡。
三、余 论
二里头文化后,二里岗文化以郑州城为中心,向周围急剧扩张。就陶器而言,“无论是中心地的伊洛—郑州地区,还是周边的山西省西南部,豫北地区,其在二里头时代都是拥有不同特征陶器组合形式的地区。而进入二里岗时代以后均出现了高度的共通性”。虽然在陶器上也可以观察到二里头社会的文化韧性——“在中心地区的遗址中还发现了属于漳河系形态的深腹盆”依旧沿用伊洛系常用的修整方法,但最终还是为二里岗文化高度统一的标准化陶器所取代。而郑州城、偃师城、望京楼、大师姑、焦作府城、古城南关、东下冯以及盘龙城等城址,大都处于水陆交通的要冲,同时在筑城技术和布局上更注重军事防御能力。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二里岗文化在其开始阶段就以陶器高度的同一性和筑城防御的策略展开强硬的扩张态势,这与二里头文化的扩张模式完全相反。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二里岗文化的统治阶层吸取了二里头文化“疲软”的外交策略导致社会崩溃的教训?就短期效果而言,以武力先行、再进行文化扩张的二里岗模式比二里头模式更为成功,但就长远来看,二里岗文化终究未能摆脱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始终以礼制文化维护其统治秩序,而且其礼制文化为之后的周人所继承,并最终形成古代中国礼制文化的大传统。
本文仅基于考古材料的发现建构二里头文化的社会转型和崩溃,以尝试摆脱文献本位的阐释模式。正如徐良高先生所言:“模式是多元的,对考古发现的解读和对历史叙述的建构也应该是多元的……二里头文化下一步的研究应该更加开放、多元,除了来自传统文献的夏商周王朝体系,还应该有多视角、多层面的解读与建构。”因此,对二里头文化与同时代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任重而道远,应更多地借鉴、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不断丰富我们对当时社会的认识。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许宏先生、徐良高先生和秦小丽先生的指导,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