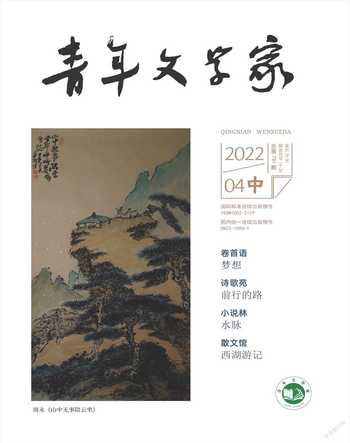浅析李商隐对屈原、杜甫诗歌艺术的接受
王杰


朱长孺曾说:“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张采田也说:“李商隐诗,拓于楚辞。”可见,李商隐特有的诗歌风格不仅与自己的经历、情感有关,也多与前人的创作心态密切相关,但很明显,其诗歌受屈原、杜甫的影响较多。李商隐诗歌中典雅精丽的语言、瑰丽雄奇的想象、情致的哲理性阐释、比兴手法和神话的运用都是接受了屈原诗歌的艺术手法,而忧生念乱、爱国爱民的思想和揭露腐朽政治的批判精神,以及情感深厚、气势飞动、诗律严谨的律诗创作风格则是来源于杜甫。
一、李商隐对屈原诗歌艺术的继承
比兴象征是屈原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总览其诗歌,此艺术技巧的运用是诗人内心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纵观李商隐的诗歌,其在抒情的诗篇中熔铸“真情”并进行哲理化的阐发,借“香草美人”意象寄情深远、善用比兴、巧用神话等表现特征都是继承了屈原的诗歌创作手法。李商隐在《谢河东公和诗启》中曾说:“某前因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阳,聊裁短什。盖以徘徊胜境,顾慕良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香草美人”是屈原诗歌中的代表形象,象征其高洁自守的品德,江蓠、木兰、芰荷、芙蓉等幽花香草也被诗人作为比托,与秽花杂草形成对比,以表达诗人内心对高贵纯洁君子的赞美和对丑恶小人的不满,同时还借助美丽瑰奇的想象和华美纷呈的神话典故来抒发其内心的哀怨之情和矢志报国的爱国精神。很显然李商隐提及的“芳草”“美人”意象在诗中是有所寄寓的,这实际就是他对比兴手法的继承,对屈原象征艺术的接受。李商隐虽然明确提到“芳草”“美人”意象,但没有谈论过对比兴象征手法的运用,不过从其诗歌创作中可见,李商隐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仍有例可援,清代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也曾言:“义山诗寓意俱远,以丽句影出,实自楚辞来。”李商隐运用的比兴手法,并不是单纯的比托,而是建立在真实情感不得不发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并运用哲理加以阐释,在继承屈原“疾痛惨惮”感情的同时形成了朦胧多义、情深词婉的诗风。
例如,李商隐的《梓州罢吟寄同舍》中“楚雨含情皆有托”一句就表明,诗人认为只有感情真实强烈,然后才能有所寄托。再如,李商隐的组诗《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和《无题·闻道阊门萼绿华》两首,目前学界对这组诗的理解聚讼纷纭,对君臣遇合、窥家姬贵妾、追想京华游宴等说法各执己见。但不论作者内心的真实想法为何,诗中渗透的难以如愿的怅惘之情和萧索孤独的情景之慨都是诗人身不由己的表达。错综跳跃的意象和深挚缠绵的感情被诗人巧妙地化入诗句中,既抒发了内心的“离忧”之感又不失语言的优美自然。
李商隐多首诗作中表达的情感与屈原诗歌中饱经忧患、爱国恤民的情致相差无几,他有善感多叹的困恼,也有坚定执着的情思,更有九死未悔的决意。例如《暮秋独游曲江》,此诗赋中寓比,给予荷叶以人的情感,将其化为多情之物,以荷叶春生秋枯的生长变化来传达其内心感情和人生感叹,曲尽其妙地诉说自己至死不渝的爱情。文字上的回环往复使诗歌在格調上别具民间风味,读来自有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情韵。结尾以景结束,闻声起哀,触景伤情,同时运用通感,视觉、听觉和感觉互通,引发了诗人对红尘客梦的追忆、往事难追的怅恨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嗟叹,最后虽戛然而止,却有曲江流水悠悠不尽之势。
诗人不仅自己内心饱含深情,还赋予宇宙万物款款情意,在李商隐的笔下,似乎天地间的事物都是蔼然可亲、脉脉含情的。例如《二月二日》,全诗以乐景写哀情,以春景的妍丽反衬自我身世的凄楚,以明快流转的笔调抒发郁塞难舒的情绪,以清丽委婉的语言表现辗转迤逦的情思,乐景哀思相辅相成,更增内心的愁苦。诗人又赋予花、柳、蜂、蝶等动植物多情善感的特质,如同屈原赋予“香草美人”高洁的品质一般,乐境愁思跃然纸上。
神话作为一种民间文学,饱含了原始民族对超能力的崇拜、对自然的理解与想象,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神话中天马行空的想象被儒家本能地排斥,却被李商隐本能地吸收,成为其诗歌内容的素材,而李商隐诗中运用的神话渊源正与屈原一致,大都是未被儒家改造的原生态神话。李商隐笔下的神话采用中性的叙述策略,没有明确的政治伦理性,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反而更加自由,读者可以不断地从问答中寻找某种动态的平衡,使解读结果循环往复、生生不已。
众所周知,屈原诗歌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这与其选用的神话题材密切相关。纵观诗篇,李商隐所化用的神话颇有悲剧感,抒情诗句所具有的措辞深婉、黯然孤寂的特点与其运用的神话传说也是分不开的。例如,“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一句,借刘晨艳遇的传说,点明爱情阻隔,“已恨”“更隔”层递而进,加深了阻隔无法度越的无奈,表达了男子对身处天涯海角的情人的深切思念之情。再如,“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银河吹笙》),诗句连用“缑山”“湘瑟”两个典故,由《楚辞》中“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一句化出,表现了诗人对真挚情感的执着追求,对贤良亡妻的沉痛怀念,感人肺腑。再如,“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一句,运用“蓬山”“青鸟”的神话传说,抒写诗人对爱人的深沉情思和绵绵情意。尽管学界目前对这首诗的理解存在争议,但不论是陈情求荐的渴望还是肝肠寸断的失恋,诗句字里行间透出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痴情苦意和深沉感叹都是诗人内心深处真实情感的写照。
李商隐抒情诗中神话的采用并非《离骚》一般带有儒家政治伦理性的特点,而是《九歌》一般更具原始性,既非政治也无爱情,是对某种终极性事物的炽热渴求以及由追求的缥缈而生发的无可奈何的怅惘。不论是在神话的运用上还是在神话题材的选择上,李商隐的诗歌和屈原的《九歌》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马茂元也曾说:“在《九歌》的轻歌微吟中却透露了一种似乎很微漠的而又是不可掩抑的深长的感伤情绪。”“隐隐约约地笼罩着一层从生活深处发散出来的忧愁幽思,感伤迟暮的气息。”这一评论甚至可以视为李商隐的诗歌点评。在李商隐的诗歌中,意象因典故神话而华美繁丽,营造的氛围因神话而柔婉缱绻,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因神话更有共鸣感、空间感,诗歌也更具生命表现力。
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婉转沉挚的表达方式,千锤百炼的艺术构思,借景托情、驱遣想象、化实为虚的表现手法,以及措辞深婉、善用典故、朦胧隐约的艺术特征构成了李商隐诗歌独特的艺术风格,给人以意境空灵、索解无端、余味无穷之感。
二、李商隐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接受
李商隐对杜甫诗歌的借鉴和继承,前代学者不乏精深的见解,王安石曾盛赞“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多数学者也都认同:唐代真正学到杜诗精髓的,当为李商隐。
李商隐首先继承的便是杜甫忧生念乱、爱国爱民的思想和揭露腐朽政治的批判精神。身逢乱世、命运多舛、忧国忧民的心态和怀才难遇的压抑,使李商隐的诗颇有浓重的沉郁之气,这种诗歌基调,本是杜甫特有,也成为李商隐诗歌散发浓郁馨香的原因之一。李商隐流传的诗歌中,题材触及时政的,占有相当比重,这些诗歌也如杜诗一般具有反映广泛、开掘深刻等特点。甘露之变后,李商隐写下《重有感》(诗人曾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故题曰重),全篇情词激越、忧深盼切,一气呵成、喷薄而出,诗的神理气脉与杜甫议论时局、指摘将帅的《诸将》极为相似。《重有感》和《有感二首》记叙了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对宦官幽禁皇帝、屠杀士人百姓的暴力行为痛加抨击,表现出诗人不凡的政治胆略。在《随师东》中,李商隐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忠奸不分,纲纪废弛是藩镇割据形成存在的关键原因,“积骸成莽阵云深”一句,更是形象地描绘出沧、景地区战后的凄惨景象,颇有杜甫的诗风。
再如《曲江》一诗,李商隐的创作构想深受杜诗《哀江头》的启发,曲江作为唐代著名的皇家园林,见证了唐王朝的盛衰兴废,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萧瑟荒凉的景象抒发家国残败的感慨,颇具浓重悲凉的时代色彩,面对颓壁残垣的曲江,李商隐也自然而然发出了相似的喟叹。《曲江》诗句化用华亭鹤唳、泣铜驼的典故暗示事变期间宦官大肆杀戮朝廷官员和禁军士兵的历史真相。末联全篇结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甘露之变尽管痛心刻骨,但更加令诗人悲痛的却是唐王朝衰颓凋敝的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的目光没有局限在事件本身,而是深入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地意识到事件背后所反映的不可阻挡的事势趋向,这正是此诗情感意义更加冷峻、深刻的原因,也是风格更加深广、沉厚的关键。
七律是唐代的新体格律诗,真正把七律从各方面建设起来的是杜甫,而以律体反映时政、抒发感慨,正是杜诗的优良传统,李商隐则直接继承了这一点。从艺术渊源看,李商隐主要学习杜甫入蜀以后的七律,将雄浑壮阔的境界、工整严谨的格律和仁民爱物的情怀相融合,从而形成了音韵铿锵、沉郁悲凉、锻炼精粹、属对工切、情韵深长、章法精妙的诗歌特色。一般而言,律诗讲究浑古凝厚又重流转自如,这既是优点又是难处。怎样才能在厚重中见流动,杜甫的诗歌中便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其中虚词的锤炼和运用是一法。如杜甫(《诸将五首》其二)将“本意”“拟绝”“岂谓”“翻然”“不觉”“犹闻”“独使”“何以”等虚词斡旋诗中,因而显得兴会尽致,颇具雄浑奔放的气势。再如“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等句都是巧用虚词、感情激荡而笔触熨贴入微,是极为成功的范例。
李商隐对虚词的锤炼和运用亦有深刻的体会,且手法精湛。他的咏史诗《隋宫》中“不缘”“应是”“于今”“终古”“若逢”“岂宜”等虚词的运用使全诗流转自然、用笔灵活、语气跳脱,读来如一篇流畅隽永的散文。纪晌曾说此诗“纯用衬贴活变之笔,无复排偶之迹”“跌宕生动之极”。李商隐以虚词转折唱叹的诗句很多,如“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等,大都锤炼和运用虚词。后人评李商隐的七律多赞其“一气灌注”“一气鼓荡”“一气喷薄而出”,都是看到了他在整首诗律中能做到厚重中见流走,流走而又亦不失飘举的优点。
李商隐的七律,多是苦心精刻之作,细致周密而富有变化,从谋篇、炼句、铸境等方面都能见其匠心,而思力的沉厚更是得杜律之妙。李商隐的《杜工部蜀中离席》是诗人刻意拟杜之作,此诗将抒情、叙事相融合,苍劲雄浑,沉郁顿挫,情韵深厚,笔力极为老成,与杜甫感慨身世的《登楼》《恨别》等七律相比毫不逊色,而尤神肖《登楼》。李商隐学杜绝不是袭貌遗神,也不是个别诗句的酷肖逼似。
杜甫诗歌中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心态、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和忧国忧民的深沉思想是哺育李商隐强烈历史责任感的关键,也是其学杜最着力之处。罗宗强先生曾深刻指出:“李商隐之与杜甫有相似之處,实不在写法,而在情思沉郁上。”情思沉郁正体现了两位诗人在创作精神上的高度契合。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成就,离不开对前人的广泛学习,愤悱恻怆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表现手法源自屈原,伤时忧国的怀抱和精严顿挫的律体承自杜甫,转折深层的构思方式启自李贺,词旨隐晦的作风取自阮籍,而清新流丽的语言显然脱胎于六朝民歌和齐梁文人诗。屈原、杜甫、李贺、阮籍等都是在诗歌长河中的著名诗人,如此大家,效仿其一,得几分颜色,已十分不易,况且兼学多人仍得神韵,这样不可思议的目标,竟在李商隐这里实现。李商隐没有机械地学步前人,而是温故知新,将前辈的宝贵经验熔铸到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在才人代出、难以为继的诗国高潮后,独辟蹊径,开拓出寄情深婉的新境界,成为唐代诗坛上异军突起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