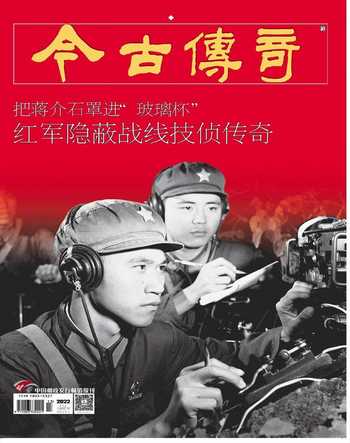军委二局 无线电技侦英雄群体奏响革命凯歌



1931年冬,曾希圣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次年,曾希圣参与创建中共中央军委二局,被任命为该局首任局长兼红一方面军二局局长,为后来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提供了大量准确情报。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曾希圣和他领导的二局,多次截获并破译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密码,为保障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二局,称“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神秘莫测的二局用信念走完长征
“红星纵队二大队”隐藏在历史长河七十年。大家只知道部队的番号,不知道他们的任务、战斗成果,更不知道他们曾为党中央提供快速、及时情报的历史事实。
这些红军将士跟着红军大部队穿草鞋、吃野菜、爬雪山、过草地;他们抬着沉重的发电机、收发报机,每日强行军上百里;他们不分昼夜接力开机,不间断地捕捉空中的无线电信号,当好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
邹毕兆回忆:“长征途中,二局同志都是行军时走路,到宿营地就截取敌人的密码情报,有时连续工作,直到第二天部队出发,他们的睡眠时间是极少的。有时,我边走边睡,常常跌跟头。为了不中断收取当面敌人的电报,二局常要分前后梯队行进。”
侦收员李行律回忆:
红军长征期间,我是做无线电报务工作的,这个工作在行军中比一般的工作辛苦。我每天要比部队早出发三四小时,凌晨两三点钟就出发;或者是晚出发三四小时,等部队走完之后才出发。即使是在过雪山、草地时,我晚上也必须通宵工作,每天平均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
长征时期的环境恶劣,生活极其艰苦,但战士们的思想却非常纯洁健康。当时我们没有什么杂乱思想,只知道跟着部队前进,死也得跟着,从没有想到过脱离部队之类的事情。
那时,我虽尚未透彻认识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和光明的远景,但是确信跟着红军走是唯一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对个别不坚定的份子中途脱离革命开小差的事情,我表示极大的鄙视。
侦收员贺俊侦回忆:
长征中,军委一局、二局、三局和机要科等部门一起编在军委红星纵队第一梯队的序列中,与军委首长一起行军。为了不漏掉敌情,二局的20余位报务员24小时守机工作。他们将工作人员组成小分队,小分队每天要提前三四个小时出发,走40里就开始架机器工作,直到后面的大部队到达,然后由另外一个人接着工作,一直到大部队走后一个小时,再撤机追赶大部队。到了晚上,他们碰头交换情况,这就是所谓的“接力赛二部制”。我和战友们用“接力赛跑二部制”,对国民党师以上电台进行严密监控。
由于连日挨饿,我发了三天三夜的高烧,浑身没有劲。此时,钱江(红军战士)为了照顾我,渐渐掉队了。休息的时候,钱江在附近的庄稼地里找到点谷子,用石头将谷粒压碎并煮了一碗粥。两三天没有吃饭的我喝了这碗粥顿时有了力气,于是我们一起奋力追上了大部队。
红军四渡赤水时,在贵州转战三个多月。由于没有口粮、蔬菜、油盐补充,天天都要行军打仗、饥寒交迫的红军将士面容憔悴、骨瘦如柴。
据曹冶、伍星两位教授记述:
曹祥仁不分昼夜地工作和行军,体力严重透支。曾希圣总把马让给曹祥仁骑,他总是让给体弱、生病的同志。
一天,曹祥仁终于跑不动,无力跟上疾行的队伍了。他拖着虚弱的身躯,跑一阵歇一阵。天色渐暗,大队越离越远,已经能看到村旁地主民团手中闪动的火把。这些残忍的武装民团见到负伤和掉队的红军,不由分说地捅红军一刀。
曹祥仁想:坏了,我这下大概要完了。正在此时,路上传来了马蹄声,原来是红3军团老8军4师的黄克诚主任来了。黄克诚见到躺在路旁的曹祥仁,立刻把他扶上马,驮着他向前走。半路上,他们遇到一位走不动的团长,那位团长跪下来哀求:“老表,你行行好,驮我一段吧!”两难之中,黄克诚硬下心来,驮着曹祥仁继续赶路。
在黄克诚的救助下,曹祥仁总算赶上了大队。曹祥仁后来多次回忆这段经历,总要伤感地说:那个团长多半是被民团杀了。
准确及时的技侦情报,加快了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进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对经过长征考验的二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一再称赞: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
曾在曾希圣身边工作的邓伟志回忆:“毛主席对曾希圣所领导的二局评价是:‘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这是对二局侦察技术情报工作的最高褒奖。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二局的工作十分重视,对二局人员的安全和生活关怀备至。红军进入甘南地区,敌情复杂,毛泽东亲自向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交待:“要保证二局的绝对安全,一个人也不能丢。”
红军视二局为革命的“宝贝”。每天队伍出发时,左权都亲自站在路边,检查队列,清点人数,直到二局人员全部走完了,才动身去追赶部队。朱德亲自给二局加夜餐,行军中毛泽东的担架经常抬着二局的病号。长征时,红军的生活条件比在苏区时艰苦不少,但是红军的首长们力所能及地给这几个搞破译的年轻人一些照顾,给“破译三杰”配了两匹马。在行军的时候,他们可以在马上稍微睡一会儿。
贺俊侦回忆:“1935年6月,红军快到达川西天全地區时,遭到6架敌机的轮番扫射,雷永通(红军战士)的小腿被炸开一个铜钱大小的洞,鲜血直流。当时,我和二局战友李力田按着雷永通的身体,协助傅连暲医生给他处理伤口。由于没有麻药,雷永通疼得浑身直抖。包扎完毕后,曾希圣局长让大家找材料做担架。这时毛主席过来了,他用手轻轻拍了拍雷永通,让警卫员去把他的担架找来。贺俊侦把雷永通抱起,移到了担架上,一直到雷永通可以骑牲口了,才把担架送还毛主席。”
毛泽东从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就亲自管理军委机要科的工作,亲自批阅与抄写电报并在机要科过党支部生活。他经常亲临二局,与二局的同志交往密切。鲁迅从上海给毛泽东送了些腊肉,他把腊肉分给了曾希圣。
毛泽东两次为二局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周恩来也曾为二局题词:“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所有的技术,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这些意味深长的表扬,真实地反映了红军信息技术人员在毛泽东等领导人心中的地位,更反映了红军中科技人才通过使用现代信息手段,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邹毕兆在回忆录中写到:
周副主席几乎了解二局的每一个同志,还和同志们下棋,做过二局不少同志的思想工作。他对二局工作,一直是满意的;对二局的需要,一直是支持的。凡是二局提出来的问题,他都尽可能解决。他常对我们讲:“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二局的侦破对象必然要扩大,对技术要求更高,人员一定要多,而且要用最先进的设备武装起来。”
朱德总司令更是对情报工作情有独钟。他在黎川时,几乎天天到二局来。1931年我刚到二局时,抄收了一份残缺的电报,无头无尾,认为不能通报,没有送译。接班的同志送去翻译了,恰巧有要紧的内容。为此,朱总司令找我交代说:“今后抄收的残报要一律送译,哪怕一个字也不要丢掉。”他几乎有空就来,还经常给二局同志讲课、作报告,和二局同志们打篮球。
任弼时誉称这支特殊的部队为:“红军的密码脑袋。”
彭德怀曾说:“凭着二局出色的侦察工作,红军才免于全军覆没,到达陕北。”
叶剑英1975年回忆长征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十分清楚,有了二局及时的军事情报,我们才能指挥英明,机动灵活,多谋善断,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调去,就像放在手中玩那样。”
红军破译国民党军密码1050个,而国民党军破译红军密码数却是0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破译国民党军密码1050个,而国民党军破译红军密码数却是0。数以万亿的密电是红军的“生死大命脉”。为什么国民党军一个也不能破译呢?关键在于三点。
第一,红军密电码的设计非常先进。
1933年,蒋介石亲自下令在自己的侍从室组建了专门破译密电的机构,让他手下密码破译第一干将黄季弼破译红军密电。
8月24日,黄季弼埋头苦干了两个多月,沮丧地报告:“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察其情形,匪方对于电报之打法译法与及密本之编制法,均属精细周密,甚有心得。细查所得赤匪各报,其内容自首至尾均用密码,似系以号码数目替代密本之名称,其译电法似系引用复译法编成表式,百数十张随時按表将密本之大小码变换。故密本究竟共有若干种,每种用若干时日,及何时更换,均无从分析。”
第二,红军隐蔽战线工作人员纪律严明,与密码共存亡。
中国共产党的机要人员有一个誓词:“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方志敏的红10军团在怀玉山覆没,当时的报务员张文才夫妇在国民党军队冲到发报机所在的小屋之前,来不及销毁密码,干脆把密码直接吞进嘴里。两个人一面抵抗,一面砸机器,在敌人冲进来的时候,二人都牺牲了。国民党军从他们两个人的嘴里掏出来一些密码碎片,这些碎片已经沾满鲜血,无法辨认。
第三,红军隐蔽战线工作人员不仅有铁的信念、铁的纪律,而且有铁的担当。
1939年2月,曾希圣由延安来到重庆,被安排在南方局军事组工作。随着曾希圣的到来,八路军办事处也开辟了对敌特机关的特殊情报工作。
蒋介石虽然被逼抗日,但处心积虑想要消灭共产党,指使军统破译南方局的密码电报。为破译八路军办事处的密码电报,国民党特务在红岩村周围架设了侦收台,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可始终没有什么进展。
1942年,戴笠(时任国民政府情治机关军统局副局长)聘请了美国破译专家雅德利来指导。
据当时从事破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军统人员张成信回忆:“中共驻重庆延安间,使用的密码有周期性、固定性,容易出现破绽。”戴笠欣喜若狂,对这些破译人员给予优厚奖励,发给他们藏青色中山服、皮鞋,还从美国搞来“维他命丸”给他们滋补服用。殊不知,这些让戴笠视若珍宝的“情报”,实际上是南方局机要人员主动抛出来的诱饵。
原来,为保护核心密码的安全,中共对国民党破译活动采取了“以假报掩护真报、以外围掩护核心”的办法,即:故意使用一些简单的密码来拍发战报等一般性消息,吸引特务机关集中力量来破译,以保证通报机密事项使用的高级密码的安全。军统能够破译的只有《大公报》《救国日报》上的社论或社会新闻。
原南方局秘书处长童小鹏回忆:“虽然国民党的破译机关把我们的电码都抄收下来,并且请了许多破译专家、数学专家进行破译,但我们的密码没有被破开过。”
红军和其他军队在密电破译方面横向对比
太平洋战争中,情报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有8万人投入与密码相关的工作,相当于四个甲种师团的人数。后来美国利用计算机破译了日本的“紫密”密码,在中途岛海战给日军致命一击。
美国密码史学家戴维·卡恩说:“除了原子弹外,‘超级情报的存在是整个二战中最重要的秘密。这件事的保密程度仅低于原子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贫穷孱弱,基本没有工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侦察部队。
1927年11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周恩来续任军委书记,并筹建中央特科。随着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李强的秘密电台研制成功,周恩来亲手编制的共产党第一部密码“豪密”的启用,以及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结业,中共不仅有了第一座电台、第一部密码,而且无线电队伍不断扩大。
红军没有国际先进的恩格尼码、“图灵炸弹”机、“巨人”机,却能够破译敌军所有密电,在蒋介石百万大军“围剿”下,成功地运用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手段,扭转了战争危局,夺取了战略主动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作出了重大贡献。
把中国工农红军这段光辉历史,放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密码战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研究,就会更深层次地学习和理解红军破译国民党军密电留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
没有机械、电力基础,长年在高山大峒奋战的中国工农红军,破译了当时蒋介石中央军、各省军阀军队“所有密电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二战时英国有近2000名操作人员、211台“炸弹”,这些机器24小时运转,却只破译了90%的德军密电。
情報的第一价值在于速度。长征中,红军总司令部比敌军将领更早看到被破译的蒋介石的手令、密电。
曹祥仁、邹毕兆经过反复练习,拿起密电数码,立即就能在脑海里变换成汉字,直接报出密电内容,而此时国民党军还在收发电报、校对、对照密码本译电。
有了这样的对比,就能对“没有二局,长征胜利是难以想象的”这句话有更深的体会。
邹毕兆将中央红军破译工作成果详细记录在《心血的贡献》一书中。1942年3月,邹毕兆离开二局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将《心血的贡献》交由曹祥仁保管。解放战争时期,曹祥仁又把它转交给接替他职务的彭富九。
原总参三部部长、政委彭富九说:“邹毕兆亲手记录的登记本,完整地记录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破开的所有密码,邹毕兆同志还给它取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心血的贡献》。建国后,我把这个见证技侦创业史的珍贵小本子交给保密室,现已成为技侦档案的‘镇馆之宝。”
中革军委二局是难得一见的无线电技术侦察英雄群体,是共产党打造的高科技战斗堡垒。总参三部档案馆镇馆之宝《心血的贡献》,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掌握“制信息权”的真实纪录。
(来源/《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朱德军事文选》,朱德著,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吕黎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刘统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曹冶、伍星著,时代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等)
责任编辑/王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