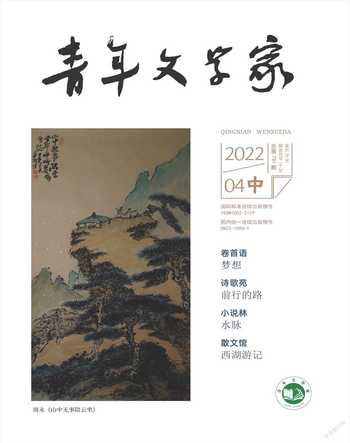念念
冬梅


姑 嫂
“咳、咳、咳……呸……咳、咳、咳……呸。”舅姥姥咳了老半天,拿起个大茶缸子,张口把痰吐在里面。她是齁巴,就是气管炎,我姥姥也是齁巴。她们说,都是年轻时候被自个儿男人气的。
舅姥姥家就在姥姥家后院,她是姥姥的嫂子,她们的男人早早就没有了。这姑嫂二人,前后院一块儿住了几十年。一人拉扯一大帮儿女,到老了,又都享到了儿子和闺女的福。
从前的事,谁也没看见什么样,若说知道一点,都是姥姥碎嘴子的时候,嘟囔出来的。
有时候,大白天的,没事情做,我和姥姥坐在炕上,她用碎布拼拼凑凑缝坐垫,缝累了,就讲她年轻时候的事儿:“我呀,可怜着呢!八岁没妈,十四岁沒爹,落在哥哥、嫂子手里。”我问她:“那你妈呢?”“死了呗!她身上来了(月经)就不走,躺炕上半年。那天后院柴垛一场大火,烧了半个家,她一股火上来,就窝囊死了。”我叹了口气:“你和我一样,都没有妈!”她可不兴我这样误解我妈,她一着急就气喘:“你可不是没有妈,你妈在城里好好的呢。别没良心,每个月,那大苹果,是谁给你捎来的?小没良心的!”
她喘起来,非得找茶碱片顶一顶,那么长一帘茶碱片,她就压在炕席底下。
她喘完了,接着嘟囔:“我那嫂子,你舅姥姥,年轻时,可没少给我气受。”我问她:“咋给你气受的?”“才十四,就叫我做饭、洗衣服、喂猪,喂鸡,带孩子,除了下地干活,啥都得干,没爹没娘的孩子,谁疼呢!”
她讲的事情,按理应该很痛苦,可她的语气和表情,又像说着玩似的,好像无论一件再怎么痛的事,时间长了,都能当玩笑讲了。
我问她:“那你怎么不恨她?”她说:“咋不恨,恨起来,我都不想理你舅姥姥!”我说:“你骗人!你恨她,还天天上她家和那些老太太看小牌!”她说:“看小牌,也恨她!”
我不听她的了,从二舅妈的抽屉里翻出几块粉红色崭新的枕巾,系在腰上,蒙在头上,扭秧歌玩。扭得欢了,把枕巾踩在地上,踩得脏兮兮的,我又塞回抽屉里去了。中午,舅妈回家,发现了脏枕巾,生气了,就说我:“小老婆,净能祸害人!”姥姥生气了,拉着我,抬腿就走,往后院去,上舅姥姥家。
到了舅姥姥家,她往炕头上一坐,就气。舅姥姥又是“咳咳咳……呸”,吐完了,就说她:“齁巴不能生气,越生气越齁巴。”
这时候,舅姥姥的大儿媳妇,笑眯眯地走过来,问她:“老姑,不生气了,中午,我给你包酸菜馅大菜干粮吃!”姥姥对舅姥姥说:“你看你多有福,同样是媳妇儿,你家老大媳妇,从来不敢给你甩脸子看。”舅姥姥就笑她:“你呀,活一百岁,也是个急脾气,说来就来。”姥姥说:“咋的?我生气了,还不兴回娘家呀?到多大岁数,有你在,我也把这当娘家。”舅姥姥伸出干巴巴的手指点着姥姥:“小媳妇儿呀,一生气就回娘家!”
天晚了,姥姥也不回家,舅姥姥家的大儿媳妇又要张罗着做晚饭了。我二舅妈,怕我二舅回来说她,就心虚了,她搭讪着,也来了,一见门,就叫:“妈,我包了饺子,回家吃饭吧!”舅姥姥也赶紧说:“你二媳妇给你包饺子,我可不敢留你喽。”
姥姥也就顺着这个劲儿,拉上我,回家去了。
过不了几天,大天白日,她没事的时候,又会嘟囔着:“没爹没娘的孩子,谁疼呢,受了嫂子多少气谁知道呢……”
但是,等哪天,当她和儿女、儿媳赌气,抬腿就又上后院,到舅姥姥家去,说:“我不把这儿当娘家,把哪儿当娘家呢?”
洞 房
大石头哥,是舅姥姥的大孙子,小时候老是生病,取个贱名,图个好养活,什么最不值钱,就取什么名字,后来就取名叫大石头。
那一年三月,大石头哥定了亲,六月就盖了房,八月过了小礼,单等十月娶新媳妇过门了。
红砖青瓦的新房里什么都齐全了,新做的被褥,整整齐齐地码在炕柜上,枕头绣一个鸳鸯戏水,被褥缝一面金凤朝阳,门上挂一幅百年好合。炕上铺着新席,地上镶着新砖,灶上坐着新锅,院里堆着新柴。一对新人的好日子,眼看着就在眼前了。
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大石头哥本来在手工业作坊里做事,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人见人夸。可是,有一天,作坊里发现丢了三块钱。
三块钱不是小数目,干一个月也不过十块钱。于是,人们开始追查。查来查去,就查到大石头哥头上了。到最后,大家一致断定,是大石头偷了这三块钱。
作坊师傅,把大石头关在小黑屋子里盘问。从早上到晌午,从晌午到傍黑,一直问到了半夜里,也没问出个究竟。
作坊师傅急眼了,不叫大石头回家,不叫给他饭吃,不叫给他水喝。大石头开始一直在喊叫,叫屈,叫冤,叫得声嘶力竭了,渐渐就没了动静。家里因为他一夜没回,就寻到作坊来,一看大石头被关了起来,就不让劲了,一来二去,家里人和作坊里的徒弟们就打了起来。等他们打累了,才想起来,大石头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放出来一看,大石头缩在墙角,正抽着风呢。
从那以后,好好一个大石头哥,就得了抽风病。三块钱和人们的谣言,就把好好一个人给毁了。
大石头天天站在街上,穿着本来预备结婚穿的蓝衣裳,头上戴着蓝帽子,就像马上要当新郎官一样,时而清醒,时而疯癫,时而沉默,时而狂乱。
定下的姑娘,倒也没有那样心狠,也张罗着要给大石头看病。可是,在缺医少药的农村,一个身强力壮的人都说没就没,谁还会在意一个背着小偷名声的疯子呢。慢慢地,那姑娘就不再来了,半年后,她又寻到好人家远远地嫁了。
还有谁管这可怜的大石头哥呢!那间新房,因为不吉利,没人愿意住,归大石头了。那是大石头永远没有入得进去的洞房!
大石头一个人日夜守着他的新房,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偶尔,在他清醒的时刻,小房子里会传出悠扬的口琴声,那声音凄美又欢欣。淘气的孩子们听见,立即放下手中正飞舞的泥巴,驻足在窗外,静静地聆听。正路过扛着锄头的农人,也情不自禁地立住,享受片刻的安宁。出来搬柴烧饭的主妇,立在篱笆边上,忘记了抽柴草。所有经过的人,知道这个故事的,不知这个故事的,都情不自禁地聆听着。知道这个故事的,心里酸楚,叹息一声;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心里一软,忘了眼前的苦楚。
渐渐的,房子越来越旧,越来越下沉,像一个行将老去的人,直不起腰身了。大石头病得越来越重,一个人独自守着他的小屋,在他时而清楚,时而糊涂的意识里,却一直记着,那是他的洞房,里面有他的新媳妇儿。
煤 烟
大劈柴一个劲儿地往灶坑里扔,炕烧得烫屁股了,可北炕上的窗户,还是结着厚厚的冰花。
姥姥叫着:“二媳妇,弄盆炭火来吧。”
二舅妈找了一个破了洞的搪瓷脸盆子,扒拉了一堆炭火,还冒着烟,放在屋地中央。
傍黑的时候,姥姥迷迷糊糊地起不来了,她叫着:“让煤烟(一氧化碳)熏着了!”再一看我,干脆不动弹了。二舅妈打开了南北窗户通着风,左邻右舍都跑过来了,一群人围着醒不过来的我。
“这一冬,呛死好几个了。”有个招人烦的人说。
“让冷风吹一吹,不少都缓过来了。”有人赶紧安慰姥姥。
“这玩意儿可邪乎了,有的都装棺材了,还醒过来了呢。”
“只要没死透,就有救。”
一帮人,有用的没用的,一咋呼,我姥姥没了主意,号啕大哭起来:“姑娘蛋子呀,你要是有事,我也不能活了……”
后来,还是找来了大夫,人人都叫他“小迟子”,是村医。那时,他都四十多岁了,可全村老的少的,全都叫他小迟子。小迟子给我打了针,不长时间,我就醒了,开始呕吐,吐得到处都是。姥姥那么爱干净,这要在平时,准保又气得唠叨我。
一顿折腾,迟大夫问我:“你认得我是谁吗?”我说:“你是小迟子。”大伙都乐了。
姥姥紧着说:“好了就好,你想吃啥,姥给你整去。”
我说:“要吃酸菜心儿。”
二舅妈赶紧从结了冰碴儿的酸菜缸,捞出酸菜,扒了心儿送过来。
我说:“不许再把我妈捎来的大苹果锁箱子里了!”
姥姥赶紧说:“不锁了,让你一顿都造了。”
一屋子人,再也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
桲椤叶饼
转过年,春风一吹,大门上的红对子褪了色,一截枯树桩抽了新芽。鸡栏、猪圈、栅栏边,钻出绿茸茸的小草,猪食槽子、鸭食盆子里有了新采的灰灰菜、野苋菜、婆婆丁、水芹菜……
农历六月初六就在眼前了,女人们开始钻山采桲椤叶,要做桲椤叶饼啦。
姥姥家的房子是东西屋。西屋借给了杨家住着,两家共用一个外屋地。一家灶前一口锅,东一捆柴,西一捆柴,东边炒菜,西边也香。谁家做了好吃的,都盛了上尖一大碗,端过来,于是推让、道谢,唠上一阵子,唠得菜都凉了,还在唠着。
杨家姑娘,脸红扑扑的,爱搽胭粉。她坐在小炕桌前,对着镜子照,用烧黑了一头的柴火棍描眉,铁丝做的火钳子烧热了卷刘海。她妈气哼哼在外屋嘟囔:“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个愁。”
二舅妈早早就买了猪肥膘,炼了油,把油梭子(油渣)搁在高高的碗柜顶上,怕狗扒拉,怕馋嘴的孩子偷吃。桲椤叶采回来,又大又鲜,玉米面加淀粉,开水烫面。“咣咣咣”,菜板子上剁碎了豆角,和上油梭子拌馅,一片叶子摊一层面,做成一个饼子,一个饼子像一本书。
可杨家的女人,还没动手,山上就传来了消息。几个上山采桲椤叶的女人,在一棵桲椤树上,发现了吊死的杨家姑娘。
灵棚就搭在院子里,一样的有灵幡、火盆、供桌、棺材,一样的人来人往,吵嚷闹腾。死了人,却是热闹的。村里人都来了,几个女人哭红了眼,在一边小声议论。
“听说,她上吊前脱下了毛衣毛裤。”
“迷信讲话儿,穿了带毛的死,来世就托生成带毛的了。”
“这孩子,临死,也不糊涂啊。”
“为了啥呀,好好个大姑娘,都十八了。”
“听说,是搞对象,她妈不同意。”
“唉,傻呀,这个傻孩子啊。”
二舅妈把一盆桲椤叶饼放在供桌上说:“别饿着上路啊。”
天不亮,棺材就抬上山了。横死(非正常死亡)的人不吉利,不能进祖坟,可埋在哪儿呢?满山都是桲椤树(柞树),就埋在桲椤树底下吧!
春风年年吹来,桲椤树叶年年绿,可是,有一个和桲椤叶饼有关的故事,却是那么心酸……
桦皮村二姨
傍黑了,我玩累了,拉开姥姥家那道沉沉的木门往屋里跑。
我一骨碌就爬上了炕,连鞋都不脱,却看见桦皮村的二姨,正坐在炕沿上笑。她一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露出一嘴黑牙。
二姨是姥姥的外甥女,管姥姥叫老姨。她刚从桦皮村来,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翻出里面粉紫色的秋衣领子,脚上穿一双黄色的胶鞋。姥姥说,她们家上镇里,就这一套好行头,谁来谁穿。
二舅妈帮她把绑在背上的孩子往下解。那根不知用了几代的老式背带,绣的花都褪了色。那么长的绑带,绑得可结实,好不容易把孩子解下来。二舅妈心眼好,对亲戚认亲,谁来她都满招待。那孩子憋不住尿了二舅妈一身,二舅妈一边笑,一边拍着孩子开裆裤里露出来的小屁股说:“你是想看看我湿(实)交不湿(实)交(与人交往是不是实心实意),是不是,嗯?”
二姨拎着个柳条筐,里面放了些鸡蛋,用碎稻草盖着,还有一包她种的黄烟。她从兜里摸出个旱烟包,卷上一根旱烟点着了,老旱烟又呛又辣,把她的牙都染黑了。她说话爱咧着嘴儿,拖着长音儿,就像她慢吞吞的好性子:“老高一分钱也不给我,没招儿了,我攒几只鸡,上集卖了,还有我自个儿种的黄烟。两只脚走了几十里地,从中午走到这时候才到。”
炕烧得滋滋热,摆上一张用得发黑的炕桌,大饭盆先端上来,炖大豆腐,酱缸咸菜,都是农村饭菜。吃饭了,二舅妈特意给二姨盛了满满一碗大米饭。
姥姥气她软性子,不敢和男人硬气,但又可怜她,没了第一个丈夫,找了这个后男人尽受气。姥姥说:“管夠了吃!常年啃苞米面大饼子,你们家那‘高小扣儿,留着细粮卖钱,卖的钱啊,到不了你手吧?是不都给先头娘们儿生的孩子攒着呢?看你个没用的样儿,人家说,二房香,二房香,没看人家把你怎么香香。”二姨光知道咧个嘴乐,露出一嘴黑牙。
晚上,二姨带着孩子睡炕梢,把老猫挤到箱盖上去了,半夜,老猫冻得又跳下来,钻二姨被窝里去了。
第二天在大集上,有熟人看见二姨,都很惊异:“哎呀,丁二花,你咋变这样了?看头发白的!你才不到四十岁吧?”
“你咋穿了身男人衣裳上集呀?”
“这黄烟,家家都有,拿集上,没人要哇。”
二姨咧着嘴笑,可眉头却是蹙的,一种像胃疼的表情僵在脸上。
这帮农村人,又在背后讲。
“原来人长得多俊。”
“就是,看看现在累得,没个人样儿了。”
“白长个好模样,偏偏没有心眼儿,什么都听别人的,自个连个主意都没有。”
“就是,头一个男人死了,也没孩子,找啥样的找不着,偏听她哥的,找了这个拖着两个孩子的‘高小扣儿。”
“唉,这都是命啊。”
赶完集,二姨要趁着天亮往回走了。二舅妈给她装了半柳条筐大米,姥姥给她塞了十块钱,她还是那样咧着嘴,像胃疼的表情:“还是我老姨疼我。”
二姨走了,穿着男人的衣裳,男人的鞋,身上绑着沉重的孩子,迈开像男人的脚步。她走得快极了,那花白的齐耳短发,从后面望去,就是一个老太太了。
同样的情节,一直都没变过,二姨每次来,都是老样子。可能,就像人的命一样,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吧。
一只银耳环
从小,我就爱翻姥姥的箱笼屉柜,老想找到点值钱的东西,可是连一粒珠翠,一点金银也不曾见过。
简朴的姥姥,总是灰衣蓝褂,干净清爽。她的衣衫,她的鞋袜,她的面庞,她的头发,和农村老太太一样,没有一点颜色,永远是灰扑扑的。
她一辈子不离身的,就是干活,她永远是忙碌的样子。到了晚年,她不能下田了,就拾掇房间,就缝缝补补,打开任何的箱笼屉柜,都收拾得整整齐齐。
意外地,我在一个桦皮笸箩里,竟然找到了一只银耳环。那是一只式样普通的耳环,就是一个圆环。它和一些纽扣放在一处,灰暗得没有了光彩。可是另一只呢?姥姥说:“掉了,不知道掉在哪儿了。”
那是她成亲时唯一的首饰。耳环丢失的时候,正是姥爷出事的时候。
那时,姥姥怕姥爷出意外,每天对他寸步不离。可是,有一天午后,她从河边回来,发现一只耳朵空了,不知道耳环掉在什么地方了。姥姥顺着路往回找,贴身久了的人和物,都已是生命的一部分,有感情了。她在炎炎的午后,在乡间小路上,来来回回地找,她从不曾珍惜过什么金银,却一定要找到那只银耳环。
她总觉得那丢的不是金银,而是那个人。等她空着手走回家的时候,乡里工作队的人正在等她。只是短短的一个中午,在她没有相随的短短几刻钟里,姥爷出事了。他累了,他用一根麻绳了结了自己。
从那以后,日子更加苦难了,姥姥摘下剩下的一只耳环,挑起家庭的重担。一个寡妇,领着四个儿女,顶门立户,既当男人又当女人。
饥寒交迫的日子,人关心的只是今天的粮食,哪有心情在意奢侈的装饰。慢慢地,姥姥褪去所有的装点,生活和生命蜕变为极简。那只丢失的耳环,和姥爷一起珍藏在了岁月的深处,时而沉没,时而浮现。那忍痛深埋的,是男欢女爱,是情郎小妹,是青春,是爱恋。
所以,女人一生中最珍贵的首饰,非金银,非珠翠,姥姥十九岁那年,掀开她盖头的人,就是全部的风花雪月。
桂 兰
那时候,姥姥家后院搬来一户姓周的人家,周家有个女儿叫桂兰,不知不觉,桂兰对小舅有了喜欢的意思。过年闹秧歌的时候,小舅和桂兰一班,姑娘小子在一处厮混,出了正月,小舅对桂兰也动了心思。可是两人谁也不肯先说出来,就那么放着,等着,让人心焦。
姥姥和二舅都不同意。桂兰虽然是个好姑娘,可是命太苦,家太穷,负担太重。她一个人,上面有三个老人等着她来养。一个是她爹,一个是她大爷,还有一个是她叔叔。她叔叔,大家都叫他周老三。周老三生来眼睛斜,有几分残疾,没娶上媳妇。桂兰这一家里三個汉子,只有桂兰她爹娶上了女人,可那女人生下桂兰,因为嫌他们家穷,也跟人跑了。这一家的三个大男人,守着这么一个小女娃,好不容易拉扯大,自然要指望着她养老送终的。因此,姥姥家的人不愿意娶桂兰,桂兰家也不情愿把桂兰嫁过来,他们盼着的是找一个上门女婿。
很快,就有人给小舅介绍了夏家村的姑娘,小舅心里不愿意,整日躲着不回家。可是,家里却把亲事红红火火地张罗齐备,不由分说地把媳妇娶进门来了。
这新媳妇进门后,隔一年就生下一个小丫头。那时候,小丫头睡觉的时候,我就在窗下唱,因为我喜欢这个小丫头,想时时刻刻地跟她玩耍。可是,新舅妈不许,她把门拴住,不让我进来。我就在窗下唱,终于把小丫头吵醒了,不停地哭闹。新舅妈出门来,瞅着没有人在旁边,用眼色吓唬我。当有人走来,她就换作哄我的语气,我看着她做戏一般的样子,就讨厌她了。我觉得,这个新舅妈,不如后院周家的桂兰姐好。可是,小舅却仿佛早把桂兰姐忘了似的,只一心一意和新舅妈过日子。
桂兰不久以后,真的招了一个上门女婿。
这女婿表面看来什么都是好的,可是,他是有肺痨病的。他们家每一代都有几个人死在肺病上。嫁给他们家的女人,仿佛就能看到守寡的日期。可是,桂兰这样的家境,就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肯入赘。
那男人在桂兰生下孩子后,就开始吐血,他再也不干农活了,因为他自认为死期将至,整日混在看小牌的人家捱日子。结果桂兰找了男人也像没找,反倒多养了一个男人在家里,多了一份负担。后来,桂兰的男人一直也没有死,只是这男人常常走在路上,会突然不停地咳嗽起来,并且大口吐着血。
那以后,姥姥总是说,如果咱们家娶了她,桂兰不会这样命苦的。
小舅却从未说过什么,偶然在路上碰见桂兰,他们也不说一句话,眼里没有爱也没有恨,仿佛从未发生过交集的陌生人。可能,男人和谁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就把心交给谁,对没缘分的情意,还是忘掉好吧!
三姥姥的刺绣
在姥姥的箱子里,藏着一块粗布刺绣。
那是一块泛黄的白棉布,很粗的纹理,却是很结实的布料,那上面绣着一只五彩的凤凰。
姥姥说,这是三姥姥绣的。三姥姥是姥姥的三妯娌,就是姥爷的三弟媳。
这块刺绣一直藏在姥姥的箱子里,我见到的时候就问姥姥:“为什么要一直留着这块刺绣呢?”
姥姥说:“因为她绣得好看啊!”
可是,我长大后才明白,姥姥的针线也是数一数二的,她一直留着那块刺绣,是为着留作纪念。
那是一只怎样美丽的凤凰呢?它是用亮亮的丝线绣出来的,五彩绚丽的,古色古香的神鸟。每一个针脚都是那样的仔细,每一根羽毛都是那样光鲜,密密麻麻的,数不清有多少针,就像看似漫长的人生,数不清有多少秒。
三姥姥是要数着这些针脚过日子的。她有一个抽大烟的丈夫,她整天守着一个小小的儿子,过着困窘寂寞的日子。人生对她来说,是一场漫长的戏,她必得找到办法消磨,才能磨去那些孤苦伶仃。
我见过三姥姥的照片,是她七十多岁时照的。那时,她唯一的儿子,我的大舅,已经学业有成,能够奉养老母了,这样的结局,算是一个好的结局。
照片上的她,眼神很亮,脸小小的,很精致,那大眼,那小脸,年轻时候的她,该是多么美啊!守着独子,坚守完一生,而不推脱责任的,总是伟大的母亲。柔弱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扛的女人,用一枚小小的绣花针,绘出悲苦一生中一抹花红柳绿的色彩。
到如今,她们都故去了,一切已成云烟,一切都已落幕,不留一丝痕迹。亘古以来,无数的生命都是这样消失的,草芥一样的人,又怎么能留下故事,凡能留下的,都是不平常的人和不平常的事。然而,每个人的故事里都有不为人知的苦楚。
再次看到这一块粗布刺绣,抚摸着那些细细的针脚,如同抚摸着百年前刺绣的那只手,虽然已没有一丝温度,却依然能在眼前浮现出旧日时光。
姐 妹
那一年,我五岁,大表姐十四岁,我是快嘴儿,大表姐也是,我们俩谁也不让着谁。
那次,我和大表姐杠上了。
她在北炕上,我在南炕上,你一嘴我一嘴,谁也不让谁。
我说:“瞅你那样子,蠢得像头猪!”
她说:“我是猪,我们全是猪,你咋还赖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好几年?”
我说:“你以为我稀罕住呀,我是来看我姥姥的。这是我姥姥的家,是你家啊?”
她说:“难道是你家吗?你回你自己的家去吧。”
我一听就急了,过去把她正在绣花的东西全扔在地上了。那些红的、粉的、绿的、蓝的丝线,全都缠作一团,再也厘不清了。她对着南炕上的姥姥说:“奶呀,你看看她,小厉害,你再不管管她,长大能上房揭瓦了。”
我姥姥气喘着喊:“她都没个豆儿大,你那么大个姑娘了,还跟她一样的。”姥姥一边说,一边越发喘得厉害了。
大表姐见姥姥生了气,就害怕了,一声不吭地捡起那些丝线,把气憋回肚里去了。我赶紧跳过去,给姥姥拍后背,一拍,我姥姥就乐了:“你呀,不气我比什么都强。”
姥姥家是大家族,三十多口人前后院住着,不分家,家里又和气,孩子都孝顺,谁要是惹姥姥生了气,那可不行。
大表姐好几天都不理我,她拿她绣的那些花呀朵呀的可当回事了,那都是她的宝贝。天天的,她除了下地干活,就是坐在炕上绣哇绣哇。门上的门帘,被子上的盖布,缝纫机上,都蒙上了她的“丹凤朝阳”和“国色天香”。可是,我这一搅,她的线全都乱了套,她又得等下次赶大集去买花线了,她能不生气吗?
她越是不理我,我越是受不住。我姥姥说我:“人家不搭理你,你还老往人跟前凑,你就是能请神,不能送神。”我说:“我能送神。”大家正坐在屋里唠嗑呢,听我这么一说,都忍不住乐了,就逗我:“你咋送这个神呀?”我想了想,就跳上北炕,给大表姐赔不是去了。
我说:“大姐,你对我真好,你忘了,春天那会儿,你上山摘指甲草给我染指甲。”
我说:“大姐,我的衣裳不都是你给洗的吗?你忘了?”
大表姐气哼哼地说:“这话,都该我问你呢?你忘了吧?我对你有多么好。”我见大表姐接了我的话,就知道她气已经快消了。
她拎起土篮子,要上北地去起些土豆晚上吃,我赶紧屁颠颠地跟着她去了。到了地里,她拔了几株土豆秧,用力甩掉那些粘在土豆上的泥。我见了,也用力去拔,拔断了土豆秧子,把自己甩了个后腚蹲儿,一个土豆也没拔出来。大表姐说:“不是下狠劲儿就能拔出来的,要一点点摇晃着,把土弄松了,才好拔呢。”我就试着再去拔,果然拔出来了,我一个劲儿地夸赞着她。
她用手去土里摸那些没拔出来的土豆,我也下手去抠,不一会儿,就抠得满嘴满脸的泥。但我很认真,撅着小屁股努力地抠着,由于注意力太集中,半张着的嘴里,流出了许多口水,当我捧着抠出来的土豆,捧到大表姐的土篮子里去,她见我嘴角淌着口水,鼻子下面挂两条大鼻涕,又笨又脏的滑稽样,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当我跟在大表姐后面,带着那篮子土豆回家时,我们俩已经是最好的姐妹了!
到了家,她把我的脏衣裳脱下来,把我抱上炕,打来一盆水说:“洗洗你的小狗脸儿!”我的小脸儿就在她的大手底下揉搓着,她一捏我的鼻子,甩掉了那兩道挂着的鼻涕。我说:“你洗脸像我妈,老狠劲儿了!”
我一这么说,大伙都想起来,我妈把我寄养在姥姥家好几年了。我妈是大表姐的小姑姑,大表姐像我这么大时,我妈已经进城上班了。那时,我妈总是给我的姐妹们带回花围巾、绿围脖、红头翎子。她们因为很爱这个小姑姑,所以把一种报答回应给我了。虽然,一和她们吵架时,她们就说:“她是老蒋家的姑娘,不是咱们老罗家的人。”可是,她们却从没有真的把我当外人。
每次包饺子,都单独给我包我爱吃的韭菜馅;每年包黏豆包,我要吃多拌糖的红豆馅;地里的黄瓜结个小纽儿,我就悄悄摘走了;西红柿没红,就被我摘下来啃一半,扔一半……
姥姥一给我们断官司时,就说:“人和人,在一块儿,不就为个感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