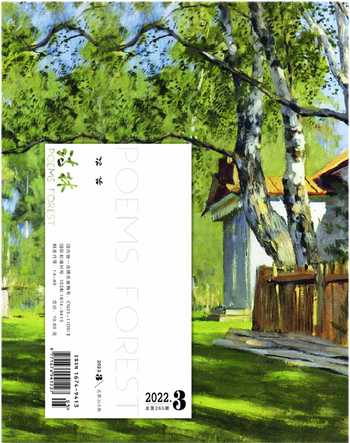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史诗
娜仁琪琪格 李轻松
李轻松(以下简称轻松):你好娜仁,我习惯性地叫你娜仁,简洁亲切,仿佛邻家妹妹。这是个标准的蒙古族名字,它在你的诗歌中承载了什么使命?
娜仁琪琪格(以下简称娜仁):轻松姐好,我习惯这样叫你,读你的作品时总是油然而生出亲切感,一直觉得你是可以交付情感的亲人。
蒙古族女孩子的名字,大多都与自然风物相关,因为祖辈在草原上逐水而居,和大自然贴得很近。娜仁在蒙语中是太阳,琪琪格是花朵,我是一朵太阳花。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是难产,也就是说我的出生把母亲折腾得很苦。父亲讲起我的出生时描述了一幅画面:在内蒙早春四月的一个清晨,太阳正在升起,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的母亲死里逃生,而我的父亲正在请医生的路上返回。我是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吗?为什么走得那么缓慢、犹疑?母亲生下我用了三天的时间。父亲一只脚踏进家门的时候,听见我的哭声,他的心突然豁亮起来。
我初来北京时和很多刚到这里追梦的人一样,特别茫然,偌大的北京哪里是我的开始?我在迷茫中问询、探索,而诗歌是我与生俱来的热爱,它一直跟随着我,每当我如处深渊时,它就在我的生命中闪动起光亮,那光尽管是微弱的,却在明明灭灭的闪烁中牵引着我,一次又一次给了我希望。从那时开始,诗歌就是我生命的灯盏,无论生活有多么困苦、艰辛与无奈,我都会在生命中为自己点灯,为自己照亮,并且告诉自己,我要通过诗歌去探索、发现更多的美好,去传递温暖、仁善、美、勇敢、坚定以及慈悲。
轻松:我一直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持着好奇心与崇敬心。我曾经在2001年走遍中国大地,为一家卫视做的纪录片《体验生活》撰稿,主要的采访对象就是少数民族。我觉得在他们的生命里有着奇异的密码,也有特别值得我珍视的品质,我也非常喜欢国内几位少数民族诗人,你是其中之一。简单、纯粹、善良往往是少数民族诗人最基本的性格特征。少数民族那些独树一帜的文化基因,你认为它们是如何作用于你的诗歌的?你在相互融合中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娜仁:我想,你的那次走遍中国大地不仅会作用于你的《体验生活》的撰稿,而且对你其后的文学创作都是受用的。你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吸收的能量太大了,那个过程也是一次又一次打开自己的过程。尤其是行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多民族文化产生了碰撞、交流与交融。你生命的河流是向外敞开,是海纳百川啊,我真是羡慕!
正如你所说,少数民族的这些特征确实作用到了我的诗歌中,并且是一直贯穿性的。我认为好的作家、诗人一定是用生命写作的,好的诗歌一定是在生命中提取出来的,是在身体中提取的神,在骨头中敲出的髓。
我在融合中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我对自然的热爱,对宇宙世界的痴迷,对生命最本真、质朴的感动,我甚至认为世界本来是非常简单的,简单到万物本是一体。
轻松:你运用的语言特别能代表你的性格与文化认同感。你不紧不慢,不疾不徐,像一曲悠远的蒙古长调,一唱三叹,既奢华又质朴,既喜悦又忧伤,既平静又起伏,仿佛大草原上的河流千回百转,却潜伏着词语背后那惊人的力量,这样的能力你是如何炼成的?你认为草原文化赋予了你哪些气质?
娜仁:轻松姐你谈到的这些,其他朋友也和我这样说过,他们说,你的诗歌气质就是草原长调的气质,你说你不是在草原长大的,这就是很神奇的事情。我的回答是,这是来自我生命深处的河流,它流淌的是蒙古族人的血液,我的血缘在那里,它滋养着我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胞,在这些细胞里发芽生长出蓬勃的青草,凭借长生天的恩赐,逢着太阳、雨露、月华,梦想就在青草上冒出了美妙的花骨朵,然后就开出了起起伏伏的花,在风中奔跑。我们曾一起去过科尔沁草原,我想草原给我们带来的感受一定很深,当诗人们都沉浸、陶醉在草原的大美中时,我在那里找到了自己语言的根性。每一次到草原,我生命中最深的记忆都会被唤醒。这就是民族基因的缘故,它从文字中流淌出来,自然带着独特的密码。
我认为草原文化赋予了我坦荡、简单、自然、纯净的气质。
轻松:我与你是同一条河流哺育出来的女人,奔腾于辽西大地的大凌河,古称白狼河,它也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作品中。不同的是,你有着丰美的牧草气息和羔羊般的圣洁之美,而我有着泥沙俱下般的恣肆汪洋,这大概也是因为你在上游我在下游。如果从我们共同的地域与心灵属地出发来考量我们的异同,你认为那条河流给了我们什么相同的基因与不同的风貌?
娜仁:我们对彼此的认同与心灵的亲近,我想与同饮一条河的乳汁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凌河的蒙古语叫敖木伦,说到大凌河,我便想到清澈的流水,玉带飞舞,想到春天里玉骨清白的梨花,满山满岭的桃花、杏花与槐花。我们的心灵属性是流着同一条河的血液与基因以及它给予我们的精神气质,都喜欢把事情简单化,真诚相待。通过你汪洋肆意、奔腾汹涌的文字,我得以见到属于你身体中河流的样貌,这条河流不仅使你的文字汪洋肆意,而且具有魔幻主义的巫性魅力。
轻松:你现在既是诗人又是画家,我固执地认为你的画也是出自你的诗。我好奇你是如何從诗转向画的,你认为是画拓展了你诗的边界,还是诗成就了你的画?你最初的灵感来自何处?它是你随身携带的基因还是后天养成?
娜仁:你的感觉是对的,我的画确实是出自我的诗,我的诗人精神以及我几十年的诗歌创作培植了我的画,也可以这样说,是我多年来通过文字呈现着一幅又一幅画。我是天生就热爱美、迷恋美的人,经常会被出现在眼前的美所打动,震撼了心魂。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站在天地间,无论是花开花落、流水潺湲还是飞云横渡、满天星斗,我都会想,我能把它们画下来多好,有时也会有一种冲动,很想能端着一盆色彩猛地把眼前的美景泼出来。这些想法在大脑中无数次闪现,又很快无数次溜走。我具备了一个艺术家最基本的气质:恍惚、走神、迟疑、多愁善感。
在我们的常识中,成就一个画家需要很多条件,我的成长过程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当有一天我明确了自己是一位诗人,也写出了使命感,我从生命的混沌状态走了出来,一切事物以及行走的方向明晰起来后,我便有了自己的艺术追求。我要成为怎样的一个我,我要去表达什么,替世界表达什么,怎么表达得更好,这样的创作理念也在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都力求使我的诗歌具备和呈现画面感、戏剧性,以及音乐的节奏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笃定地走在诗歌创作之路上的同时,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内心发出的另外一个声音,那就是我要把我想表达的在画布上呈现出来。我久居于生命中的这个期待、这个机缘终于来了,绘画的神秘性被我在偶然的一次相逢中看破,于是犹如闪电撕开了厚重的天幕,天光闪烁,灵感降临,我身上被封闭的死穴打开了。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原本是具有两翼的人,一个是诗歌,一个就是绘画。
我先是通过诗歌在这个世界获得了行走的路径,多年后绘画的大门得以打开,虽说它们是彼此滋生、互养的,但我得说,我首先是通过诗歌汇聚并打通了这些能量,绘画使我的诗歌创作边界得到了拓展。从我的个人感受与成长经历来说,我认为我是随身携带了这些基因,并且很幸运,在生命颠簸、流转的路途上,它们没有被湮没,一直跟随着我,并成全了我。
轻松:请谈谈你的成长经历,你认为哪些转折使你成为一个诗人?它一直是你的理想吗?你从中获得了什么?有一天你会因为画而放弃写诗吗?你在诗与画之间是如何完成自由转换的,在其中得到了什么乐趣?写诗與画画哪一种更接近你的灵魂?
娜仁:我小时候多是处于迷离、恍惚状态,到了高中更变得一塌糊涂,很多时候都处在一种冥想的状态中,经常会为一些东西而忧伤,而感动,而魂不守舍。风啊,雨啊,窗外飞过的燕子啊,会突然把我的心魂带向一个莫名的世界。那个时候我自己在笔记本上写了大量的诗歌,并且配上了插图,将一些掉落的树叶、花瓣加进去,也正是那个时期开始发表作品。然而真正走上诗歌之路、成为一个诗人,应该是我来北京后。
诗歌是我一生的理想,与我的生命水乳交融,它不仅仅是一种爱好,它使我成为了我,我通过它找到了我。绘画与诗歌在我的生命中完美结合,它们是彼此滋养的,我不会因为绘画放弃诗歌的创作,当然也不会因为诗歌放弃绘画的创作,它们在我的生命中是并行的,是我生命得以飞翔的双翼。轻松姐,这就像你写小说、写诗歌,同时一直从事戏剧创作一样。说到戏剧创作,我便又想到了你的诗剧《春江花月夜》,你把诗歌与戏剧创作融合得那么浪漫与唯美,令众多诗人倾慕不已。
轻松:读你的诗是一种疗愈,那些焦虑、抑郁、浮躁、崩溃等时代病,会在你马头琴般的倾诉中得到舒展与抚慰,你从不会歇斯底里,而是在那种从容的空间里走走停停。但你在画中不是这样,我发现你的画色彩浓烈大胆,大开大合,有时会有越轨的笔触、实验的画风,给我带来的冲击很强烈。我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你,抑或是你的两面在诗与画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它们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吗?你在哪一种实践中更快意享受?
娜仁:有些东西确实是与生俱来,我喜欢安静、简单、典雅,喜欢更古雅的事物,我迷恋这些,渴求这些,我想我少年的迷茫与恍惚,正是在寻找这些。那是漫长的酝酿与等待,等待着各种机缘的成熟。我想说,诗人的我是在一个范围、尺度中形成、生长,我想要的那个模样在前面等着我,成为了我。尽管我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努力去突破,去蜕变,但最初的教养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们已经成为了我身体中流淌的血液。
而绘画的那个我,它是野性的,仿佛一直寄生在原始的状态,当一切能量得以打通,它获得了出口,就恣意汪洋,奔涌而出,没有任何约束与限制,它是没有被教养规范过的生命,它是原始的蛮荒之力,完全听命于自然,服务于自然。它让我发现另一个我的存在,那个混沌的、澄澈的、天马行空的我,浓烈、奔放、张扬肆意。这个在绘画中的我更快意、酣畅淋漓。
轻松:你是如何处理生活与写作(绘画)的关系的,你的写诗或画画对现实生活有什么作用?你的核心指向如何超越世相而直达精神高地?你如何选择诗与画的素材?把它们转化成作品时,你认为是技术重要还是内容重要?
娜仁:诗歌、绘画、编辑工作,它们共同成就着我,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现实生活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法回避的,我们必须学会和生活相处,才得以在艺术的空间中绽放。人到中年,会清晰地认识到生活才是培养艺术之树的沃土,一切艺术都离不开生活。我很幸运,我所热爱的艺术,它们都已经反过来回馈、滋补了养育我生活的沃土。我的工作,就是我热爱的艺术创作,它们得以结合在了一起。
艺术引领我们的精神到更高的境界,我会在艺术的创作中顿悟,精神因此获得飞翔,反过来,生活、世相是一种藩篱,我们无时不想通过艺术的形式超越这一切,正是这个不断想超越的过程集聚了能量与突破的勇气,使我们走在了不断超越自我的途中,这正是生命的意义。
我的诗画都源于生命的感动,一个被诗神与画神眷顾、宠爱着的人,总会被某些事物所触动。人到中年经历了很多过往,它们都成为资源和能量,储备在了生命里,当我们与自然世界的某一事物相逢、碰撞,它们就来到了我想表达的出口,有的是画,有的是诗歌,有时两者同时赶来。在创作的过程中技术与内容同等重要。
轻松:在多年的写作过程中,你是否遇到过危机?如何度过的?现在是否又遇到了新的瓶颈?你是如何认识这种瓶颈期的,如何去应对?
娜仁:在创作中突破自我,我想是每个作家都必须面对与经历的。一个作家、诗人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这是阶段性的,是进入了新的能量蓄积、储备的阶段。这个“瓶颈”,我把它看作休眠期。我遇到瓶颈的时候,不会为此焦虑,我是要蜕变了,进入新一轮的绽放,并且一定会上升到新的层次。我如十月怀胎一样,让自己安静下来,倾听生命更迭、自然生成的声音。我停下创作,静静地读书、听音乐、画画,很少看电视的我,也会去看看电视。我更多的时候选择行走,到大自然去,在大自然中获得巨大的能量补充,也会在大自然中获得新的启示,于是灵感再次降临,创作的春天再次来到。
轻松:我认为自然性在你的诗歌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你的作品中有信仰、有悲悯、有宽容。这肯定是你在经历过人生诸多的苦难之后所达到的境界,是对世间万物、对人、对所有人的信仰。你的笔下是花木葱茏、人间大美,你以母性的视角赞美、拥抱、歌唱,它体现在每一个文字中、每一种气息中、每一次凝神中。你从不介入所谓的宏大叙事,但我认为真正有关生命的书写就是宏大叙事,它有关人类的命运、人性的美与探索,你认为这是你诗歌的特征之一吗?
娜仁:我喜欢自然又美好的事物,诗歌中一定有美的艺术呈现,这种美不是表面上的文章,而是发自生命本真的自然流淌,这种自然的美如美酒,经过了漫长的酝酿、提取与珍藏,如宝剑经过了烈火的淬砺与铁锤的锻打。我能感知到宇宙世界有多维度的存在,很多的生命存在于不同的空间。
一个人有信仰,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做事就会有尺度;一个人相信万物有灵,就有共情的能力,对弱小的生命有悲悯之情。人在尘世上行走、生活,都会遇到很多的无奈,然而,只要不被打倒,所集聚的能量就会越大。我认为,一个人最大的能力是,经历了苦难所带来的疼痛、悲伤等所有的无奈,而依然相信美好的存在,身陷深渊,仰头却看见了天堂的光芒。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史诗,当你有了能量的储备,并有了与万物共情的能力,你对宇宙、自然、人生会产生新的认知,这些足够一个人去抒写,并且永远写不完,因为宇宙是多维的、无限的,自然世界中的万物也是无限的,诗歌也给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只要你把自己的生命史诗写好,就自然参与了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写作,也就是如你所说:真正有关生命的书写就是宏大叙事,它有关人类的命运、人性的美与探索。这是我一生的努力方向,希望通过不断地探索、践行,去呈现我所参悟到的真相与洞彻的光芒,并通过我的作品得以向这个世界传递。
轻松:你以一己之力创办大型女性诗歌刊物《诗歌风赏》,而且做得有声有色。是什么契机让你做了这样一本刊物?你又为何如此关注女性诗人及女性诗歌?你想在这本刊物中彰显什么理念?一晃儿几年下来,你一定在其中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与困境,是什么信念让你坚持下来?
娜仁:2012年底,我结束了在《诗刊》社的工作,离开的时候我对自己说:结束就是开始。可是,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开始?我在辗转难眠中思考了很多。机缘巧合,我的一位朋友在电话中与我谈到了合作,于是开始了一本刊物的创办工作。做刊物不容易,最不容易的是对它的定位,怎么做出一本有特色的刊物来,这很重要。当时我给时任长江文艺诗歌出版中心主任的沉河打电话,谈到和他们合作,他很高兴,同时对我说,你可以在每一卷中策划不同的选题,可以策划女诗人小辑,这对我是个提醒。女人成为一个诗人特别不容易,女诗人是多重身份的结合体,是社会、家庭身份之后的又一个角色。这个扮演多种角色的人,是在人和神仙之间行走的巫,她承担起诗人这个角色,就要付出比男人更多的酸甜苦辣,我就是她们其中的一位,我在其中感同身受。我就想为女诗人们做一本专刊,建立起一个百花园,使她们独立、自主、简单、快乐、优雅、从容地绽放,不用担心什么,更不必隐忍什么。我愿意为她们做园艺师,在这里等着与她们相逢。我想了很多方案,最后确定了做一本女性专刊。
《诗歌风赏》从2013年创刊到如今9年了,创刊之始就得到了朋友的鼎力支持,这些年确实经历了很多艰难、坎坷,但我特别感恩,在每个节点都会遇到贵人的支持。《诗歌风赏》的创办与继续不是我一己之力能做到的,要感谢我的朋友们给予的无私奉献,他们不仅是目光高远的人,更是品德高尚的人。同时我也算得上是有韧性与耐力的人,这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将这种基因传递给了我,我一旦选择一件事情,就会坚持下去,善始善终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轻松:在文坛上,娜仁与笑嫣已成为光芒四射的母女作家、诗人,为人所称道。笑嫣少年成名,现在更加成熟与宽阔,出版了近十部小说、诗歌、散文,参加了青春诗会,获得了新锐作家奖等多种奖项。值得一提的是,她与你同样诗画俱佳,我知道《诗歌风赏》的封面设计就是出自她手。笑嫣的成长让我好奇和羡慕,你觉得笑嫣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有你引导的作用吗?你认为作家是培养出来的还是自我生长出来的?你们有写作上的交流吗?都交流什么内容?年轻一代对你的创作有所启示吗?你对她有什么期待?
娜仁:谢谢轻松姐对我和笑嫣的褒奖!笑嫣自小就是很乖的孩子,一般的孩子都喜欢哭,因为哭是小孩儿和这个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当Ta需要什么的时候会用哭的武器来获取,笑嫣不是,她喜欢笑,懂得倾听与交流,出生没几天我就发现了这一点,你和她说什么她仿佛都懂得,这让我很喜悦。她说话早,并且一说话就让人吃惊不已。我的亲人、朋友们都被惊讶到了,他们开玩笑说:这不是孩子,是妖精。她小时候就表现出对听故事、读书的兴趣,如果我给她讲故事,她就很安静地听着。笑嫣四岁的时候,很多书都能通读了,并且看书快得惊人,看完后自己能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个时候去书店,她的书都由她自己来选择。她的处女作应该是三岁时候自己口述被我记录下来的《小月亮》。她10岁在《诗刊》发表组诗,作品几乎发遍了国内所有儿童文学的刊物,16岁在《青年文学》《民族文学》开始发表小说、散文。如果说我对她有影响,那更多的是来自潜移默化的濡染,笑嫣自己也这样认为。在接受一个访谈时,她说:妈妈给我的影响是她自己的努力以及她对我兴趣的发现与呵护,我从小就有喜欢的书读,她给了我自由的空间,让我一直保留了对文学艺术的兴趣。
笑嫣从小表现出对读书、写作的兴趣,同时对绘画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们发现后给了她呵护与培养。她的本科专业是学艺术设计的,她的这个能力对《诗歌风赏》的创办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创刊号到现在的封面设计,都是她负责,她是《诗歌风赏》的艺术总监。
我们不仅是母女,也是知音,因为懂得,彼此珍惜,我们在交流上无障碍。她现在虽然学习紧张,也会经常和我谈谈感受,会突然给我发来微信说:娜仁老师,你给我说过的什么什么,误导了我多年,其实是如何如何。这个时候我會说:是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是我错了,不该把一知半解的东西说给我女儿,看来我真是井底之蛙啊。我在她的作品中看到那些独属于她的光芒四射的才情,为此感到欣慰。我们都用欣赏的目光去看彼此,给予对方更多的赞赏,偶尔在哪个地方提出一点建议,在创作中都保持着独立与对彼此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