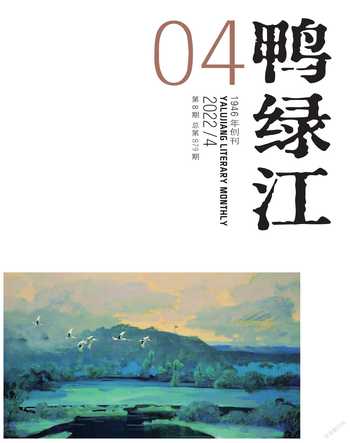清明节的思念
许是因为清明节,前天晚上梦见婆了。
婆去世的时候,我不到5岁。婆在我脑海中的零散记忆,无外乎我惹怒了婆,婆拿着扫帚,一边蹒跚着一双小脚撵我,一边装怒叫骂。看着婆撵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我拍着手做着鬼脸故意气婆:“来些,来些,来撵我啊!”每每巷子里的大爷大妈也来凑热闹,他们大笑着怂恿我喊我婆的名字。年少的我在他们的鼓励下,站在粪堆上,双手叉腰,大声地喊着婆的名字。我的叫喊声让半条小巷沸腾了,笑声、调侃声一片。婆被我的阵势逗笑了,一屁股坐在碾盘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看到大人们笑,我更加得意忘形,在大爷大妈的教唆下,继续挑衅:“来些,哈(坏)老婆,来撵我啊!”婆起身拍了拍土,对着身边的大爷大妈笑骂:“一个个哈怂,光知道给我娃胡教!”又回过头,忍住笑对着粪堆上手舞足蹈的我劝说:“我娃乖,再别听你这些哈怂爷哈怂婆的话,赶紧下来,咱回家,婆给你烫醪糟!”
一听到醪糟,我在粪堆上安分了许多,但又怕婆骗我,就和婆谈了条件:不能骗我,不能回家打我,要给我烫一大碗醪糟。看到婆信誓旦旦,我才下了粪堆,心有余悸地向婆跟前靠拢,嘟着嘴边磨蹭边说:“婆,我要喝醪糟!我要喝醪糟!”
在一步之遥时,我被婆一把拽住,婆用笤帚在我屁股上轻轻拍打了两下,问我:“以后还叫大人名字不?”为了喝醪糟,我回话(道歉)像打盹儿。
婆拽着我朝回走,身后响起一阵笑声:“娃呀,以后想喝醪糟,就喊婆的名字!”
婆做的醪糟在小镇很有名。听妈说,我爷当年孤身一身从富平逃难过来,婆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一贫如洗的爷。为了在小镇站住脚,爷给人打短工,婆支起了醪糟摊子。爸说,婆做醪糟选最好的米,做出的醪糟又香又甜。谁家媳妇坐月子,买几斤婆做的醪糟胚子,定会奶水充足;谁家老人病了,喝一碗婆做的醪糟鸡蛋,定会神清气爽。巷子里谁家生孩子,谁家有病人,婆都会记在心里。端一碗醪糟送过去,送的不仅仅是温暖,更多的是一份乡情。每每有家境贫寒的人登门,婆都会慷慨赠送,看到对方千恩万谢,婆总会挥挥手:“客气啥,谁还没有个难处?”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是婆醪糟摊子红火的原因。每天起早贪黑,辛勤劳作,几年后,爷和婆拆了小土房,盖起了大瓦房。上梁那天,乡党们带着凑钱买来的鞭炮、带着镢头铁锨前来帮忙。看着燃放的鞭炮,看着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婆激动得又是倒水又是道谢。“谢啥呢,婶,这只能说明我婶的乡行好啊!”大家伙异口同声,身后一片爽朗的笑声。
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庄稼人,点滴恩情都会铭记于心。他们能做的就是用淳朴的方式去感恩,用最质朴的语言去感谢。
和婆相处了短短5年,我没见过婆红红火火的醪糟摊子,但我喝过婆做的醪糟。看着婆从黑瓦罐里舀出一勺如羊脂玉般的醪糟放在碗里,在开水的冲击下,碗底的醪糟欢快地跳着芭蕾,瞬间漂浮在水面。不用放糖,稍稍放凉,只一口,就会甜进心底。那时候,虽说婆不卖醪糟了,但隔三岔五总有人上门求教,婆会和盘托出自己多年做醪糟的经验。有人打趣,这个瓜老婆,把自己祖传的秘方都卖了!婆听了大笑:“又不是啥值钱的东西,难道还要把这醪糟方子背到阴司去?”
和婆唯一的一張合影是我扎着冲天辫,噘着小嘴,一脸不高兴。记得那天,婆带着我和表哥去县城看望二姑,午饭后,我们一起去照相馆。年幼无知的我,面对镜头,依旧自顾自地吃着麻饼。在摄影师的提醒下,婆费了很大的口舌才把麻饼从我的手中哄走。看着婆手里攥着的半块麻饼,我气得噘着嘴巴,任摄影师怎么逗都无济于事。
时隔多年,那一幕幕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第二年冬天,婆去世了,爸把合影中的婆单独洗了一张作为遗照。看着满屋子忙碌的大人,我问表哥:“婆干啥去了?”表哥哭了:“婆死了。”我继续问:“死了还能活过来吗?”表哥默默地摇头。看着泪流满面的表哥,我使劲摇着他的胳膊哭喊:“我不要婆死,我不要婆死……”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
几个月前,因为小镇建新小区,爷和婆的坟再一次被迁。如今,爷和婆的骨灰被安置在几里外的陵园里。前天回娘家,听到巷子里几个婶子叹气:“陵园还是别去了,去了也不让烧纸!”我接过话茬,笑道:“避免火灾,现在都是文明祭奠呢。”
又是清明节,站在楼顶,遥望着陵园的方向,又想婆了。
虽然和婆仅仅相处短短几年,记忆中也就零星几个碎片,但那些场景时不时浮现在眼前,每每回味,如婆做的醪糟,又香又甜。
作者简介:
王宁子,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选刊》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各大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