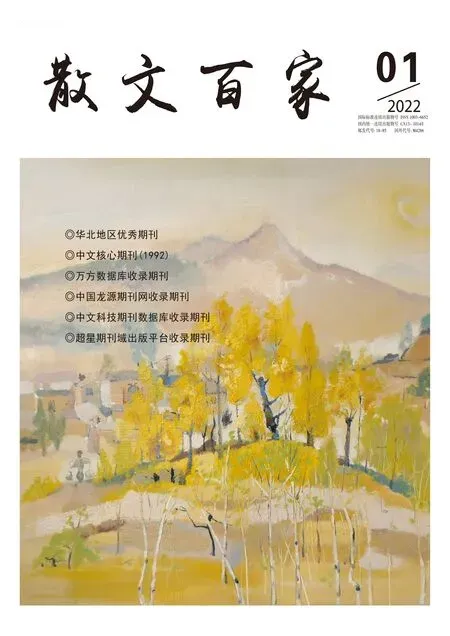虞世南书法美学思想探考
俞晓漪
上海体育学院
书法作为一种笔墨语言在具备实用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其艺术美的发展历程,而书法能成为艺术的核心基础取决于线条,文字线条是展现书法美的第一特性。在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唐就以文字线条之美筑基,对书写之“法”及艺术线条美的追求极大体现在楷书之中,对楷书书写的技巧追求到达了历史的巅峰。
唐是继魏晋后,一段书法历史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时期,在晋完成“尚韵”的历史使命之后,唐对书法的线条美提出了法制化的新要求,唐太宗李世民开始了从“王”背景下的“尚法”时代。在此期间唐太宗甚至开辟了“书法取仕”选拔人才的考试形式,唐也真正进入了书法体格健全化规范化的重要时期。唐太宗强力的政策影响推动唐朝法度加快严谨化的发展,以及唐对晋之“尚韵”总结的历史使命使其在书法体格完整化建设上更加快了脚步,唐对书法的技法、观念和准则等各方面的体格化的完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唐代书家们在此背景下,对书法思想理论的探究实现了突破性的成就,诸多宝贵的美学思想通过对具体书法美学范畴和命题的思辨,揭示了书法美学在审美意象和审美创造上所展现出来的“法”之奥秘。
虞世南是“初唐四大家”之一,其家学深厚,性情疏淡,经陈入隋,晚年归唐。虞世南书法得力于智永,可谓王羲之书法的嫡系传人,其性好耐静,静思不怠,少年时期读经学史,树立了儒家忠孝礼义的观念并终身以儒学为规。虞世南作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及“十八学士”之一,唐太宗称其具备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乃“五绝”品格。唐太宗李世民师法于虞世南,虞世南深受唐太宗器重并对唐太宗具有颇深的影响,对后世对书法的崇尚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从虞世南的用笔方法和结体形势、书法气息风格入手,窥探虞世南在书法线条美的形态中对技巧把握与线条美内涵的深层哲学领悟,可客观地探究虞世南对书法艺术创作“自然之妙”命题所展开的具体范畴之思考。
一、“尚法”的书写实践
虞世南楷书造诣极深,其“自有篆之玉筋意”的笔画尊法尚道,内含圆润,极具古朴之厚思,虞世南作行书之时也时常由楷法入之,对虞世南用笔方法的衡量,是窥探其书法艺术水准的重要基础和辨别其书法艺术特征的重要内容。
虞世南书写字体大小和字形变化不掺私意,崇尚自然之法,在结体方面的构造如自然之斧。虞世南书法结体主要以横势为基调,整体表现较为平和静雅,一行落笔却极少带笔走势,所展现出来的是笔致的圆润顺畅和结体的色润气秀,虞世南落笔画转折不露圭角,其字雍容沉着、体态稳健。虞世南作行书比较侧重于单字结体的姿态展现,其书写结体精妙绝伦,章法却平淡自然,舒朗从容,恬静优雅,字字都有不同的形态,追求极致的自然结体美,因其深厚的积累以及内心体悟自然之“道”于书法的玄妙之用使其在用笔方法和结体形势上表现出精辟绝妙的造诣。《夫子庙堂碑》是虞世南楷书之传世力作,全文书写线条质感厚实,笔笔行走交代清楚,文字姿态平中寓奇,用笔含蓄但入驻精气,一旦落笔成字便水到渠成,虽字与字不随意连带,但往往内含笔断意连之法,运笔速度较为沉着且流露自然真情,无刻意造作,笔调之缓和展现出舒展典雅之美,运笔的轻重变化在技法微妙之中显现。虞世南的《破邪论》是其小楷代表的重要作品,一如其楷书尚法之道,含蓄敛气,点画形态多以藏锋为之,每一笔画起止分明、沉劲入骨,落笔多以逆取势,故而其书笔意紧敛,点画线条刚健中止,用笔缓转流美而静,务求骨气中含、近古浑朴。
后代书谱记载虞世南书法之美,对其书法评价常常有“合含”、“圆浑”、“温润”等诸多美学范畴的概括,虞世南也著有其自己的书法理论总结其书写心得与感兴妙悟。宋《续书断》记载“气修色润,意和笔调”、“合含刚持,谨守法度,柔而莫渎,如其为人”,虞世南书法的书写功底和书法美学涵养造诣,是由其重视法度,做事恪守法规,深造学问修养,通过书写书法持续地修身养性所奠定的,虞世南对书法创作的精妙思辨承托于其出色的政治修养和个人修养之中,这也是是虞世南书法境界深造的重要原因;“虞则内含刚柔”,“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宋代《宣和书谱》强调虞世南书写笔触干净、安静自然且深谙藏器之法,一笔一划清楚展开,运笔外在不激不厉,笔笔书写暗藏才器,点画质感厚实,结体相当稳健,《宣和书谱》将《周易·系辞》之“君子藏器于身”,借以表达虞世南书法造诣蕴藏着弘大之才器;清《承晋斋积闻录》记载“虞世南字圆,近钟无常、智永”,且“圆浑温润而不露圭角”,虞世南继承“二王”的书法涵养,善于藏器,温和润雅,整体章法上保持安详简约的静雅风貌,“圆浑”、“温润”的归纳是对虞世南善用圆笔且笔画精炼周到和点画组合谦和高雅之法度的极高肯定。
二、“感兴”的书法理念
虞世南在拥有过人天资的同时,依然发挥其刻苦求学的精神,积淀了深厚的书法和儒学修养,著有《笔髓论》、《书旨述》、《劝学篇》等书论,在前人对书法风格不断突破创新之上,虞世南提出书法创作主体“心”的感应以及书法用笔的自然之“妙”对于书法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对推动后世书法美学思想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深远影响。
汉代、魏晋的书家都是通过不断书写中才体会到书法精髓的奥妙,虞世南在前人的基础上,以《笔髓论》系统地论证心手关系对书写的影响以及将书法与“道”之最高道德和审美理想关系,其《笔髓论》对用笔的微妙阐述对书法内核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辩应》篇以心手关系论“应”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性,手感应到心的体悟指令,将心之所感作用于肌肉动作挥动笔势,由心“感”而手“应”之,以毫为士卒带动笔势动向,字如城池将心之所应现于纸上,“心”之所感是依靠日月的积淀所凝练形成的体悟,刻苦练习书写技法后通过手之感应以纯熟的技巧得以表现书法的自然奥妙。虞世南强调“心”为君如一国之主掌控全局,“手”为辅如君主之臣辅佐左右,由此可见心手关系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口所不能言也”,在《释真》篇中心手关系的地位再次等到强调,字虽然有其基本结构和规律,但在具体的艺术创作时,字的结体、运笔风格却不受限制,心想要造字之形态,手就能通过具体技法如用笔迟速、虚实,将心之所感应于纸上,这种妙造之法是无法用口诉说的。书法创作中运笔的轻重变化在于内心的运用,妙造之法就在于手腕的适应和发挥,心手感应的作用显现在任何字体的书写创作之中。以心和手相感应为基础,继而《释草》篇中提到“兴”的三个阶段,即“引兴”、“取兴”、“兴尽”的感兴过程,人作为审美活动的主体被客体打动内心而“引兴”,形成主观意想后继而“取兴”进行艺术发挥创作,笔笔承接直至“兴尽”而收,“兴”这个范畴可谓是虞世南书法审美意识的重要理论结晶。虞世南的用笔方法是受到审美意识的直接影响,在用笔方法上注重书写内质的追求,故能呈现舒朗从容的和美风貌,强调创作主体“心”的重要作用,重视“起兴”,故其书法提笔一气呵成,难看出痕迹。只有尊重自然和人之阴阳二气的运动规律,才可通过书法表现自我性情和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该篇中对草书的“不为笔意”的书写方式是虞世南对自然无为的崇尚,也是影响唐初对晋韵总结后上升的思想倾向。
当然,虞世南书法的气息风格离不开师承与学养,也反映其书法创作的艺术理念,故虞世南的书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了“二王”的用笔缩影。“二王”之书法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玄妙,又表现以儒家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冲合,虞世南在精熟前人书写理念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多年对“法”之实践积累,更加丰富了自己的用笔技法,由心手感应为书法创作基础,感兴三阶段为书法创作方法,虞世南对书法理念的自然追求逐渐明晰,虞世南书法笔致圆润遒劲、外柔内刚,又呈现风神萧散之态,虞世南的书法风格自开面貌,颇显自然之真妙。
三、“同自然之妙有”的美学命题
“道”——“气”——“象”是老子美学三个相互联结的重要范畴,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重要源泉,“道”即是万物,“气”即是精,“象”之物的形象不能摆脱“道”和“气”,“道”和“气”是自然万物之本体与生命。虞世南的“契妙”之论实际指出书法之“象”应该表现造化自然的根本,艺术创作应取自于“象”之外,如此才可通向宇宙无限,即通往“道”“气”。
在《笔髓论》之《释行》篇中,虞世南通过对运笔走势阐述了自然之道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作用,覆笔抢毫之际按住笔锋,运用牵动手腕力量从而紧敛笔意,掉笔连毫也如玉石之纹理出自自然之妙,书写动作一气呵成而非矫揉造作刻意为之。在《契妙》篇中,虞世南探讨心手感应与纸笔契得的关系和自然阴阳规律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影响,进行书法创作时,应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凝聚心神是书法的核心修养,写作书法应排除外界干扰,排除心中杂念,重视集中精神、重视内心体悟,只有如此才可以心神化,以心神往,使自己处于心正气和的绝佳创作状态。“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只有在良好的书法创作状态之下,书法艺术创作的意象才能表现造化万物之“道”、“气”,才能通向自然之“妙”,如此书法创作才可达到“同自然之妙有”之美。以鲁庙之气为喻,虞世南比喻书法创作的状态不能虚也不能满,而是要寻求一种中正平和的冲合之态,书法的创作需要以内心的平和专注才能把握自然之妙。书法创作的玄妙之处在于“必资神遇”,只有心中安定澄清,在至微至妙之间才能心神感应透彻体悟,创作灵感才会涌上心头,审美思维才能活跃涌现。书法意象当表现自然之象,书家需要在自身体悟的基础之上,契合自然规律之发展变化,心中思索感悟天地之微妙,才可使“心悟非心,合于妙也”,“道”契于心而不可言,但“心神”却因感悟而通透,主体精神的感兴对书法创作的重要可见一斑,由“心”至手,书写万物自然之“道”,即范畴“妙”也。
虞世南将“尚法”视为书法书写的基础,感兴为书法创作的手段,书写取妙为创作的最终目的,追求取法自然的最高境界,通过重视“心”之主体精神的作用和心手感应之法,取“兴”入笔,如此创作书法意象才能表现“妙”之造化自然,才是书道的玄“妙”对“道”与“气”的自然显现。正如《兰亭序》正是王羲之在酒意正浓之时起兴有感而发,提笔在纸上肆意挥毫,通篇血脉贯注随势而生,但当王羲之酒醒后想再重写却自感得不到其中精妙。“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点画之间皆有意”中王羲之的“意”即是凝结了创作主体感“兴”之情感而形成的自然天成之笔墨意趣,故只有内心对自然的领悟达到高深的境地,才能在书法创作上到达无为而治的绝“妙”之域。
《笔髓论》将虞世南同自然之妙的美学理解充分表现,遵循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观察世间万物调和阴阳之气再造字成形,才能通过书法创作寄寓人的主观情感以及自然变换之规律,才能使书法创作成为审美和道德的艺术呼唤,才能以书法之象通向道和气。虞世南的书法美学与其儒臣的身份密不可分,对书法创作美的体悟无疑是建立在“中庸之道”之上,虞世南的书法之“妙”实则妙在无为,妙在创作之人以中庸之心反馈了客观世界之美。
四、结语
通过对虞世南书法创作中“尚法”的书写实践、“感兴”的书法理念及“同自然之妙有”的美学命题的具体剖析,不难看出虞世南的书法之形是以自然之形为基调,其书法之势是以自然之势为基础,其书法艺术创作是永恒追求“妙造自然”之书法原则。虞世南重“法”,重心悟,重起兴,强调创作主体“心”在书法艺术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在“二王”的影响下,通过切身不断实践与理论归纳升华相结合的方法,以自然之“妙”将抽象的哲学思辨转现成为活灵活现的书法艺术再现,追求书法审美中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发展出了更为贴近“道”、“气”之妙的和美书写之“法”,对现今书法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