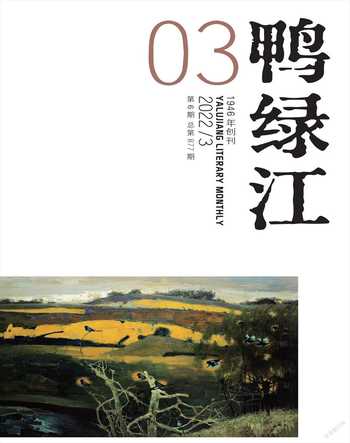又见痴鱼
小时候,村后有一条大河,河边芳草丰茂,河中水清见底。每年农历三四月间,父亲都会来这里捕取河鲜。青虾、昂刺、鳜鱼……品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河鲜中我最喜爱的还是要属痴鱼。
痴鱼是我们农村的叫法,它的学名叫塘鳢。清代诗人袁枚的《随园食单》里曾这样描述:“杭州以土步鱼为上品,而金陵人贱之,目为虎头蛇,可发一笑。”这土布鱼就是我们所说的痴鱼。
痴鱼浑身紫褐色,有细碎黑斑,头大而多骨,鳍如蝶翅,正面看时甚是憨厚。听父亲说,它虽被我们叫作痴鱼,其实一点儿也不痴。它善于伪装,且极凶残。它喜欢躲在水草或石头背后,待青虾等小型生物经过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张开大嘴对其攻击。它们食量极大,有它们的地方,青虾所剩无几。
父亲还说,痴鱼虽然凶猛,但对生态的要求却极高,水质稍有污染,它们就会即刻死亡,所以它们是天然的生态检测仪。
痴鱼肉汁鲜美细腻又少刺,是难得的河中佳肴。它的烹调方法有很多,红烧、白汁、炖蛋、油炸、蜜汁、烧汤、制羹无不适宜,而在我们当地最著名的一种烧法莫过于痴鱼粉丝了。新鲜的痴鱼去除内脏、鱗、腮,热锅冷油把其两面煎黄,再加开水、盐、味精,煮至肉与刺分离,剔除其刺,然后与炒香的肉末、泡好的山芋粉丝一起炖至汤汁黏稠即可。痴鱼肉、猪肉、山芋淀粉的完美组合,把痴鱼的鲜美发挥到了极致。
“田园蔬果农家宴,自酿杯醇塘鳢鲜。”小时候,来客人时,父母用痴鱼粉丝、自家酿的米酒与屋后刚采摘的果蔬招待客人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天朗气清,春风拂面,广袤无垠的田野里,阡陌纵横,麦浪此起彼伏。不知名的野花开满了塍间,一阵微风吹过,飘来淡雅的芬芳。母亲端上了飘着香气的痴鱼粉丝,舀上混浊、醇厚的自家米酒,在屋边搭建的葡萄架下,父亲与客人谈笑风生,推杯换盏……
到我上中学时,由于工业污水、化工污水的排放,那条大河总是泛着绿油油的一层浮沫,仿佛洁净的玻璃刷上绿漆一般恶心。微风吹过,不时有一股难闻的臭腥味萦绕在鼻翼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痴鱼的身影。它的那种憨厚、那种鲜美,只能到童年的记忆中去找寻。后来每当和朋友吃到河鲜时,总会想起小时候那痴鱼的味道,并不时地向他们吹嘘着痴鱼肉的鲜美。
渐渐地,我淡忘了它——那憨厚、鲜美的痴鱼。
近些年,污水处理的完善,淤泥的清除,清流的引入……一系列举措让记忆中的那条河又回来了。春天,河旁杨柳依依,芳草萋萋,水中鱼儿追逐、欢腾,不时泛起圈圈涟漪。不远处,连片的蟹塘一望无际,好似一面面亮晃晃的镜子,在春光下熠熠闪光。夏天,河中又出现孩子戏水的身影,他们扑腾着双脚,在水面溅射出雪白的水花。大河连接的沟渠边,那葱绿挺拔的芦苇像一群群年轻妙曼的女子,在风中摇摆着婀娜的舞姿。秋天,乡亲们带着从各个沟渠里采摘的菱角,会集到了这条大河边的码头,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乡亲的脸上。冬天,大河似乎恢复了宁静,只有那沟渠旁白色的芦苇花还在风中摇摆飘舞,仿佛在向人们叙述着大河往昔的辉煌。
上个星期天,天气格外晴朗,湛蓝的天空悠闲地飘着几缕如薄纱般的云朵。我驱车驶在故乡的村间大道上,宽阔的水泥路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条雪白的丝绸飘带,缠绕在炊烟袅袅的村庄之间。一排排装修考究的楼房规则地排列在路的两旁,像受阅的士兵般精神、整齐。
车刚停稳,父亲就拿着面盆,笑呵呵地迎了过来。几条硕大的痴鱼,在面盆里来回穿梭着,溅起的水花打湿了父亲的前襟。
时隔多年,再次吃起痴鱼,依然那么鲜美,只是这鲜美之外,却多了些厚重……
作者简介:
徐志俊,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百家》《鸭绿江》《参花》《翠苑》《苏州日报》等报刊,散文《南门坛上》入选北京丰台区高三语文阅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