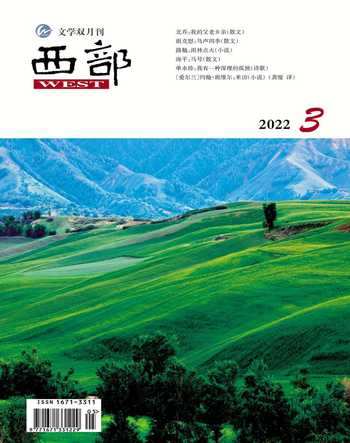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唐女
鬼柳
每次去往东山,上了云栖岭,就看着车窗外胡思乱想。这是进入东山的门户之山。据说当年日本鬼子爬上这座山,看了一眼东山就撤军了。他们身在迷雾里,什么也没看见,周边高大的树木穿云戴雾,从天空上压迫下来,像些张牙舞爪的天兵天将。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日本鬼子,站在云栖岭上却有些害怕了。其实,很多难民和当时的县政府机构,就躲在这片山林里。这座高山的云雾和山上的众多树木,挡住了战争,护住了躲进东山的万千难民。
看见石板路,我就想去走走。路在梯田中间。下面田里,一条黄牛伸长脖子啃田埂上的草。一条水牛妈妈带着牛宝宝,在上面的田埂上边吃边走。阳光打在它们裹满泥巴的身上,反射到我的眼睛,我接到了温暖的信息。旁边篱笆上的丝瓜藤,毛茸茸、亮晶晶的,青石路前方的河流、古村與古木,都在古老的阳光下散发迷人的气息。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走走?况且,燕子不会马上到。
那条古亭前的小水沟,也在几丘田外,匍匐前行。到了村口,石板路的左侧是清一色青砖黛瓦的老屋。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墀头林立,飞檐错落,小巷四通八达,都是石板路。巷子前头,还有古门楼。一切都完好如初,只是少了炊烟,人气没落,显得寂寥荒芜。右侧是开阔的田野,深秋时节,稻子归仓,禾蔸孤立,颇为苍凉。不过,我马上忆起曾经见到过的初春情景,田野里全是金黄的油菜花,蜂蝶乱飞,香气熏人,衬着这个古老的村庄和古老的树木,我就站在村前,远远地看着它们,心里爬满美妙的感觉。
小水沟也来到村前。村民称它为白竹江。这么小的水沟也叫江?也是,这地方地表江河真的很稀少,权且就把它当作江吧。村口修了一道水坝,水域突然宽阔了许多。水坝上是一座踏步桥。村民打此过江种田,打此引水灌溉。这么好的石磴,刚好一大步一个,在晃荡的水光中那么敦厚老实,我当然要踏着它们过一过这踏步桥了。桥的两头分立着两株硕大无比的古树,上面缠满青藤。它们婆娑的身姿倒映水中,与水中的阳光嬉戏游玩,温情荡漾。我仰头看着这两棵古树,它们隔着白竹江,日夜相守。村民说这是鬼柳。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它鬼柳,跟鬼有什么关系,听起来挺诡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榉柳,鬼柳。其树高举,其木如柳,故名。山人讹为鬼柳。”这里巫文化曾经极为兴盛,莫非他们认为这树上当真住着鬼不成?再往树上看,树叶亮晃晃的,好像有无数双神秘的眼睛正看着我。古道旁边的树下铺了几块青石,可以蹲在上面洗手玩水。我蹲在青石上,捞起一把水朝天空扑去,突然想起,这种树的花,就是我最喜欢的。它们一串串的,像绿色风铃,吊挂在树枝上,阳光照亮它们花序间的露水,仿佛发出银子的声响,非常迷人。前面的河岸还有很多鬼柳,都很古老。最大的还是这两棵,树围都达到了六米以上,高也有一二十米,树冠的遮阴面积很大。劳作归来的村民,挑担的路人,肯定爱在这树荫下逗留乘凉。来了一阵风,鬼柳树叶飒飒摇动,响了一阵儿。我是真没听懂它的话,只好祝愿这些村民心中的鬼神,能够幸福快乐地生活在鬼柳树上。
古驿道穿过村前的田垌,拐进了村。村里很多巷子都经过村口的几块水田连接到这条驿道上。村里宽阔的主道两旁还有林立的店铺,只是铺面紧闭,没了生机。本来想好好享受一下我这个游荡者的孤独时光,但想到那个原始树林,想到燕子可能已经在凉亭边等我,于是乖乖地打转回去。
燕子刚到。他见我从村里走出来,指着村子中间的几棵大树说,他的家就在老白果树下。经过大仁村时,也有一棵树围六米二的大鬼柳,撑开宽阔的树冠,立在古村一旁。古村上宽下窄,长条形的,像只船。村民说,这棵鬼柳是他们村的船篙。它早于大仁村,大致有千把岁了。谁也不能动它,动了它,村里就会发瘟病。更不能砍了它,没了它,这个村子就成了一叶孤舟。凭着这个信念,它幸存下来。陪伴它的,除了一片古民宅,一片水田,一条水沟,三岔路的古驿道,还有另外两棵鬼柳。有一年,村民正在田里插秧,看见一炸雷打下来,把这三棵鬼柳树都削去了一部分。中间那棵最严重,被削掉了一半,如今它的树心裸露在外,伤口再难愈合。头上那棵长了新树皮,慢慢抹掉了伤痕。古树的伤在上枝,我抬头望见了它。按照民间的说法,鬼柳树上住有妖魔,这些妖魔定然是鬼神界的坏蛋,才遭此天谴。
村右有一片石林。旁边有一条青草路。我绕到它们身后,发现它们都面朝西,背对朝阳。南边站着一个雄壮的武士,前面那个衣着华服的美丽女子对他回眸一笑。我定睛再看,此女的脸又是男相,让我迷惑。有擎天一柱,上面缠满青藤,阳光照亮藤叶和下面茂盛的白花,我看见了它的头上有红色光圈,紫色红色的光斑一串串垂下。这是他们的神器吧。如来佛祖的手掌伸向天空,宽厚包容,不知它是否真的能够抑恶扬善。一个王,端坐高堂,双手支在宝座的扶手上,面对西天,霸气十足。观音站在最前方,正在聆听人间苦声,普度众生,长长的白纱巾拖在地上。她最接地气,也最受民间尊崇。
一块石头缝里长着一棵小树苗,村民说,这是石槠木。石槠木?我环视周边,没见到这样的树木。想必曾经有过。这里山石裸露,只有一棵银杏幼树。不过,离全部砍伐的日子也三四十年了,难道这棵小树已经生长了三四十年?我知道石槠木有漫长的寿命,是不是它的童年也无比漫长?
村民顺着武士宽大的肩膀指向远方说,那几棵是枫木,再等一段时间就红了。
光秃秃的山岭只剩下那么一排枫木,显得突兀。
村民说,它们不燃火,才留住的。枫木背后的那座山,最高的叫鸡公山,山下很多树木的那座,就是原始树林,叫水源山。鸡公山与水源山之间长着矮小灌木的山叫堂堂亮。左边的叫凤山。右边的是大寨山和小寨山。寨山旁边是落花山。
鸡公山和堂堂亮上都是些高山矮小灌木和草甸,落花山上没有树,也不知道曾经落的什么花。凤山上枫木独占,大寨山、小寨山的树木只圈在山顶,唯独水源山层峦叠翠。莫非也是神灵护佑住的?不要心存妄想,这里神灵这么多,也没保住树木。
铁栎木
燕子把车停在竹林旁边的广场上。这是祖湾村的村口。相比大仁村,它是个非常小的村庄,才二十余户,六十几个人,外加二十多个两边扯的,才八十余人。两边扯的婚俗在东山瑶乡非常普遍,就是一对夫妻两边都照顾,两边的田地家产都分。我们的户口簿上一个地址,他们有两个。一会儿住这边,一会儿住那边,孩子也分着姓,当然老人也要两边都养。说白一点,就是拥有两个家。村里非常寂静,大多锁着门,见不到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有些老人也跟去带孙子。
村后的山,就是大寨山和小寨山。上面长着一些古老的树木,树冠繁茂,村民叫它们“铁力木”。还特意强调,是力气的“力”。铁力木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算是珍贵树种。村民说,这种树木相当硬,做砧板最好。他用刀剁了剁碗柜上的砧板,说,你看,非常结实。我也拿刀剁了一剁,果真很密实,不见刀印。我注意看了看这块圆砧板,想着那棵被拦腰斩断的树木,不知道它具体长什么样,也不知道是不是铁力木。
小寨山和大寨山的山顶有白石围立,像人修的石寨,所以称之为大小寨山。小寨山在前面,上有白石柱,像孙猴子变成绿房子后余下的尾巴,突兀地竖立在一旁,煞是好看。我让村民带我上去看石头和树木。这些树木非常喜欢石灰岩,专拣悬崖峭壁上长。那么险峻的地方,没有路,我们到不了那些大树身旁,只能接近两棵小一点的。村民说,大炼钢铁时期,这两棵树的枝也都被放下过,只剩树干。经过三四十年,那些枝条也长起来了。我说呢,这么老的树干,却长着嫩枝条。我拉近镜头,拍了带锯齿的树叶,也拍了裂痕很深的树干。岩石上的那几棵非常丰茂,我们虽然爬上了孙猴子尾巴前面的小石山,还是没办法靠近它们。根据树冠估计,它们的树围起码有两米以上。村民说,那几棵是原始树木,斧头发疯的时代也没办法将它们砍下来。
这种树木,在不远的坪香村的后龙山上有很多,曾经砍了一棵四五抱大的,做了木榨油机。现在还有六十多亩野生树木,最大的树围有两米多。有人花大价钱买这些树,村民不卖。这是他们的风水山,上面的花草树木都不能动。他们也很少进那山里,据说山里的五步蛇非常壮,野猪也多,野猪专爱吃五步蛇。只在饥荒年代,他们去山里捡过果实,把捡回的果实晒干,打掉它的果帽,打开四瓣,用来酿酒。那酒真是好喝,存放一年都不变味。也把它们磨成粉,煎粑粑吃,有些苦,但救过他们的性命。
我们踩着石山,看着脚下那些胡乱堆叠的碎石,心里有些发怵。我反身摘了一把石山旮果实放入嘴里,嚼了嚼,有些唊,也有些甜。最后看了一眼那几棵老树,穿过细密的鸟竹下山。脑子里放映着坪香村那一片黑黢黢的“鐵力木”。我是在夜晚去看它们的,没有月亮,夜光很淡,我们用电筒扫射它们。它们高高的身影,占据了我头顶三分之二的天空,成压迫之势。电筒光肯定引起了它们的骚动,打扰了它们的美梦,还有隐居其间的各种野生动物。
后来把照片发给广西林业部门的树木专家看,他说,“铁力木”是老百姓对硬木的俗称。这种树木不是铁力木,图片不太清楚,应该是壳斗科植物,有些像青冈。青冈树是栎属,别称铁栎,也许就是村民所称呼的“铁栎木”吧。
野果
正午时分,有些渴。见到有柿子烂在路上,举头看见红彤彤的一树,有些嘴馋。燕子爬上树去摘了几个最红的递给我,我尝了尝,好甜,一点涩味都没有。他在树上嘀咕,这个被鸟吃了,那个也被鸟吃了。橙黄的柿子,鸟一个也不尝。它们比我们更熟知这些果实,所有成熟的果实,它们都有权利去吃。
路边有一口古井,以前全村都来挑这井水吃。吃了两个柿子,不想喝水了。井水流入池塘,池塘里有一群鸭子,有的把头埋进水里找吃的,有的蹲在旁边的树荫里打盹。说是池塘,其实只有一条塘埂,其他三面都是天然的石头,石头上方是树林。如果塘里有那么几株荷,不管是绿还是黄,都会韵味十足。塘埂上还铺设了青石,地上长满了地毯一样的绿草,两边开着一簇簇紫色野菊。走在上面,突然感觉虚幻起来,我成了童话里幸福的小公主,要是身边没有这些村民,我定会一路蹦跳。如果这个村里住着一位王子,他们就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了。真正是远离尘嚣,贴近自然。风那么清新,天那么空灵。发出的声响都是自然之声,你想听的时候,它们在你耳边,不想听的时候,它们藏进大地。到处都是阳光和草木的气味。还有不远处那座水源山,和从山里流下来的泉水。村庄被各种古老树木包围着,地上掉满了果实。酸枣可以捡来吃。鸡爪莲,可以捡来泡酒,也可以当水果吃。
村右是水田,水田间有水沟,通向那个原始树林。水沟里有清冽的泉水流动。水沟之上,架设着各式各样的水槽,最古老的是古桥的石板边上凿的水槽,有木头凿的水槽,还有用废弃的电线杆做水槽的。这口水灌溉祖湾和大仁两个村的农田。水沟上方的峡谷里,于一九五八年修建了一个水库,现在只剩一个水坝,和一排石洞(曾经的水闸)。后来迷了路,走进熟透了的草籽仔里,枣红的一大片,挨上它们,浑身上下便全是它们带着剪刀钩的种子,一团一团的,刺到皮肤,又痛又痒。后来看见了一条石板路,就在身边,隔着刺蓬,没办法到达。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草籽仔里跋涉。草籽不怕,是有些怕踩到厚厚的草丛下面藏着的蛇。走到草籽尽头的时候,终于可以弯腰穿过荆棘下到石板路上。后来遇上了一位摘辣椒归来的村民,请他当向导,带我们进山。他把背上的半塑料袋辣椒放在路边,带我们上山。沿着石板路走了一段,又进入了草籽地,有了这位向导在前面开路,就不怕了。经过很多覆盆子,正好口渴,摘了几粒漂亮的放进嘴里,酸甜的汁立即缓解了口渴。来到入山口,发现一个大水池,村民说,它供应大仁和祖湾两村的人畜饮水。水源山是这两个村的公山。目前还剩六百多亩的原始植被,其中养育着五口泉水。他说,这是他们的命脉山,只有保住这些树木,才能保住这五口泉水。周边的树木都砍光了,这座山死命也不能动。他们周边没有河流,真的就是靠这座山里的水育田活命的。
开始进山。这是一座让我迷惑的山。
我在地上发现了一种漂亮的果实,像红石榴籽,整齐地排列在一个椭圆球上。村民说,快扔掉它,它是天南星果,有毒,沾上它的汁,会发痒起肿,吃了它会让喉咙肿大,导致窒息。我赶紧扔下。他说,其实它也是一味蛇药,开的花像个蛇头,黄色的。我忍不住回头再看了它一眼。却被藤蔓抓住了头发,举头看见无数小青果垂挂着,被我弄得晃荡起来。这又是什么植物?想问村民,他已经不见了踪影。只听见他在前方喊,怎么不跟上来?马上到。我解开头发,爬上一块巨大的岩石,走了一段跳下去,就看见了他们。旁边又有藤蔓上挂满茶果一样的果实,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我来不及问,他们又转了个弯,没入树林。我望着高高树冠外的太阳,暗自庆幸,如果来的是大雾天气,那就诡异了,别说看野果,就是离开他们一步,都会胆战心惊。这样的密林,什么野兽没有呢?乖乖地跟着这位向导东拐西拐,拐到了一处井泉。他坐在井边的石头上,忽而看看树冠,忽而看看流水,不再催促。我终于可以好好看看周边的东西了。
他突然站起来说,看完了吗?快点回去了。其实他惦记着放在路边的辣椒。燕子也说回去吧,已经到了午饭时间了。我看了一眼树叶间偶放光芒的太阳,只好跟着他们回去。
没过几天,我又来了。这回,我特意让燕子找了几位熟知树木的村民做向导。村支书、大仁村和祖湾村的两位蒋哥,他们能够叫出这一树林树木的名字来,也能分辨各种野果。
他们把我带到了一片大树中间,各自忙着捡果实去了。
我正围着一棵大树拍照,大仁蒋哥拿来一个奇怪的果实,递给我说,尝尝这个果,很甜,很补,比香蕉还好吃。我说,这是什么?我们叫它牛卵泡。这么难听的名字!我不知道吃什么,那果瓢里有一根带黑籽的白色东西,有些像剥开的香蕉。去抓它,软乎乎的,抓断了,咬了一大口那黏糊糊的果肉,满嘴都是细细的籽儿,不过,果肉还真是香甜无比。大仁蒋哥把我剩下的果肉吃了。燕子正忙着摘牛卵泡,他说,我摘了回家泡酒,你们来我家喝酒。我连忙发了一张照片在微信朋友圈,求证它是什么。刚发上去,就有一个贵州的朋友说它是八月瓜。在网上一搜,有图有真相,还真叫八月瓜,也叫九月炸。这位朋友还唱了他们的民谣:八月瓜,九月炸,十月摘来诓娃娃。那果还真是炸开的呢。它用果肉的香甜让动物把那么多的籽儿带走,达到传播种子的目的,真是聪明的植物。我找到它的植株,竟然是藤蔓。这么大的果实,以为是什么大树上结的呢。那些高大的植物,反而结小指肚那么大的果实,是不是很反讽?
祖湾蒋哥猫着腰在那里捡了很久了。我很好奇,过去问他捡到了什么。他递给我看,是赭红的小指肚大的圆锥果实,果帽很小,果尖很锋利。我的脚一崴,被果球的刺刺伤了脚背,痛得我哇哇直叫。看那些果球跟板栗差不多。他说,果球这么多,找不到几粒果实,都被果子狸吃了。这是一棵非常大的栗树,树围有三米多,他们叫它金刚栗。果真,锋利如金刚,它的刺和果实的尖锋,我都领教过了。不过,它的果肉味道甘甜,比板栗要细嫩。
山里还有一种栗树,他们叫它卷栗。果帽稍大,一圈圈的,比石槠木的果实长点儿,也是可以吃的。仅栗树,种类就如此丰富,大自然真是奇妙。
我还想吃石山旮的果实,但这里的石山旮已经长到了一二十米,两三抱大,我够不着了,除非它完整地掉落一串果实。想必,樹上的松鼠、果子狸没那么大方,地上一粒也看不见。
还有一种大木,叫酸枣树。这个我认识。我认识酸枣,如果树下没有这些果实,我是认不出这些大木的。捡一粒剥了黄色的皮,放入嘴里,酸酸甜甜,丝丝滑滑,别有风味。吃干净果肉吐出骨头一看,一头有五只眼睛,这里的人也叫它五眼果。能有剩余掉落地上,大概不太受树上居民的欢迎。我想象不出会有何种动物喜欢吃酸枣,它是要含在嘴里慢慢吮的。松鼠会有这耐心?鸟儿也不太喜欢吧,啄破皮之后呢,果肉酸也罢了,就一个大骨头,那些果肉也粘连在骨头上,只能拉出一条条长丝,鸟儿叼不出一丁点儿肉。还真好奇,这酸枣长成这样是想吸引谁呢?大仁蒋哥说,一般是野猪把它吃掉了。其实,它的营养价值挺高,又可通便解毒,还是减肥药,我们叫它“五福临门”。这么好?真是不可小觑。
没想到,这原始树林里有这么多果树,可以养活很多野生动物了吧?大仁蒋哥说,最多的是果子狸,还有野猫、黑山羊、松鼠、撬田鼠、野猪、黄鼠狼、猫头鹰、老鹰等等。消失了的是麂子和豪猪。蛇很多,有五步蛇、乌硝蛇、小眼镜蛇、金环蛇、银环蛇……不要再数了,我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忽然感觉腿上有点刺痛,又有点痒,莫不是被蛇咬了?我最怕蛇了。他呵呵一笑说,没什么可怕的。
石槠木
这是一座高大的森林,为了抢夺阳光,树木都齐刷刷地往上长,每一棵树都有一二十米的样子。中间地带,全是或深或浅或粗或细的树干。可是,这都是些什么树木呢?大仁蒋哥说,这些长在石头上的大多是石槠木。非常坚硬,放进水里会沉下去。只有那棵大的,看见了没有,中间那么空,阳光最多的地方,就是被二〇〇八年的那场雪压垮了一枝。我定睛一看,那些高大的树木果然都是盘踞在青灰的石头上。真是个奇迹,它们是吃石头长大的吗?不然个个都坐在石头上?我知道这些石灰岩,没有花岗岩坚硬,怎么着它也是石头呀!泉井上方的那一排石头上的树木最茂盛,可能是离水近的缘故吧。其中一棵像条巨蟒,尾巴盘桓在突兀的石头上,身子却一个回旋,直上九天去了。我扫上一眼,发现这个树林的树木真的非常喜欢石头,有一大片石头,就有一大片树木立在上面。与村前屋后的石槠木相比,它们没有那么从容,能够尽量舒展身姿,长得宽宽大大、雍容华贵。它们只能长得高高的,枝叶也尽量生长在高空,下面阳光太少,长了也白长不是。在这山里,最坚硬的东西除了石头,就是这些树木了。我突然想起石林的那棵幼苗,估量了一下它们的生长时间,这些高大的石槠木至少生长了上千年。特别是那几棵两抱大的树木。大仁蒋哥说,不知道它们有多少年了,反正我生出来就见到这些树木了,它们一直没变。
我看到了一棵巨大的石槠木。这棵树让我想起了美国巨大的红杉,人们可以开着小汽车从它的树洞里经过。这棵石槠木也有这样的大洞,我从中间穿来穿去,抚摸它巨大的树根,感到无比亲切。它有一个巨大疮疤,正面看像只发威的山羊,侧面看,则是一只微笑的狮子,很像将帅府邸门环上的狮子图腾。我看到了它的果实,黑褐色,灰白的果帽罩住了半边脸。人们曾经用它的果实磨豆腐吃。隔不多远,还有一棵有洞的大石槠木。这么大的树,却很难见到它的果实,是不是什么动物在树上把它们吃光了?
猪血木
大仁蒋哥指着一棵树枝平展成层、姿态优美的树说,这是猪血木。我一听,惊愕得张开嘴巴,说,这可是国家濒危重点保护植物,全世界只剩不到一百来株,残存在广东省阳春市八甲镇,成年植株不到二十株。祖湾蒋哥接着说,这里的猪血木多得是。我瞪大眼睛看着祖湾蒋哥,说,真的吗?真的,我带你去看,有一棵树围有三四米,在这林子里算得上是老大了。是不是?说实话,我的心里是有些小激动的。
经过一片灌木的时候,祖湾蒋哥在前面大声说,倒了,可惜了。啊!我一边避让着灌木,一边朝前方望去。灌木有一人半高,看不见前面的情景。我一着急,就被刺莓拖住了衣服。顺着刺的方向,把衣服取下来,最后一个来到那倒伏在地的大树旁。树围真的有三四米,高约二十米。大仁蒋哥站在树蔸上方的石头上说,原来是生长在这里的,连石头一起倒塌了。会不会也是二〇〇八年的那场雪灾闹的?我脑子里经常冒出二〇〇八这个年份。看树的腐朽程度,大约也就五六年的时间,没有树洞,也没有见到朽坏处,树皮完好,树干也完好,树枝有断裂的痕迹,大概是被雪压断的吧。问题是,它到底是不是猪血木呢?我仔细查验了一番。树皮纹理细腻,灰褐色,皮很厚,里面是土黄色。树干断裂的横截面很奇怪,一个圈圈都没有,围绕着树心成光芒放射状。它的颜色也太过丰富,没法一下说清楚,越是靠近树心,颜色就越红艳。大仁蒋哥说,生树的树干就跟猪血一样,以前拿来做扁担,那扁担红得非常漂亮,把树干泡在水里,水也会像猪血一样红。猪血木的叫法就是这样来的。以前砍来做扁担?猪血木很多吗?多,漫山遍野都是,大炼钢铁的时候全部砍完了。
在一个小天坑旁,有一棵猪血木,两根小苗从它的树蔸上长了起来,已经有三四米高。我突然记起在小寨山的路旁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小苗,也都是从被砍掉树蔸上长起来的。大仁蒋哥说,对,小寨山、大寨山、落花山都有这样的小苗,就是没留给它们长大的机会,长到杯子粗就被砍了當柴烧。坪香村的后龙山上也有猪血木,大的有两米多的树围。东山也就白竹这一带山岭常见,其他地方很少见到。
这里还有一棵大的。祖湾蒋哥在树林里喊。多大?我问。树围两米多。我们跳下大树,爬上高石,急忙往那边去。乖乖,它也选择了一块高石,临着小悬崖,看得我心惊肉跳。不过,看它上面,树干壮硕,枝繁叶茂,让人感觉踏实。它的树皮间寄生了很多细微的苔藓,树干看起来泛着轻微的绿。蒋哥说,那有一棵,这有一棵。我顺着他的手看见了另外两棵,都距它十米左右。跟这棵不同,那两棵非常笔直,包括倒伏的那棵,只有枝干断裂后留下的一个个凸起,我跟前的这棵于两米高处开了三个大枝杈,占据了较为广阔的空间,有些霸气。现在,我基本能认出猪血木了,特征之一就是树干上很多像乳房一样的凸起(它自己断臂,为的是向上长见阳光?);特征之二就是左边生有六七根侧枝,右边不生,右边生有六七根侧枝,左边空着,这么对称,一点不凌乱,是不是很特别很美观?要是满树是花,那不更美?对了,我问大仁蒋哥,它开的什么花?蒋哥说,它不开花,也不结果。咦,不会吧?不开花结果,如何繁衍生殖?我就是不信这个邪,不正是结果的季节吗,我拍了几张树冠在相机屏幕上放大查找。天光比树叶还晃人眼,来来回回地放大,突然发现了两个黄色的圆球果实,藏在黄绿色的树叶间,谁也看不见。整棵树也就发现了这么两个,可见,它的果实确实少见,也许是因为果子狸太多,它们爱吃这样的果实。有果实,肯定就有花。真不知道它的花是啥样。大概是浅淡的小花,非常隐匿,而且,要长到一定的高度才开花结果,要不,村民怎么都说没见过它开花呢。真是一种神秘的树。
其实,数了数水源山的成年猪血木,也只有七棵,当然,还没做地毯式搜寻。后来在大仁村的马路边发现了两棵,一棵树围一米二,一棵树围一米四,水井边的一棵老猪血木,已经砍了。
大仁蒋哥给我砍了一枝猪血木,它的叶是革质的,正好看见一棵野茶树,我拿叶子跟它们比较,发现猪血木的叶子要大,颜色要浅,边缘没有锯齿,猪血木也是山茶科的。我手里拿着那根猪血木,发现它的横截面越来越红,越来越漂亮。它的材质很细腻柔润,摸着有丝绸的感受。我是越来越爱这种树木了。
我抓着那根猪血木高兴地走着,忽然手掌感觉有些刺痛,低头一看,满手掌的细毛,一擦,啊——我痛得尖叫。大仁蒋哥闻声过来一看,发现这截猪血木上有一个什么虫的育婴室,周围布满了这样伤人的细毛。我的手掌红肿起来。他递给我风油精,说擦了会缓解疼痛。他也曾经被刺过,非常难受,不过一夜就好了。看着这小小的一截树木,不禁慨叹,一枝一叶皆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动植物相互依存,相互循环,可见一斑。一棵树的消失,必然会带走依赖它的动物,像人缺了一颗牙齿,势必造成其他牙齿的松动,加速人的衰老。
为了证实这种树木是不是猪血木,我把带回的枝叶拿给那个树木专家看。他轻轻扫了一眼,说,这不是猪血木,是厚皮香。树干很红,俗称猪血柴,跟猪血木同属山茶科。它开花吗?我问他。开淡黄色的花,结圆球形的果,跟浆果一样。什么是浆果?我好像什么也不懂。他说,就跟葡萄、猕猴桃是一样的。那就对了,我对自己说,我看见的那两个果实正好符合。
虽然证实它不是那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我依然喜欢它。如果真是猪血木,我的喜欢有些胆战心惊,好像在走悬崖上的钢丝绳,危险得很,说不定哪天它就灭绝了,岂不让人惆怅死。知道了它是猪血柴,悬着的心马上着陆,突然体验到平凡的好,平凡才最有力量、最有生机,最让人感觉踏实。记得唐支书说,如果确定它是猪血木,并且是国家濒临灭绝的二级保护植物,我们一定会严格保护起来,再不许人砍它。到目前为止,我不想把真相告诉他们,不管它金贵不金贵,它也是稀少的植物,也需要我们保护起来,把疯狂的柴刀支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