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图修古籍

去蒙尘,要先医治。
古籍得以被后人所见,继续它作为一册书的使命,离不开一代代修复师的妙手回春。
他们日日守护在这些残败破碎的纸片旁,用指尖完成与前代修复人的对话,延续古籍的生命,映照文明的厚度。
【引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古籍保护利用”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许多业内专家认为,这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呼吁大众重视古籍文化的价值。
古籍是国之瑰宝,是中华文化血脉传承的重要一支,蕴含着丰富灿烂的人类文明。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也发声呼吁推动古籍保护传承与发展,“让古籍活起来”将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起到强力的助推作用。
但去蒙尘,要先医治。古籍得以被后人所见,继续它作为一册书的使命,离不开一代代修复师的妙手回春。他们日日守护在这些残败破碎的纸片旁,用指尖完成与前代修复人的对话,延续古籍的生命,映照文明的厚度。
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北京纪事》有幸探访了国家图书馆典籍馆文献修复组,看到“古籍修复国家队”传承书业千百年薪火的过程。在这里,国之重宝《永乐大典》、敦煌遗书、清宫“天禄琳琅”、《赵城金藏》、西夏古籍、西域文献得到重生。
这是一份路窄且长的小众职业,每一个修复周期,都足以用百年为计,周而复始,漫漫无期。
对于修书人而言,与旧物交手,“时间”早已超然物外,他们的技艺与记忆,都沉浸在了纸张间,无名无我,倾尽一生,指向永恒。
与时间博弈

杜伟生
想找到文献修复组的工作室,似乎并不容易。
进入国家图书馆,人流会向南北迅速变为两支。往南去,走到尽头,是一座落成于80年代的建筑群。10年前,这里以“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名字挂牌开馆,成为我国第一家典籍博物馆。文献修复组,便藏身于主建筑的某个拐角处。神秘低调,自成它的气场。
每个工作日的早8点半,被称为“古籍医生”的修复师们,会准时到岗。
这里安静似出尘之世。采访这日,修复组的90后女孩宋玥,正为一幅馆藏的拓片题签揭命纸。她将头深深“扎”进操作台,手握毛刷,蘸取清水,浸湿题签,然后用镊子小心揭开,轻而又轻。
题签不大,却足够考验耐心。命纸乃为托纸,与题签融为一体,起保护作用,重要如性命。但其质地纤薄,稍有不慎,便会牵动全身。宋玥要保持绝对的专注,每一个动作,都如履薄冰。
几米外的工作台,四位修复师以同样的姿势,围坐在一件藏品旁,各自入定,互不打扰。这间640平方米的开放式工作室,就这样被无形无声地划分出多个区域。
追溯历史,北魏贾思勰在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书有毁裂,郦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疮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薤(音械)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这是文献中有关古籍修复的最早记录,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这是一群与时间博弈的人,但他们从不用速度来衡量手中的工作。
修书是一个“慢活儿”,且遵循古法。过程往往要经过配纸、制浆糊、分解书叶、补破页、喷水、衬纸、捶平、齐栏、订本、装书皮、包角等几十道工序,每一步都极为考究。操作者要在细碎中,寻得条理。
即便如此,他们出手还是要“快”。竞争者并非他人,正是手中的纸张——随着时光推移,这堆故纸正面临着酸化、絮化、霉蛀、虫蛀等诸多问题。
数据显示,国家图书馆共存古籍善本近300万册,其中近1/3有待修补,近1/10处于濒危状态。按照现有的修复人力估算,完成这项浩大工程,还需数百年。
“古迹重装如病延医”,自古至今,匠人都被托付重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所谓不药当中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补天之手,贯虱之晴,灵惠虚和,心细如发。”这是《装潢志》中描述的大国手的特质,同样为他们一生的追求。
板凳要坐十年冷
在文献修复组,“35歲职业危机”“内卷”都不会成为被探讨的议题。但“没有危机”,曾一度成为危机。
人才缺失,衣钵难续,对于一门手艺来说,是尤为致命的。出于历史原因,上世纪60年代,古籍修复的传承培养曾被迫停滞,老师傅守着技艺,却后继无人,面临严重的断层问题。
那段青黄不接的过往,如今只能在老一辈修复师口中听到。
全国技术能手、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资深修复师朱振彬,便是历史的见证者之一。1980年,古籍修复休眠已久,亟需被唤醒。彼时,18岁的朱振彬,进入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工作,“当时馆里就剩下几位老师傅在做修复了,有识之士说要培养人才,图书馆选了三个年轻人,其中就有我。”朱振彬对《北京纪事》回忆道。
就这样,在前门外香厂路的一个招待所里,朱振彬和其他两位同门,开始了懵懂的修复之路。“吃住学都在那儿,打一屏风,一半睡觉,一半搁四张桌子学习。”师徒四人就这样挤在一个屋子里。
他们的师傅张士达,被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誉为近现代古籍修复“一代国手”。他的履历记录了古籍修复过往的辉煌:16岁时,曾在北京琉璃厂肆雅堂做学徒,而后开了自己的书肆“群玉斋”,鲁迅、郑振铎、冯友兰等文化名家,都是座上客。再之后,北京图书馆在民间寻觅贤才,张士达成为一员,为国家做修复至退休。这一次,他以近80岁的高龄再度出山,只因“修补破书是最喜欢做的事,若使古老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才是最幸福的”。
不过,教学才进行了一年多,因身体原因,张士达不得不回到南昌休养。所幸,经馆里协调,徒弟三人可以一同南下,在江西图书馆又一起度过两年,最终学成而归。
1983年春,朱振彬回到国家图书馆善本组,成为一名修复师。朱振彬记得,那时候的条件很艰苦,也很简陋,“修复室是在老馆的平房里,也就40多平方米。只有五六个修复人,环境不行,设备也不行”。
起初,朱振彬并不上手修复珍贵古籍,板凳要坐十年冷,修复要看十年功。技艺的精进,更多来自心性的磨炼。几经沉淀,朱振彬守住寂寞,90年代,开始陆续参与《永乐大典》、“敦煌遗书”等诸多国宝级的修复项目工作中。
不久前,作为项目首席专家,朱振彬宣布:历经8年的清宫“天禄琳琅”修复工程完成。这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最大的一次针对珍贵古籍的专项修复项目。入行42年,功德圆满,今年年末,他即将退休。说来奇怪,或许修复即修心,掸去旧尘的同时,岁月会被凝固。若不是头上的白发,很难看出眼前的朱振彬已年届花甲。
择一事,终一生。在这件事上,连时间也给予宽容。在每一本古籍中,修复的痕迹,同样是匠人的底气,他们虽无名,但今生所留,在未来都会有迹可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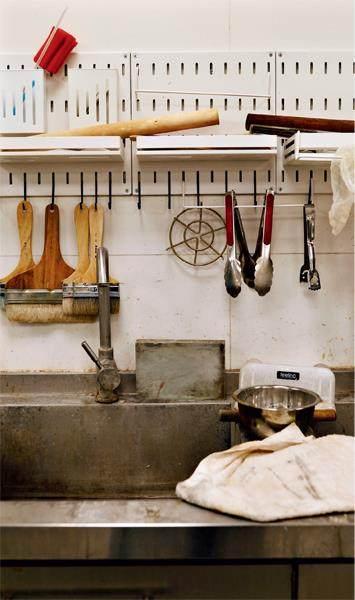
先救命 后治病
“我现在是闲人一个。”
一口京腔入耳,说话的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曾经的修复组组长杜伟生。入行40多年,如今虽自嘲为退休的“闲人”,但每天上午半天,他还会出现在办公室。
“就转转,反正离家也近。”杜伟生笑道,“他们有问题了来问我一下。但都干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了,问题基本不多了。我现在就是个摆设。”
一切是那么淡然。甚至聊到入行的机缘,杜伟生也惜字如金:“就是工程兵退伍分配到这里的”,“当时挺满意,起码不用像之前那样在外头风吹日晒了。”
打开话匣子,还是要将话题落到具体的工作上。说到那些过手的、饱经沧桑的藏品,便有了抑制不住的成就感:
《四库全书》《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都是国家图书馆尤为重要的珍藏。后三项的修复工作,杜伟生都有参与。
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挽救国宝“敦煌遗书”。1989年,大英图书馆修复组人员来中国考察,他们认同杜伟生对纸张保护的观点,邀请他去英国修复大英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在国外工作的半年时间,杜伟生学到了英国的处理手法。
1991年,国家图书馆启动“敦煌遗书”修复项目,主持工作落到了杜伟生的肩上。“根据过去裱画的手法,以及大英图书馆的修复经历,做了一个方案,得到了领导同意。”在同冀淑英、方广錩等馆内专家共同商讨下,
最终定下“ 整旧如旧”“最少干预”“可辨识性”“可逆性”四大原则——这也是第一次,将修复原则明确落实到文字上。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1.6万余号敦煌遗书,约占全部存世数量的1/4。所以,他们要与时间赛跑。在操作过程中,杜伟生提出要“先救命后治病”。“对那些马上就要坏的,进行抢救性修复。然后再去修理那些有毛病的。”
此外,杜伟生还发现,“敦煌遗书”打开后,“卷子弯弯曲曲的,有的是大弧形,有的是S形。”这说明,在唐代做书时,没有上墙晾干这道工序。“过去没用过的技术,不能用。”杜伟生决定用压平替代上墙,保障对古籍的绝对安全,也为后世的修复留有余地。
谈及最为棘手的事情,杜伟生认为是“找材料”。所谓旧物难觅,补纸要在材质、颜色、纹理等等方面,无限接近原件本身。“敦煌遗书”由皮纸和麻纸构成,麻纸在国内近乎绝迹,修复时他们最先选的是文物级的乾隆高丽纸,但厚,补出来不好看。几经比对,最终选定桑皮纸、构皮纸完成修复。
严苛,是属于手艺人的一份真。在纪录片《古书复活记》的镜头中,我们看到,杜伟生为了寻找合适的修复配纸,特意来到手工造纸坊,和店主一起用时两年,研究古纸制作工艺,复原古籍纸张。
采访这日,文献修复组的几名修复师正在为 “敦煌遗书”配纸。新一轮的修复,即将开启。这一次,年轻的修复师尝试了自己打浆,全过程制造补纸。
作为外行人,实在好奇这项庞杂的工作是否存在一个“考核打分系统”?杜伟生连连否认,
他说这一行“无过即是功”,评定修复质量的好坏,绝不是现在,而是后人说了算。
“过了百年,你修复的东西经得住考验,后人说你修复得好,才是最好的评价。”
“这行容不下那么多人”
近年来,随着宣传及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热播,古籍保护渐渐走出深阁,许多人开始关注到这一领域,并对这项工作心向往之。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2007年之前,全国古籍修复师不足100人。
在文献修复组,人员可按年龄分两个梯队,一组为退休返聘或即将退休的老师傅,修复年限多在35年以上;另一组则以80后、90后构成,他们在2007年后入组,修复年限最久的在15年。
2007年,是被古籍修复师视为“春天”的年份,是分水岭般的存在。这一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在培养修復人才方面,采取“培训班、高等院校、传习所”三位一体模式,人才队伍自此开始壮大,长期的空档期,得到添补。

朱振彬
紧接着,2008年,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1年,传统书籍装帧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甲骨传拓技艺、敦煌遗书修复技艺入选北京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保护工作宛如新生,前景愈发明朗。
据相关报道介绍,国家图书馆为全国2000多家古籍存藏单位培养、培训古籍保护人员超过1万人次,修复专业人员目前已超过1000人,学历涵盖大专到研究生。
依舊存在“物比人多”的境况,但杜伟生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很多人说古籍修复后继无人,但我觉得,不要这么说了,因为这行是小众的小众,它容纳不了那么多人。”
古籍修复,需要“绵绵若存”式的延续。“为了保证传承,绝不能一下投入太多人力,古籍修完了,技术也就断了。我们这个路,非常窄,但是很长,只要古籍还在,修书人就得跟着活着,这个技术就能存在。”杜伟生说。
朱振彬也有同样的看法,“修复的对象太珍贵,这一行出才的比例非常低。”古籍修复更考验综合性素养,朱振彬打了个比方,一个培训班有50人参加,但最终能干这行的,可能仅有一两个人。新人必须要过“心理素质”这一关,过关的条件是:修复珍贵古籍。“必须有这个经历,才能进步,才能提升。”

就是要稳得住,要精益求精。
技术角度则有什么绝技?朱振彬语气平淡:
这也是从张士达师承而来的,“我的师傅每一步都特别讲究。比如配纸,别人可能配个一天半天的,就差不多了,他不行,他要特别精致。”
老一辈的做派,成为一代代职人追寻的信仰。
采访完毕,走出修复组,正巧偶遇一群正在典籍博物馆门前拍照打卡的游客,恍如隔世。他们或许不知道,就在这些展厅、这些古籍展品的楼下,一群修书人正在自己的清修之地,吐故纳新。
旧纸张一页页翻过,个人在其中早已无足轻重,他们的世界更为宏大,那里藏有历史的生息。
摄影 马捷 编辑 张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