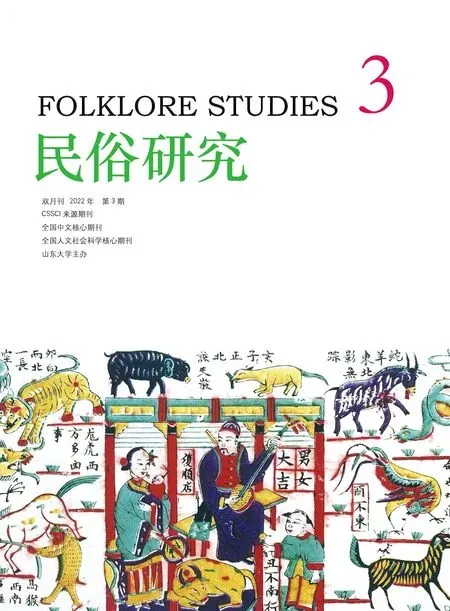图文共现的民俗档案:清代至民国时期妙峰山庙会的多元记录
林海聪
自清代以来,妙峰山庙会在京津地区享有盛名,吸引了文人墨客、官员家属以及香会组织前往观游、朝圣,在他们撰写的岁时笔记、碑刻铭文、地方史志中留下大量关于妙峰山庙会的记录。这些文字记录一方面描绘了妙峰山的自然风景与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也会钩沉庙会的历史源流、仪式程序以及庙会情境。受书写媒介的物质性限制,这些文字记录大多篇幅短小,很难详尽记录妙峰山庙会的热闹场景。不过,除了依托于文字而呈现的这类记录之外,尚存一些委托定制的妙峰山庙会风俗画和石印插画,以及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和无声纪录片。这些图像资料一部分采用了传统的绘画技法来设色构图,艺术性地描绘庙会的活动图景,另一部分则使用现代视觉技术来纪实地呈现庙会现场。这些图像类民俗资料虽然制作风格和技术各异,但都共同以直观形象的视觉元素来记录和描绘北京妙峰山庙会期间民俗主体的仪式活动,成为一套视觉表达妙峰山庙会的另类“民俗资料”(1)就载体而言,本文涉及文字、图像和影音三大类民俗资料。如就功能而言,这些民俗资料游可分为研究记录型和生活实用型。有关民俗资料分类的论述,参见王霄冰:《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民俗研究》2020第3期。。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妙峰山庙会青眼有加,已围绕妙峰山庙会及其香会组织的历史发展过程、碑刻文献资料的文献价值、进香朝圣的仪式活动场景等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编纂了当代妙峰山庙会的节日志。(2)相关研究,可参见顾颉刚编著:《妙峰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晓莉:《碧霞元君信仰与妙峰山香客村落活动——以北京地区与涧沟村的香客活动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陈建丽:《北京妙峰山碑刻文献与香会(花会)组织的集体记忆》,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韩同春:《北京幡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张青仁:《行香走会:北京香会的谱系与生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美]韩书瑞:《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周福岩、吴效群译,《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岳永逸主编:《中国节日志·妙峰山庙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然而,很少有学者针对妙峰山庙会的记录方式进行梳理,也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大量珍贵的图像类民俗资料。循着这一思路,下文将以特定资料的创作时间和记录模式为梳理的线索,讨论不同媒介的妙峰山庙会民俗资料在还原历史现场、呈现民俗关系等话题上所具有的民俗书写与文化阐释的力度及限度,希望对妙峰山庙会的研究略做补充。
一、妙峰山庙会的传统文字书写
妙峰山因其地势峻挺、风景优美而成为京西一带的名山奇胜,不少前往观游的古人选择使用文字的形式,记录和描绘了他们对妙峰山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个人体验和身体记忆。同时,妙峰山还是北京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圣地,吸引了大量京津香客前往朝圣,并留下不少香会碑刻。因此,关于妙峰山庙会的记载常散见于北京地方志、文人岁时笔记以及碑刻等文献中。成书于清代的这些文献,就文体而言多数属于岁时记类文人笔记,还有一部分则是侧重于记录史实的地方志和碑刻;生成于民国时期的文献除少量碑刻外,多为实用性为主的旅行指南类书籍。
(一)地方志、碑刻中的妙峰山庙会
通过检阅相关妙峰山资料汇编(3)本文所使用的文献汇编资料,出自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8-62页;孙景琛、刘思伯编:《北京传统节令风俗和歌舞》,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43-63页;北京市东城区园林局汇纂:《北京庙会史料通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135-252页。,可知最早直接记录妙峰山庙会的文献出自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宛平县志》,该志卷六“艺文”一节引述了张献《妙峰山香会序》的全文,将其作为当地比较重要的一通金石古文收入县志中。(4)该志的准确名称应为康熙《顺天府宛平县志》。序文内容详见张献:《妙峰山香会序》,王养濂等纂修,王岗、易克中等点校整理:《康熙宛平县志》卷六,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整篇序文虽以里人朝顶妙峰山为引,但张献只是借题发挥,意在提倡县民孝悌持家,移风易俗。实际上,这部县志将该序收录于艺文卷内,更多的是看重它作为当朝艺文碑刻的文化意义,用以彰显一县文教的深厚。张献为宛平籍“邑人”,时任“钦差督理街道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一职,编纂者将张献这一地方大员所作之序录入方志之中,实是希望借此来增附该县的文化资本。不过,这也在不经意间为后人研究妙峰山保留了一份珍贵的碑刻史料,成为容庚、顾颉刚等人用来考证妙峰山香会源流的直接证据。
除《宛平县志》外,光绪年间编纂的《顺天府志》引述《文宗圣训》,谈到咸丰二年(1852)“禁京西妙峰山夏秋二季烧香人走会”的朝廷政策。(5)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故事二·时政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40页。妙峰山在咸丰、光绪年间隶属顺天府宛平县,府志的这条记载与《清文宗实录》第五十二卷“咸丰二年正月辛巳”中的记录是相符的。(6)中华书局编:《清实录》第四十册《文宗显皇帝实录》第五十二卷“咸丰二年正月辛巳”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702页。这说明咸丰朝曾对妙峰山庙会出现的礼俗教化问题严加禁止,只是当时的清廷忙于“剿捻”,无暇顾及妙峰山庙会的查禁事宜。《宛平县志》与《顺天府志》的编纂时间不同,记录的角度各异,分别从民间风俗和官方政策两个方面勾勒了妙峰山庙会在清朝的历时发展过程,为后世追溯妙峰山庙会的源流衍变提供了史料。
除上述地方史志外,还有大量由清代统治者、官员和民间香会组织所立的香会碑刻。根据陈建丽的统计,妙峰山现存清代碑刻共六十通,多为乾隆、同治和光绪三朝镌刻,最早的是清康熙二年(1663)初立、道光十六年(1836)重刻的《清引善老会碑》。民国的碑刻有十通,最早的是立于民国八年(1919)四月的《张帅夫人重修碑》。(7)陈建丽:《北京妙峰山碑刻文献与香会(花会)组织的集体记忆》,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8-22页。受书写材料的物质条件限制,这些碑文常常篇幅短小,其内容无外乎称颂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灵验,阐述香会组织的立碑缘由、行善活动情况以及立碑过程,最后再刻录香会组织成员或捐款刻碑的信众名单。此外,根据碑刻内容可知,清代至民国时期香会立碑的时间多选择在“春香”期间,仅少数清代香会碑立于“秋香”时期。而且相较于民国碑刻而言,清代立碑成员的身份更加多元化,其中不乏皇室成员、地方官员及其家属以及京津一带的商户、民间香会组织。
(二)文人笔记中的妙峰山庙会
相较于地方史志极少记录妙峰山庙会这类风俗活动,清代的文人墨客却极为关注妙峰山庙会,相关记载尤常见于各类竹枝词、笔记和岁时记中。(8)妙峰山在清代之前被称作“妙高峰”。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曾作小品文《妙高峰记》,简述妙峰山的地理山势以及法云寺、香水院这两处山中建筑的格局和环境。在袁氏之后,还有明代吴侗、于奕正合著的笔记《帝京景物略》(1635),该书提及仰山、滴水岩、法云寺等妙峰山的自然景观、佛教场所,并搜录了不少山水诗文。然而这些记录皆未曾提及庙会,故本文暂不将之纳入讨论。参见袁宏道:《妙高峰记》,陈梦雷编纂,蒋廷锡等校订:《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卷十《西山部汇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刘侗、于奕正著,孙小力校注:《帝京景物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0-331、463-472页。这些文献包括清嘉庆二十年(1815)刊印的满人得舆著《草珠一串》(又叫《京都竹枝词》)、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印的让廉著《京都风俗志》、成书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满人震钧著《天咫偶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印的满人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9)得硕亭:《草珠一串》,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7-58页;潘荣陛、富察敦崇、查慎行、让廉:《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人海记·京都风俗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除《草珠一串》为竹枝词诗集外,其余文献多出自清晚期满人之手。(10)受限于材料,让廉的生平暂不可考。《天咫偶闻》与地方志的体例大致相似,关于妙峰山的内容载于该书卷九“郊坰”,而《京都风俗志》和《燕京岁时记》则按照岁时记按时间顺序行文,主要介绍北京城的历史掌故与风土民俗,其中关于妙峰山庙会的记载罗列于四月间诸节俗之中。上述文献中关于妙峰山庙会的内容,详列如下:
西山香罢又东山(天台山与妙峰山),桥上(宏仁桥俗名马驹桥,桥头有娘娘庙,俗呼桥上)娘娘也一般。道个虔诚即问好,人人知是进香还。(11)得硕亭:《草珠一串·游览》,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7页。其中“宏仁桥”应为“弘仁桥”。

京北妙峰山香火之盛闻天下。陈文伯《颐道堂集》中有诗咏之。山有碧霞元君祠,俗称娘娘顶。岁以四月朔开山,至二十八日封山。环畿三百里间,奔走络绎,方轨叠迹,日夜不止。好事者联朋结党,沿路支棚结彩,盛供张之具,谓之茶棚,以待行人少息。食肆亦设棚待客,以牟厚利。车夫脚子竟日奔驰,得佣值倍他日。无赖子又结队扮杂剧社火,谓之赶会。不肖子弟多轻服挟妓而往。山中人以麦秸织玩具卖之。去者辄悬满车旁而归,以炫市人。(13)震钧:《天咫偶闻》卷九《郊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4页。
妙峰山碧霞元君庙在京城西北八十余里,山路西四十余里,共一百三十余里,地属昌平。每届四月,自初一开庙半月,香火极盛。凡开山以前有雨者谓之净山雨。庙在万山中,孤峰矗立,盘旋而上,势如绕螺,前者可践后者之顶,后者可见前者之足。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趾,香无断烟,奇观哉!庙南向,为山门,为正殿,为后殿。后殿之前,有石凸起,似是妙峰之巅石。有古柏三四株,亦似百年之物。庙东有喜神殿、观音殿、伏魔殿,庙北有回香亭,庙无碑碣,其原无可考。然自康乾以来即有之,惜无记之者耳。进香之路日辟日多,曰南道者三家店也,曰中道者大觉寺也,曰北道者北安河也,曰老北道者石佛殿也。近日之最称繁盛者莫如北安河。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以各路之人计之,共约有数十万。以金钱计之,亦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14)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潘荣陛、富察敦崇、查慎行、让廉:《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人海记·京都风俗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2-63页。
相较于其他三则记录,《草珠一串》这首风俗竹枝词限于文体,篇幅极为简短,点到即止地提及包括妙峰山在内的北京四月诸庙会及其方位,并指出香客口称“虔诚”即是“进香回家”的标志。其他三则文人笔记记载相对较为丰富,几乎都将妙峰山庙会视为北京西郊一带极富代表性的地方民俗“巨观”,皆提到妙峰山的地理位置、自然风景和会期等信息,以及香客和香会组织的仪式活动内容。尤其是《京都风俗志》,还描述了庙会期间文会所设的茶棚布置及其仪式功能,以及开路、秧歌、太少狮、五虎棍、杠箱等武会进香献艺的表演内容及其使用的各种表演道具。只是仅从这些文字记载,我们很难判断作者的文字记录到底依据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抑或是道听途说。
那么,为什么关于妙峰山庙会节俗的文字记载多出自晚清满人之手呢?正如前文所言,妙峰山庙会于道光、咸丰二朝遭到官方的禁止,当时的国家局势也不稳定,香客难以自由往来妙峰山。直至光绪朝时,该庙会才因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重新回复了生气,因此晚清民众有机会亲眼见证了妙峰山庙会由衰落重新复兴的过程。而且,北京城内的香会按照旗、汉分居的格局,形成了“井字里外”的香会等级制度。无论是得硕亭、富察敦崇还是震钧,他们都是满族官员的后代,自然对满人主导的妙峰山香会活动十分了解,乃至引以为傲。然而,晚清时期满、汉关系的日益紧张以及满人地位的逐渐衰落,促使这些满人后裔对以妙峰山香会为代表的清都旗人文化产生了一种怀旧心态。
第一,尽快研究制定《合作社法》,确立合作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包容上述各种合作社类型。目前,农机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都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有的在工商部门注册,有的在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前者注册为合作社法人,后者则不具备经营职能。这种情况说明,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无法容纳实践中出现的合作社类型,不能满足广大农民发展合作经济的需要,必须制定一部统一的《合作社法》,对上述各类合作社的运作规则进行具体规定。
(三)旅行指南书中的妙峰山庙会
第三类关于妙峰山庙会的文字记载来源于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北京旅行指南书。这类工具书主要记录了当时北京的历史地理、政治机关、社会团体、街巷地名、名胜古迹、礼俗习尚、食宿交通等诸多实用信息,它们的出版有助于旅客们按图索骥地考察、参观北京各处的名胜古迹,了解北京的地方风土礼俗。其中,提及妙峰山庙会的代表性指南书有徐珂编纂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北平民社编的《北平指南》、马芷庠编著的《北平旅行指南》以及金禅雨的《妙峰山指南》。(15)参见徐珂编:《增订实用北京指南·第二编 礼俗》,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4-15页;北平民社编:《北平指南·第十编 附录·走会》,北平民社,1929年,第7-8页;马芷庠编:《北平旅行指南》,北平经济新闻社,1935年,第180-181页;金禅雨:《妙峰山指南》,名胜导游社,1936年。尤其是金禅雨的《妙峰山指南》是一本专门针对妙峰山庙会展开旅行导览的大众读物,它大体记录了妙峰山庙会的各类进香程序、香会组织的种类名目及相应的仪式活动、特殊香客的进香方式和提醒香客的“进香须知”等,内容细致翔实。
相较于其他三种指南书将妙峰山庙会编排在“庙会/走会”条目之下,内容多侧重于交代游览路线、庙会活动内容以及食宿条件等信息,马芷庠将关于妙峰山庙会的文字编入“古迹名胜”条目之下,还对妙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净山雨归功于“娘娘法力所为”的说法“殊为可哂”,并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妙峰山天气骤变如寒冬,致使朝山香客多有冻死的事件反驳“人间善恶、世态不古,略施佛法,以示警戒”(16)马芷庠编:《北平旅行指南》,北平经济新闻社,1935年,第180页。的神秘说辞。马芷庠这种截然不同的编纂态度颇值得细究:一方面,自晚清至民国以来,时人立倡“反迷信”运动,对妙峰山庙会等民间信仰活动多持批评态度,思想开放的马芷庠显然也受到影响。或许,这也是为何上述指南书多将妙峰山庙会的性质定位为“礼俗”而非“宗教”的原因;另一方面,作为“名胜”的妙峰山风景秀丽,而且妙峰山庙会对旅行指南书的受众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妙峰山理所当然地成为出版商关注的旅游地。马芷庠也未能免俗,他遵循地方志和文人笔记的旧例,在《北平旅行指南》中详加介绍了妙峰山。只是,他将包括妙峰山娘娘庙在内的宗教信仰场所一律视为“名胜古迹”,试图弱化它所蕴含的宗教色彩,以迎合民国读者们的思想观念。
二、妙峰山庙会的图绘记录
如果说受限于记录技术,中国的文人墨客多采用文字书写的形式来记录他们对妙峰山庙会的个人体验,那么清末至民国时期实际上还流行另一种以图绘为媒介来记录妙峰山庙会的形式,即诉诸视觉化表达的风俗画和石印插画。
(一)风俗画中的妙峰山庙会
风俗画是以社会风俗民情、日常生活场景为题材的绘画类型,是一种保留特定历史时期民俗活动样貌的技术方式。作为当时首都的“标志性文化”,妙峰山庙会同样受到清代画师的关注,留下不少以“妙峰山进香”为题材的画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首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清后期纸本《妙峰山进香图》轴。(17)关于《妙峰山进香图》的详细图绘内容、绘画风格等信息介绍,可参见李露露:《清代〈妙峰山进香图〉》,《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0期,1989年。这是现今最直观反映清后期北京妙峰山庙会活动的一幅风俗画。整幅图为立轴纸本,纵长205.5厘米,横宽114.6厘米,画师信息暂不可考。该图画中的人物、建筑呈设色风格,古朴而笔触细腻,整张图轴按庙会活动时空分门别类地呈现了信众进香的盛况:上部分画幅为妙峰山金顶的核心建筑物惠济祠,中间部分画幅呈现的是前往妙峰山庙会进香的信众,最下部分描绘的是涧沟村在庙会期间的生活场景。全图以特定的“一场”妙峰山庙会为视觉表达内容,按照文化空间的特性将整个妙峰山庙会的宗教性、娱乐性与商业性三种活动立体地呈现在同一幅图轴之中。相较于文字,视觉化的绘画可以更为一目了然地向它的观众呈现清代妙峰山朝山进香的活动场景,更为直观与形象。
这种以图像为文化表现形式的传统风俗画不仅在中国民间被普遍使用,还曾获得来华日本留学生的青睐。1926年3月,青木正儿利用在北京留学的机会和东北帝国大学的资金支持,曾委托北京友人董理延请北京画师刘延年等三人,绘制了117张彩绘风俗图,其中有两幅题为《刷报子》《耍狮子戏》的画作恰好描绘了妙峰山庙会活动。(18)[日]青木正儿编图、[日]内田道夫解说:《北京风俗图谱》,张小钢译注,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186-187、236-237页。不过,青木正儿在编图时将《刷报子》编在“市井”类,而《耍狮子戏》则编在“伎艺”类,而不像其他岁时笔记那样将妙峰山庙会归类在图谱的“岁时”类别之中。这两幅风俗画抽离了画面人物行为原初发生的妙峰山及其庙宇空间,对画面主题采取了去语境化的构图方式,而这种描绘手法在其他风俗画或外销画中随处可见。其优点在于突出了画幅上所描绘的内容,而且节省画工的创作时间,但也为阅读者带来了不便。例如,《耍狮子戏》里的“舞狮子”在中国民间并非是妙峰山庙会所独有的一种民间技艺,它可以出现在正月的街头巷尾,也可以出现在店铺开业的场景之中,就此难以断定这种技艺展演的文化语境。
的确,如果阅读者对北京风俗并不了解,加之画面并未绘制妙峰山的风景与建筑,因此很难让读者将这两个仪式场景与妙峰山庙会直接联系起来,这就需要借助图文的解说。内田道夫通过文字补充了图像内容的历史语境,点出这两张风俗画所描绘的民俗活动实际上属于妙峰山庙会的仪式展演。作为一位北京本地的风俗画师,刘延年选取进香朝圣的香会组织作为代表“妙峰山庙会”的标示性视觉元素,而非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或者山中庙宇、神像。相比于《妙峰山进香图》整体勾勒庙会的活动内容、仪式空间以及民俗主体,北京人刘延年绘制的风俗画则是片段式、多图幅地展示了妙峰山庙会的两个仪式活动环节,但他所描绘的人物形象比《妙峰山进香图》更为生动细腻。
(二)石印插图画中的妙峰山庙会
19世纪40年代左右,石印这种新型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促进了《点石斋画报》等新式画报的大量发行,也为中国人带来了先进的现代视觉技术体验。(19)关于石印技术从晚清开始传入中国的研究,可参见韩琦:《晚清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石印术的传入为例》,韩琦、[意]米盖尔主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4-127页;[美]芮哲非:《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张志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0-138页。《点石斋画报》虽然发行地远在上海,但它的主创者也曾关注过北京地区的妙峰山庙会,并以不同的构图思路绘制了石印画像,向画报的阅读者们介绍了这项极富北京地方文化特色的民俗活动。
1885年5月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丁集曾刊载一幅《妙峰香市》,由海派画家顾月洲绘制原稿。(20)顾月洲绘:《妙峰香市》,《点石斋画报》第四十四号,1885年5月,第64页。妙峰山主峰及惠济祠布局在整张图的中轴区域,左、右两部分画幅描绘的则是妙峰山香道以及进香的香客们。由此可见,《妙峰香市》主要表现妙峰山作为“风景名胜”的视觉符号内涵。而且,该石印插图最上部分的空白区域,由绘制者增加了题名以及一段描述妙峰山香会场景的文字说明。(21)详见林海聪:《妙峰山庙会的视觉表达——以甘博照片为中心的观察(1924-1927)》,《民俗研究》2019年第5期。受限于画幅,顾月洲有选择性地描绘了一些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或节日物品来“标记”这幅风俗图的文化含义,帮助它的受众们可以有效辨识出所绘图景即为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值得注意的是,《妙峰香市》的画面与题图的文字说明实际上并不是绝对的一一对应。这篇文字说明,一方面写意性地勾勒了妙峰山的“景观”特征,另一方面则意在解释这幅风俗图的制作源流,却并未提及图像所描绘的“朝顶进香”的香会成员、香客以及行乞的乞丐。
作为一份主要发行于上海地区的画报,《点石斋画报》并未局限于所在地的社会新闻动态,而是不断向其读者展现外地新奇热闹的民俗文化,这从侧面说明北京碧霞元君信仰及其妙峰山庙会活动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京、津一带,早已声名远播,连现代世俗化的上海《点石斋画报》创作者都会对其产生兴趣,并多次以石印图像的形式呈现这种传统的民俗信仰场景。
那么,是不是所有图绘妙峰山的资料都是以一种正面的、赞颂的态度来创作的呢?并非如此。天津地区发行的《醒俗画报》上曾经刊印了一张题名《烧香无益》的石印风俗画。(22)本文图版转引自侯杰、王昆江主编:《清末民初社会风情:〈醒俗画报〉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8页。该书未列明该图创作和刊布的具体时间,然根据《醒俗画报》的创刊历史可知,这张石印画大致绘制于1907年至1913年间。正如前文所言,熟悉北京庙会文化的阅读者们都知道“报单”是庙会中最常用的一种标志性仪式用品,生活在京、津一带的画师与他的受众共享这些民俗知识,他特意选取粘贴在某处深巷门墙上的“报单”以及“代香会”(23)“代香”即顾颉刚提到的“寄香”,指代替他人烧香或上香。据李世瑜的说法,清末妙峰山香火鼎盛,远近闻名,连天津人也热衷去“朝拜进香”,还出现一些代香会。那些无力亲自去妙峰山的信众可以买个檀木制作的“香牌子”,将许愿的内容写在其上,再交些钱和香烛纸品,代香会就可以替许愿者带上山。详见李世瑜:《天后宫里的王三奶奶》,蔡长奎主编:《天津天后宫的传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页。这种特有的香会组织作为图绘对象,以之表现妙峰山庙会在民众生活中的具体展开情况。
烧香无益
昨见沿街之上粘贴报单,上写“京西北金顶妙峰山天仙圣母、王三奶奶有求必应”,亦有在自家门傍贴“某人代香会”,又在妙峰山附近数十里山路之上,有善士办理路灯、铁栏杆、茶棚,施舍茶水、姜汤等等,所用银子甚广。想数年前有一次,善男信女正在烧香求福、虔心拜佛之时,忽然天降大雪,将上山烧香的人冻死无数,可见烧香的事毫无好处,不能得福,反倒须得祸。前者马师夫坟地,亦是因为烧香,淹死多人(见第三期报)。有此二次,想同胞亦可以省悟一点,像茶棚、路灯等项的银子,若办理点公益之举,岂不是较比着这迷信妄想求福强的多么?(24)侯杰、王昆江主编:《清末民初社会风情:〈醒俗画报〉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8页。该书誊录的《烧香无益》有个别文字错误,本文已据图上文字略加订正。

图1 《烧香无益》(原刊于《醒俗画报》(25)侯杰、王昆江主编:《清末民初社会风情:〈醒俗画报〉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作为一份面向普罗大众发行的即时性新闻画报,《醒俗画报》选择北京妙峰山庙会,图文并茂地呈现了北京地区平民百姓有关岁时节俗的风土民情。不过,就《烧香无益》这幅石印风俗画的审美价值而言,由于画面没有出现任何与庙会有关的人物形象,它的构图要比《点石斋画报》显得单薄和冷清。因此,贴着报单的门墙虽然处于画幅的视觉中心,但题文以及图像中出现的文字才是真正完成意义建构的文化表现形式。整幅石印图从图画到文字都将“妙峰山庙会”视为有待风俗移易的“迷信”进行描述,以一种讽刺与劝诫的口吻传递画报试图通过“醒俗”来改良社会风气的办报意图。妙峰山庙会在清中期曾与民间宗教“四大门”关系密切,庙会人员鱼龙混杂,且存在有违礼教之处,因此即便获得诸如慈禧太后等帝国统治阶层的支持而迅速兴盛,但仍然受到清廷的管控和限制。的确,妙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对民间具有道德教化功能,但是庙会活动过于追求“抢洋斗胜,耗财买脸”(26)吴效群认为“抢洋”即是香会在行为上标新立异,“斗胜”则是智慧上的较量,“耗财买脸”则是指庙会活动表现得慷慨大度。本意是通过精力、智识与财力上的竞争,表现优异的香会获得民众更多的称赞和关注,而香会的主事者们还会成为众人敬重的民间权威,以此来拓展香会的社会声誉和人际关系网络。但是,过度竞争容易导致浮夸虚荣的现象,最终浪费钱财,自然不受鼓励。详见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4-138页。,空耗民众的钱财,香会之间偶尔也会出现殴斗的暴力事件,还有一些非法之徒假借民间信仰活动敛财诈骗,损害了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道德感召力。正如高万桑等学者所述,经历庚子事变后的新知识分子开始运用西方科学观念将中国的宗教信仰视为“迷信”,以偏概全地借助某些偏激的社会新闻对妙峰山庙会习俗进行舆论批判,甚至自上而下地推动“庙产兴学”,希望以此来启蒙社会民众,改良社会习俗。(27)关于清末宗教政策与“庙产兴学”运动及其对妙峰山信仰变迁的影响,可参见[法]高万桑:《近代中国的国家与宗教:宗教政策与学术典范》,黄郁琁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4期,2006年;岳永逸:《教育、文化与福利:从庙产兴学到兴老》,《民俗研究》2015年第4期;李俊领:《晚清京西妙峰山信仰礼俗变迁三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4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28页。
那么,毛笔彩绘的风俗画和石印的画报插图是如何将妙峰山庙会从文字书写转变为视觉表达的呢?两者在“妙峰山庙会”这同一个民俗文化主题的视觉表达上有何异同之处呢?相较于毛笔彩绘的《进香图》与《刷报子》《耍狮子戏》等风俗画,《妙峰香市》《烧香无益》虽然创作技术采用的是当时最为先进的石印技术,但是画面的取景方式与绘画风格还是相当“传统”的,两者有其一致性与差异性:第一,就题材分类而言,两者皆为表现庙会民俗活动的风俗画,都属于图像类民俗资料。石印画在成像技术上是现代化的,但给阅读者带来的视觉效果依旧忠实于绘画手稿的工笔山水风格,仍然呈现出传统的视觉审美趣味。第二,这批图像类民俗资料仅《进香图》这幅立轴彩绘图从宏观的、整体的全景角度勾勒了庙会的自然与文化空间,细腻地呈现了朝圣民众的各种活动场景与神态,其他风俗画都是采用中景的角度,截取庙会期间特定的仪式场景或民俗主体进行描绘,展现的是妙峰山庙会更细节化的图景,它们的制作形式与传统图谱是类似的,因而图幅并不像《妙峰山进香图》那般可无限延长。而且,石印画在笔触上比毛笔彩绘的风俗画更加细腻、真实,表现的人物形象自然丰富多姿、生动形象。第三,不同于《妙峰山进香图》《刷报子》《耍狮子戏》等彩绘画主要依赖视觉元素表达文化主题,《妙峰香市》《烧香无益》等石印画都增加了题文作为“文字框架”。首先是因为这些石印画的阅读者多是不熟悉妙峰山的外地人,需要依靠文字来补充信息,其次也是画报类刊载物在体裁上的必然要求。这些石印画作为图像部分与图上的文字说明相结合后,共同构成一则图文互见的新闻报道。题词与视觉呈现的图像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它们或描绘妙峰山的秀美风景,或记叙娘娘庙庙会的热闹场景,或向读者讲述一段与妙峰山庙会相关的社会奇闻。第四,这批传统绘画题材的庙会图像在构图上是否描绘具体的背景存在巨大的差异,它受到图幅比例和物质媒介两个方面的限制。相较于刘延年等北京画师绘制《北京风俗图谱》时,需要将庙会不同人物和场景绘制成多幅画面,难以再费工费时地绘制背景,《妙峰香市》作为大开画幅的立轴,给画师提供了足够的图像空间进行庙会场景的刻画,但是它的背景描绘仍然是写意性勾勒。不过,石印画利用现代视觉技术为创作者和读者提供了体验复杂的现代视觉观感的机会。新技术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线条在细节上颇为流畅细腻,以往不被重视的背景得以重回读物的图像描绘之中,将人物、背景和情节三者有机结合,让阅读者看图时能够更为完整地把握图像内容。
三、妙峰山庙会的影像档案
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报刊画师、民间香会组织,都已借助文献、碑刻、绘画等传统的民俗书写方式,针对妙峰山庙会进行过民俗记录。除此之外,随着摄影技术自近代以来传入中国并为不同身份背景的拍摄者所用,这为妙峰山庙会留下一批带有旅行纪念与实地考察意义的现代影像资料。得益于影像制作者的真实在场,这些早期的庙会影像记录为我们还原历史中的妙峰山庙会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视觉化的图像类民俗资料。
1925年,民俗学家顾颉刚等人曾前往妙峰山,进行朝圣进香调查。顾颉刚在考察过程中细腻地发现了金顶娘娘庙的客堂里有一张拍摄于光绪丁未年(1907)的香会成员富斌的肖像照。(28)详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85、617页。从现有材料来看,这应该是最早记录下来的一张妙峰山庙会影像。(29)韩书瑞认定第一张妙峰山照片拍摄于1919年,然据顾颉刚的记载可知,韩书瑞的断代说法并不准确。韩书瑞关于妙峰山照片的说法,参见[美]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下)》,朱修春译,稻香出版社,2014年,第247页。可惜的是,顾颉刚一行并未翻拍这张珍贵的照片,其拍摄者信息也湮没于历史尘埃中。另据顾颉刚日记的说法,同行的孙伏园虽然拍下一批关于“妙峰物品及带福合影”的庙会照片,但却未见刊印,致使如今难以追寻这批照片的详细信息。由此可知,作为学者的顾颉刚、孙伏园等人,开始意识到摄影这一新兴技术在保存资料方面的便捷性和可复制性,试图以摄影技术来记录庙会信息。但是,顾颉刚并没有用照相机来记录完整的庙会仪式过程的打算,而主要是出于一种文人的赏玩心态,希望拍摄一批会启照片并编印成册,以“备大家的鉴赏”(30)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顾颉刚民俗论文集(二)》,中华书局,2011年,第331页。。

图2 蒋维乔于1919年拍摄的妙峰山灵感宫
另一套关于妙峰山的早期照片则收录于蒋维乔出版的风景名胜影集《西山二集》中。(31)蒋维乔,中国近代教育家与佛学家,曾著《中国佛教史》《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等。他于1896至1914年间在商务印书馆任职,1919年转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该影集出版信息,详见蒋维乔编:《中国名胜·第十四种:西山(二集)》,商务印书馆,1920年。他于1919年4月拍摄了这批照片(32)蒋维乔曾于1919年4月6日与彦明允、徐森玉等人前往黑龙潭、秀峰寺,次日乘坐轿椅登上妙峰山,并于8日骑驴至大觉寺后乘火车返回。参见林盼、胡欣轩、王卫东整理:《蒋维乔日记》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17-1118页。,以珂罗版洗印后结集发行。该影集既包括了从京城内至妙峰山朝圣时沿途经过的黑龙潭、大觉寺、清水院、金仙寺、朝阳院、瓜打石等名胜景观,更包括妙峰山上的松林、峰顶、灵感宫、法雨寺以及东岳庙。这本影集还有一篇蒋维乔撰写的短序,内容更多地着墨于妙峰山一带的自然景观。此外,随序还有一篇“旅行须知”,简要介绍游览妙峰山的路线以及交通、食宿的具体安排和花费。尽管蒋维乔非常熟悉妙峰山庙会,但他并未选择在庙会期间前往游览。翻阅整本影集,照片中几乎没有出现人像,更没有记录妙峰山庙会的场景。而且,从蒋维乔的拍摄手法可知,这本介绍“中国名胜”的影集更倾向于视觉表现妙峰山作为“风景”的审美内涵,而远非它作为朝圣地的民俗内涵。与之类似的,还有当时居住在樱桃沟的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拍摄的一张妙峰山风景照,刊载在1928年的《艺林旬刊》上。(33)庄士敦于1904年来华,后为已退位的溥仪教授英文、数学、地理等课程。时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将位于妙峰山下的一座别墅送给他,即名“庄士敦别墅”。该别墅位于离涧沟村不远的樱桃沟村南,虎皮石墙,硬山卷棚顶,上方原挂有溥仪手书的“乐静山斋”匾额。该照片的具体拍摄时间暂不可考,其图版详见[英]庄士敦摄:《妙峰山》,《艺林旬刊》第1期第四版,1928年9月。这张照片以较高的妙峰山金顶为主要的拍摄对象,隐约可见山顶的惠济祠。照片中的香道沿途草木稀疏,没有人烟。据此推断,这张照片大概并非在庙会期间所拍摄。刊载时,照片下面添加了一段说明文字:“妙峰山,在宛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昔不著名。山椒有元君祠,香火最盛。其地高出海面四千二百尺。登临远眺,环畿诸山,皆在其下方也。”(34)这段文字的作者信息不详。详见[英]庄士敦摄:《妙峰山》,《艺林旬刊》第1期第四版,1928年9月。这段说明文字虽然篇幅简短,却清楚交代了妙峰山的地理位置和宗教内涵。相较于蒋维乔的摄影作品,庄士敦的照片反而更像是一张略显单薄的山水画,缺乏表现庙会的民俗元素。
马芷庠于1935年编写《北平旅行指南》时,也曾大量使用铜版印刷的方式刊印了近200多张照片。在提及妙峰山的卷一《古迹名胜之部·庚 北平西郊》中,编辑者在文字内容前插入了25幅照片,其中包括两张妙峰山的照片。(35)马芷庠编:《北平旅行指南》,北平经济新闻社,1935年,铜版照片第54页。根据文字说明,其中的《妙峰山上》这幅照片是由李尧生在1929年所摄。仔细辨认这张模糊的照片可知,它是在妙峰山香道上拍摄而成的,照片中有一远一近的两位正在沿着石板香道前行、前往金顶进香的香客身影。另一张照片则是灵感宫内供奉的一尊王三奶奶像(36)有意思的是,《北平旅行指南》关于妙峰山的文字内容并未提及王三奶奶信仰,而编纂者却偏偏选用了《妙峰山王三奶奶像》而非其他碧霞元君神像的照片。指南书对此并未有所说明。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推测有三:第一,编纂者确实无意为之;第二,因为照片数量不足,编辑者无从选择;第三,王三奶奶信仰在妙峰山庙会乃至北京一带影响日益壮大,对游客或香客的吸引力远胜于碧霞元君。,由邓祖禹拍摄。这尊王三奶奶像与顾颉刚1925年所见的“青布的衫裤,喜鹊巢的发髻,完全一个老妈子的形状”是相符的,而非周振鹤于1929年所见的“手上戴着凤冠,身上披着黄色华丝葛大衫。她左手边是拿着一支长杆烟筒的侍者,右边是手牵一匹黑毛驴的驴夫”(37)顾颉刚:《游妙峰山杂记》,《顾颉刚民俗论文集(二)》,中华书局,2011年,第410页;周振鹤:《王三奶奶》,《民俗》周刊第69、70期合刊,1929年7月24日。那般形象。不同于蒋维乔、庄士敦拍摄的照片,《北平旅行指南》这两张照片中出现了香客这一人物形象,且近距离拍摄了王三奶奶的神像,这让妙峰山不再只以超然物外的自然风景形象示于读者,更是直观地揭示了它作为“进香朝圣”的宗教圣地的文化内涵。
由于印刷技术有限,《北平旅行指南》中刊印的照片质量不佳,但是使用照片来补充说明文字内容的做法,却使整本指南书图文并茂,给使用者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风景名胜的大致情境。很快地,这种插入照片的编辑方式得到其他指南书出版者们的青睐,纷纷效仿。
除上述诸多照片以外,就目前笔者目力所及,还有西方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Gamble)于1924至1927年间拍摄的119张照片以及1部无声的纪录片《朝圣妙峰山》(PilgrimagetoMiaoFengShan),以及德国女摄影师海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于1934年前往妙峰山拍摄的139张庙会照片。(38)相关影像资料的信息,详见Sidney D. Gamble Photographs Collection, Duke University Library,https://repository.duke.edu/dc/gamble,浏览时间:2022年3月5日;“Funerals, weddings, Miao-feng Mountain album. Part 2”, Harvard Library, https://hollis.harvard.edu,浏览时间:2022年3月5日。此外,时任美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的外交官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一家曾于1928年10月23日携艺术家客人莉莲·米勒(Lilian Miller)前往他们在西山租住的居所,还在妙峰山、龙泉寺、滴水岩、潭柘寺一带游玩了五天,并运用摄影技术拍摄了一部名为《妙峰山等地之旅》(Trip to Miao Feng Shan etc.)的纪录片。整部纪录片长达11分钟,从3分1秒开始至8分27秒间的镜头都是马慕瑞等人妙峰山之行的所见所闻,占据了整部纪录片将近一半的时长。由此可见,妙峰山之旅确实给马慕瑞一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仔细辨别他拍摄的这些镜头,其内容多为妙峰山一带的自然景观、村舍寺庙等建筑物、车船等交通工具以及当地村民、和尚的日常生产生活场景。不同于甘博出于社会调查目的而将镜头聚焦在庙会活动上,尽管同样是按“上山—下山”的顺序进行的线性拍摄,马慕瑞更多的是将妙峰山视为“风景名胜”来看待,注重旅途过程的视觉体验,所制作的纪录片带有强烈的个人记忆色彩。纪录片《妙峰山等地之旅》的详细信息,参见Helene van Rossum, “Renting a temple in the Western Hills”, Seel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https://blogs.princeton.edu/mudd/2010/08/renting-a-temple-in-the-western-hills-1925-1929/,发表时间:2010年8月17日;浏览时间:2022年3月5日。相较于中国拍摄者多受器材简陋的掣肘,西方摄影师们的拍摄技术更加专业,因职业和国籍的便利,也更容易获得上好的照相机和胶片。甘博和海达·莫理循所拍摄的妙峰山照片无论是拍摄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了上述中国人所拍摄的妙峰山摄影照片。这些照片按摄影内容的主题进行分类,可大致分为“自然风景”“村落生活”“神圣建筑”“神像”“节日用品”“香会组织”“香客”“僧侣”“商贩”“乞丐”“调查者”等类。许多照片特别注重呈现庙会主体的具体行为,画面中往往可以看到香客、香会组织等人物在香会活动中的忙碌身影。诚如笔者在《妙峰山庙会的视觉表达》中所提到的,“相较于文人笔记、风俗画等传统民俗文献侧重于勾勒妙峰山作为‘风景’的文化内涵,这批老照片作为连续性的、叠写式的‘视觉集合’更加突出香会、香客以及商贩等民俗主体的仪式实践和文化互动,纪实而系统地运用视觉表达手法再现了中国庙会的宗教性、娱乐性与商业性”(39)林海聪:《妙峰山庙会的视觉表达——以甘博照片为中心的观察(1924-1927)》,《民俗研究》2019年第5期。。
及至1929年5月,身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员的顾颉刚、魏建功等人再度展开“妙峰山进香调查”,他们有意识地采用了摄影这一现代视觉技术,一共拍摄了41张庙会照片,以插图的形式刊载于《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上。(40)在出版奉宽的《妙峰山琐记》时,魏建功不仅为该书标点,还特意增加了25张他在这次调查中拍摄的照片,作为具体文字资料的图像印证。相关出版信息,可参见《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民俗》第69、70期合刊,1929年7月24日;奉宽:《妙峰山琐记》,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9年。通过检阅资料可知,该期专号一共列印了41张照片,其中第2至6页共35张照片标明由魏建功所摄,其余6张照片根据周振鹤文末的致谢可知出自罗香林之手。不同于其他拍摄者仅针对碧霞元君庙选择性地拍摄了5张照片,魏建功从调查团于清华园出发就开始拍摄,以社会调查者的身份全程运用照相机记录他们在庙会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团员在调查过程中的工作、休息场景,获得了35张社会调查摄影形式的庙会照片。这些照片与调查文章最终形成一种图文参照对读的互文性文本,成为一份颇为珍贵的关于妙峰山庙会的“视觉集合”。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妙峰山庙会的记录手段经历了一个从以文字为中心向图文共现的形式转化的嬗变过程。尽管各类民俗资料依赖的书写媒介和书写的侧重点各异,但最终都汇聚成为多元呈现妙峰山庙会这一“礼俗互动”的文化场域的民俗档案。
以书写媒介的物质特征为标准,记录妙峰山庙会的民俗资料可分为如下三类:1.以文人笔记、碑刻、地方志、旅行指南等为代表的文字书写资料。它们的创作者多为文人墨客、地方官员或者香会信众,所记的内容或简明记叙庙会的发展历史,或记录创作者参与庙会活动的岁时记忆和个人经验,或呈现人神互惠的民间信仰观念。2.以风俗画、石印插画为代表的图绘记录。它们的绘制者多为本地画师,熟悉北京的风俗民情,画法多借鉴传统的山水画技巧,偶尔增补一些带有补充说明性质的题词。就图幅内容而言,它们或以妙峰山作为图像主体,在不同图画空间中呈现相应的庙会人物行为及其活动场景,或者选取带有“礼仪标识”功能的人物、物品为绘制对象,呈现妙峰山庙会的某些特定民俗事象。3.以老照片、纪录片为代表的影像档案。它们的创作者为各国的旅行者、摄影师以及学者们。早期的妙峰山庙会影像多为单幅,且以自然景观等静物为主,得益于摄影技术的革新,后期的庙会影像多采取纪实性的社会调查摄影方法,系统而全面地呈现了妙峰山庙会的方方面面。相较于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图像和影像类民俗资料能更为直观、形象地呈现妙峰山庙会,甚至是不懂中文的西方人,也能通过视觉体验的方式直接领略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神韵。不过,研究者也应正视图像资料的局限性。(41)对此,可参阅王加华:《让图像“说话”:图像入史的可能性、路径及限度》,《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这些图像资料固然在意象呈现上具有自我指涉的独立性,然而使用者如需把握它们背后的文化脉络,仍需借助说明文字来补充、佐证,以免过度阐释。
实际上,中国学界不断在挖掘、搜集和整理海内外的各类民俗文献,出版了诸多汇编类成果,业已为我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获取资料的便利。本文虽以妙峰山庙会书写为研究个案,但意在反思过往研究多依赖文字材料来挖掘、阐述民俗文化内涵的路径,希望打破文字与图像的媒介壁垒,并借鉴“图像入史”(42)王加华:《让图像“说话”:图像入史的可能性、路径及限度》,《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的研究思路,对零散于各处的图像资料加以利用。当然,在“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的学术视野下,如何运用图文互参的文化模式来“发掘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以小见大地阐述中国社会的人文传统”(43)张士闪:《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从而更好地提炼出一套源自中国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学术话语体系,仍待更多的有志者加入讨论。
- 民俗研究的其它文章
- 迈向科学的民俗学:范热内普的人生与学术